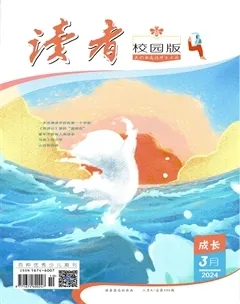有只丑小鸭,没有变天鹅

我并不喜欢丑小鸭的故事。在我看来,这表面的励志背后,其实是一种高傲的命中注定。以为在成长的某个时间点后就会脱胎换骨,这样坚定而无凭据的希望,总带着一股天真的悲情。
养过鸭子的城市小孩不多,我恰巧是其中一个。并不是我对这个物种有特别的喜爱,而是我妈在筛选之后,认为鸭子可以自己洗澡,养起来比较干净。小时候的我有着泛滥的悲悯之心,凡是我妈带回来做菜的活物,我总是阻止她“处决”。我一定要亲眼看到鱼翻白肚了才准吃,而一只本该拿来煲汤的母鸡甚至拖到下了一个蛋。看着那个蛋,我妈觉得,或许应该给我养个什么转移一下注意力。
于是,我得到了五只毛茸茸的小黄鸭,它们稚嫩,弱小,惹人怜爱。喂食,散步,我在它们的吵闹中感到欢喜,认真准备它们的下水仪式。在一个日光倾城的午后,我把它们放进蓄满水的水池。也许是想给它们一段自由玩耍的时光,我走开了一阵,回来时看到的却是它们集体“躺尸”的场面。
鸭子游泳被淹死了。这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个吊诡的笑话。鸭子在长出尾羽分泌脂肪之前,是不能浮在水上游泳的。这是我之后每次和别人聊起宠物时必背的内容。惊讶者有之,淡定者有之,我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赎罪者。
而在当时,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妈把它们捞起来,用报纸垫着,让阳光照在它们身上。一只,两只,三只,我看到它们羽毛渐干,有了微弱的呼吸,而另外两只,却怎么都不再动了。我守着它们直到太阳落山,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产生面对死亡的无力感。
劫后余生的三只鸭子,连叫声都蔫儿了,没过多久,又有一只悄无声息地死在了纸盒里。剩下的两只,莫名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我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它们:一只精力明显旺盛一些,整日围着安静的那只打转;安静的那只冷淡而傲娇,偶尔回应一声,吵闹的那只就越发欢天喜地起来。
如果时间再长一些,我大概会给它们取名字。它们却没有等到。某个清晨,在比平时更加聒噪的鸭叫声中,安静的那只再也没有醒过来。剩下的那只,明显焦急起来,它将盛食的小碟拱到死去的同伴面前,绕一圈,再拍打几下。不知重复了多久之后,它依偎过去假寐,隔一会儿就抬头看看,期待着某一次会有回应。直到我们把那只不动的小鸭子拿出来,它的半边身子还沾染着同伴的温暖。
我最终没有给最后这只鸭子取名字,全家人都只是叫它“鸭子”。
鸭子再也不复之前的吵闹,连着两天,似乎都只呷了点水。赶它出来散步,它也不肯挪动,倔强地缩成一团,表达着它的悲伤和寂寞。我将鸭子造型的闹钟放进它的窝里,按下模仿鸭叫的闹铃。听见声响,它精神一振,连忙凑近,依偎着团起来。但很快它就发现自己受骗了,灰心丧气地走开,然后以十倍的冷淡来对抗我。
我想尽办法,也没能获得它的丝毫理睬。“喂,”我对它说,“等你长大了,我就带你去游泳。”我以为,“长大”是所有未解问题的终极答案。它缩了缩脖子,我把这当成约定的示意。
鸭子依然每天团在窝里,偶尔被带下楼在草地上晒太阳。它执着地孤僻着,我很少再去看它。
它再回到我的视线时,我几乎认不出来。它黄色的绒毛已经脱尽,长出了灰黑的杂色羽翎。真丑。在我的认知里,所有的“长大”都是关于美的魔术。这样的变化,我始料未及。
它依旧孤僻,但随着丑陋的羽翎一起长出来的,还有它的坏脾气。它像是突然进入了青春期,不耐烦于安静地蹲在纸盒里,在家里和楼道间横冲直撞,上蹿下跳,将羽绒散到各处,时不时还顶一下人。我妈只好用一个箩筐把它罩起来,只在喂食的时候让它放风一阵。除了短暂的嫌恶,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烦扰。
在我久违的一次给它喂食时,我发现它的步态有些不正常——不知何时它长成了一只驼背鸭子,背部怪异地高耸着,像一只变形的骆驼,丑陋、肮脏、畸形。它显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放风规律,别扭地摇摆着,在木质的楼梯间努力地踱着步子。它年少时期的忧伤气质已经一扫而光,我却已经难受得发不出声。
我没有再把箩筐罩回去。
我妈回来时,看到的是鸭子在床单上留下的污渍。又过了几天,它变成了桌上一锅热气腾腾的肉汤。那顿饭我一口都没有吃。
我认得它,是因为那高耸的畸形骨架。
它的长大,并没有给它带来闪亮的新生。它的命运,让我对某种认知埋下幻灭的因子。
我并不相信丑小鸭的故事。因为我始终记得,有一只丑小鸭,没有变天鹅。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简影录”,胡晓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