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义》中的教育方式探究
李长伟
(1.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2.湖南师范大学 古典教育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法义》(1)本文使用的《法义》中译本为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本文引用相关文字时,除较长征引标明具体页码外,其他部分仅按照惯例标注希腊文本的边码。另外,《法义》的希腊文是Νóμοι,国内对Νóμοι的翻译有多种,有译为“礼法”,也有译为“法”以及“法律”的,为保持前后的一致性,本文统一采用“法义”这一译名,包括引文。是柏拉图(Plato)晚年最后生育的一个“孩子”,讲述了雅典异乡人(雅典人是立法哲人)与克里特人克勒尼阿斯(Kleinias)以及斯巴达人墨吉罗斯(Megillus)(两位多里斯人是立法者)在对话中建构次好城邦的事情。《法义》是柏拉图专论教育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部是《理想国》),其教育思想是复杂、丰富的,本文只关注其中的一个问题,即“教育方式”的问题,或者说“怎么教”的问题。
在“怎么教”的问题上,首先要明确的是,“怎么教”不是随意的,即不是教育者想怎么教就怎么教,因为教育者的随意完全忽视了“怎么教”的目的。“怎么教”是教育手段,它服务于教育目的——学生愿意且能够接纳教育者所传达的知识,这就要求教育者在选择教育方式时,必须考虑到学生的情况。如果教育者只从自身的偏好出发去选择教育的方式,丝毫不考虑学习者的灵魂性质,那么教育的目的是无法达成的。《法义》中雅典人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他为此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理性与神话,或者说logos与muthos(2)柏拉图给了希腊语muthos(mythos)一词以神话的意义。参见吕克·布里松等著、梁中和等选编《追随柏拉图,追寻智慧:吕克·布里松古典学术访谈与论学》,孙颖、李博涵、张文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20年。。
一、两类教育对象
教育的对象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不同。我们若欲把握雅典人的两种教化方式,就需要首先把握雅典人所言的不同的教育对象;欲把握不同的教育对象,就需要从雅典人所欲构建的“次好的城邦”之性质入手。“次好城邦”是“混合制”,不是“单一制”,它融合了寡头制、民主制和君主制。它的卓越之处,就在于让不同的邦民在“平等”之中生成出了“友爱”,“友爱”又生发出了“团结”,从而保存和稳固了城邦。与之相反,无论是民主制、寡头制还是僭主制,它们都是作为强者的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作为弱者的被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它们没有从公共利益出发,实现自愿的统治者对自愿的被统治者的统治,而只是自愿的统治者对非自愿的统治者的统治。在这一意义上,雅典人认为它们不是着眼于平等与友谊的“政体”,而只是着眼于不平等与私利的“派系”(832c),与之相关的法律,也不是正确的法律(715b)。非政体的派系,非正确法律的法律,只会让城邦遭受毁灭而不是保存。
这一卓越的混合制(3)“为了友谊,在每片土地上和城邦里,我们应该混合属于平民的个人与不属于平民的个人。”见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2卷,759b,第110页。另外,在选举的方法上,也是混合制,既有选举,也有抽签,还有公推。《法义》中的混合制至关重要,是我们把握《法义》所阐述的教育的基础。进言之,正是因为混合制的出现,所以《理想国》中被严重贬斥的“民主”被纳入到政制当中,从而面向大众的普通教育才成为可能。,就公民的构成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爱智慧的人与爱自由的人,前者是占少数的统治者,后者是占多数的民众。这两类人,恰如织物中的质地不同的经线和纬线:“经线应该有力,自身具有一定的牢固性,纬线应该较柔软,质地具有某种适当的柔韧。”[1](735a,P.93)“因此,就那些担任城邦中统治职务的人而言,在各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他们与只受过少许教育的考验和巩固的人的区别开。”[1](735a,P.93)混合制中两类不同的人的存在,意味着对他们的教育,若要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在教育的方式上有差异。忽视差异教育,不能因人施教,便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鉴于混合制的平等性,两类教育对象也必然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二者有差异但不至于差异到完全是两类人。
二、作为教育方式的理性
对于雅典人来说,那些数量不多的统治者,拥有理智或智慧(必须注意,他们的理智不是哲人的理智),这使得他们所受的教育是“理性的教育”,或者说,雅典人这样的教师以“理性的方式”教导他们。理性的方式(4)古希腊的理性不是现代的理性,现代人的理性集中体现在对自然的改造上,而古希腊的理性不是,它最初的意思只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说话”,与政治生活关联在一起,就此而言,希腊理性是城邦的女儿。参见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99页。,即严谨论证的方式,也就是logos的方式:“logos是一种只以理性为根基的话语,换言之,logos完全不依赖经验,它要求确定性与普遍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logos发展出了柏拉图同时代的数学家们(在几何学家那里尤其典型)所提出的那种证明方式:演绎法。”[2]
对于统治者的理性的教育,鲜明地体现在夜间议事会的教育中。夜间议事会是城邦的锚,城邦法律的拯救者和保护者,因为法律会因为政制的增长而变得不完善,法律也会在时间之中走向衰败,这就使得必须有一个卓越的统治者,也就是夜间议事会。夜间议事会由城邦中最优秀的两部分人构成:理智的老人和感觉敏锐的年轻人,他们共同拯救和保护城邦:
城邦本身是躯干,而护卫者中的年轻人可谓最顶尖的头脑,他们因有最好的天性而受选,在灵魂的各方面都最敏锐;他们环视整个城邦,守卫时把诸感官交给记忆,并把城邦中的一切汇报给老年人。老年人是理智的影像,因为他们出类拔萃,能审慎思考诸多值得探论的事物,深思熟虑,并在集体商议时把这些年轻人当成助手。因此这两种人一道拯救了整个城邦。[1](964e-965a,P.264)
如果夜间议事会的成员,是最为卓越的护卫者,是迷途羔羊的法官和教育者,那么他们的卓越体现在哪里呢?或者说,他们凭什么去拯救城邦?在雅典人看来,夜间议事会的成员需要接受高于普通大众教育的两种教育,进而拥有两种知识,才能成为夜间议事会成员。这两种高级教育是辩证法教育与神学教育。
就辩证法教育来说,教育者必须让未来的夜间议事会成员知道多种美德是如何统一为一种美德,也就是美德本身,因为所有不同的美德都被称为“美德”。对作为“一”的美德本身的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所有政治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目标,倘若失去这一目标,城邦就会如航船那样失去正确的方向(5)多里斯政制的问题,就是忽视了整全的德性,只重视单一的勇敢德性,更进一步,其中的立法者不具有为整全德性寻求最终根据的能力,因为正是“一”使得“多”成为了“整全”,而不是四分五裂或相互对抗。。“难道我们没说过,那个顶尖的匠人和护卫者,在每件事上都必定不仅能注意到多,也能追求并知道一,正因为知道一,他就能以整全视角安排一切指向那个目的”[1](965b,P.264)。这里,毫无疑问,从“多”中寻“一”,就是典型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获得,又只能依赖于教育者的论证方式,即以严谨的精确的论证的方式引导顶级的护卫者学会从诸多的美德中上升,寻找到作为“一”的美德本身。如果要追问为什么非得用论证的方式,那我们的答案就是,美德本身超越了护卫者的感觉经验,唯有通过他拥有的超越的理智才能去触碰,而理智抓取美德本身的工具,就是正确的严谨的“论证”。既然美德本身显现在论证当中,那毫无疑问,教育者就必须以论证的方式引导护卫者们去学会论证。
就护卫者的神学教育来说,由于神是万物的尺度,是法的来源,所以高级护卫者必须学会敬神,但他们的虔敬和一般大众的虔敬不同,他们的虔敬建立在对诸神存在证明的理性掌握上,而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遵守关于敬神的法律。进言之,他们必须掌握两点:一是“在分有生成的万物中,灵魂最古老,灵魂不朽且统治一切物体”;二是“在星辰中,据说正是存在者的理智在控制,并掌握必然先于这些事务的学问”。[1](967d-967e,PP.266-267)
这两类知识都体现在卷十对神的存在的三个证明当中。在那里,雅典人通过严谨的复杂的证明的方式,教导城邦中最卓越的护卫者掌握关于神的知识,从而获得有根基的虔敬德性。(6)卷十中,雅典人预言了宗教法(宗教法以书面的方式宣告给新城邦的公民们)可能会遭到无神论者的批判,为此,他要为受到批评的逻各斯辩护。这种辩护,被斯勒扎克称为“对逻各斯的帮助”。在帮助的过程,雅典人离开了一般的水平和迄今的论题,阐明了运动的概念、灵魂的自我运动、灵魂相对身体的优先性、宇宙中善与恶的作用及万有由神驾驭(891b-899c)。见斯勒扎克《读柏拉图》,程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68页。卷十是如此地强调严谨的精确的普遍的论证的方式,以至于天性和基础较弱的墨吉罗斯是沉默的,他只是认真的倾听者和学习者(论证超越了习俗和经验,不需要他的丰富经验的参与):
卷十涉及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学、基于运动论的灵魂学等较为艰深的论证,采取“颇为陌生的论证方式”(891d6)。可想而知,要是这一卷的讨论放在《法义》的前面部分,雅典异方人的两位年老对话者定然无法进入——他们必须在雅典异方人的充分教导后,方能展开这样的对话。在这一卷中,主要的对话者是雅典异方人和克勒尼阿斯,墨吉罗斯只说过两句简短的话。此时的克勒尼阿斯已具有哲学的心性,他并不畏惧陌生的论证,甚至表示可为此“走出立法的领域”(891d7-8)。卷十的神学可谓是雅典异方人对两个年老立法者的最高教育。[3](PP.3-4)
三、作为教育方式的神话
“次好城邦”中,作为纬线的数量众多的民众,他们在自然天性的卓越程度上,弱于作为经线的数量较少的统治者。除此之外,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智的多少上,即二者虽然都有理智,但民众为灵魂中的苦乐感支配,统治者则被理智支配。数量众多的民众的灵魂性质,决定了教育他们的方式,主要不是理性论证的方式,而是神话的方式,后者会更容易说服民众自愿接受和信从教育者所传递的有利于城邦和谐和稳固的观念和法律。对于雅典人来说,由于受苦乐感支配的自由公民是城邦的主体,统治者也是他们通过选举和抽签的方式选举出来的,所以他极其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并为此设计了复杂和完整的民众教育体系,反倒是培养统治者的高级教育被他弱化了。由此而来的,就是整部《法义》在教育方式上非常强调“神话”,即以神道设教。
如果我们所说为真,那首先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凭什么说多数人为苦乐感支配是教育者使用神话的原因?这就需要从神话的特性讲起。按照布吕松的分析,与逻各斯一样,神话也是叙述和话语,但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又不是根据某种严格的规则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它不使用推理演绎的方式,不会发展出连贯的论证(7)最初,神话与逻各斯并不对立,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哲学阐述和历史调查中,神话与逻各斯才对立起来,带上了贬义的含义,泛指一种没有严谨的论证或可信的证据支撑的、虚妄的论断。参见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10页。在卡西尔看来,神话与逻各斯是最初象征之书上的两根平行树杈:“起初,言语与神话彼此存在着某种无法分离的联系,只在作为独立元素时才循序渐进地脱离这种联系。言语与神话是促使象征形式诞生的唯一冲动上的不同枝叶。”转引自马特《柏拉图与神话之境》,吴雅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所以,神话并不与理智对话,它总是诉诸感情,而且它尤其会利用人类与动物在感情上相同的那部分,即关于快乐与痛苦的感受。神话之目的是要改变人类的行为,但它的方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它总是通过模仿来达成目的,这使得它与魔法及咒术显得有些类似。”[2](P.5)
当神话成为塑造大众的恰切的苦乐感的根本方式,使用神话的教育者,也就成了“教育诗人”,而不是“教育哲人”。(8)王柯平将柏拉图所用的神话分为三类:“创构型神话”(created myths),“转换型神话”(transformed myths),“传统型神话”(traditional myths)。柏拉图创作三类神话的原因有三个:“实用原因”“哲学原因”“承传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其实都是柏拉图推行其道德修养和哲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王柯平《〈法礼篇〉的道德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7—328页。神话最初是古希腊的诗人所创造的独特的丰富的话语实践,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将这种丰富性称为“像普罗透斯那样千变万化”(9)“神话像普罗透斯(Protée)那样千变万化,涉及多种多样的事实,其中当然包括神谱和宇宙谱,但也包括传统中各种类型的传说、系谱、童话、谚语、寓言和格言,总之包括人们自发地口耳相传下来的一切。因此,在希腊背景中,神话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而是在随意的交往、见面或闲谈中被一种无形的、匿名的、无法捕捉的力量传递并散播开来的全部内容,这种力量被柏拉图称为‘传言’(Phèmè)。”见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11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说,“所谓神话,其实就是诗人们所创作的故事,他们将集体所希望留存下去的那些记忆进行信息的重新组织,并赋予了它们一个特殊的形式”[2](P.1)。当诗人创作出这样的神话故事以后,又将自己投入到自己所创作的存在物当中,通过诉诸感性、愉悦和敬畏,去模仿存在物,以劝说受快乐感支配的民众去信从。[2](P.3)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作为教育者的雅典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称为模仿最好生活方式的“肃剧诗人”(由法律主宰的“次好城邦”,可以视为对克洛诺斯时代的生活方式的模仿:克洛诺斯时代,精灵统治我们;现在,法统治我们):“我们本身也是诗人,我们已尽全力创作了最美而又最好的肃剧;无论如何,我们整个政制的构建,都是在模仿最美而又最好的生活方式,至少我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是最真的肃剧。”[1](817b,PP.155-156)不过,我们必须注意,教育者是诗人,绝不意味着教育者完全站在了诗人的立场上,恰切的说法是,汲取了诗人的有效的教化方式的教育者,仍然是“教育哲人”。对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给出阐释。
教育诗人运用非论证的神话教导大众,以神道设教,体现在《法义》的各卷当中,我们这里只能有选择地进行陈述和分析。
其一,用神话去传达正确的观念,最为经典的,也许是卷一所提及的“木偶喻”,即把人喻为神手中的玩偶。雅典人之所以选择采用神话,根本的原因,是克勒尼阿斯他们在理解雅典人的一个论断(“好人就是那些能够控制自己的人,坏人就是那些控制不住自己的人”时,遇到了困难,于是雅典人只好“借助一个形象”来为他们阐明(644c)。这个形象,就是神的木偶,这个木偶有铁质的绳索,即痛苦和快乐;也有金质的推理的绳索。对于推理的能力而言,除去少数的知者是自己拥有的,多数人的推理能力都是从知者那里获得的。这很好地解释了多数人的灵魂本性,以及木偶喻作为教育方式所指向的特定的教育对象。
在木偶喻中,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木偶喻以木偶的“形象”模仿了灵魂“整体”。人虽然是神的木偶,但神用金质的绳索在牵引人时,也可以说人拥有了推理的能力,另外铁质的绳索意味着人的痛苦与快乐。由此,木偶喻就显现了不可见的灵魂之整体:理性、情感与欲望(与《理想国》的灵魂三分是相通的)。进言之,灵魂是人的本质,是整体的而不是单一的,但灵魂又是不可见的,木偶喻的价值,就在于让不可见的可见。教育的对象是灵魂,目的是培育灵魂的整体德性,教育若要达成目的,就需要首先知晓灵魂本性,尤其是让普通公民理解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模仿整全灵魂的木偶喻就显现了它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马特(Jean-Francois Mattéi)对柏拉图神话的界定去把握:
倘若定义一语在此还具有某些意义——该语从根本而言旨在揭示理性,那么我斗胆定义柏拉图神话如下:一定数量的戏剧章节的连续叙事,借某个陌生的叙事者之声说出,目的在于通过特殊的模仿影像,显示那浮现于不可见的诸种存在之整体。 [4](P.8)
其二,木偶喻之后,雅典人又在第二卷提及了“西顿的神话”(Σιδωνíου μυθολóγημα)。之所以会提及西顿的神话故事,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逻各斯所确立的东西即使是真实的,让人信服也并不容易,或者虽然在逻各斯上不是真的,但对人又是有益的,那又该怎么办呢。这里的“人”不是拥有哲学天性的或者理智天性的人,而是大众中的年轻人。为了让年轻人信服,雅典人就说,立法者为什么就不可以出于好的动机向年轻人撒个有益的谎言呢,譬如不可信但容易让人信服的“西顿神话”:
播种龙牙,从中长出全副武装的巨人。其实,这个神话是极好的例子,它向立法者表明,有可能让年轻人的灵魂信服几乎所有事情,只要他去试一试。接下来,立法者应该寻找的只是最有益于城邦的说服方式,他也应该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法,以有助于整个共同体尽可能用一种口吻谈论这些事情——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这样,在歌曲、神话和论述中也都这样。[1](663e-664a,P.34)
西顿的神话,涉及底比斯城邦的建立。按照布里松(Luc Brisson)给出的版本[2](PP.136-137),卡德摩斯(Cadmos)听从了德尔斐的口谕,放弃了寻找妹妹欧罗巴(Europe),跟随一头母牛的指引,来到了未来建立底比斯的地方。他决定向雅典娜(Athena)献祭,于是派人去附近的泉眼中取水,但是看管泉眼的毒蛇杀死了前去取水的人。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卡德摩斯杀死了毒蛇,并按照雅典娜的指示,将毒蛇的牙齿种在土里。刹那间,从土里长出了全副武装的武士,也就是斯托巴依人(les Spartes)。为了摆脱他们,卡德摩斯向其投掷了石块,由于不知道是谁在攻击自己,于是他们就相互攻击,最后只有五个人幸存:厄卡翁(chion)、许珀瑞诺耳(Hyperénor)、克托尼俄斯(Chtonios)、珀罗洛斯(Péloros)与乌代俄斯(Oudaeos)。这五个人与卡德摩斯共同建立了底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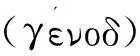
虽说神话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话语,但是对于集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分享的那些基本知识,神话又是其交流的手段。交流,确保了这种知识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另外,虽然神话不同于论证性话语,其中并不包含必然性,但它既然是故事,那么便天然地可作为改变人类灵魂中较低部分言行举止的手段。神话中的行为具有超凡脱俗的一面,它起到如同魔法或咒语的效果,而就其最一般的效果而言,它也会与寻常意义上的说服发挥一样的效用。[2](P.132)
其三,立法者向诗人学习。无论在《理想国》还是《法义》,理智的立法哲人向来对诗人的教化保持警惕,因为诗人会站在大众灵魂中的低级部分去进行创作,从而不是来培育正确的灵魂德性,而是败坏灵魂德性。不过,《法义》卷四在谈论法律序曲时,雅典人又代表诗人在立法者面前为诗作了意味深长的辩护(719c-719e)。雅典人首先提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说诗人们一坐上缪斯(Musae)的三角凳,就如一股泉水往外喷涌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他又继续说道,他之所以无法控制自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不可自我控制的模仿者,他也因此被迫自相矛盾,塑造相互对立的人。不过,他自己又不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所模仿的彼此对立的人所说出的话,哪一种话是真实的,哪一种话是虚假的。总之,他能够对同一主题给出不同的说法,但又不觉得自相矛盾。譬如对于不同人的不同葬礼,诗人都会给出称赞,即诗人既能称赞富人的相当繁复的葬礼,也能称赞节俭的穷人的葬礼,还能称赞有适度财产的人的葬礼。与诗人的一题多说不同,立法者只能一题一说,譬如葬礼,立法者只能选择一种适度的葬礼,并无条件地指定和称赞它。
雅典人站在诗人的角度在立法者面前为诗人辩护,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简单说,就是要求作为教育者的立法者,向诗人学习。因为诗人在他的无知的自相矛盾中,在他的一题多说中,显现着对大众灵魂的理解和尊重,因着这份理解和尊重,诗人对民众的灵魂产生了有效的影响。的确,作为教育者的立法者,根本上不是诗人,不可能有着无知的自相矛盾以及一题多说,他必须有知识,必须一题一说,但他作为城邦民众的教育者,必须考虑到教化的效果。如此这般,他就必须向诗人学习,学习诗人的对民众灵魂的了解、尊重,学习诗人所体现的了解和尊重的说话方式。
向诗人学习如何教化众人的立法者,最终要具备这样的说话技艺:就同一主题,“能同时向不同的人说明不同的情况,而且立法者的话还能在所有场合下产生同一的结果:对他所制定的法律的服从”[5](P.74)。立法者的这一卓越的言说技艺,体现在他制定的法律序曲之中。法律序曲是用来给出法律命令以及法律惩罚何以如此的理由或原因的,民众能够在立法者的非暴力的温和解释中,自愿接受法律的命令。民众之所以能够自愿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立法者能够如诗人那样了解民众的灵魂和需求,然后在此基础上给出法律的命令。为了说明这一点,雅典人将好的立法者视为自由民医生:自由民医生,一方面依据自然从源头探究病因,另一方面通过与病人和病人的朋友的温和的交流,了解了病人的真实的疾病状况,开出了有针对性的药方,并尽可能地让病人理解为什么会开这样的药方。显然,这时的立法者如诗人那样对民众的灵魂有了深切的理解,而一旦有了这样的理解,此后的法律教化不可能没有良好的效果。另外,立法者将法律分为“法律序曲”与“法律”或者“劝说”与“威胁”,就已经在形式上表明,立法者的话语已经不是单一的话语,而是双重的话语,“至少在长度上变成了双倍”[1](721e,P.84),这是一题多说,但又是一题一说,因为法律的规定是普遍的而不是相对的。这显然也是向诗人学习的结果。如果立法者忽视了向诗人的学习,那么他们的法律教化必将是没有良好效果的,即使立法者发布的指令有利于邦民,因为立法者会如僭主或独裁者那样,不肯理解和尊重民众的灵魂,只知道发布单一的命令,用暴力强制民众去守法。如果民众自身得不到尊重,他们怎么肯自愿接受哪怕有利于他们的法令呢,而不自愿接受法律统治,城邦怎么能和谐稳定呢?
其四,在法律的序曲的劝说方式中,神话是非常重要的方式。布里松就发现,在《法义》中,法律序曲的“劝诫”与“神话”是双关的,二者因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对柏拉图而言,序言首先是一种劝诫(paramuthia)。通过双关,柏拉图将劝诫(paramuthia或paramuthia)与“预告法律的神话”(ho pro tou nomou muthos)联系起来。在《法义》中,muthos后十四次出现都是在加固这种对比。其中有九次,这个词语指涉古希腊的传统神话,而另外五次,它所指涉的则或许不能称作神话,而是某些与这些神话有确切关系的话语。归根结底,柏拉图对神话的十四次不同寻常的用法也是从上下文我们讨论过神话的普遍用法中而来的。为了说服公民,让他们遵守各种各样的法律,立法者讲述起了神话,神话使得法律所要求的行为变得具体而生动。譬如,有一则法律要求女孩进行和男孩一样的体育锻炼,在讲到这则法律时,雅典的异乡人也提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muthous palaious)——这些神话或许与亚马孙有关——以此来支撑这项规定。[2](PP.138-139)
拉克斯(Laks)曾经分析了《法义》卷五到卷十出现的十五篇法律序言,并将之分为三类:与理性论证接近的序言;与褒奖和谴责关联的序言;起源于神话的序言。与理性论证最为接近的序言,只有一例,就是卷十中统摄全篇的那个反对无神论的著名段落,第二类和第三类则与神和神话相关:第二类意在晓谕人们遵循神的本性行事;第三类则意在晓谕人们要依循支配凡人命运的属神法律行动(这一类的特别在于,它变相地运用了胁迫的手法)。[6](P.77)
既然法律序曲与神话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由于整部《法义》可以被看作为一部法律序曲,那么神话以及从神话衍生出来的话语,就贯穿了整部《法义》。英译本《柏拉图对话全集》的编者汉密尔顿(Edith Hmailton),在为《法义》撰写的提要中认为,垂暮之年的柏拉图在回到尘世中实现他看到的某些真理时,放弃了诗性思维和讲故事的方式。[7](P.36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暂且不谈布里松和拉克斯的分析,雅典人自己就说过,《法义》是一部在诸神的启发下写成的一首长诗(811c)(11)最为明显的应该是《法义》第三卷,它谈论了长时段的历史,这历史就是“古老的传说”(以“大洪水神话”为开端)中的“真实”(677a)。,雅典人还说过,《法义》所欲建构的次好城邦是法律统治的城邦,而法律的统治又源于对克诺索斯时代的精灵统治的模仿。这些充分说明,《法义》不可能放弃诗性思维和讲故事。
其五,神话,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化方式,不仅仅体现在法律序曲之中,还体现在种种具体的教育活动之中。雅典人在《法义》中所提及的paideia,即教育,是非常丰富的,有音乐、体操、唱歌、舞蹈、文学、故事、会饮。这些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诸神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他们也不把理智的培养视为目标,因此不强调理性的教育方式,而是把正确的苦乐感受视为培养的目标,强调让孩子(老人)在欢快和愉悦之中接受教育。(12)《理想国》重点言说的是哲人教育,但它也谈及了对普通护卫者的音乐和体操教育;《法义》并没有谈哲人教育,而是重点谈论了音乐和体操教育,也包括会饮教育。不过,虽然都谈论音乐和体操教育,但是它们之间是有大的差异的:前者朝向对理念的爱,尽管与理念有很远的距离,但方向是确定的;后者则没有理念的位置,甚至也没有高贵理性的位置,教育就是塑造正确的苦乐感,即爱应该爱的,恶应该恶的,然后与成长起来的理性保持一致。与之相关,施特劳斯比较了《理想国》与《法义》中节制教育,认为前者以爱美为其顶点,后者则强调羞耻感或敬畏感的培养。参见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71页。作为教育方式的欢快与愉悦,不就是诗人所创造的神话所蕴含的吗?当诗人投身于丰富的神话时,人的身心就充满了愉悦。用雅典人自己的话说:
上述诸神作为舞伴赐给了我们,诸神还赋予我们欢快的节奏感与和谐感。诸神运用这种感觉打动我们,并用合唱队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载歌载舞中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诸神授予“合唱队”(源自“快乐”)这个名称的原因——这些活动天然就有“快乐”。那么,首先我们接受这点吗?我们能否说,教育最初来自阿波罗和缪斯,或是什么呢?[1](654a,P.25)
理性主导下的教育过于严肃和道德化,并不适用于对大多数孩子的培养。柏拉图教育的卓越之处,就是看到了理性教育的限度和边界,引入了诗人的教育,倡导面向多数人苦乐感的情感教育。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教育(paideia),就是通过游戏(paidia)对儿童(paides)的引导[8](P.19);游戏充满了快乐和愉悦,它同样显明了教育中的诗性。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强调一下,雅典人所言的诸种教育,尽管如灵魂的咒语那般是欢愉的(《法义》多次提及灵魂咒语或魔力),但这种欢愉并不纯然都是诗性的,而是必然伴随着正确性和严肃性。这是因为雅典人终究是教育哲人而不是诗人,通过正确的教育将人引向整全的德性,是他思虑和关注的。教育的正确性和严肃性亦来自神圣性。诚如雅典人在卷七所言,所有的合唱和所有的歌曲都要神圣化,都要与向神的献祭关联起来,因为唯有神圣才是最严肃的,神的严肃性又带来了教育的严肃性。因为作为教育的游戏,其实是神对作为木偶的人的玩耍。就此而言,《法义》中的教育,的确可以看作是朝圣路上的歌舞。
四、两种教育方式的共通性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在看到《法义》中教育对象的差异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们又具有混合制所体现的平等性,以及由这种平等性所带来的两类教化方式的共通性。
《法义》中两类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理想国》中哲人王与辅助者之间的绝对的不平等关系。就前者而言,虽然两类教育对象分别是爱智慧和爱自由,但二者都拥有一定层次的智慧,且都受着智慧的引导,即使顶级的夜间议事会成员,他们所拥有的智慧与普通公民所拥有的智慧,也不是在种类上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已经知道,《法义》的独特之处,就是努力消解法律的内在暴力,提出并重视法律序言的劝谕功能,劝谕不是命令和告知,而是尽力给出解释并使得自由公民能够理解。自由公民能够理解立法者的解释,就说明自由公民一定具有智慧和理性,否则就谈不上任何的理解,或者说,当立法者用劝谕的方式对待自由公民时,就意味着“对公民自我推动道德发展的真正能力的尊重,也显示这对这种能力的确认”[9](P.189)。当然,自由公民的智慧和理性,在程度上肯定不及立法者和夜间议事会,但它们并没有种类上的实质上的差异,毕竟次好城邦的统治者也是由自由公民选出来的。柏拉图即使赞颂了立法者的智慧,但在《法义》中也极少谈论“哲学”,哲学的字眼只出现了两次,即使被后人视为“哲学家”的夜间议事会中的老人,雅典人也说他们拥有的是“理智的影像”。与之相反,《理想国》中的哲人王与辅助者,尽管在腓尼基人的神话中,都由一个母亲(土地)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二者的差异是根本的,哲人拥有瞻望善的理念的高贵理性,辅助者则不拥有这样的高贵理性。当然,辅助者有理性,但他的理性与哲人的理性有种类上的差异,由此《理想国》不会允许辅助者去推选哲人王。
对于《法义》与《理想国》的这种差异,埃尔文(Terence Irwin)有相当到位的分析,我们不妨转引一下:
对智慧和理解的要求表明,《法义》在实质上而不只是在言辞上与《理想国》有所不同。柏拉图相信,普通公民应当拥有某种层次的智慧,因为他相信可以合理地期待某个层次的理解,它超出了单纯接受一个人被告知的东西。柏拉图保留了苏格拉底式的确信,即美德不仅要求正确的行动和正确的信念,也要求理解和理性。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没有承认他的确信的含义;特别是,他没有说明,可以指望多少人能满足他对一种理性论述的要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依靠苏格拉底式的确信来捍卫自己的主张,即只有很少人才能成为有美德的。在《法义》中,柏拉图暗示了《理想国》中的立场过于受限;他想要保持苏格拉底式的确信,却又要坚持认为它令美德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法义》比《理想国》更符合苏格拉底式道德探究精神。[10](PP.563-564)
由着两类教育对象的平等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尽管面向数量较少的统治者的教育方式是理性论证,面向数量较多的普通大众的教育方式更多的是神话,但两种教育方式又具有共通性,那就是它们都承认任何教育对象都具有程度不一的理解能力,都能理解教育者的劝说内容。(13)严群先生认为,柏拉图以神道设教,是一种愚民:“柏氏晚年提高宗教的地位,很显明地是从功利主义的心理出发,在他以为当时人民的程度还够不上讲知识——谈哲学,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宗教范围它们。于此可见柏氏也曾采取愚民政策。”见严群《柏拉图及其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2页。这样的观点,忽视了柏拉图对普通民众理解能力的认可。当教育者通过神话故事去传递有益于城邦公共利益的观念和知识时,他绝对不是一味地宣讲,而一定是在努力寻求受教育者的正确理解,也就是说这一教育方式中蕴含理性和对理性的承认和尊重。(14)对于大众,我们不能说“神话”是唯一的教育方式,在某些时候,理性的方式也是需要的,尽管大众学习起来不容易。我们可以在卷十的一段对话中,体会到这一点。克:立法者“应该援助礼法本身和技艺,表明它们源于自然,或源于某种不低于自然的东西,如果它们是心智的产物,依据正确论证的话”。雅:“热情无比的克勒尼阿斯呵!这个呢?向大众讲述这类论点,他们岂不是很难领会?此外,这岂不要长篇大论?”克:“如果法规一开始难以听懂,那也无需担心,只要学习吃力的人能反复研究就可以了。倘若法规冗长但有益,那至少在我看来,每个人若因这[法规冗长]而没有尽其所能援助这些论点,就是完全不理性也不虔敬。”雅:“确实,墨吉罗斯哟,我们应当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参见林志猛《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2卷,890d-891a,第208页。否则,诉诸神话故事的教育者,就变成了纯粹的诗人,即他只是通过挑动起受教育者的粗俗的快乐的方式,去传授神话故事中蕴含的观念。总之,神话、理性、愉悦、德性,融合在雅典哲人的神话教育当中,或者说,逻各斯与神话在神话教育中不是对立的。
最后,对于两种教育的共通性,还想从“限度”的角度简单谈一谈。这一角度,是马特(Francois Mattéi)在《柏拉图与神话之境》提及的。马特认为,在柏拉图那里,理性也好,神话也好,都在坚守“限度”。加缪(Albert Camus)亦有言:“古希腊思想永远坚守限度。它永远不走极端,无论神性还是理性,因为它从不否认什么,无论神性还是理性。”[4](P.68) 在《法义》中,柏拉图将真正的教育,视为将年轻人塑造为坚守限度的实践活动,这一限度就是尊奉“正义”:“我们所指的是童年起就进行的德性教育,那种教育让人渴望并热爱成为一名完美的公民,懂得如何依正义行统治和被统治。只有这种教养,在我看来,目前这个讨论才愿意界定,并称之为‘教育’。”[1](643e-644a,P.17)由此可说,无论是理性教育还是神性教育,它们的一致之处,就是遵循正义这一限度并引导学生走向正义这一限度。不过,在现代社会,如马特所言,“现代理性是过度的孩子,拒绝服从限度。现代理性在自然之中置入权力意志,把善丢回历史的终结,丢回给某种无尽的总和的结局,一切形式的限度就此消失”[4](P.68)。与现代理性相应,呼应现代理性的现代教育,也丧失了限度,教育者教给孩子们的是无限度的技术理性以及相对主义的道德。自然的,尊奉限度的神话教育,也不可能被传承和留存,而是被现代教育所排斥。对于这样的教育现实,人们需要反思,因为失去了限度的教育,无法引导人追寻生命的意义,因为生命的意义发生于限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