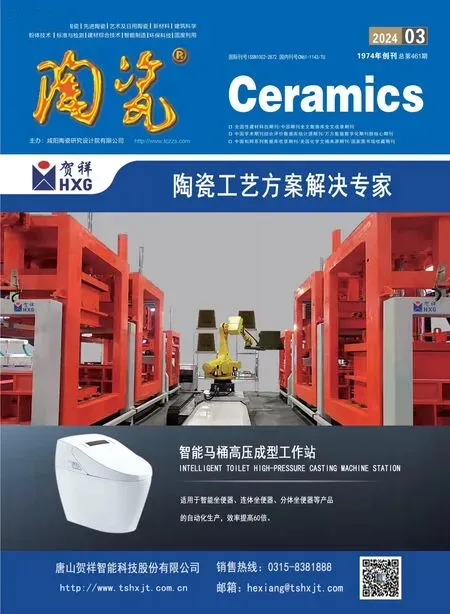论怪诞风格在陶瓷艺术中的应用*
刘思维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怪诞”一词本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学术术语,其字面词义为怪异荒诞、离奇不羁。怪诞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或艺术特征在原始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然而其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内的审美形式却很晚形成,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人对其进行正式而严肃的探索。19~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认知和审美的发展,怪诞风格的表达也由最初的“单纯想象”转变为“对现实的异化”,这种与现实相连的艺术手法也逐渐使得怪诞被认为是一种人类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在陶瓷艺术领域,怪诞风格也以其独特的形式为人类审美提供新的视角。
1 怪诞风格的概述——从被否定到被肯定
怪诞作为一种艺术现象由来已久。在怪诞正式成为风格流派之前,罗马时期的建筑家维特鲁威就曾对这种艺术现象做出过评价:“细小的花茎支撑着人头或兽头,花顶上画着莫名其妙的不和谐的小雕像。这些东西过去从未存在过,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他认为这些不合理的组合完全背离了世界的秩序,是一种混乱的想象。这种“混乱的想象”在15世纪以意大利语词汇洞窟(La grottesca 和Grottesco 与洞窟(Grotta))为基础,演变为“怪诞”一词,成为了一种风格流派。
随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推崇理性、秩序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数量日趋庞大,直到18世纪,怪诞的“非理性化”性质致使其仍然只能作为普遍意义上的贬义词存在,它是“可笑的”“歪曲的”“反常的”以及“荒谬物、对自然的歪曲”的代名词。至19世纪,怪但仍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表现形式,即便是黑格尔也对其感到厌烦:“我们不能在这种骚动混乱中找到真正的美”[1]。
人们对怪诞的认知,在社会阶级矛盾激化、战争频发的19~20世纪发生了极大转变。在文学、艺术领域,怪诞的“扭曲”“异化”“不合理的拼接与组合”逐渐成为一种人文主义情感的发泄与表达方式而不再遭到贬低和排斥。
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在其剧作《克伦威尔》的序言中,把怪诞从虚妄的幻想中拉回到现实世界,使其与现实关联而非单一的想象。沃尔夫冈·凯泽尔发扬了雨果的论断,在其著作《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中,他称其论述的怪诞是一种极具现代性且精辟的经典批评,他突出强调了其中阴森、恐惧的指向,是“疏远或异化世界的表达”[3]。此外,还有菲利普·汤姆森在《论怪诞》中就怪诞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阐释,“怪诞乃是意图祛除世界上一切邪恶势力的一种尝试”。他指出:“怪诞乃是作品和效应中的对立因素之间不可调节的冲突。”[2]所以可以认为,怪诞的一系列定义是“有着矛盾内涵的反常性”。怪诞是以矛盾的方式呈现的,是由滑稽与恐怖、过分与夸张构成的不可调和之存在。
2 怪诞风格在陶瓷艺术中的表达形式——对现实世界的异化
怪诞艺术的怪诞性往往和真实性对立统一,完全凭借想象所产出的作品不能被视作怪诞,因为它并未与现实产生联结,只作为一个孤立的精神产物而存在。只有将作品与现实有意识地结合,才能产生怪诞。因此,在陶瓷的艺术创作中,适当对真实事物采取夸张和变形等艺术手法以达到“怪诞意趣”的目的更能体现出一种艺术的自由张力。
2.1 异化的人
从人类世界的第一尊造像出现以来,人物一直是艺术创作中最重要题材之一。从史前世界到现今,人类对自我的塑造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不过我们依然能从这些遗留下来的塑像中看到怪诞形式的影子:公元两万多年前的《维伦多夫的维纳斯》,采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女性的身体部位,如丰臀宽胯,硕大的胸部造型,以表达原始人类的母神崇拜与生殖崇拜(见图1)。然而,这些造型并非现实的真相,而是通过夸张的手法表达远古人类的生存希冀。

图1 多地区均有女神像出土

图2 《Two Views One Window》
当代艺术家也依然会采用这种类似方式去表达带有“怪诞”风格的人物,如Patricia Rieger的陶瓷艺术作品《Two Views One Window》中长着四只胳膊的双面人像,他的胳膊伸向不同的方向,仿佛在实现某种摸索与探寻。这样的人体全然不属于真实的人类形态,难免让人产生怪异的感受,不同的观者自会由作品引发联想,从而对其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也是怪诞艺术作品想要呈现给人们的结果,即并非单纯的以“让人产生怪诞之感”为目的,重点在于“产生怪诞之感”之后的,人们的自我深省以及外化的行动。
2.2 异化的物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曾提出了关于原始人的哲学基础理论“万物有灵观”。如缅甸的克伦人相信植物也像人和动物一样有自己的灵魂。远古先民也会赋予动植物崇高的意义,通过对其本来面目的改造和再创作,最终使其偶像化,或成为人们拜谒的对象,或成为统治者以统治、震慑为目的,用以加强“君权神授”这一观念的手段。
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当一件艺术作品将物的形象通过某种程度的拼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人类前所未见之物,或者为其赋予人性、神性或怪奇性,使之与“人”产生瓜葛,成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人”,无疑会引发人们的惊诧、恐惧,甚至是崇敬之感。一些考古发现也佐证了这样的畸变形式:在古埃及《亡灵书》中就画着长有豺头的死神阿努比斯的图像,这些怪异的结合无疑对当时的人民产生了一系列的精神操控作用。而在当今陶瓷艺术领域中,将物进行畸变改造的创作也是十分常见的,但这样的组合早已与政治和神性脱离,艺术创作更多的关注当下社会问题:人类对世界的观点以及对自我的反思。
以色列陶艺家Ronit Baranga以其设计的“Body of Work”系列作品(见图3)而被广大中国艺术爱好者所熟知。在她的作品中,手、口等器官被编排安置在精致的餐具上,这似乎很难用常规的美学来定义。但是当这些餐具汇聚到一起时,手指唇舌相互交错,给人一种莫名的紧迫感,而这种紧迫感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源于观者内心的某种渴求。

图3 Ronit Baranga作品
另一位陶瓷雕塑艺术家Jessica Sallay-Carrington也擅长将不同形象进行重组和再创(见图4)。或将动物的头部与女性人体相结合,或将不同动物的特征组合到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形象,陶瓷的易碎性与脆弱性恰好也符合作者对集体中的个体,自然中的生物以及男权社会下的女性问题的关注。

图4 Jessica Sallay-Carrington作品
3 怪诞风格的艺术价值
从传统美学的角度来说,美是指一种使人感到舒适的,一种理想化的形象。而怪诞风格中的扭曲畸变形象往往与传统意义上的美相去甚远。随着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思考,人们对美的认知逐渐多元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终其一生去追求“恶之花”,并将这种与传统的美背道而驰的意象表述为一种“英雄气概”。在传统的秩序世界里,人们需要遵循准则:怪奇故事的出现,是为了使群众从中得到教化。强调善恶有报,以达到某种理性的统一;幻想中的巨兽被赋予特定的灵性,使人感到恐惧,其目的与前者别无二致。而当怪诞成为一种审美形式而被人们接纳之时,时空以及固有的秩序被打破,从而为人类看待世界增加了新的可能:怪诞风格的艺术作品取材自现实,却突破了素材原本的样式,为观众提供了比现实更自由的想象空间。刘法民曾对怪诞艺术形象进行概括,即用最熟悉的构成最陌生的,用最美善的构成最丑恶的,用最现实的构成最超现实的,用最非人的构成最人体的[4]。总之,怪诞脱离了正常逻辑和思路,是带有解放和颠覆意味的。
4 结语
怪诞风格的艺术价值通过对现实的异化表现出来,可将其总结为对自由愿望的满足,对陌生惊奇的创造、至情至理的表现,对自我的深层关注以及对哲理或观念的表达。其语义已由艺术审美转变为对人的精神的关注。在陶瓷艺术中,怪诞风格还处在相对冷僻的的境地,依然缺乏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但怪诞作为一种艺术风格颠覆了传统的秩序与美学,在其与陶瓷艺术融合时,能够充分利用陶瓷泥土的可塑性,烧成后的易碎性、脆弱性等特质去表达自然与社会中种种关系的“不适感”,这种“不适”往往隐藏着人类最本质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