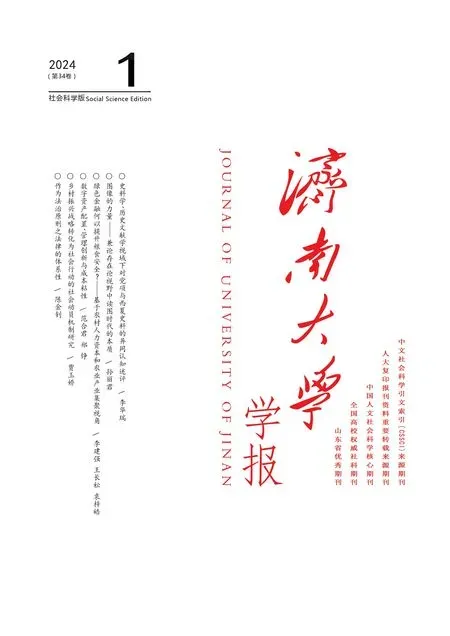经济体制转型下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伦理
——以《活着之上》《所谓教授》《第十一诫》为例
张艺瀛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发展,市场文化崛起,文学生产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写作方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进行重新编码。进入新世纪之后,市场经济的巨型话语地位凸显,知识分子在传统价值观念与市场化思潮的矛盾冲突之下,努力寻求个人价值认同和群体和谐。
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传统象牙塔逐渐式微,大学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构建出新的发展模式,而作为叙事空间的“大学”,也在经济体制转型之际,呈现出新的面貌。大学是文学生长的重要场域,作为文学想象的“大学生活”,投射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婚恋伦理和情感生活是探索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婚恋既是私人化的,又是社会化的。“婚恋关系是建构在情感与伦理之上的社会关系,其中也融入了一些极具时代特色的影响因素如物质、欲望。”①徐杨:《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婚恋小说中的伦理叙事》,《当代文坛》,2016年第2期。学院知识分子的婚恋关系和情感生活,无法剥离于经济市场化所带来的思想冲击。
一、大学叙事语境与知识分子价值传统
市场经济时代,商业逻辑凸显,都市化进程加快,大众文化发展,大众传媒崛起,这一切都导致90 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转向。“随着文化的高雅目标与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与市场的逻辑,交换价值开始主宰人们对文化的接受。”①[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后现代特征的消费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竞争和效率统摄下的学术生态得以酝酿和成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过程,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权利,大学内部的生存环境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作家们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纷纷以小说的形式去表现大学和大学知识分子的精神情况和物质状态。陈平原认为,“大学叙事”小说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大学教育调动了各种文学想像,直接促成了新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校园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描写对象”②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小说一改以往曲高和寡的境遇,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出现了如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马瑞芳的“新儒林”三部曲(《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以及袁越的“大学三部曲”之二(《大学恋》《大学梦》)等很多优秀的作品。新世纪以来,大学叙事长篇小说更是呈现出蓬勃之势,如张者的《桃李》《桃花》,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黄梵的《第十一诫》、葛红兵的《沙床》、汤吉夫的《大学纪事》、邱华栋的《教授》、倪学礼的《大学门》、王宏图的《风华正茂》、阎连科的《风雅颂》、黄书泉的《大学囚徒》、阎真的《活着之上》以及李洱的《应物兄》等,此等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李洪华的《20 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研究》将“大学叙事”界定为“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叙事空间,以各类大学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并由此表征不同大学形象和精神气候的小说作品”。③李洪华:《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页。而大学叙事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叙事人物,因此,这类小说在建构叙事内容时,必然呈现出在知识分子价值传统规约下的特殊意蕴。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以修身为己任,提倡安贫乐道,坚定地认为对精神境界、道德修养的追求要高于世俗利益和社会地位,而这份坚守提升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格调。但当市场以合法身份介入大学后,这种局面便被打破,消费主义注入了大学知识分子的价值谱系,物化、功利化的欲望被释放。大学知识分子本应是市场经济浪潮中最难以撼动的群体之一,但当象牙塔不再与世无争,知识分子不再独善独行,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情感理念开始转向。市场化语境统摄下,情感的逾矩和伦理道德的越轨成为了大学叙事小说中市场书写的重要部分,这对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是知识传播和道德教化的高地,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有些知识分子可能倾向于回归传统,有些则选择顺应市场潮流,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面临着精神世界的重建。虽然这些变化的反映,不是孤立于象牙塔之内的,而是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在一个特定范围内的呈现,但是知识分子思想和价值准则的独特性,使得市场经济时代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伦理呈现出既顺应又抵触,既含蓄又露骨的文艺质素。总的来看,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情感欲望为主导的婚恋,二是以功利或身体欲望为主导的婚恋。在这两类婚恋模式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
二、妥协与泛滥:以情感欲望为主导的婚恋书写
以情感欲望为主导的婚恋是恋爱和婚姻的主流,这类婚恋关系虽然也会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制约,但爱情是其内核,所以在这类情感关系的形成阶段,精神和物质之间,前者应该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但婚恋关系是具有延续性的,在恋爱或婚姻维系的过程中,外部条件和内在感受都可能发生转变,婚恋对象的爱情理念和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变化。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经济因素对婚恋过程的影响,使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呈现出多种矛盾和困境,这从大学叙事小说中可窥见一隅。
(一)精神对物质的让位
《活着之上》是在婚姻框架下的知识分子精神流变,与赵平平的婚姻是主人公聂致远精神层面对物质做出妥协的重要推手,经济考量对情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进步知识分子”与“现实主义的小市民”两类人物形象代表着“精神/物质”“理想/现实”的二元对立。聂致远与赵平平的婚姻是典型的以情感欲望为主导的,两个人既是同乡又是校友。聂致远是身为“研究生”的有为青年,面对自己的“最爱”,还是会自我怀疑,“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一个穷小子,白手起家,有什么底气面对赵平平这样一个漂亮女孩?”①阎真:《活着之上》,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并做出了“钱才是硬通货,才是底气,才是骄傲”②阎真:《活着之上》,第17页。的价值判断。虽然因为聂致远考博碰壁,又一穷二白,赵平平碍着母亲的关系和他分开了,但在聂致远考上博士以后又火速与他复合,这个过程中,赵平平即使对聂致远仍然有感情,但是物质的匮乏确实也动摇了她的情感天平。她说“要一个女孩一点都不现实,那也是不现实的”③阎真:《活着之上》,第27页。。可见,在两人的情感中,赵平平的爱是有条件和底线的,正是这种以物质为砝码的情感度量,为聂致远婚姻里的精神困境埋下了伏笔。
小说叙事中,在意识形态层面,聂致远在对市场化的“认同”与“不认同”之间游离。聂致远评价市场时代是“往钱眼里钻的时代”。《活着之上》多次出现“市场”一词,聂致远本科生的第一堂《中国思想史》课上讲到“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追求那个(金钱)的合理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以自身的逻辑即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统摄了我们的价值观,对精神的价值发出了严峻的挑战……”④阎真:《活着之上》,第117页。。聂致远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市场经济环境中,他不会为了金钱放弃内心对学术的坚守,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生活的重压下,我对钱有了更深的理解……感觉到它是活的,有着感性的生动,又有一种盲目的力量……这盲目中裹挟着快意,让人感到了恐惧。”⑤阎真:《活着之上》,第174页。可见聂致远已经感受到金钱对固有思想的冲击,但他同时抗拒和不安于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在不断的自我检视中,聂致远自我诘问“一个知识分子,他怎能这样去想钱呢?”⑥阎真:《活着之上》,第32页。金钱和权力成为了时代的巨型话语,情感趋向于物质的附庸。婚姻生活也是围绕着钱和权的现实问题,房子装修需要钱,考编制依赖权,赵平平和聂致远的婚姻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抱怨中徐徐展开。不满足于物质生活和工作现状,赵平平甚至萌生了打掉孩子的念头,她嫌弃聂致远工资低,聂致远就出去找兼职,可她又觉得赚钱慢,比不上“别人几十万几十万地赚”,聂致远对“做学问”和“赤裸裸的谋生”⑦阎真:《活着之上》,第152页。之间的转变不想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生活中几乎一切物质基础和物化想象,车、婚纱照、衣服、护肤品等等,都成为赵平平攀比的标志物。市场经济时代,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是人们物化思想的引信,“比一比就有感觉,还是有钱好啊!看了好的就不想看坏的了,你说人怎么会不变质?”⑧阎真:《活着之上》,第160页。赵平平的物欲追求得不到满足,这对丈夫聂致远形成了无形的压力,让他产生了“我算什么英雄好汉”⑨阎真:《活着之上》,第171页。的潜意识,而这种自然生发出来的意识形态转变恰是知识分子在金钱面前丧失自信的外在表征,金钱在婚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凸显。聂致远涨工资时,赵平平不冷不热地说“这年头知识要变现,那才叫知识。”①阎真:《活着之上》,第184页。而对比学历不高靠关系“搞了个办公室主任”的聂致高,聂致远深感资金拮据的困窘,这种困窘使聂致远自尊心受挫,也造成了其在感情方面的自卑感。赵平平背着他在网上联系生意,他便怀疑妻子和原来有过恋情的老板旧情复燃,他内心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自卑感却被赵平平点破。这种对感情的不自信来源于经济的不自主,虽然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却无法冲破因金钱的匮乏所陷入的精神困境。
聂致远作为坚守知识分子传统价值理念的代表,在《活着之上》呈现的市场环境中处于他者的地位,从最初的坚守到最后的妥协可见知识分子被环境“治愈”的深层逻辑,与鲁迅的《在酒楼上》、丁玲的《在医院中》等作品中知识分子被环境“治愈”的过程具有互文性。人的情感和思想特质会受到个体主观能动性与群体意识能动性的双重影响,个人行为会在环境的不断磨合中趋向于群体和谐。特别是,“婚恋”本身就并非个人化的,正如聂致远是坚守道德准则的典范,但他的妻子赵平平却是被物欲化的代表。妻子对他长期的精神施压,甚至以未出生的孩子相威胁,使聂致远最终不得不做出妥协。虽然他保留了师道尊严的价值底线,但也不得不在钱和权面前,为家人折腰,精神最终会向物质让位,呈现市场化的时代特点。
(二)情感的泛滥化
市场经济时代,大学叙事小说中情感的泛滥和寄生,婚姻与恋爱的剥离和畸变,使婚恋书写在和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念的碰撞中呈现出游离和复杂的一面。《所谓教授》里教务处长白明华公然包二奶,酒醉后又吐露出他在党办当秘书的妻子和老书记有非正当的男女关系;副教授刘安定婚内爱上了同学的老婆并发展为恋人关系;宋义仁教授(刘安定的岳父)的现任妻子是在舞厅跳舞时认识并离婚再娶的。《第十一诫》中学术声望极高的齐教授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却出轨了女摄影师、女弟子等多人。香港的慎教授和助教江夏都与齐教授的妻子有染。婚恋的暧昧化和复杂化是与经济市场化相联系的,群体意识中情感泛滥是与金钱直接相关的,这在《所谓教授》中普通民众的议论里有鲜明的体现,“老话说福贵生淫欲,贫穷起盗心,以前的教授一是受管制,二是没有钱,想风流也没条件,现在的教授谁怕谁,又有本事又有钱,不搞不风流也不大可能。”②史生荣:《所谓教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情感的泛滥化还体现在小说让婚恋的暧昧与复杂合理化。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中对于情感忠贞和节操的重视,婚外恋情被赋予许多美好而纯洁的想象。《所谓教授》中刘安定和何秋思的婚姻都缺少感情基础,又渴望刻骨铭心的爱情,两人虽然是婚外恋情,但刘安定却称之为“初恋”,他甚至觉得“只要能长久在一起,看着她,即使再不干什么,也心满意足了”③史生荣:《所谓教授》,第74页。。而宋义仁和现任妻子许慧是在舞厅认识从而离婚后在一起的,演戏的许慧和学者宋义仁的结合,似乎有悖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但小说并无贬义辞藻加诸之上,反而将之描绘成一份弥足珍贵的爱情,一份令女婿刘安定感动到流泪的真情。而这份婚外恋情也被刘安定定义为“现代青年的热情浪漫”,从而“觉得岳父是个真正有情有义的男人,他为爱情而痛苦,他为爱情而快乐,快乐和痛苦,都使他觉得活得很有价值”④史生荣:《所谓教授》,第22页。。作为刘安定的岳父,宋义仁对于刘安定和何秋思的婚外恋情,竟然更多地表示了理解,他觉得“年轻人有激情,互相有点爱慕也可以原谅”⑤史生荣:《所谓教授》,第255页。。而且宋义仁为刘安定理性分析情人和妻子各自的优缺点,没有丝毫的责备,客观阐明事情的利弊,希望他能做出正确选择。刘安定和宋义仁两位教授对彼此的理解,固然一定程度上源于相似经历下的情感共鸣,但这种对婚外恋情较高的接受度和包容度,也是经济市场化条件下知识分子思想开放程度提高的表现。
大学叙事小说中情感的泛滥化是大学知识分子在市场化语境统摄下,现实浮躁与内心固守之间相互矛盾作用的结果。这是竞争与效率并重,压力和欲望共存的时代特征下,滋生出的情感模式。
三、迷失与功利:以功利或身体欲望为主导的婚恋书写
经济体制转型赋予了大学知识分子新的婚恋观,在时代观念的导向下,大学叙事小说中所表现的婚恋模式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特征,区别于情感欲望导向下的婚恋模式,以功利或身体欲望为内驱力的婚恋模式更多地呈现出情感的功用性表征和身体的“类商品”属性。
(一)情感的功用性表征
市场经济时代,大学叙事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情感导向从纯粹的感性演变为以功用性为目标的工具理性。如《天眼》中学院院长史可亮衡量两次婚姻的价值皆基于利益考量。《裸体问题》中高校教师肖牧夫年轻时为了一张大学入学推荐表,放弃了他的女朋友和她腹中的孩子。《风雅颂》中杨科对旧时恋人——农村姑娘玲珍的背信弃义,以及与博士导师女儿的结合,也是一种将情感的工具理性凌驾于感性世界之上的行为。而杨科与赵茹萍的结合同样出于功利,这从杨科处理妻子与李广智的婚外情时的态度就能看出,他表现的不是伤心,而是一种得失权衡和自我疗救。赵茹萍与李广智之间的婚外情,则更多的是一种交换关系,李广智帮赵茹萍拿到了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最高奖和一套房,赵茹萍利用关系协助李广智当上了校长。《沙床》中主人公给裴紫的信中将爱情定义为基于身体、智力、地位和金钱等多方面权衡下的交换关系。市场经济时代,大学叙事小说中情感的功利化成为模式化的特征之一,投射出知识分子在经济市场化历史进程中的情感转向。
《第十一诫》中师母与第一任丈夫以及数任情人,都是以功利欲望为主导的婚恋。师母在去香港时,认识了经济殷实的慎教授,慎教授用疯狂的金钱攻势俘获了她的心,游山玩水,购物吃饭,为她购置的精美华服让其产生了“慎教授的秃脑袋已经惹得她怪喜爱的”①黄梵:《第十一诫》,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85页。错觉,这是物欲获得极大满足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情感转嫁。回到家,师母便向齐教授提出了离婚,这是典型的趋利行为,情感的趋向只建立在利益权衡之上。师母在丈夫受伤瘫痪在床时毅然离开,又在情人身体每况愈下,而经济状况又比想象的相差甚远时,审时度势地想要回到丈夫身边。后来,齐教授在压力下身心俱疲猝死在医院,师母又迅速攀附上了新来的主任。这种情感演变,没有给读者任何喘息的机会,对师母在功利欲望驱使下的情感依附进行尖锐批判,同时也投射出以情感为表象遮蔽下的灵魂在欲望泥潭中的挣扎。大学教师王标为了去美国而背着女友和一位来自檀香山华裔家庭的丑女人来往。齐教授背着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出轨了又老又丑的女摄影师,而这并非出于情感驱使,是因为在貌美又自信的妻子面前,齐教授自惭形秽而丧失了身体自信。面对“粗矮臃肿”的女摄影师,齐教授获得了权力压制的幻觉,体会到权力控制的满足感,而对这种满足感的追求也是情感功用性的重要表征。另外,小说中未具名的有钱中年男人和女大学生之间的暧昧关系,昭示着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群体也是被物欲腐蚀的对象。
《活着之上》中对于情感的功用性呈现得比较隐晦,赵平平在因为聂致远的不得志而和他分开的一年中和一个经理在一起,经理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去推测,但为了安抚赵平平,经理给了她八万块钱,这利用感情作为砝码换来的金钱,也是个人在物质、情感和道德面前所做出的交换和妥协,而当情感成了货币的等价物,人便沦为了物质的附庸。面对赵平平用曾经的情感换来的金钱,聂致远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度,他虽然对于这种事发生在自己妻子身上一时难以接受,但却表示可以理解“一个女孩利用青春为自己的生活打个基础”①阎真:《活着之上》,第37页。。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对于情感的功用性是秉持一种默许和不排斥的态度,这种价值转向,是知识分子群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钱、权巨型话语统摄下的妥协。聂致远对自己的研究生贺小佳产生了超越师生的特殊情感,出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道德约束,聂致远把它深埋在心里,只是想尽办法地去帮助她,而这次的碰壁也彻底激发了他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贺小佳表示有个有钱但有家室的男人想要帮助她,当然其中的代价不言而喻,面对学生的人生抉择,作为导师的聂致远没有第一时间反对,连他自己都觉得并没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可以去反对,这也是知识分子对于情感功用性的默认和妥协。而贺小佳最终选择不妥协也代表着新一代知识分子对道德准则和纯粹情感的坚守,这也寄托了作者阎真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未来的美好期许。
(二)身体的“类商品”属性
“商品”是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当身体作为私人物品,以交换某些利益为目的的出让,让身体具有了“类商品”属性,身体不再是欲望的客体,而是功用性的客体。文本中被性赋值的色情也并非仅仅是时代的欲望化想象,而是知识分子物欲追求的表征。
《风雅颂》中赵茹萍为了国家论文评比的最高奖将身体出卖给了副校长李广智,身体和奖项形成了等价交换关系。而耙耧山脉后寺村不识字的乡村姑娘付玲珍在杨科回去退婚之际却提出要将身体给他,她什么都不图,只是为了让杨科一辈子记住她。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赵茹萍与隔绝于市场之外的大山中的付珍玲,形成了价值观的强烈反差。这也意味着,市场带给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甚至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迷失,而是价值观的颠覆。《第十一诫》中江夏对师母产生的畸形迷恋是以身体欲望为主导的婚恋。小说中对师母性感身材的直白描绘,以及热情而暧昧的态度,都使这份畸恋抹上了浓郁的欲望色彩。江夏对相亲认识的女孩甜言蜜语并发生性关系,却没有投入任何感情,是江夏在身体欲望驱使下亦或是为了躲避寂寞而开始的恋爱。这里,“身体”是情感生发的主要源泉。《第十一诫》中马厉为了获取留校名额,买通了一个妓女冒充自己的表妹,在年级主任和他的“表妹”发生关系后,便不得不在分配工作时为他做周全考虑,将留校的名额给了学业欠佳的马厉。在这个利益环链中,“表妹”的“身体”充当了交换的筹码,产生了“身体”和“留校机会”的等价关系,给商品经济的利益交换赋予了新的想象空间。除此之外,还有为了留在省城而将身体出卖给班主任的女医生,重复着“身体”的利益索取。这种关系可能是非常短暂的,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婚恋模式,但却代表了畸形化的两性关系。
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书写并不完全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但因为群体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体性认知的影响不容忽视,所以讨论文本中边缘人物的情感选择也是很有必要的。《所谓教授》中飘飘为了吸毒卖淫,后来虽然找了老实的刘三定成了家,但还是会为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将身体出卖给了白明华。而白明华为了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将自己的情人悦悦送给了计委主任赵全志。悦悦靠出卖身体给赵全志,不仅自己从一个博物馆的解说员当上了地方旅游局的副局长,还给自己的男朋友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这个以身体为交换砝码的利益链条中,作为大学知识分子的白明华只是其中一环,但是婚恋关系所具有的社会性,使得任何个人都无法脱离群体去探究婚恋和情感,知识分子的婚恋观也是在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嬗变的。
经济市场化浪潮下,“身体”不仅仅是欲望想象的空间,更成为了明码标价的“商品”,用于交换,获取利益,被赋予了“类商品”的属性,赤裸裸地呈现出物质化和欲望化的特征。
四、结语
大学知识分子在专业、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是异质的,他们或以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与“克己”约束自身,如《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或披着“为人师表”的外衣肆意宣泄自己的欲望,如《第十一诫》中的齐教授;或身在象牙塔中却致力于钻营个人利益,如《活着之上》中的蒙天舒和《所谓教授》中的白明华。大学叙事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均质化的个体想象,而是影射着多样化的人物和社会情状,小说以生动的笔触见证了经济体制转型对大学知识分子情感生活的影响。一直以来,知识分子都有“出于清高耻言钱”和“出于隐私讳言钱”①陈明远:《何以为生 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的传统,但婚恋的选择却赤裸裸地透射出知识分子的金钱观念和价值取向。经济体制转型下,市场经济时代的进步就在于承认个人欲望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是有限度的,正如阎真在一次访谈中所谈到的,“功利主义和欲望都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不是无边无际的,它不能任性,也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平衡的力量,人就会变得欲壑难填。”
与以往知识分子“耻言钱”“讳言钱”的传统不同,鲁迅对“钱”“经济”一直非常关注,也对妇女的经济独立,尤其是婚恋关系中女性的经济权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强烈呼吁,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鲜明地指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②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而这种超前的经济意识在市场经济时代得以深化,女性的经济意识广泛觉醒,对“钱”的重视在合理范围内,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市场经济时代,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会在意识形态上无一例外地受到市场化语境和市场规律的制约,大学叙事小说中对婚恋和市场的书写,敏锐地捕捉到了婚恋伦理在市场导向下的新情态。也可以看出,学院知识分子在对尊严和名誉极端看重的前提下,仍然会在市场导向下存在某种妥协和迷失,这种情感的逾矩和道德的越轨,是内心主体意识与市场化群体意识双重作用下,以及个体主观能动性与群体能动性交锋下的产物。经济体制转型下,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书写无法剥离于市场经济的底色之外,在婚恋与市场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既有对人性的消极物化,也有对经济意识的积极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