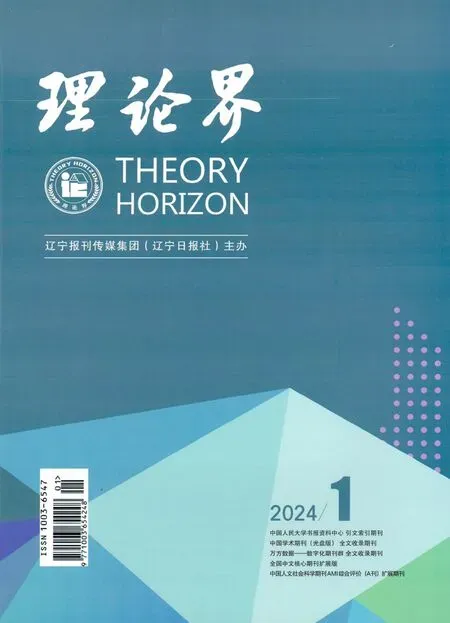蓬舟与归处:论艾朗诺的李清照研究
葛涵瑞
美国学者艾朗诺(Ronald Egan)的著作《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1〕(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LiQingzhaoandHerHistory in China),以下简称《才女之累》),2013年由哈佛出版社出版,又于2017 年译成中文,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出版之前,《才女之累》已经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在中文刊物上。〔2〕对海外汉学界来说,该书极大地弥补了向来薄弱的宋代文学研究。〔3〕而对国内传统的古典文学文献研究而言,艾朗诺的最大贡献在于采取女性主义视角,为李清照这一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基础。这一点也往往是评论者最关注的地方。但比起20世纪,当《才女之累》出版时,女性主义批评已然不能算作新鲜话题,为何艾朗诺的研究仍能引起相当程度的讨论?
原因或许有二:其一,研究落脚点不同。以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女作家,该模式先前多出现在明清时段和小说领域,在明前的诗文研究中尚不多见。虽然也有《彤管:中国帝制时期的女性写作》(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这 样对女性诗人进行介绍与评价的著作,但如《才女之累》一般,以专书的形式进行专人研究,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二,具体研究方法的进步。20 世纪90 年代,国内的李清照研究中已经出现“女性形象”“女性色彩”等话语,但大多停留在直观感受,如“思深情浓的形象特征”〔4〕“女性特有的含蓄美、矜持美、纯真美、崇高美”〔5〕等,并非系统的女性主义理论批评。而艾朗诺将性别研究作为理论依据,在《才女之累》中,对李清照女性身份的性别敏感贯穿始终,性别建构的观念是解读李清照的关键因素。〔6〕这对于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创新。
一、新意:女性主义视角
艾朗诺在结语中说,引入女性主义是“借此提供一种全新视角和理论基础”,并且“依凭女性主义的相关研究对老问题提出新方法”。艾朗诺并非女性主义学者,他的出发点不是“要用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李清照”,而是在当下女性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利用近来女性文学批评的看法,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女性词人。他的研究方法是中性的,但《才女之累》的结论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7〕
第一章至第三章,艾朗诺的关注点从宋代社会背景逐渐聚焦至诗人本身,通过对比“不赞成女子为文”的社会风气与李清照强烈且自觉的写作意识,突出了李清照的两点特殊性:作为女性,她是以书写为荣的写作者;作为写作者,她是“本不该”出现的女性。诸如此类的对比在书中比比皆是。除了时代社会与诗人个体的对比之外,还有关于男性书写者(士大夫)和女性书写者(尤其是闺阁文人和名媛文人)面对相同事情时所获评判的对比。宇文所安点出,艾朗诺将李清照及其作品不但置于女性创作,而且是才女创作的语境之中。
第一章“宋代的女作家”中即提到,男性为文,在科举取士的大背景下,是必要且受到鼓励和宣扬的;而女性为文则受到掩藏和压制。第二章言及李清照因《词论》中评判当世男性文人而遭到指斥,艾朗诺敏锐地指出,南宋胡仔之所以借韩愈“蚍蜉撼树”之语批判李清照,“更在于她是个女子”,而后世评论家针对诗人性别的贬损更为直接,“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在针对李清照的早期评论中,无论赞誉或否,总格外挑明她的女子身份,暗示她的才华无法突破性别制约;或是将她的文才与改嫁之事相结合,批判诗人德行的缺失。这种“失德”无法被才华弥补,女性诗人的才华无法脱离名节而实际存在。在评价情爱直露的词作时,他们严厉指责李清照作“荒淫之语”“无所羞畏”;而当同样风格的词作出于男性时,尤其面对欧阳修这类政治地位很高的词家,他们的评价却温和得多,甚至会替人讳隐,认为那些词作是旁人的诋毁,并非真正出于欧公之手。第三章中指出一种预设,即读者默认用典,拟题和代作是男性写作者的基本技能,而女性写作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在阅读男性作品时会深求其隐藏含义,而面对女性作品时,则认为它们直白浅薄,只是“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女性词作较男性词作更容易被读作自传的重要原因。人们对男、女词家作品的标准是不同的,承认女性也具有代言的能力(男性的写作能力),会让长期占据写作和阅读主导地位的男性感到被冒犯、愤怒和无所适从。在第七章至第九章的李清照接受史部分中,艾朗诺着重探讨了诗人的再嫁与否,而再嫁之所以在明清至近现代几百年的李清照研究中成为焦点,正是因为世人对“男子再娶”和“女子再嫁”截然不同的道德评判。
但在引入女性主义批评的同时,《才女之累》的重点仍落在李清照研究的具体环节上。厦门大学教授、宋代文学研究者钱建状认为这是一种“务实的学术态度”,避免了借李清照来证实欧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所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盐在水,不见踪影。〔8〕
二、破除:传统的自传解读
立足女性主义视角,《才女之累》进一步挑战传统的易安词读法,即破除自传式解读。艾朗诺敏锐地意识到,人们对男性作品与女性作品的态度是不同的:默认男性作家具有拟作和虚构的能力,从而并不会将每一篇作品都读解为作者的自传;但在面对女性的作品时,则有着“女性不具备如男性一般的写作能力”“女性作品必定直白浅显”等先见预设,从而将女性词作解读为作者的自传,将作者与词作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即使是李清照,也不能免于遭受这样的自传式解读。《才女之累》通过还原李清照的创作背景,分析其创作意识,证明李清照和男性写作者一样拥有虚构艺术形象的能力。她的词作并不一定就是自己的传记。
在第三章“易安词的相关预设”中,艾朗诺集中论证了易安词自传体解读的困境。传统阅读中总会将易安词中的角色等同于诗人自己,并且从借助词风、意象、地理特征等为易安词系年,力证某词是李清照在某一时期所作。但李清照完全可能具备一般男性词人拥有的写作能力,她可以虚构出人物形象,并代这个虚构的形象发声,正如“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体一般。除此之外,词常在饮宴间歌唱,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也应如古时乐府一般,具有便于即时创作的程式与套语。作为一名与高级文人圈有接触的贵族女性,李清照不应对填词的程式一无所知;兼之博闻多才,未尝不能借助常见套语与传统题材,创造出无涉自己实际生活经历的词作。宇文所安认为,中国学者投入巨大的学力和心思为易安词系年,并对其进行传记式的语境化,而没有想过这些词作是否真的可以直接表现作者的生活经历。李清照通常被用作证明“实人”之“证据”的作品,可能实际上是某种形象的建构,而这些作品就是建构这些形象的文献基础。〔9〕
破除自传式解读的另一种重要途径是对易安词进行辨伪,《才女之累》花费了大量篇幅讨论易安词的真伪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和第十一章。第三章集中于易安词的传播史,艾朗诺通过分析收录易安词的词选与易安词集的编纂事件,指出系名李清照的词作随时代发展而增加,但大半作品却没有可靠的文献根据。而传统的自传式解读对易安词真伪并不做分辨,以至出现循环论证:以词作细节贴合诗人生活情景,并用这种贴合反证该词确然是李清照所作。但以出现年代与文献出处而论,这些词作的真实性是可疑的。判断一首词是否为李清照作品,标准应是年代先后与早出晚出,而非自传式解读者所认为的词风与情感表述,盖因后者可以被模拟和伪造。第十一章中,艾朗诺对几首晚出易安词进行文本细读,并将之与早出易安词进行对比,指出部分易安词最初并非系名于李清照,在逐渐“成为”易安词的过程中,它们塑造出李清照在明清时期的新形象:情投意合的夫妇中的一方。自传式解读青睐于这样的诗人形象,却忽略了这种形象本是通过某些词作的系名塑造出来的。李清照是否为其实际作者尚存疑,更不必说词作内容能否表现她的真实生活。
艾朗诺并不是要将李清照本人与词作中的角色彻底分离,相反,他肯定了传统自传式解读的合理性。比如李清照词作中的女性都与自己的贵族女子身份近似,其间并没有宫妃或下层歌伎。将易安词简单划归为代言或自传都是不合理的,与其试图指出李清照有哪几首词是虚构,哪几首讲她本身的,不如说正如其他中西诗人一样,她的作品是本人的经验和想象的复杂结合体。〔10〕但《才女之累》无疑为解读易安词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我们可以如同阅读其他传统士大夫的作品一般,将易安词看作接受过经典教育的、有优秀的写作能力的“人”所作,而非“女人”所作。她的性别没有她的技巧那样重要。〔11〕易安词具有化用、虚构、代言甚至是练习、应酬和游戏的成分,理应拥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视作一位妻子关于自己生活的写照,并且这生活仿佛只与她的丈夫息息相关。
三、文本细读:《词论》与《金石录后序》
《才女之累》择取多种文类,对李清照部分作品进行了独到而精细的文本分析。对易安词的分析集中在第十章与第十一章,易安诗的分析集中在第二章与第五章。除诗词之外,还涉及李清照的文作。
以《词论》为例,艾朗诺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李清照作为女性,试图跻身男性主导的文人圈并争取认可的努力。与其他论词文章不同,《词论》坦然接受词是卑俗文体,并将词体文学独立出来,将之与“学”分离。在阐述词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艺术特征同时,对前代与当世词人进行批评。艾朗诺着重分析了《词论》开篇李八郎的故事,认为闯入女性歌伶竞技世界,并最终凭才华获得认可与称赞的李八郎就是李清照本人的化身。艾朗诺对比了《词论》中李八郎之事与原《唐国史补》的记载,强调了李清照对故事中表演场景的格外渲染,并从地域差异、应酬场合和人物之间的差距三个角度,证明了李清照在征引这个故事的同时对它进行了改写,使李八郎的形象更加符合她的内心写照。艾朗诺敏锐地注意到,在李清照改写的故事里,面对李八郎,众人“或有怒者”,并以此为切入点,引入女性主义立场的解读:故事中的李八郎作为异性,闯入了女性歌者的领域;而李清照同样作为异性,闯入了男性写作者的领域。阅读与写作的世界原本是男性的,纵是通常被认为较诗文卑下的词,也是男性的领域。作为女性,李清照的闯入无疑激起了他们的警惕、讥讽,甚至是愤怒。钱建状认为,无论是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逻辑,还是从《词论》引用、改编这一则唐人故事的动机,结合李清照生前作品受到的无端指责来看,将李清照代入李八郎,都有其合理性。〔12〕
第六章名为“《金石录后序》”,艾朗诺以一整章的篇幅集中解读此文。在对《金石录后序》进行文本分析的同时,艾朗诺着眼于文本之外,力图通过还原李清照的创作情境,来重新审视《金石录后序》的传统读法。出于保护藏品以维持经济、在再嫁又离异后重获尊严等多重目的,李清照写下《金石录后序》,非常清楚这篇文章的性质不是私密言语,它将在更大更公开的场合被人阅读,所以她对回忆进行了选择性的呈现。在艾朗诺之前,宇文所安也对《金石录后序》做过文本分析,但宇文所安的重点更偏向文章的前半部分,即李清照的收藏与以收藏为载体的回忆。这些回忆并不像传统解读中惯常表现的那样美好。李清照从支配收藏到被收藏所支配,写下一篇如何评判价值的论文与一部价值观的历史。〔13〕而艾朗诺更着重从文本中探求李清照的创作动机,将《金石录后序》的创作置于一个情境之下:创作者身为女性,遭受国破家亡的沉重打击,并且自己几近身败名裂,她需要这样一篇文章为自己发声正名,达成一些关乎切身利益的目的,而非单纯的感怀抒情之作。钱建状认为传统解读将《金石录后序》的目的集中在怀旧,既与这篇文章承载的资讯不相称,也易脸谱化李清照;而西方学者注重心理分析的传统,注重细节分析,甚至可以进行超文字的解读,更能凸显出时代、背景与人性,值得我们借鉴。〔14〕
四、女性意识:预设与循环
《才女之累》揭示了李清照自传式解读的循环性,但心理学分析如果缺乏有效的材料支撑,容易陷入过度阐释,或会导致另一种循环论证,即预设李清照具有女性意识,而后又对其进行证明。本身的结论已经内置许多女性主义批评的假设。〔15〕钱建状从“女性主义批判”和“隐喻与心理分析”两个角度评价《才女之累》,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也通过明清文人在保存李清照作品中起到的积极作用、钞撮的错漏与宋代词选的选取标准这几个方面,指出艾朗诺存在的偏颇与误读。在此,笔者也提出一些有待商榷之处。
首先,是身体修饰对判断人称指代的可靠性。这一判断方式直接影响到,如何辨别女词人笔下的女性是“自己”(第一人称)还是“他者”(第三人称),即为何女词人的作品常被解读为作者的自叙。作为海外学者,艾朗诺从翻译的角度指出,读者需要对易安词中的人称指代更加敏感。将词作主语理解为第一人称时,词中的主人公是李清照自己;而将词作主语理解为第三人称时,词中的主人公正在被写作者观察。在第十章中,艾朗诺举秦观“独卧玉肌凉”一句为证,认为该词上阕是第三人称叙述,因为叙述者不可能用玉肌一词提及自己的身体,即,自叙时不会进行身体修饰。此处是旁观者的观察,写作者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观赏词中女子,并且拥有描写她外貌和情感的权利。
这本是非常符合女性主义批评的解读。许多男性作家的词作因其对女性心理的理解而受到称赞,女性主义批评可能会指出,大多数这样的词,告诉我们的并非女性自己的想法或感受,而是男性作家如何看待女性,〔16〕女性处于男性的凝视之下。但艾朗诺此处的论证或可商榷。即使以“玉肌”一类具有修饰意味的文辞描述身体,也不尽是旁观者的观赏。这类对身体的形容,本也是词体常见的套语。李清照《词论》中评价的先代或当世词人,其作品中都有类似修辞,如欧阳修“瘦觉玉肌罗带缓”“青衫透玉肌”,晏几道“月脸冰肌香细腻”,柳永“玉肌琼艳新妆饰”,苏轼“玉肌匀绕”“玉肌铅粉傲秋霜”。在早出的易安词,即被艾朗诺认为最可信的一批李清照作品中,也有“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句。正如前文所言,作为与高级文人圈交往的贵族女性,李清照不会对男性填词的程式一无所知,而她也具有借用化用等写作技巧,未尝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主动使用这一类修辞。对身体进行修饰性描述,并不足以成为判定人称叙述的依据,更不足以成为区分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笔下女性的判断依据。欣赏与描绘词中女性角色的身体,并不是男性词人的专利。如何判断女词人的作品中哪些是自叙,哪些是作为意象或套语,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其次,李清照作诗时,是否有与男性文人相争的“女性意识”。换言之,“女性意识”是否为造就易安诗强硬风格的原因?在第二章“李清照的诗及其阳刚风格”一节中,艾朗诺认为,李清照深知自己的作品因性别而备受质疑与敌视,所以她反其道而行,着力创作阳刚风格的诗作,以此证明自己的才学与力量不在男性之下。此处的问题仍在于前文所说的循环论证,即已经预设了李清照是具有清晰女性意识的写作者。诗人认识到自己无法如当世男性文人一样扬名,并不是才力不及,而仅仅是因为性别,从而进一步希望在男性的领域用男性的题材与风格战胜男性,所以她的诗作立场比男性更加强硬。但此处问题有二:其一,李清照并非没有传统意义中婉约的“女性化”的诗,《才女之累》所参照的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中,即有《春残》《偶成》等作。与其说李清照在部分诗作中“男性化”的措辞与立场是感于因性别遭受不公,有意以男性风格压倒男性,或以时事诗与咏史诗的题材风格来解释更为妥当。其二是诗词有别,传统写作里诗体与词体的题材与风格本就多有不同。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多用成语典故,多发议论,李清照的时事诗与咏史诗,尤其是《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相当鲜明地体现了这些宋诗特征。〔17〕部分易安诗中的阳刚风格与“深有思致”,或是题材、文体与时代风气所致,而非李清照的女性意识驱使她与男性写作者相争。
另外,在这一节中,艾朗诺认为其他的宋代女作家从不写关于政事的作品,因此,更显现出李清照的独一无二。此说存疑。王灼《碧鸡漫志》载子宣夫人魏氏,即《才女之累》第一章“名媛文人”一节所言“魏夫人”,作《虞美人草行》咏项羽虞姬事,〔18〕清《柳亭诗话》评其为“方见英雄气概”。虽然此诗作者是否确为魏夫人尚不可知(胡仔认为是许彦国所作),但正如艾朗诺在第一章所言,作为接受经典熏陶的上流社会女性,她们饱读诗史,极有文化涵养,家族中男子担任朝廷官员,她们未尝没有写作指涉政事的作品的能力。只是社会并不支持女性为文,阻止她们的作品在外流传,所以作品不见于世。但女性之间未尝没有自己的交流,如陆游为宣议郎孙综之女所作《夫人孙氏墓志铭》中提及,“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20〕李清照想要将自己的才学传授给更年轻的女性。尽管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似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在帝国末期之前,中国有一个独立的女性文学传统,但将李清照作为唯一有意愿且有能力创作政事题材作品的女作家,似乎有失武断。
五、归处:女性如何接受女性
虽以“接受史”为题,但在李清照的接受史方面,《才女之累》的研究仍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书中该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七章至第九章,其中涉及南宋至明清时期的女性对李清照的接受。作为以女性主义视角为亮点和重点的李清照研究,《才女之累》在后世女性对李清照的接受,尤其是明清能文女性对李清照的接受上,仍有深入的余地。或可从女性作家的创作、女性编辑的选本、关于女性的图像呈现,如绘画与刺绣中,探寻明清女作家对李清照的接受。
明清时期女性写作得到长足发展,统治阶级女性正式把文学创作纳入她们作为有教养有德行的闺秀的成就之中,在出版的别集和选本里她们也被看作作家。现在关于明清女作家已经有成就不菲的大量研究。〔20〕张宏生认为,明清女词人对李清照作品最为关注的语意,主要集中在《如梦令》“绿肥红瘦”与《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两处;对《凤凰台上忆吹箫》的情调表现和感情脉络也多有偏爱,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模仿。〔21〕明清女词人对于李清照,基本上回避了男性文人所作的道德评价;与此同时,也难以避免地接受着男性文人的影响。
无法忽视也无法否认的是,在帝国晚期得以留下文字的女性,无一能够脱离其男性亲友的资助。她们的话语经过了择取、检选,才能公之于世,而在被听到的过程中,又被解读为各种女性应然的美德与高行。并非说这样的传播与解读就全然违逆她们书写时的“本意”,甚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们自己也在有意且主动地宣扬这些女性美德。〔22〕但在此之外,她们自己的声音还余下多少?隐藏在那些“合德”“合理”的文辞下,赧于、耻于甚至是惧于被知晓的女性自己的声音,借文字留存下来,等待被知音关注、发掘并与之对话。这些知音者或是同时期的能文闺秀,或是世外比丘尼,或是选集刻版的女性编者,又或是经年之后的女性读者。
作为女性书写者的典范,李清照在漫长的时间洪流里被持续地注视。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认为,李清照的时代没有形成女性传统,她与之前及之后的女作家在创作上是各自孤立的。李清照的诗词不曾受到以前女性作家的影响,对之后的女性作家影响也不够,没有多少证据支持宋元时期具有独立的女性词作的书写传统。关于李清照被女性当作榜样的研究文献很少,但她成为后来几乎所有女作家的衡量标准。〔23〕作为一名非凡的女作家,李清照生活在一个男性对女作家不屑一顾、对女作家有规范期望的时代,“一定意识到她会被视为一个决心创作文学作品的女性”。〔24〕而一首通常系于她名下的《渔家傲》云:“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此问或可置于文末。女性主义视角之于李清照研究,正如一条崭新的蓬舟,以新的方式进入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指引学人进入更深更广的空间。她的言语归于何处?她的形象归于何处?在明清时期数量猛增的女性作家及作品里,如何找到这位先驱与偶像的复现?她为她们带来了什么?她们又是如何看待她的?此处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