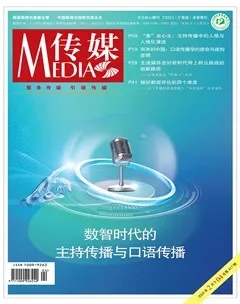在媒体变化中发掘自身潜能
敬一丹
探讨“数智时代的主持人实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数智时代给主持人实践场域带来了哪些不同层级的变化?对主持人群体的主体能力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总体来看,数智时代所引发的一系列变革激发了主持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应对能力。从“发展”到“生存”,从“弘扬”到“坚守”,不同时期传统媒体内容生产者所谈及的关键词的变化,映照出传统媒体行业的式微。过去,内容本体层面“节目”和“格局”是媒介生产实践的核心考量标准。进入以深度商业化为主要表征的数智时代,“商务”和“经营”似乎已成为包括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在内的内容生产实践无法逃避的关键议题。
由此可知,应变已成为刚需,而在此基础上所生发的应变意识和应变能力,是媒體工作者实现突围的关键。回望不同媒介生态格局下笔者所参与的媒介实践,从广播播音实践到电视主持实践,后来又经历了新媒体的挑战和媒体融合的进程……一系列职业体验让笔者意识到,积极的心理构建和可行的职业设计,是一个可持续性的课题。在不断调适、持续思考、重新认识的过程中,主体的韧性得到了综合提升,进而获得了应对变化的能力基础和心态基础。由此可知,与职业生涯设计动态调适有关的话题不仅与学生群体相关,更应成为所有媒体从业者持续性关注、常想常新的元话题。
更为关键的是,变化更能发现传播主体的潜能。这里所阐述的“发现”,既包括他者层面的被动式发现,也涵盖主体层面的主动式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智时代的媒介生态格局拓展了主持人群体的职业可能性,这就为主持人群体重新发现和发掘自身潜力提供了契机。笔者职业生涯的主持人实践大都聚焦于新闻节目主持实践,在人文地理节目《直播中国》的主持实践中获得了诸多新鲜的职业体验。究其根本,这种新鲜的职业体验实质上是创作主体的主体能力被拓展的过程。直到遇到全媒体环境,笔者才实现了通过文化传播实践进一步拓展主体能力的媒介生态格局。概括而言,笔者在全媒体视阈下的文化传播实践大致包括节气文化传播和文博文化传播两个内容创作维度。具体而言,笔者的节气文化传播实践大致呈现为如下传播链条:微博—书籍—音频(央视新闻·夜读)—小屏视频(《节气·长城》)—电视大屏(《地理中国·一丹说节气》)。上述传播链条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印刷媒介、音频媒介、电视媒介,也包括全新形态的社交媒介,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在传播实践中表现为深度互嵌的融合样态。而笔者聚焦于小微博物馆的、以“一镜到底”为基本形式的文博文化传播实践《博物馆9分钟》仍在持续中。
全媒体传播环境呼唤具有多元复合型主体能力且能驾驭不同类型、不同形态传播实践的内容创作者。具体来说,全媒体时代媒体人应既能熟练运用口语在镜头前表达,也能够运用文字在印刷媒介或其他社交媒介平台传播。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镜头”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大屏,也涵盖短视频社交平台上更具日常属性和互动特质的手机小屏。从业务的视角来看,全媒体主持实践也从“传播”“对象感”“话语表达方式”等更为微观的层面拓展了笔者对于主持人职业意识的认知。
表面上看,传统意义上主持人群体的实践场域面临着不断被挤占的困境。换种视角来看,全媒体环境其实延展出常态化主持人实践范畴之外的更多元形态的更广阔的创作场域,以深度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全媒体创作场域为拓展主持人群体的主体能力、丰富主持人实践的创作样态营造了创作空间。必须要明确的是,对于全媒体时代的主持人而言,创作空间需要通过创作主体积极主动地探索来拓展和开掘。什么是主持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核心能力?笔者认为,主持人的核心能力大致包括如下基本维度:运用资讯的能力、理解受众的能力、生发话题的能力、镜头前的呈现能力。全媒体时代不缺乏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而需要有个性的、有扎实的知识功底、具备全媒体媒介素养的主持人来驾驭更具互动感和人格化特质的主持传播实践;全媒体时代更不缺乏传播渠道,需要的是能适应不同传播渠道的、契合社会心理的扎实而有共情力的优质内容。对于主持人群体而言,如何更从容有效地呈现内容和传播内容,这是核心竞争力;创造靠谱的内容,记录时代的千变万化,这是具有长足价值的主持人实践该有的职业本色。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
(本文为作者在第七届中国主持传播论坛上的演讲,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王宇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