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王
贺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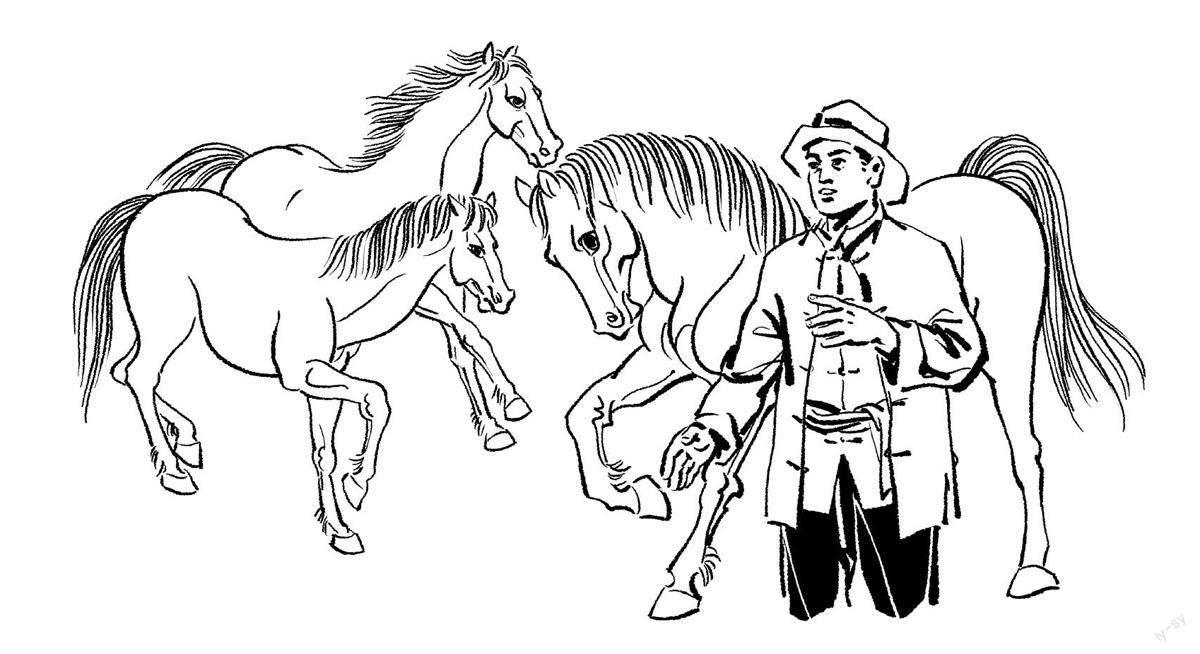
我爷爷人称“南梁王”,但不是土匪,也非恶霸,而是一名牲口牙行,官话叫掮客。一个买卖牲口的人,怎能称王呢?三层缘由:一是我家姓王,二是他的眼忒“毒”,三是做事有行止。全南梁一带,说起王金玉,十人九个竖大拇指。
我爷的眼力有多“毒”?这么说吧,一头牛、一匹骡马,几岁牙口,调教了没有,脾性如何,有无病殃,搁一般牙行,没半个一个时辰,审度不清。我爷爷,掀起牛鼻马唇,只一眼,就知几岁了、健壮否、那牙是真的还是洗的;攫住牛角马尾巴,拧巴几下,顺脊梁一捋,就能判断出勤快不勤快、驯服不驯服。
当然,这本事也不只他一人独有,偌大个南梁,方圆二百里,仨星俩北斗还是有的。问题在于,好的牙行,除了眼力,还得心里有杆公平秤。人家双方托付了你,卖的期盼能得其所应得,买的希望能获其所期待。有的牙行,为多赚点儿中介费,或因别的目的,这边捅咕一番,那边鼓捣一气,一晌也说不拢一宗。我爷爷从不为准星外的事费心思,而是完全站在双方的利益上,物有所值地给大家衡量,两只手朝这只袖筒里一擩,往那个袄襟底一伸,三捏两掐,买卖就成了,双方都很满意。
故而,每到牲口集市,他总是被团团围得,过手的牲口,占不到整个集市的七成,六成以上没问题。至于成交后能得几钱碎银,他从不计较。爷爷虽有看牲口的禀赋,但他并不把这当作主业,他更主要的营生是自己贩牲口,从青海内蒙古河北山东,把骡马牛羊赶回来,再卖出去。
帮别人说合,好说;把自己的卖出去,更需德行人品。做买卖,谁不希望多赚几个?但我爷做买卖一样坦诚公平,尤其守信。据说,在南梁,只有他能从外省赊账赶回成群的牲口来。不过他卖牲口,也赊账。你是真正的庄稼人,靠老天、汗水挣命过日子,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先赶回去用,秋天收庄稼了再还上。灾年歉收了,还不起,下年给也成。再不行,把牛马给我赶回来,权当替我喂了一年。
当然也有拖成呆账死账的,也有有了钱不想还的。世道不宁,人心不古。但我爷从来不赖账,他说赖账就不是人了,连赊出去的牲口都不如,且,再也从口外关外赊不回骡马牛羊来了。可是别人赖了他的账,周转不过来,怎么办?他就把自己的田土卖了,准时把钱汇给赊账给他的人。
日本鬼子打进来,世道更加不安宁了,赖账的人愈发多起来,我爷的地就越卖越少。可屋漏偏逢连阴雨,1941年,日军竟劫走了他的五十匹骡马。他跟他们要钱,鬼子说:“八嘎,你的私通八路!”我爷说:“这是明抢啊!”二鬼子说:“狗脑袋叫驴踢了,想叫皇军赏你一刀?”我爷爷吼:“强盗!五十匹大牲口呀,我拿什么付人家?”有人劝他:“是鬼子抢了你,又不是你赖账。”我爷说:“鬼子抢的是我,凭甚不给人家?”回到家,一咬牙,我爷把剩下的一百亩地一口气全卖了。不够,又把祖上传下来的一座四合楼院也卖了一半。
我爷凑了些钱继续贩牲口,试图把损失补回来。可仗还在打,他非但没把亏空补起来,反而把家产卖得只剩下一孔窑。
那年底,四叔的奶妈来要奶子钱。我爷一掏兜,半个铜板也没有,心一惊:吃了人家的奶,不能不付钱呀,那奶是一把米一把糠通过血肉凝化成的!他一时无招,便硬挣挣地说:“干脆,把孩儿抵给你们了。若不想要,插个草标,到集市上卖了!”
我四叔就姓了刘。
1949年后,我爷还做过合作社社长、村委主任,當了几十年的村干部。
当村干部后,我爷不再贩牲口,而是一门心思搞生产,领导大家干得红红火火,那个时期我们村也是全县的红旗村。古稀之年,我爷才来省城跟我们同住。一年,我安排他参加了一个赴南方的老年旅游团,回来他给孙辈重孙辈每人买了件饰品——男的观音玉坠,女的翡翠玉镯,外加一只金戒指。我爷说:“希望你们像玉一样做人。”不想我老婆经营珠宝店的闺蜜看了说:“除戒指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几个孙子就取笑他,说:“爷爷你一辈子看牲口一看一个准,咋看人总是走眼呢?”爷爷说:“我把他们当人看,谁晓得他们——唉!”然后正襟危坐对担任国企厂长和下海经商的我的俩堂弟说:“你们搞生产,做买卖,一不能欠工人薪水和生意伙伴的钱,二不能造假冒伪劣品坑骗人。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我王家子孙!”他们跟他开玩笑:“爷,难不成你把我们也抵了债?”他嘿嘿笑了,又瞪起眼说了句颇富禅机的话:“阳债阳还,阴债阴还!”
2010年重阳节,金风和煦,我们簇拥着老人家,照了张五世同堂全家福,姓了刘的四叔一家也参加了。当晚,爷爷在卧室永远地睡去了,他活了整整一百岁。装殓时,在他枕头底下发现张麻纸,上书几行毛笔字,曰《罪己书》,云:
“立德吾儿,汝父无能,卖儿抵债,失德失亲,为人不齿。父亲此去,阴朝受罚,来世变牲,还报吾儿。”
四叔跪在灵前哀哀痛哭,怎么劝也不起来。
[责任编辑 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