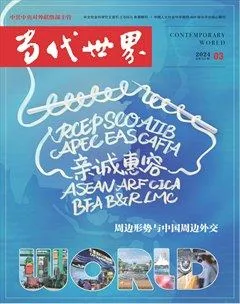世界动荡变革期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韧性与张力
刘洪钟
【关键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开放的地区主义 东盟中心性 经济再平衡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战后贸易和经济体制面临各种复杂挑战。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停滞不前,新冠疫情“综合后遗症”阴云不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以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导致多种形式的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和全球供应链中斷。这些因素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微妙影响,一些中小国家在大国之间左右摇摆,希望通过平衡或对冲策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亚太各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依然强烈,因为过去几十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使得各国确信,只有继续加强区域合作才是确保本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正确选择。面对持续动荡的国际环境和不断积聚的外部压力,亚太各国政府需要展现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决心,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干扰作出正确决定,推动区域合作不断走向深入,确保良性发展格局持续下去。
历史视角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危”与“机”
通常来说,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努力形成的市场和分工层面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即所谓的“区域化”;二是由国家主导、以制度建设为前提的自上而下的合作范式安排和机制构建,常被称作“地区主义”或“新地区主义”。[1]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来看,半个世纪以来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纵观历史进程,这种进步是在不断地变“危”为“机”中实现的。
亚太作为一个经济区是逐步形成的。二战结束后,在美国资金、技术支持下,日本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实现高速增长,于20世纪60年代末重返发达国家行列。此后,日本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中间品出口等经济手段,在亚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和分工布局。该地区其他后发国家则依据自身比较优势陆续参与到这一进程之中,从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20世纪80—90年代的亚洲“四小虎”和中国,再到2008年之后的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后发国家,亚太各国(地区)充分利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带来的机遇,你追我赶,形成了梯次的区域雁行发展形态。这种雁行发展形态在不断为后发经济体打开“增长和繁荣之窗”的同时,也把亚太打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网络最为密集和复杂的地区。总体看,这种依靠市场和分工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非制度区域化的过程。
不过,亚太地区的雁行增长并非一帆风顺地线性向前,而是历经两次大考验,并通过启动区域主义制度合作才最终摆脱困境,走上新的区域共同增长之路。第一次挑战来自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在东亚地区多米诺式的蔓延和对一些国家经济灾难性的冲击,使东亚各国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彼此之间紧密相连的共同命运,以及仅依靠市场自发的区域化合作不能确保各国摆脱危机。而美国选择袖手旁观,以及本应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施以援手但附加严苛条件,非但未能有效遏制危机蔓延反而使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进一步使东亚国家意识到,寄希望于西方国家援助摆脱困境是靠不住的,走出危机只能依靠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相互合作。[2]
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12月,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届非正式会晤,拉开了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的序幕。1999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三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就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原则、方向达成一致,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正式迈入制度推进阶段。此后,东亚领导人会议由非正式改为正式,并形成了从决策到执行的一整套机制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该地区迅猛发展的区域主义合作,[3]对于东亚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快速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经历的第二次重大考验来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返亚太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经由贸易渠道对东亚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危机带给东亚各国的启示是,重商主义发展政策下形成的“东亚生产—美欧消费”全球分工格局,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危机之后东亚经济的再平衡调整就成了学术界和政商部门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4]不过,随着域外市场的快速复苏,东亚各国依靠重商主义摆脱危机的强大惯性思维“战胜”了经济再平衡的长期需求。虽然后来东亚经济再次走上了复苏之路,但经济的再平衡却停滞不前。甚至相反,作为一个整体,东亚的货物贸易顺差从2009年的4803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7752亿美元,增长了61.4%,特别是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在2018年达到4505亿美元,相比2009年增长幅度高达124%。[5]
美国通过主导TPP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更多是基于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考虑。但在经济层面,美国非但无意与东亚经济“脱钩”,甚至想要通过签订自贸协议强化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不过,由于TPP在本质上对东盟的整体性具有分化作用,同时还会弱化东盟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中心性地位,因此也引起了东盟的担忧。这种情况下,东盟在已建立的6个“10+1”自贸协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16个亚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从2013年到2020年,经过30轮谈判和历次领导人会议与部长级会议,RCEP最终达成并于2022年生效(2019年印度退出协议谈判,RCEP目前拥有15个成员国)。特朗普在上台的第一天就废除了TPP协议,从而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得以继续沿着“以东盟为中心增进区域身份认同、强化区域合作共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逻辑推进。

2015年7月31日,美国夏威夷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部长级会议闭幕,日本TPP担当相甘利明(左二)和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左三)等出席联合记者会。
总体来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克服第二次重大挑战的路上有得有失。从“得”的方面看,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助推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区域分工合作,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则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亚太各国的区域身份认同和区域合作意识。换句话说,亚太各国虽然并不简单地排斥美国主导的TPP框架,但也不想让亚太自身的区域合作被域外国家主导的TPP所取代。从“失”的方面看,亚太各国虽然通过危机看到了传统“东亚生产—美欧消费”国际分工所具有的巨大风险,但重商主义思维和政策选择最终没能让亚太摆脱对域外市场需求的严重依赖,区域经济的再平衡依然任重道远。
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突变,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以及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实施,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遭遇第三次重大挑战。与奥巴马时期以强化与亚太地区经济关系、平衡中国影响力为主要特点的重返亚太战略不同,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以重构全球价值链、破坏亚太地区基于市场竞争而自发形成的区域分工网络为战略出发点,地缘政治逻辑已经超越经济发展逻辑,成为美国处理与亚太地区关系的行动指针。这一新的变化无疑加大了亚太国家应对和战胜挑战的难度。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应对当前挑战的“四个支撑”
地缘政治变动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透过历史可以发现,未来并不必然悲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逐渐形成了四个鲜明特点:雁行的区域经济增长和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东盟中心性以及以发展促安全的区域合作观。这四个特点赋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足够的韧性和张力克服当前困难,继续推动亚太经济走向有序的结构调整和稳定增长之路。
一是雁行发展模式使亚太经济在充满活力的同时,也推动了亚太国家复杂价值链的形成。亚太地区之所以能够形成雁行的经济增长格局,一个重要前提是该地区各国在产业结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梯度差,这使产业在各国之间进行转移成为可能。而亚太后发国家先后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则使产业转移得以顺利推进。20世纪90年代,雁行发展模式曾被视为“亚洲奇迹”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渐超越日本成为亚太供应链新的枢纽,区域内中间品贸易的迅猛增加推动地区合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特征,但国家间的梯次产业分布依然存在,越南等东南亚后发国家的崛起就是雁行模式在亚太地区的最新实践。这种发展模式为所有采取开放政策融入区域合作的后发国家提供了充裕的增长空间。

2023年4月13日,海南海口,参观者在第三届消博会韩国馆了解展出的锅具。除中國外,有10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的企业参展此届消博会。
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亚太各国经济逐渐紧密融合在一起,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分工和发展模式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多次自然灾害的考验,显示出强大韧性。从近几年的变化看,虽然国际局势在动荡背景下面临着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但亚太的区域价值链依然保持了足够的韧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研究,自2018年以来,世界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出现了收缩,从2017年的74.2%降至2020年的71.8%。与此相应,亚太地区与世界的全球价值链联系也出现了下降,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68.4%降至66.2%。与此趋势相反,这一时期亚太内部的区域价值链参与率从50.0%上升至52.2%,表明亚太区域供应链联系在不断加强。[6]
二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赋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更大的包容性和发展张力。亚太区域合作是在自由国际秩序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为应对复杂地缘政治和国家差异所带来的挑战,亚太各国一直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推动区域合作。开放的地区主义首先意味着包容和非歧视。从最初集中于东亚地区的“10+1”“10+3”,到2010年之后过渡到亚太地区的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太区域合作不断吸纳新成员加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开放式发展格局。2023年7月,CPTPP甚至批准英国正式加入该协议。此外,亚太地区以东盟为中心,还将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太平洋东岸国家等外部力量纳入亚太地区的合作进程,形成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各种对话机制和制度安排。开放的地区主义坚持区域制度安排补充而非取代全球多边规则的合作原则,比如清迈倡议货币互换多边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挂钩,打消了人们对清迈倡议储备货币制度会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担忧。开放的地区主义本质上意味着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主义。虽然RCEP和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具有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功能,但亚太国家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共同承诺使该地区成为反对保护主义、抵御反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堡垒。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这种开放性,无疑使其具有更大的张力化解各种外部冲击所带来的风险。
三是东盟中心性(东盟方式)确保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更大的调整弹性和发展韧性。以“中小国集团”东盟为中心和平台推进区域合作是亚太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些学者批评东盟只是形式的提供者,而非实质的推动者。[7]这种批评显然是戴着“有色眼镜”机械地以欧盟制度化合作为“最佳实践”而产生的错误认知,它忽视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联盟在塑造新型地区经济秩序过程中所发挥的集体作用。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虽然不是区域主义的完美或唯一模式,但这种“务实的渐进主义”恰恰是适合亚太地区复杂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唯一可行的制度选择。以东盟中心性为基础所创设的“东盟+3”(APT)、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平台,为域内外主要国家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区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沟通渠道。东盟的这种中心性地位被形象地描述为领导者、驱动者、设计师、制度枢纽、先锋、核心或支点。[8]《东盟宪章》体现了东盟中心性,强调维护东盟在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和积极作用,是其主要宗旨和原则之一。因此,当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以“印太自由开放战略”重组亚太秩序后不久,2019年东盟国家就发布了再次确认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东盟印太展望》,事实上这也是对美国的回应。

2023年5月10日,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第42届东盟峰会开幕。本届东盟峰会的主题为“东盟要旨:增长的中心”。
东盟方式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确保东盟中心性被各国所接受的重要前提。东盟方式以协商和共识理念为基础,体现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决策的集体原则。[9]因此,它既是国家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也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决策过程。[10]这种决策方式成就了东盟今天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广泛差异性的亚太国家能够走到一起,开启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东盟方式首先应用于东盟内部的一体化进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多个“10+1”自贸协定,并最终在2020年完成了涵盖15个亚太国家的RCEP自贸协定谈判。RCEP在谈判中表现出独特的东盟方式,尤其是在强调区域合作机制硬约束的同时,也照顾到谈判各方的利益,包括赋予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最不发达国家以特殊和差别待遇,允许其享有最长18年的关税取消过渡期。[11]此外,在印度最后一刻选择退出时,RCEP也承诺,印度如果未来选择加入依然享受创始国的特殊待遇。

2023年11月15—17日,美国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图为街道悬挂宣传海报。
四是以发展促安全的区域合作观是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念支撑。虽然亚太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但在持续动荡的国际环境下,亚太各国之间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互信不足、安全和治理问题突出等挑战。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指出“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倡议通过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12]此后,习近平主席还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重申这一观点。可以说,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也是对过去20多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历经坎坷仍持续向前之动因的精准阐述。通过区域合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但能够增加各国内部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減少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有助于增强集体安全保障,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虽然近几年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部分亚太国家的外交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摇摆,但各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并未减弱。这表明,“经贸合作作为压舱石、以发展促安全”作为一种基本信念依然在处理亚太国家间关系和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与前景
依靠上述“四大支撑”,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它们也赋予亚太各国克服各种挑战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韧性与张力。不过,受美国遏制中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影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近年来国际市场动荡导致全球贸易投资下降,RCEP成员国的经济和贸易遭遇空前的下行压力,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出现一定波动。[13]因此,实现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持续深化,还需要亚太各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将“四大支撑”基础夯实加固。
一是推动RCEP升级扩员,建设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区域自贸协定。作为全球现有最大经济规模的自由贸易区,RCEP生效实施两年多来,对贸易投资的促进效应初步显现。为更好遏制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RCEP成员国可以考虑加快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步伐,提高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尽快启动原产地规则、投资、政府采购等章节领域的后续谈判,进一步提高协定规则标准,推动RCEP升级版建设,从而为促进商品、资本和服务流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区域融合,营造更加自由便利的区域发展环境。同时,积极探讨RCEP的扩员问题,通过吸纳更多新成员以扩大协定覆盖范围,进而增大协定的市场规模效应,进一步提高亚太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外,由于RCEP 与CPTPP拥有一些共同成员,可以通过积极开展对话合作,推动RCEP与CPTPP的相互衔接和制度融合,进而为提升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水平、激发更大区域贸易投资活力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023年4月18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喷气式客机ARJ21完成雅加达至巴厘岛的首航,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图为首航的旅客合影。
二是高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各国发展战略、区域和国际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协同增效。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10年多来,以互联互通为主线,经过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合作,打造了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缅油气管道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为亚太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总的来看,基础设施落后依然是制约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亚太国家需要继续深化合作共同开发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为进一步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需要更好地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之间的有效对接。为此,中国可以有序推动与合作基础较好、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围绕各自的发展战略和合作规划加强对接,找准深化务实合作的结合点、对接点,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并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14]此外,战略对接还要注意高标准和高水平,也就是需要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2023年12月14日,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和香港国际航空学院联合举办的“亚太地区创新科技及能力提升展览会2023”在亚洲国际博览馆开幕。
三是推进基于发展安全和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合作,努力催生区域合作新增长点。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环境政策议程中最受关注的两大议题,其对人类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共识。[15]对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亚太地区来说,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不但是推动各国经济增长与创新的重要引擎,而且有助于该地区通过数字商品、服务和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自由流动,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数字能力和经济差距的步伐。为更好利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所蕴藏的巨大机遇,亚太各国应努力推动区域内数字贸易与绿色产品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区域内跨境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环保等产业的国际合作提供更多便利。为此,在维护数据安全基础上,各国应努力合作加强区域内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各国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标准互认,创新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等,以促进各方共享数字与绿色经济发展红利,进而赋予区域经济合作新动能。
四是推动亚太经济发展模式从以生产和出口为主的区域分工网络向区域内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东亚经济圈”转变。在国际市场持续动荡低迷、美欧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劇、全球供应链区域化调整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美欧对亚太地区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增速必然会呈下滑态势。因此,降低对美欧国家等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形成以域内消费需求为主、域内外均衡发展的东亚分工新模式,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均衡发展的“东亚经济圈”形成的关键是要扩大区域内最终消费品市场规模,从当前各国的经济规模和消费能力看,中国无疑将扮演关键的引领角色。这就需要中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与出口拉动为主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变。这种需求不但要体现为对国内产品的消费,还要体现为进口特别是从亚太邻国进口的增加,从而对保证东亚供应链稳定发展起支撑作用。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1] 黄大慧、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评析》,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135-149页;迈尔斯·卡勒:《从比较的角度看亚太的地区主义》,载王正毅、卡勒、高本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92页。
[2] 彼得·卡赞斯坦:《地区主义与亚洲》,载王正毅、卡勒、高本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3] 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三波区域主义浪潮中,全球范围内的自贸协定从2000年的82个增长到2023年底的363个,激增了3倍以上,而其中50%左右都是由亚太国家缔结的,从2000年的39个增加到2023年底的198个。数据来自WTO(https://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和ADBI(https://aric.adb.org/fta)。
[4]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Eswar S. Prasad, “Rebalancing Growth in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15169, 2009, pp.1-58;维韦克·阿罗拉、罗伯托·卡达雷利著,姜睿等译:《重新平衡亚洲发展:从中国经济的视角》,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X页。
[5] 刘洪钟:《超越区域生产网络:论东亚区域分工体系的第三次重构》,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第137-158页。
[6] ADB,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23: Trade, Investment, and Climate Chang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2023, https://aric.adb.org/aeir2023.
[7] Benny Teh, “What ASEAN Centrality?” The Asian Post, January 1, 2022, https://theaseanpost.com/article/what-asean-centrality.
[8] Acharya Amitav, “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9, No.2, 2017, pp: 273-279.
[9] 戴轶等:《“东盟方式”的理论阐释、演进动态与研究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23年第5期,第1-10页。
[10] Amitav Ar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10, No.3, 1997, pp.319-346.
[11] Shujiro Urata, “Constructing and Multilateraliz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n Asian Perspective,”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49, 2013.
[12]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5月21日,http://russiaembassy.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dozys_673577/dqzzoys_673581/yzxhxz_673597/zyjh_673607/201405/t20140521_7627664.shtml。
[13] 根据东盟统计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2023年1—9月,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六国及澳大利亚对世界贸易额同比分别下降5.7%、5.0%、11.5%、9.5%和9.9%。同一时期,东盟从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进口同比也分别下降8.2%、14.2%、20.3%和10.2%,对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出口同比分别下降7.0%、2.5%和6.0%,只有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0.3%。東盟统计数据库网站,https://data.aseanstats.org/trade-quarterly。
[14]《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中国政府网,2023年11月24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6832.htm。
[15] 202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旨在实现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双重转型的报告《迈向绿色、数字化和弹性经济:我们的欧洲增长模式》,强调通过数字和绿色技术的更广泛传播和采用,推动欧洲加快向可持续、有弹性和包容性经济模式转变的步伐。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a Green, Digital and Resilient Economy: Our European Growth Model,” February3,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2DC0083&qid=1655798743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