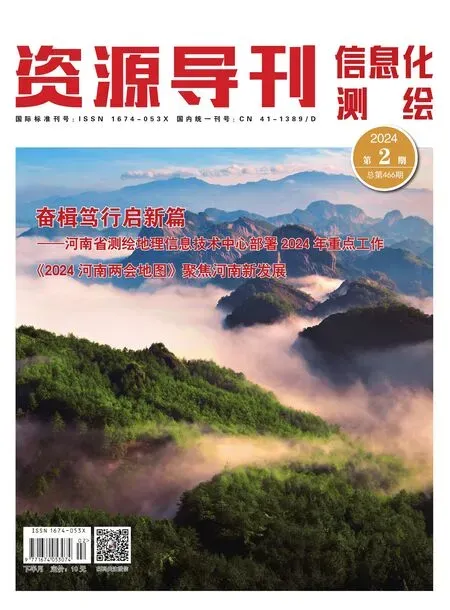过年
◎ 任广路

朔方的雪总是来得那么唐突且猛烈,睡梦里不觉得一夜寒风,醒来时窗外已是白雪皑皑。漫天飞舞的雪似飞天而坠的洁白棉絮琼花碎玉般砸将下来,顷刻间城市的楼宇和街道都披在一片银色的光里,满树的冰凌瀑布般沿枝头倾泻而下,似天宫仙境的玉玲珑。
伴着孩子们一天天零星的鞭炮声,龙年到了。一想到过年,心头不禁一阵窃喜和向往,但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成年人的漠然,这是年龄渐渐增加的人们的通病,于是不免哑然一笑。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时代洪流滚滚向前,远离案牍劳形回归田园,纵然一介闲夫,也总要一岁一岁地过年,岂能怨怪这光阴之如梭、岁月之如水!
于是,覆被高枕,闭目怀想,刹那间,那些早年间过年的景象伴着油炸的香味,和着鞭炮的炸响,如电影版一幕幕扑面而来……
除夕
除夕,传说是古时的一种怪兽,每到岁末便会出来伤害人畜。为了驱赶怪兽,人们于新年前一天在门窗上贴上红色对联,点燃鞭炮、烟花,确保新的一年吉祥安宁。记得小时候,我会拿着用刀割好的一摞红纸到街上找会写书法的爷爷,排队等着写寓意美好的对联,回来和弟妹们吆吆喝喝、欢欢喜喜地把春联贴到门窗上。大门上的对联是有讲究的,那时村里生产队的欠款户都会早早贴上对联,这样别人就不会来讨要欠款了,而存款户则在天快黑了才贴对联,以彰显自家的富有自信。我那时小,不懂这些,只知道为了养活四个孩子,终年黑天白日干活还挣不够工分四处借钱的父母会一遍遍催促我早早地贴对联,还说这就叫“大年三十贴花门”。
傍晚,几个孩子拿着油炸的咸食围在灶火旁,等着吃用猪肥肉炼的油渣和萝卜拌馅包的饺子,红红的炉火照着一个个馋涎欲滴的小脸。终于,开饭的二踢脚两响炮飞向天空,顿时鞭炮齐鸣,礼花满天。我们端着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的饺子,脸上露出了幸福的欢笑。
晚饭后,父亲点燃了用大树疙瘩堆砌的篝火,一家人围坐一起,听父母讲家里的陈年老事。老祖宗是从山西大槐树挑担来洛阳的,一筐一子,前筐的孩子放在我们村,形成了今天的任氏家族,祖爷是十里八乡唯一的晚清秀才。而母亲白家是至今还年年到龙门白园集体上坟的白居易正宗后裔,因此,母亲常嘱托我们要好好学习,传承世代耕读的家风。
炭火暖红,我看到了辛劳的父母一年难得的笑脸……
凌晨零点到了,我们飞快跑进屋内,把母亲做的过年新衣套在棉衣棉裤上,然后盖在两层被子中间暖着,在半梦半醒中期待大年初一的到来。
后来知道,这就是除夕熬年。
大年初一
一夜的鞭炮加上过年的兴奋,让人难以入眠。随着大年初一早上的鸡鸣和燃放的鞭炮声,孩子们争相穿好期盼已久的新衣,飞奔出门 ;院内,父母正将一块煮熟的猪肉放在小桌上,拜老天、祭祖宗,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一家平安!
大街上,人们穿着新衣在雪地里放炮追逐,有大人带着孩子在街旁堆起了雪人,有南极仙翁、财神爷,还有孙悟空和猪八戒,最后把眼睛、鼻子做成时,总能引起一片惊呼和啧啧称赞。小孩子们在街边滑冰、推桶箍,比赛看谁跑得快;还有的拿着从树上摘下的冰凌放在嘴里“咯嘣”吃得正欢……寒风里,红红的小脸、小手早已被过年的激动温暖得忘乎所以、不亦乐乎。
饺子熟了,我们会端着一碗碗饺子去向邻居和本家长辈拜年,老人们高高兴兴地吃着饺子,还会赏我们一些鞭炮、点心,发几毛压岁钱,共同祈求新年快乐、儿孙快快长大成才!
一会儿,大人们表演的腰鼓队、排鼓队沿街游行而来,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小孩子们一路紧跟,欢歌笑语,追到戏楼下,新年的这场大戏会一直唱到子夜……
这,就是最热闹的大年初一。
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是媳妇回娘家、女婿拜看岳父母的日子,也是过年走亲串门的第一天。父母早早地把我们喊醒,穿戴整齐后一人提一个装满油条点心、用一条花毛巾盖着的红色提篮,当然还有一块带着三根肋条的猪肉,据说这叫礼肉,是初二必拿的重礼。
我们坐在毛驴拉的架子车上,随着父亲一声响鞭,车子便汇入串亲的车流人群。路面冰冻如铁,北风呼啸,雪花飘飞,可人们却没有一丝寒意,相互打招呼,开玩笑,过年的喜悦溢于言表,恰似一支迎亲的大篷车队。秋月良明享天伦,冬雪茫茫会亲朋,人间的亲情挚爱、天伦之乐在北方的雪国里仿佛融化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到了外婆家,过年中午是两顿饭,一人先吃一碗刚出锅的热腾腾的饺子,休息聊天后再吃一顿猪肉粉条烩菜,据说这是几十年传下来的风俗,大家边说边吃,越说越亲。这也是回忆中浓浓的年味儿。
接下来几天,天天都是走亲访友,一路欢歌,一路笑语,成为几十年来长在心中的幸福回忆……
“ 嘭!啪!”一声炸雷般的鞭炮把我从长长的回忆中惊了回来,窗外高楼林立,路上汽车如流,室内温暖如春,改革开放让我们国富民强,祖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今,人们的生活天天都像过年,再也没了过去那种对过年的向往。过年开车串亲,一日数家,少了停留,少了交往,少了亲情。
又要过年了,愿我们能远离城市喧嚣,除去一身浮躁,回到故乡,回到年老的父母身边,在一盆红红的炭火旁,一家人围在一起,听老人唠叨那一遍遍的家长里短……
那一刻,你会重新体会浓浓的亲情和遗失的年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