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成:句稳江天阔
陈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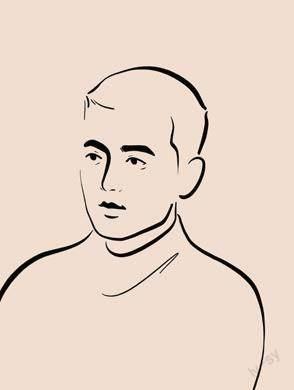
杜甫在阆州住了不到半年,作诗六十余首,佳作频出。其中有一首《放船》,很值得留意:
送客苍溪县,山寒雨不开。
直愁骑马滑,故拟泛舟回。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后人多着眼于“青惜峰峦过”一联,其实起首四句,也不可轻易放过。这几句太平实了,而且低效,题为放船,却花了半首诗写为何来此,为何舍陆路而走水路。如在记事簿上随手记下行程。世人多知杜甫的锤铸之功,其实这种随手记事的态度,与锤铸之功相济,才是杜甫为人所不及处。他那些煌煌名篇,字句足以铭刻碑碣,老杜自己是否意识到了?我想他是知道的。这种不朽的引诱中,其实包藏着一种危险。钱钟书形容快乐:“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写出诗作,希望它不朽;写出不朽之作,就希望一直写。如李东阳评李贺语,“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鉥”,怀了这念头,写作就容易“端”起来,反倒离不朽远了。意识到后世的镜头正对着自己,身姿不免僵硬,表情不免做作,于是失去了信步闲游的自在。
而老杜不动声色地掠过了这危险。他一面在石碑上凿出深深笔画,一面在记事簿上涂抹。他有些小诗,简直像写在家庭账本的背面,或日历的一角。杜甫有一种收纳癖,远方战阵的鼓角、檐间燕子的呢喃、山果的红和枯骨的白、宴会上的绮席金碗、老妻的愁幼女的病、星河的动摇岩壁的崩裂、养鸡酿酒的盈亏,他不加拣择,统统折叠成对称的形状,稳稳收纳进他平仄妥帖的句子里。他形容自己新句的最好状态,不曰“工”,而曰“稳”。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世人对杜甫的常见误解之一,以为这一句是他的夫子自道。其实后一句便是转折:“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漫與”即随兴而为,自谓年轻时刻意求工(所谓“心从弱岁疲”),而今渐老,作诗多随兴,情绪也希求平淡(虽常常求而不得),懒得再对花鸟愁思了。这话不必全当真,像一个强迫症患者,说自己近来豁达了许多,其实仍有常人不及的执拗。单拎出“耽佳句”或“浑漫与”,都有些偏颇,两句合起来才得见老杜全貌。杜甫一向有极好的分寸感,他在工与拙、用力与率意、潜心锤炼与信手点画之间,总能抓住最恰当的比例。纵观他年轻时的诗作,警策之句常有,如群马中腾一二神骏者,而缰绳始终牢牢控住,何曾为了局部的灿然而失却整体的森然?而晚年的自谓“漫与”,正合《文心雕龙·养气》所说的“从容率情”“意得则舒怀以命笔”,是一种饱满的状态,才会偶尔流露出率意。其实杜甫那些精心杰构的组诗和巨制,多迸发于所谓“老去”“漫与”时期。清代的潘德舆说得最公允:“杜公早年晚年,皆有极意研练之诗,亦皆有兴到疾挥之诗。”
这一首《放船》中,难得的是既有他的“兴到疾挥”,又有“极意研练”,而且相契无间,如江心有奇石耸峙,而江流自在。前面若句句精工,惊心骇目,如爱伦·坡所说,诗的刺激不可持久,到后面便衰竭了。阅读是持续的推进,而佳句暗示着停留。
且说“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这一联实可以同时佐证汉语的松散和紧密。我将它拿给平时读诗不多的朋友看,他们的感受相似,初看时都微微一愣,稍想一下便懂。这种微微一愣,小小的磕绊,是汉语的弹性所默许的。两句如一张印象派的小画。船行水上,青濛濛的一片,迎面而来,是山峰;看之不足,便掠舷而去,故而惜。那些细碎黄点,缀在山脚林间的,遥知是橘柚。两句都省略了一个“见”字,若按语法补全,应该是:见青而惜峰峦过,见黄而知橘柚来。这两个本不存在的“而”,正是此联精妙所在。因为烟雨微濛、水涨船疾,加之老花眼(杜甫另一首船行诗说:“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在望见青色、黄色和辨出是峰峦、橘柚之间,在感和知之间,有一刹那的缝隙,而杜甫似时间的庖丁,游刃于其间,得到刹那的剖面。这样的句法才写得出顺流而逝的恍惚。阿城的《树王》里有一段:“只见他慢慢将锄捏在手里,脊背收成窄窄的一条,一下将锄死命地丢出去。那锄在空中翻滚了几下,远远落在草里,草里就蹿出黄黄的一条,平平地飘走。大家一齐‘呀地喊起来,原来是一只小鹿。”普通的小说家,说“草里蹿出黄黄的一只小鹿”便足够,阿城就写出了感和知的空隙,与“黄知橘柚来”同理。
赵汸注“青惜”句时说:“青字黄字略读,乃上一字、下四字格。”按语意,这一联应这样划分:“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赵汸认为读时也要这样停顿,我却觉得,仍该按一般“上二下三”的读法,即读作:“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语意和音节的轻微错位,造成一种微妙的效果,也是汉语的弹性所容许的。且通篇是上二下三,仅颔联读作上一下四,读起来便和前后句不协了。后世频见这样的变格,七言句通常是二二三的停顿:“孤帆|远影|碧空尽”,二二三了数百年,人心就思变,于是便有:“况复|此宵|兼雪月,白衣裳|凭|赤阑干”“薰得|凌波仙子|醉,锦裳|零落|怯新凉”,这两例,都是一句常式加一句变格,若前后句各按语意的停顿来读,就乱了套,因此仍都读作二二三。从语意和音节的错位中,汲取一点佳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