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的特写:万玛才旦电影中的“阿巴斯”寻踪
王杰泓 蒋红玲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人安静地生活,哪怕是静静地听着风声,亦能感受到诗意的生活。”[1]这是海德格尔对人类、对生活的认知和感触,恰如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作品。 2005年,已经在文学界深耕14 年的作家万玛才旦,转型导演后伴随着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的面世,引发广泛关注。 随后,《老狗》(2011)、《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9)、《气球》(2020)等众多电影佳作不断面世,形成“藏地新浪潮”的同时,也在世界电影界独树一帜。 他将人文关怀投射到藏区人民的生活上,用朴实的镜头书写着一份诗意的现实影像,为观众铺展开了一幅幅藏区生动的俗世画卷。 万玛以风景反观人性自我,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与另一位东方导演、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很相似。 两者不仅在叙事等技术层面相似,更在影像精神层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 当“万玛·阿巴斯”成为一种经验,或者说构成影像精神的内核,这种精神的互通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就不单单是一种表象实然,更是一种“诗意”的必然,其为东西方理论的互动与对话提供了可能。 在此视野下,我们不妨聚焦于万玛电影的阿巴斯踪迹,分别从电影语言、虚构与纪实的二维统一、被创造的“心象”风景、审美品格的东方性等四个方面,来具体探讨他们电影中的风景之“特写”。
一、电影语言的相似
万玛才旦曾说:“我是藏人,迄今最大的梦想,就是拍出纯粹的藏族电影,关注最普通的那一些群体,然后完成艺术的再现。”[2]他曾经表示:“目前的少数民族电影流于表面化,太肤浅,缺少真正的民族视觉……对核心的东西理解不很透彻,只看到枝干和叶子,没有看到根。”[3]如何表现“藏族文化的根”是导演万玛才旦努力的方向。 他以藏人的身份讲述藏族的真实生活和文化,以独特的创作视角、思维、形式、题材和类型的多元化革新,以此展现日常生活中当代“藏民”“藏地”和“藏文化”。 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中指出:“我们生活、活动、实现自身之存在的媒介,是我们最终注定返回的媒介”。 他将风景定义为“文化表述的媒介”,突出强调了风景的文化属性[4]。 而万玛正是凭借单纯质朴的影像和影片中所闪耀的西方难得一见的真诚和藏区风景,得到世界性的关注。 在伊朗的阿巴斯,同样也是通过电影将本民族的风景呈现于世人眼前。 除了叙述主体和民族性主体的回归,两位导演更是通过“去奇观化”的影像,建立在乡土之上的、区域性的身份认同,从而建构起专属于当代电影文化自觉的主体性。
(一)画面构图:形式和内容之间
万玛才旦的电影,不仅是对西藏自然风景的纪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景物与其说是故事的背景,不如说是承担着电影叙事的前景。 《静静的嘛呢石》中有一个经典的镜头段落(见图1):小和尚在Z字形的山路上来回奔跑,山、路、树构成画面的一部分,在长达数分钟的长镜头中,小孩朝着山坡小路的顶上跑去,藏区独有的自然风光则在大全景的镜头里一览无遗。

图1 《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和尚在奔跑
如此经典的画面构图,在持“远景即特写”[5]创作理念的阿巴斯那里也曾出现过(见图2)。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中,也多次出现小山坡场景,主人公阿穆德在画面的Z 字形的路上跑向山上的一棵树。这条路见证着小男孩坚持不懈和朴素无染的善良,也造就了阿巴斯电影画面的诗意美。
在这两个相似的画面中,首先,风景是呈现的主题,人物则作为“点景”而被展示,从而在影像空间中保存了时间的属性。 德勒兹提出“液态影像”来形容这种影像的流溢。 定格镜头的静默造成了影片时间的绵延,观者以往凝神专注的观看方式逐渐被消解,使得风景超越叙事吸引了观者的注意。 在这个大远景画面中,人们会短暂地忘记整个故事事件,而是将目光聚焦在画面中这两个小孩身上,关注人与画面的关系,使这个构图或镜头凸显了人所处的精神环境。其次,这种构图设计,也许就是电影的最终价值指向:通过对形式美的建构塑造人与世界的关系,体现了电影中某种精神表征的概念,在超越情感的层面上影响观者,使人的视线和心跳随着银幕上人物移动而放慢。 因此,观者与电影的联系更加直接,这样的联系也就更具精神性。 当戏剧化叙事淡出时,伴随观者观看的当下,时间又绵延在电影携带的过去与未来中。
通过两个风景特写的代表性场景,不难发现万玛才旦与阿巴斯在风景呈现上的相似性,即注重对风景的描写。 不仅将风景前景化,更是电影的“一种扩散与分层”,在形式和内容之间维持了一种有机的关系,即不需要过多的表达能力,通过画面就能抵达。
(二)长镜头的运用
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说:“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面貌,吸引我的注意,从而激起我的眷恋。”[6]受巴赞影响,万玛才旦的电影一直在追求纪实性,使用冷静的长镜头是万玛作品还原藏地面貌和讲述藏地故事的一个重要方式。 《气球》的开头就是一个长达3 分钟的镜头,是孩子通过自己的视角介绍周围的环境和一切,呈现出真实的藏地环境。 除了真实再现藏地生活外,万玛电影的长镜头也能表现语言难以描述的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 影片《塔洛》的开头使用了一个11 分钟的长镜头,拍摄了塔洛在派出所用汉语熟练地向多杰所长背诵《为人民服务》,这个固定机位长镜头不仅铺垫了影片的底色,也是一个分量很重的情感前奏。
运用自如的长镜头一直是阿巴斯的个人风格,除了纪实性、伊朗真实生活的叙事节奏和贯穿全片的全景镜头,阿巴斯的长镜头里则多了许多富有趣味的点。
《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结尾有一段经典的长镜头,青翠茂盛的橄榄树林伸向远方,摄影机在远处静静地观望着,侯赛因以及塔赫莉逐渐变成画面中两个白色的小点。 侯赛因的追逐开始,随着镜头中的白色小点靠近,一起往前走,然后又突然折返。 观众的注意力一直被画面吸引,目睹了他们穿越风景的全过程。 《生生长流》(1991)结尾处也有一个长达四分多钟的长镜头,最后一镜中,出画又入画的车不断地朝着山坡行驶,经过一次又一次滑落向后又再次向上前进,汽车终于爬上了山坡。 从之前的拒绝搭载,到被帮忙推车,最后主动停车搭载,这一长镜头,巧妙地展现了地震后人们的不屈精神与勇往直前的生命力量。画面中翠绿的树林或者蜿蜒的坡道,既是片中充满寓意的风景,同时又是情节展开的场景。
(三)声音与画面构成的第三维
阿巴斯在《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中写道:“声音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暗示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给予图像第三维。”[7]在阿巴斯的影片中,“通过分割他的声轨以同时再现来建立视觉领域之外的众多空间”的场景到处可见。 如影片《随风而逝》(1999),开头画面是车子在盘山公路逡巡,但声音却是车内人物对谈的画外音。 《生生长流》中,声音是车厢内的关于地震情况的交谈,通过这样的叙事形式提供给观众主要信息,而画面则是震后灾区满目疮痍的残垣废墟以及平静整理家园的人们。 阿巴斯在听觉上呈现了一个远超任何时候观众视觉所及的广阔空间,即使摄影机与银幕上的人或物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这样,画框的限制被打破了,声音与画面构成了第三维。
深受阿巴斯影响的万玛才旦,同样在多部电影的镜头组里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修辞策略。 《寻找智美更登》(2007)中,镜头中的车缓缓行驶在路上,声场丰富的自然声音,轮胎在碎石路上发出轰鸣,蟋蟀和鸟儿在鸣叫。 尽管车辆离摄像机的位置很远,男人在车内清晰可辨的话语仍在耳边响着。 银幕上已经是远处的风景,但他们的声音依旧清晰。 他们在图像和声音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最终服务于影片所要表达的主旨。 银幕上的空间随着更广阔的空间而变化,那些在山路上蜿蜒前行汽车的镜头,偶尔切到影片主角的特写画面,这些特写在主题本身之外没有什么深度。 影片充斥着大段对白,甚至可以说全片主要部分就是剧中导演一路上不停地在絮絮叨叨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配合简单却有深意的拍摄手法,使声音填充了画面之外的信息,给予画面更多深度。
另外,这样的概念还体现在银幕外的声音的“人”,即在电影中未得到视觉上的确认的人,却仿佛是电影的“潜文本”,因为这些人都存在于画框的物理限制之外,却对从精神维度理解电影至关重要。 在阿巴斯《随风而逝》中,那位德黑兰工程师为接通外来电话,飞速驱车前往信号较好的山坡上,电影不断重复这一行动。 他不停地通过电话和一个身处远方的人交谈。 观众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个通话者,但同样地,不得不默认这个人和其所处空间的真实性。 同样的场景在万玛才旦的《寻找智美更登》中也是一样的呈现,剧中的“导演”反复地接到远方的电话,人们从他的通话中得出了对方的身份,在没有物质存在却通过他的不断交流中刻画了那个人的存在,并看到“导演”与对方情感上的转变。
二、虚构与纪实的二维统一
万玛才旦说:“很多时候,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它们的界限在哪里。 我分不清。”[8]虚构与纪实的二维统一,首先是真实的虚构与虚构的真实。 电影自诞生以来,主要强调以叙事为核心,然而,在万玛才旦的影片中会发现,其内核意志是影像有关真实的构造,并且都是归于生活。 他将镜头选择性地对准了真实的藏区,电影文本中出现的是去奇观化的原风景。 通过这些元素,导演以一种突破传统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真实的西藏高原的生存环境。 这样去奇观化的手法,颠覆了人们对西藏一贯的思维和审美观念,让人能够了解到这片土地的真实处境。 万玛才旦电影的故事、空间以及演员都来源于这片藏区,记录事实的真实感比“复制的现实”的真实性更震撼人心。 他的电影淡化戏剧冲突的背后并非因果关系的叙事链条,而是诗性思维的演绎,这意味着它“比传统戏剧的逻辑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这种具体技法和影像精神与阿巴斯殊途同归。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戈达弗雷·切西尔认为阿巴斯电影既有纪录片不加修饰的真实属性或“记录性”,又有富于诗意和艺术美感的“电影性”,电影在“真实性”与“故事性”之间,体现了一组二元性逐渐模糊并走向统一的融合旨趣[9]。 的确,阿巴斯以纪录的方式解构生活,揭开真相的面纱,也揭示真实生活深层的本质。他说:“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任何一位电影导演,会比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更具影响力。”[10]《家庭作业》(1989)的开头,阿巴斯将孩子们各式各样的细微面部表情清晰展现,自然而带有关怀气息。 《特写》(1990)中,看似纪实手法实则含有虚构的法庭现场段落和家中破案段落。 阿巴斯以挑战真实和虚构的方式在伊朗文化中奇迹般地绽放,并在世界艺术电影中大放异彩。 他寻找简单的现实,更纪录摄像机碰到现实后所发生的一切,并以此现实为基础拍摄电影。
其次,是麦格芬技巧的运用。 万玛电影的故事中,仿佛存在一个观众认为不重要也不关心的麦格芬,却在寻找的道路上虚构了生活的真实,通过摄影机媒介灵巧地唤起了一个存在于银幕之外的世界。《寻找智美更登》中,故事直接发生在乡村,剧中的导演一行人想要找一位智美更登的扮演者。 但是直到影片结束,那些寻找更像是找到每个人自己内心的答案,至于一开始的“麦格芬”似乎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各自的人生之路上的故事。 在影片《撞死一只羊》中,主角巴金开着大卡车,化身为沙漠里复仇的勇士,内心的逻辑、环境和人的关系是影片的核心,主角巴金在复仇的道路上不断地偏离、游走。
在阿巴斯的电影《生生长流》中,地震之后,剧中“导演”与男孩驾车重返灾区,试图寻找前一部作品中的两位小演员。 为了找到一条没有被地震破坏的通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停车、问路:“去柯盖尔怎么走?”问路、寻路、问路的循环一直持续到电影结束。另外,像阿巴斯电影《旅客》(1974)中的卡西姆、《特写》中的侯赛因、《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阿默德,都是在达成目的的道路上不断偏离、游走。
另外,一个富有鲜明特色的方式是电影中的“戏中戏”。 万玛在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出现的观看和排练藏戏“智美更登”,在第二部作品《寻找智美更登》中便是剧中的“导演”去寻找智美更登的扮演者。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阿巴斯的《生生长流》中也是去寻找前一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小男孩。作品之间层层嵌套的互文,揭示的却是一个有很多层面的现实,或者说,一个纪实与虚构绝非泾渭分明的世界。 《橄榄树下的情人》拍摄了戏中戏,出现导演、演员、场记打板、剧组休息、选角等活生生的摄制现场场景。 这两位导演都以很巧妙的“戏中戏”的范式消解了以往的电影阐释,即以“戏中戏”为媒介,将观众放置于虚实交替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极致化的风景呈现已然是两位导演影像精神的互通,也推动他们走向世界。
三、被创造的“心象”风景
在拙文《作为一种人造风景的“心象”影像论》中曾有过阐述:全部的艺术作品不过是作者自我内心生活的外化与“迹化”,以上细节意象恰是上述核心价值的聚焦与熔铸,它“拟容取心”而直抵本真,饱蕴着一种“摩罗诗力”和终极追问的意味,我们无妨将它们直接称之为“内心视象”或“心象”[11]。 中国美学史上,从道家的“拙朴”到理学家邵雍的“以物观物”,再到章学诚提出的“人心营构之象”[13],“意象”概念的涵义一直在不断发展。 在电影理论之中,“物”与“象”是创作者有意识的观念建构,万玛才旦的电影是一种以“朴拙”为美学根基,对人世“自然之象”的再次“观物取象”[12]。 同样,阿巴斯的电影以人为本,濡以情志,使平实无奇的“心象”成为包揽宇宙的丰富意象。 他认为“影像是万物之源”[13],常常在完成一幅“内心影像”之后,再开始建构和完善剧本。 接下来便从“以物观物”地来分析二者电影中的风景意象。
(一)动物与装饰:被拴住的母羊与自由的鸡
万玛的作品《气球》中,在女主角卓嘎前往厕所使用验孕棒的路上,导演巧妙地切换了画面,镜头中是一只被拴住的母羊(见图3)。 这个镜头与前后剧情都没有任何的联系,其实这只羊隐喻的正是此时的卓嘎,羊无法挣脱身上的铁链,正如主人公无法挣脱生活的枷锁。 这一镜头的出现为整个场景增添了一丝神秘和隐喻,呼应着卓嘎内心的纠结和不确定。 导演通过这种离心的、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的“心象”细节,特写般刻画了人物的生活困境和灰色命运,也让观众不免去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

图3 《气球》中被拴住的母羊
阿巴斯的《生生长流》中,男主人公到了被地震摧毁后的地方后,有一个老妇人在地震中房子被摧毁了,这时候镜头里的男主人公与老妇人展开了一段对话。 只有声音传递出老妇人在废墟里需要帮助,镜头跟随从这只鸡在画面的左下角移到了鸡位于画面的正中心,镜头并未跟随男主人进门,而是固定在门外这只鸡身上(见图4)。 此时,视觉上的确认正是废墟前这只昂头打鸣的“鸡”,从动物意象上不仅看到平淡和真实生活中的生命力和希望,更是让门内的人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

图4 《生生长流》中门前的鸡
(二)画作与细节:“和睦四兄弟”与地震中的画
传统的画面概念指摄影机使照片活动起来,从封闭、静止的单元转化为电影画面,流动中的微小片段。在万玛的《气球》当中,当已经出家的姑姑去学校找外甥的时候,画面突然呈现一个单一的镜头:学校板报上的一幅画。 根据剧情的推进观众便知道,这幅画所呈现的是藏地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和睦四兄弟》,这其实就是整部电影的背景和寓言,同时,这个镜头与整部电影形成互文。
在阿巴斯的《生生长流》中,主人公走到地震中被摧毁的房子,镜头同样停留在一幅画上,转而镜头透过残垣断壁的一道门,看到了远处绿色的生机。 尽管地震过后满目疮痍,但这个镜头让我们看到远处的美好,包含着对生命与希望的隐喻象征。 这种电影画面,即纯粹空间意义上的“取景”,以及时空意义上的电影“镜头”,都是单数与复数发生根本会合的辩证之所。
(三)植物与“心灵景观”:草原与树
从环境与人物的内在关系出发,万玛才旦通过草原这样的自然景物,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情绪和主题旨归。 《草原》(2004)中多次出现大远景下面一望无际的草原,这里的草原是充分支撑起人物内核的心灵景观。 在影片《塔洛》中,导演直接用黑白的色彩呈现了一个几近荒漠化的草原空间,不仅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也是塔洛生存境遇的有力注脚。 《老狗》中的草原则是被铁丝网所区隔的,充分表现了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在万玛才旦之前,“树”早就是阿巴斯电影中最为常见的风景。 《橄榄树下的情人》是青年爱情的美好象征,结尾运用几分钟的大远景拍摄橄榄树下男女渐行渐远的身影,依旧具有开放解读的空间。另外,很多时候,“树”还承载着画面和镜头运动的视点。 《随风而逝》中,车子多次开往高处的山坡寻找信号,镜头随着车行驶到三棵树这里,再到车子穿过这三棵树抵达山坡上。 “树”这个符号不仅给了观众一种位置的交代,更是在景观和心灵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关系最终服务于影片探讨的主旨。 《樱桃的滋味》(1997)中的树是生命和希望,是“我带着死亡的念头出门,却满载着樱桃果回家”的治愈。 在这一次次的忧心与怅然之间,生命早已如风一般自由,随处吹拂。
四、东方美学视角下的精神空间
万玛才旦与阿巴斯这两位东方文明之子,其作品多从地理空间出发,运用独具风格的视听语言,展示出东方美学中的精神表达。 在他们的影像中,不仅有视听语言和风景空间上“显现真实”的大美之境,更是在精神空间的多个维度上都贯彻了一种生命精神。其中既有闲笔之真,饱含诗意哲思,更是着力探讨生命与死亡这一哲学命题。
(一)延宕叙事:“无情节的影像”
爱森斯坦在《并非冷漠的大自然》中说,“在纯粹气氛(感觉的)和单纯纪实(事实的)之间,存在诗意的位置:即便在电影影像中,那也是历史叙述可以像抒情歌曲一样顿挫吟唱之处。”[14]西方学者将其称为“无情节的影像”。 而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称之为“闲笔”,即脱离叙事主线的手段。 现代电影理论也有称之为“延宕叙事”的,即设置脱离主线的延宕情节,并通过分散叙事时间来调节叙事节奏[15]。 相较而言,西方的延宕叙事是为了“消解线性”的时间锁链,实现信息断点的效果,从而制造悬念并激起观众的观影欲望;中国的延宕叙事则是生活化、自然化的产物,是创作者随意卷舒的结果,它不以制造悬念为目的,因而颇有一种悠哉游哉的感觉[16]。
万玛才旦电影看似闲笔很多,细细品来却有独特的韵味浸润其中,是藏族电影独有的注脚。 电影中,空无一人的沙漠、路边熄灭的纸火、荒山野岭上秃鹫成群、昏黄的光影,都是对那一时刻的人物情绪场景设置进行深入的意向性刻画。 就如电影《撞死一只羊》,镜头总是先对准茫茫的沙漠,车子从画框边缘入画,出画后镜头独立出来依旧定格于沙漠,如此营造出人物进出沙漠的游行之感。 当车子在画面中愈来愈小直至成为失焦的后景时,摄影机依旧使用后撤式镜头远远地观望,观者开始游离于叙事而进入心理想象的无限空间。 淡化戏剧冲突的背后不是表层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人物内心的诗意逻辑。
在阿巴斯的影片中,延宕叙事时常可见,它与闲笔相似,非关情节,却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性、趣味性与审美性。 《特写》开头,街上司机在等待时,停车,下车摘花,踢走易拉罐,这一事件无关故事,也打破了前进的时间线索,却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气息。 《随风而逝》里,导演游离主线之外,添加了从二楼房间顺着出水口掉落的一颗苹果。 《樱桃的滋味》中,路边的工地上,挖掘机正倾泻着泥沙,将人的影子碾压、慢慢淹没。 这样的设置尽管游离情节之外,却指向了导演的创作意图——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这些对叙事“无用”的物件被征用为一种观察式蒙太奇的形式,看似突兀,实则是导演刻意解构观众与电影作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让观众的理解和自我创造介入到影片之中,与影片互为文本,进而观众赋予影片不同意义。
(二)诗意哲思:“心物一体”的理想性主客关系
余开亮在《中国古典美学的生命精神》中说道:“中国美学对心物一体的审美意象世界的开辟,给个人生命铺设了一条领略‘存在境域’的诗性之路。”[17]万玛才旦的电影不是一种诗性的情绪电影,而是诗意的风景电影,这种诗意恰是“本真的生命与真实的世界是在一种意向性关联中存在的。”《撞死一只羊》中,影片一开始的画面便是西藏广阔的天地与荒凉空旷的高原雪山,人与车在画面之中行走,显得十分渺小和脆弱,全景则是苍茫茫一片的雪山、公路和远方。“车”在路上饶有兴味,无数的画面组成的一组组镜头都带有诗歌般的苍凉而壮阔、孤寂却绵延的意味。《寻找智美更登》,车也是在路上饶有兴味地不断前行。 在汽车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装载着几个人不同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车厢中的风景、人面亦是藏区的风景。 智美更登的风景,原野榛莽的风景,车厢中的困顿风景,这三者仿佛并不相及,却又那么玄妙而诗意地全部呈现出来。 道路在荒山间断续绵延,这种不断向前行驶的蒙太奇段落也是人物内心的困顿、挣扎和突破。 《撞死一只羊》中两个分身的主人公“金巴”直面自我与人生的叩问,其在精神面向上与《寻找智美更登》中的“导演”(寻找信仰之源)和女孩(追寻初恋爱情)完全相同,也和阿巴斯众多影片中用车窗“框取”的风景所包涵的意蕴高度一致,仿佛都是在用“摄影机自来水笔”回答“诗人何为”这一永恒命题。
阿巴斯《随风而逝》中的经典场景:男主人公坐着医生的摩托去为村里即将病逝的老妇人取药,途中,摩托车穿行在一片片金色的麦田间,两人就在这风景中展开了一段颇具哲思的关于生死的对话。 此时的麦田与人物不分主客、彼此融合,达到了心物一体。当衰老和死亡的对话随之飘荡在随风起伏的麦浪之中,老太太的生命也在风吹麦浪的同时随风而逝。 这种表达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最富智慧的一种诗性表达,需要观众通过“以物观物”才能来句读出其中神韵。
万玛才旦和阿巴斯都对“道路”情有独钟,二者的意象已经非常接近。 西藏荒凉的沙漠、曲折的黄土地,让我们感受到藏区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上的艰难曲折的朝圣之路。 而阿巴斯镜头里则是乡间小路、曲折的公路。 沿着阿巴斯的道路,伊朗美妙的自然风光和现实的人生百态尽在眼前,且更呈现人们不断向前、不断追问的生命历程。 “道路”在他们的电影中被赋予了别样、深刻的意义。 无论是一条通往远处山坡的土路,一片金黄的麦田,抑或是一个想要自杀的男人,“寻找”经常出现在他们的电影里,是人生之路的追寻,兼具诗意及哲学意味的隐喻。
由此可见,他们二者的电影风景绝非单纯的自然景物呈现,更重要的是有人的情感意向、文化特征、思想内容等融入其中,即通过自然空间的意象,传递出诗意的哲思。 从这个意义上看,万玛才旦对风景意象的着力选择正是他表现藏族文化之根的隐喻寄托。他用个人化与风格化的影像语言,从自己真切的体验出发向内审视藏区文化,在一个个稳固、悠长的镜头语言系统中,西藏的自然风景隐喻着一种亘古不变的存在。 万玛通过寓言叙事,将生命的本真与传统信仰一同镌刻进风景里。 因此,风景不再仅仅是描写当下的空间,而是藏区人们的生存空间、文化空间,更是心物一体的理想性主客关系这种东方美学思想的体现。
(三)文化表征:生命与死亡的哲学命题
“仓央嘉措的情歌和西亚诗歌最大的共同点是世俗的激情融合了宗教的激情,这种神秘主义的快乐是在忍耐中导向意义。”而万玛才旦和阿巴斯在电影主题上都是探讨着生命与死亡这一哲学命题。 至于更进一步,电影如何去回答源于精神的“灵魂和来世”问题,他们都作了很好的回答,即通过风景。 在他们的影片之中,理想生命的存在形态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一种当下“演示”。
死亡的符号频频出现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之中,作为具有深厚宗教信仰背景的藏人,生与死被赋予了宗教内涵,它关系着转世轮回。 《静静的嘛呢石》中刻石头老人的突然去世,《撞死一只羊》中司机金巴在梦里杀死了老人并走到了天葬台,纷乱飞动的秃鹫在天地间像是生与死的交融。 在《气球》中,人们对老人去世后会投胎转世到家中的信仰成为故事的核心矛盾,大儿子因为身上有一颗和奶奶一样的痣,被大家认为奶奶转世,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认定为是刚去世的爷爷转世的所在。 对万玛才旦而言,藏区地境便是佛法的化身(见图5)。 为此,画面的景色已经形成转喻,它们并不是镜头下目之所及的全部内涵,而是被承担着更深远、宏大的人文主义思考,换个角度说,它从非物质概念的立场出发,直接赋予了直觉中的物理更多的文化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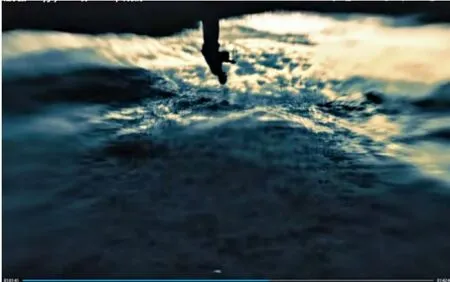
图5 《气球》中的超现实主义风景
阿巴斯也在自己的影片中提出相似的哲学命题。《随风而逝》中多次出现的墓地、老太太去世的迫近。《樱桃的滋味》全片围绕着主人公想去自杀。 这本质上是一种非情节的情绪氛围,意境中的符号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在平凡的日常中看到丰富的意义,诗意之上又多出一份宗教和信仰神秘的心物转换逻辑。 这样的境界,万玛才旦偶尔窥探,阿巴斯已经非常接近。
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书中指出,情感如何可能像意识形态一样运作。 实际上,这正是万玛才旦电影的意义所在:通过风景来展示生与死、智慧与爱等普适哲学命题的同时,散发出朴素无染的慈悲。 在这个层面上,阿巴斯与万玛才旦是一致的,万玛才旦认为阿巴斯是参照。 同样地,他们都唤起了一个存在于银幕之“外”的世界。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结尾,“最后一分钟营救”过后作业本里夹带的那朵小花;《樱桃的滋味》中,从原本荒凉的村庄的路边到开满五彩缤纷的鲜花;《特写》结尾处的神来之笔,萨布吉安捧着花坐在摩托车后座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 在这种一如既往的“阿巴斯味道的平淡”中,往往最后又给予观众一击,让人沉溺于电影画面所产生的涟漪,其带来的余韵,质朴收敛,静水流深。 无论何时,无论身在何地,都能感受到影片中生命意识的诗意。 正是由于电影的诗意思维不可复制,极具差异性的个体,偶又延续了银幕外电影的生命。
四、结语
在万玛才旦电影中寻觅“阿巴斯”的踪迹,得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万玛·阿巴斯”经验。 他们的电影都在独特的空间和环境中产生,于是,物总是作为“溢出”。 这种“溢出”不仅是一种“去符号化”,更是具有一种“去中心”的趋向。 他们去掉了主流(西方)电影的技巧,采用朴素的镜头,生活流的拍摄手法,在视听语言上进行“零度化”处理,并试图由其自身而涌动出不确定的诸多可能。 他们的电影颠覆了自格里菲斯以来定义的“电影叙事”,弱化了因果关系、剧情结构,关注自我与世界、生命与死亡的寻找与冲突,从而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张力中,反思栖息于大地上的存在方式、诗意文化和审美维度,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对未来世界的理想表达与救赎精神,像诗歌般吸引人们去反思、探究,而这也将我们引向对“电影是什么”的持续性思考。
尽管电影是一种媒介和物质载体,但是万玛才旦和阿巴斯却通过形而上学的真实现实——风景的特写——探寻和回答了精神概念的问题。 万玛才旦与阿巴斯合一的这种“东方性”,不仅是在审美意义和精神层面上,更是两位大师级导演对于一种“新电影”的尝试。 如同他们影像中主人公的不断奔跑,和对“另一条道路”的往返游走与尝试,直至远行不返……影以载道,斯道在风中,随“无我之法”而飘。 远处高楼的剪影预示城市现代化的雄心,而我们却能在伊朗黄昏下的麦田泛着金色的记忆,浮日片刻中,在藏区的沙漠里醒来,回到处处智美更登的歌声、电视机播放唐僧喇嘛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