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感觉重建人的精神世界
陈沙沙
人类拥有一个复杂灵妙的内宇宙[1],其同外在的寰宇一样,引人勘探。自20世纪初“人的文学”被提出以降,文学如何表现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文学着力表现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对人的心灵宇宙的一次关怀。位于人面部正中的鼻子其实是一个精雕细琢的感受器,它能分辨的气味至少有一万种。嗅感如此发达的鼻腔仿佛就是一处微型内宇宙!从鼻腔掘出一条通往内宇宙的道路,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开辟了不同的进路,然而,气味的难以留存与须臾易逝,使得气味难以用理性、逻辑、概念演绎,它更偏好深掘人无意识潜流的文学创作。作家、诗人被认为是最擅于探测幽微世界特别是人的精神性世界的人,科学界对嗅觉引发人深层次回忆现象的研究就启灵自“普鲁斯特效应”①,充分展露气味深具叙事力量的一面。作家老藤近年来的创作也显现出关注嗅觉—空间—心灵同构性的叙事倾向,围绕文学地理中的地景重构和伴随而来的人的精神景观的呈现与处理问题,其将嗅觉地景视作内在的叙事策略,考察气味在勾连人的(空间)住所、文化记忆、欲望想象、自我身份方面的建构功能与精神指向,为东北文学引入新的表现领域:一方面,重构新时期以来当代东北小说在解剖人的精神风景方面的景观化、奇观化旨趣;另一方面,焕新东北文学在演绎记忆、权力、身份等主题上日益固旧的想象方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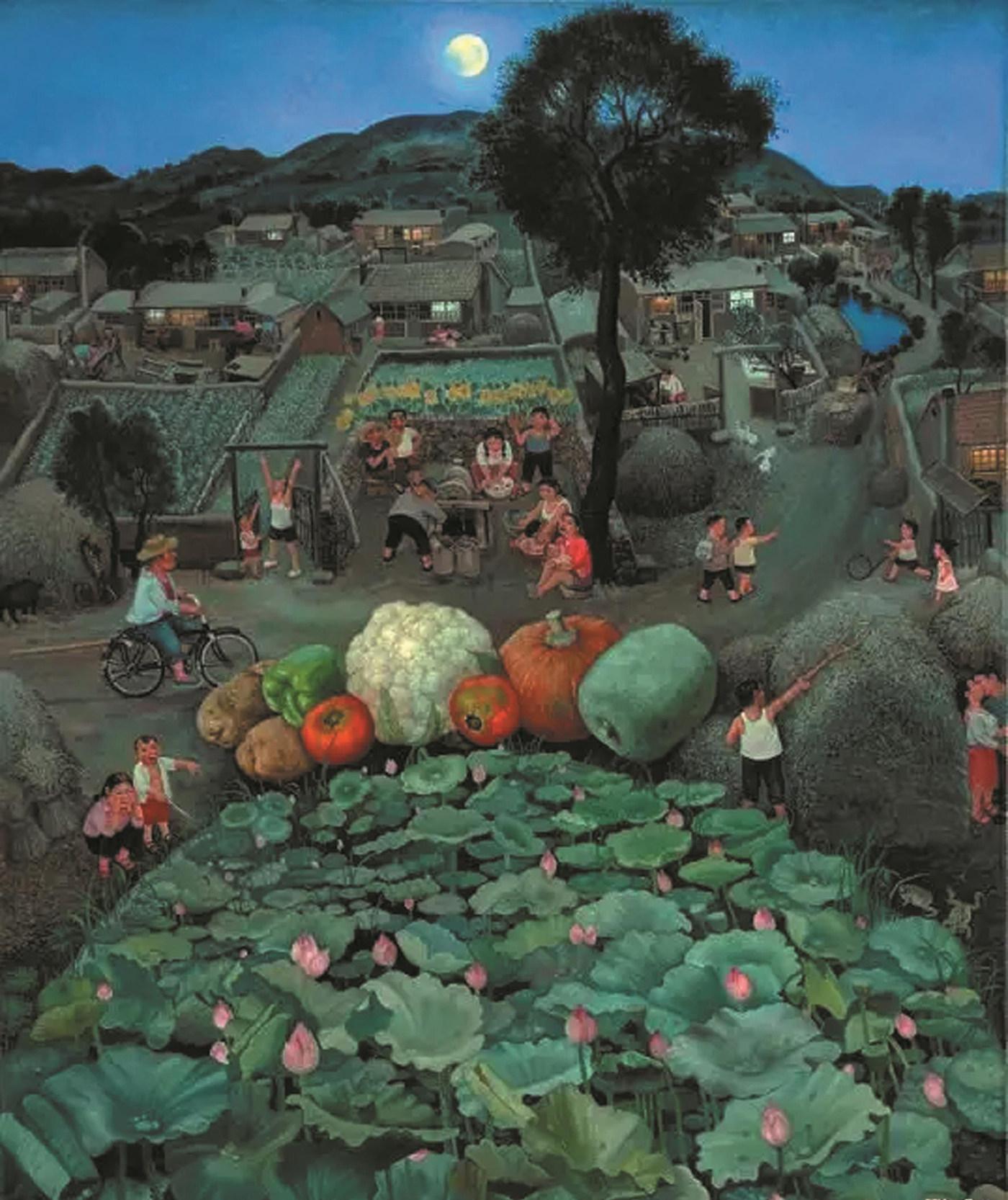
一
嗅觉,相对于其他四感尤其是视觉来说,因缺少限制,因与呼吸同在,更能直达个体生命[2],深具建构力量。但是,道格拉斯·波尔图认为气味也因深受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形塑,造成这种“非视觉”感官记录的困难,阻塞了个体智性在私我与共享空间中的流通阀门。他随之提出“嗅觉地景”②(smellscape)的概念,并指出基于文学超越时空的双重属性,在文学中探索气味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整循环的可能性,显示出嗅觉通联文学时空超越现实时空形成的嗅景在重温逝去的记忆,重构独特的地域空间乃至心理地理上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嗅景还包蕴着作家对于社会、个体世界的一种未来性想象,就比如说,“东北的白山黑水一再成为现代中国想象共同体的场景。”[3]
對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现、检视、定位是一种地理体验,亦是一种叙事过程。
“‘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累积,也是一种‘感觉结构——因器物、事件、风景、情怀、行动所体现的‘人同此心的想象、信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结晶。”[4]对东北(风景)的考古、发掘伴随着感知过程、认识装置的内化。《林海雪原》《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漫山遍野的皑皑白雪为原初、野性的山林世界赋色;《钢的琴》《铁西区》用西洋乐与中国乐的拼贴、复沓反衬工业基地的废墟图景;《呼兰河传》《平原上的摩西》中泥泞的石坑、破旧的烟盒与课本任摩挲的手掌抚摸、怀想。《刀兵过》《麻栎树》通过“干稻草散发出来的味道”嗅识关内、关外,人、事、物、景闪动的情愫……这条视、听、触、嗅的叙事脉络,“无不以地缘景观召唤东北最生动的感觉”[5],也无不以一个有色彩、有声音、有形状、有气味的“生命活体”[6]重启内在、性灵的感觉书写。在这具生命有机体中,唯有嗅觉带来的感受是永不会腐朽的。且看《刀兵过》开头铺设的一处嗅觉地标:
窝棚外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海腥味,这腥味仿佛来自许久没有洗澡的腋窝,显得有些暧昧……他登上土坎,极目南望,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呈现在眼前的是无边无际的红!这是一种从没见过的红,红得熟紫,红得自信,像连片的珊瑚,似晚霞覆地,如果不是有一群白色的鸟儿列队飞过,这情景真让人想到是连片的火海了——这不是乩文中的水泊之上燎原火吗?
绿苇红滩,地平河阔,一幅多么让人心动的图画!
拨开蒲苇,他疾步跑过去,在就要接近这红色的时候,两只脚被软泥深深地陷住了。他退回来,知道这里是海滩,要找对路径才可以进。无边的红色里,可见一条蜿蜒的小溪,正流向远处。……他忽然嗅到了那种熟悉的野燕麦干草的味道,甜而软,冲淡了先前的海腥味,他知道,这干草的味道应该来自身后的窝棚。[7]
不难想见,“气味可以活化插曲式记忆。就算无法说出气味的名称,或对此气味作更精确的描述,嗅觉仍可以充当起动机,让人记起遗忘的经验和过去的事情。”[8]老藤在创作谈中谈及为何以《刀兵过》替换《九里》时就从嗅觉的角度介入,他说:“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过刀兵的历史,翻开二十四史,间或总能嗅出血腥气。”[9]的确,九里村数十次过刀兵的历史,总有一股腥味盘桓于此。如:1895年寇贼侵扰,“风从红海滩刮来,带着一股浓重的咸腥”[10];1924年霍乱侵袭,“一片片生生不息的芦苇被连根掘起,王克笙嗅到了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泥腥味,这是一种被沉淀了千百年的味道,从苇地的伤口处散发出来,令人惶惑窒息。”[11]不同于宏阔的大场面描写,细处攒动的嗅觉表现成为特定历史风貌的镜像性显现。腥红味(私我空间)楔入绿苇红滩(共享空间),正是以集结可视、可触、可听、可嗅等多种感觉的地景突入主体性真实在场的意义域,重构一种起源性的叙述方式。血腥味是东北战争史的一个侧影,咸腥味、泥腥味是东北农耕史的独特标志,腥红味、干草味是东北文学史业已失落的感知主体……嗅景“所揭示的不仅是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更重要的是人的广阔的内心宇宙和人的生命意识的深层结构”[12]。正如王尧所说,在色彩表达上,相较于萧红、迟子建黑白色调的东北,老藤凸显的是“红”色调;在气味空间上,“腥味、碱滩、珊瑚”不仅组构了海洋性质的东北,它们还让人觉知到“被抽象为同质化存在的‘东北有着怎样具体而微的空间差异”[13]。也就是说,徘徊不散的腥红味不仅是白山黑水的物质遗产,它同时也是从嗅觉视角反视作为现代公共风景的“东北”的心理地理。伴随气味景观的积聚与人文地理的延伸,嗅觉部分恢复了我们对于现代东北“风景”的记忆,激活了我们看待现代中国“风景”的眼光,也影响了以九里人为代表的东北社群选择居住地的倾向。例如,九里建村的历史就堪称一部气味的文化史。灌注在九里世界中祁门安茶的粝香、蒲苇清香、芦花(蓬蕽)药香、道观檀香……不仅是老藤的文本世界中源源不断异彩纷呈的地域风物与地缘密码,它还发掘了作为“身体感意象”③的嗅觉书写的开源功能,树立起九里人“幸福、圆整、宁静、信赖的原初感受”[14]。
《刀兵过》这类嗅觉叙事文本,其意义在于“以熟悉且亲切的气味为坐标,由气味串联起看似不同范围内的人、事、物,复制、碎裂与重构已被遗忘的记忆”[15],从而搭建起气味与独特地理景观、理想生存环境的沟通桥梁。这就是段义孚指陈的,“如果没有一种历久不变的感官体验的帮助,比如说海藻的咸腥味,我们就不能完全重温长大之前对世界的感受了。”[16]尽管这样的气味表现还尚显粗糙,但以嗅感“唤醒”人的朦胧、感性的内在风景与主体意识,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感觉美学在崛起”。
二
面对生活实感的紧缚与自我需求的膨胀,柄谷行人将“风景的发现”升格为日本文学现代性起源的心理特权装置。正如风景的发现,“气味的发现同样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感知形态”[17]。当卷入“社会主义风景”变革进程的个体气味、嗅觉情感展演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权力认同时,“风景”也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想象物,“风景与其说是自然所提供的一种形式外表,不如说它更主要的是文明继承和社会价值的体现。”[18]“气味即心境”,在历史社会记忆的递变、文化权力的认同中,气味展览了多元的叙事风景。
(一)深描个体心灵的记忆嗅景
在老藤的小说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连接关系常被人与动物在山林、乡野等自然生态中的互动、救赎替换。这固然深受作家生态保护意识影响,但实际上,也关乎人的解放与心灵的救赎这类宏大的文学命题。《北地》这部历史小说,章节与章节的衔接处排列着无数“历史景观”,透露出历史变革巨大毁坏与再造力的当属“一处农场和两座墓碑”的变迁,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其实是由气味生产的记忆之所。这种叙事指向,创造了一种结构性的回想文本,把北地业已隐匿的过去与现在的地点重新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探源动植物身上特有的流彩馥郁的气息,逐渐演变为一场再造北地“场所力量”的叙事活动。人们意识到,在气味变迁背后,是一段个体创伤记忆的嬗变与复呈。格拉秋山农场是常克勋任职北地的第一站,在褚三禄的回忆中,俩人的交往甫一开场就充斥着五只狍子和狼群之间惨烈撕咬的血腥味,同时又混杂着类似于羊和鹿的膻味、貂的腥味、大雪冰封的冷气、扫帚梅的香气以及在寒衣节为“十八烈士”烧线衣的衣料、香火味……这一股股缠绕在老人数十年记忆中的气味终于在子辈常寒松、任多秋时隔40年后的田野采访下得以全面释放,而那股无法挥发的狍子味则出人意料地使得气味接受者褚三禄在回忆狍塚时“思维如此清晰,讲述极有条理”[19]。但是,脑海中记忆的画质越高清,越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在口述歷史事实时,一旦动用气味修辞还原历史现场,人的主观意志是否会无限飞扬?实际上,嗅觉因其特殊的生理构造被认为是唯一能进入大脑中心的感觉,故被称为“嗅脑”。相比于语言和文字,气味其实会立刻准确地把你需要了解的讯息告诉你,对这种感觉的充分调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为逝去的无法复现的记忆的一次“命名”,是对社会精神史与个人精神史的一次“绘制”,“在这个味觉的长河中间敞开了一个空洞,一个隐藏的褶皱,里面就隐藏着那种香气。”[20]
此外,“社会主义农场”这个带有自省与自审的场所还是“十七年”历史褶皱中的一个交界地带,常克勋履职生涯的谪迁地——“五七干校”原身就是一处农场,其在后辈重访时已经被改为养貂场,被贴上“味大、难以靠近”的标签。印刻着个人存在气息的农场气味,弥散在遥远的改建回忆中,个体的存在正遭遇被抹除的危机。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也调动了动物的嗅觉来回望高密东北乡的变迁史与变革史,“变”于时代来说如昙花一现,但于个体来说却如猛虎细嗅,充满未知的惊颤。经历轮回转世的“西门狗”进入人世时恰逢改革开放头十年,当它带着西门闹的肉身记忆走街观屯时,“当年,屯子里最浓郁的牛的气味、骡马的气味消失殆尽,而许多人家院里都散发出浓重的生锈钢铁的气味……。”[21]劳作汗味、动物鼻息、花香草气留下的气味印痕连同原始农耕生态,或被遗弃或被取代,机器轰隆作响,附着其上的钢铁锈味带领读者决绝地冲入西门闹投胎为“西门狗”、传统与现代交接的一瞬,再次经历初生时的创痛。而这种层级的痛感,在上述社会主义农场的故事因旅游业发展而被改写到乾隆年间,在交织着常克勋奋斗、失意情绪的农场被出租改建为养貂场时攀至顶峰,这无疑是个体的历史被商业消费的时刻。
(二)弥散于空气中的权欲嗅景
嗅觉是欲望的感官,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力量,有直达个体生命欲望与自由意志的直觉。但长期以来,嗅觉被置于感觉体系的最下层,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嗅觉和所有的种类的气味均被赋予负面意义”“如同性欲、欲望、冲动的感觉,嗅觉带有动物性的戳记”[22],气味接近原始、本能、快感的优势如今成为众矢之的,这与欲望、权力在我们的书写和叙述中所遭遇的处境如出一辙。《嗅觉的符码:记忆和欲望的语言》中指出,与影像相较,气味更为“武断、肯定”,人一生都在跟着嗅觉走。如今,艺术家们渐次发现了嗅觉的魅力,并重新审视嗅觉欲望所搭载的可靠的感性力量与直觉特性。老藤在《西施乳》《国家羊汤》中为食欲和权欲搭建文学桥梁时,就抓住了嗅觉的欲望属性并重塑了这一载体。
“食、色,性也”,食欲是人的第一生本能,在中国官场文化场域中,食味与各种权力之间更是存在一种微妙的摆荡关系,食味和权欲交互的叙事模式就发展为小说展现权力魔力的手段。由此,凭借嗅觉与权欲的特殊对应关系以及老藤在其小说中设置的特殊食香视角,书写嗅觉在社会权力追求与个体生命意志之间的表现才显得如此撩拨心弦。比方说,食思发达的古人就用“治大国如烹小鲜”譬喻国家治理,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也从“羊大为美”的体悟中初现轮廓。在这样的文化心理氛围的加持下,中国式官场世界也发展出一条“嗅/被嗅”的生存法则。老藤早期作品《西施乳》就将食欲和权欲交织缠绕的政治生态写得活色生香。《西施乳》题目本身就是一道精细加工的美食,主人公郑远桥官场生涯里几次重要变革都与这道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每遇挫时,郑远桥敏锐的鼻子总能最先闻到空气中神秘的味道,这味道提醒他三“嗅”而行,人的确是会用气味进行思考的动物。整部小说最令人咂舌的地方是:制作西施乳的厨师尹五羊虽身不在官场,但俨然一位“食官”,更因其占有着制作西施乳香所需火候、时间等关键变量的秘诀,能神龙不见首尾地牵引蓝城市长、书记等一众食客职业场与人生场复杂交织的气味红线,在用食香撩拨人的权欲上他俨然是生杀予夺的嗅觉国王。同样在以食设题的《国家羊汤》中,国家羊汤馆是照鉴榆州县政府机关官场世相的一面铜镜。在这个小小的羊汤馆里,有一群“不担要职”的干部食客,他们常年利用公权力随意签单、欠单。因为久债积压,店老板国老大决定讨要欠款,但也“讨”来了店铺拆迁的封条。羊汤馆关门之际,国老大留给唯一没有挂过单的挂职副县长“我”一段话,“国氏祖训说,羊脸,五官俱全之物,五官即五味,五味调和才能出国之大羹。”[23]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语境中,个体价值中心化、利己化,大有倾轧社群、集体价值信念之势。就像羊肉汤的烹制过程内嵌的鲜活真理所显示的那样,“欲”将人内在的本能与外在的选择通过气味的隐喻来解释,在羊汤充满隐喻的气味笼罩下,利与义、牧与治……凡此种种对权力的诘问成为盘桓在现代人价值判断与道德选择中浓稠难化的嗅觉情绪。
三
在文学创作的目的或旨归上,莫言和老藤就故乡与气味的关系发表了相似的看法,前者认为:“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24]后者亦宣称:“我对故乡的印象大都与味道有关。味道,是引领我回到故乡的最好路径。”[25]两位作家的创作在这里汇合并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气味认同在重构自我身份上具有重要作用。现代小说的叙事往往设计或内嵌着历史与道德、理性与感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如将现代性焦虑具象化表征为地域身份、阶层身份、文化身份焦虑,对人物内在精神的塑造往往趋向对抗、冲突的形式。老藤也摹写人物身份问题,但他采取的是一种较为平和、正向的叙事策略。小说的创作,是一种在对外部世界气息、残骸、碎片吸入、消化后呼出的人与世界的均衡、连续、稳定的满浸生命气味的循环活动。气味作为符号化的隐喻,在被吸入与被呼出之间“象征着人类精神中的价值和自我认同”[26]。
卡尔维诺在《美洲豹阳光下》一书的写作前言中坦言,他正在通过穿透“五感”来呼唤一种新的写作方法,嗅觉位列其中。“所有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们都首先用鼻子来获得,而不是用眼睛:猛犸象,刺猬,洋葱,干旱,雨水,它们首先是一些从其他气味中脱离出来的气味。食物,非食物,我们的山洞,敌人的山洞,危险,一切都是先由鼻子感觉到,一切都在鼻子里面,世界就是鼻子,我们是用鼻子来了解谁属于我们这一群人,谁不是。……”[27]个人如何通过气味的不同精细地辨别他人,也意味着他如何想象自我的气味。在《名字,鼻子》这一章专述嗅觉的故事中,卡尔维诺让花花公子、史前人类与吸毒的摇滚歌手皆因一位女士的体香展开了疯狂的“寻找”,带有气味的女士显然只是一个有香气的符号能指,三位男士在寻找过程中追求的是对人的境遇的把控。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则展现了闻香识人的极端化情境,格雷诺耶这位拥有极灵敏嗅觉的“无香狂徒”,自出生就被家庭和社会弃养,而弃养的理由竟是因为他没有香味,没有被颁发作为身份识别的嗅觉护照!错乱的身份感和犀利的识香能力,让他不顾一切地寄希望于在杀人取香的过程中“重嗅”自我文化身份。致命的是,由香水伪装而来的身份面具一戳即破,在最后一滴香水营造的迷狂盛宴过后,他也彻底失去获得身份合法性的可能。不同于体香、香水赋予的反向身份特征,老藤更倾向于屈原式“香草美人”的正向身份特质的营构。以对王克笙和王明鹤这两位主理九里的乡绅身份的刻画为例,作者分别赋予俩人“味”和“气”两种超拔跃升的品质:
王克笙站在酪奴堂庭院里,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对儿子鸣鹤说:“苇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弥漫着一股干土味儿。”……他知道父亲对味道异常敏感,这种干土的味道与干草的味道截然不同,给人以一种无边的焦虑和忧患。……王明鹤没有闻到父亲所说的干土味,他敏感的是气而不是味,在这个少雨的春季,他经常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天空的磁力,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要把自己随时拨到空中。[28]
对照来看,王克笙与王鸣鹤倾向于用味与气形塑可能世界中超越性的“我”,不同的是,王克笙寻味的动力乃出于对“超我”的探询与完型,临终前仍念念不忘那缕指引他来到九里的野燕麦干草味,嘴里念念有词:“我寻味去了。”[29]王鸣鹤并不追逐“味”,他最大的禀赋是在“气”的冲、撞、推、拨的回旋中为他人寻找自识的出口。这是一种于他者气味的识别中重塑己身的朴素辩证法。7岁时,他曾在苇地里迷路,正当父母和众乡亲焦急万分之时,他却自己从芦苇荡里走出来。事后,王鸣鹤解释道:“前后左右有三面在挤着自己,逼着自己往一个方向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芦苇荡。”[30]这一嗅觉地景是随着王鸣鹤身份意识的真正发生而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并不是“本我”的释放,其仍处在现实自我与理性超我的相持之中。当王鸣鹤接过父亲保护九里、建设九里的嘱托后,苇地聚集的协同、互助的气场正是他对自己乡绅身份主动确认的努力结果。这两位“有气味的人”亦让我们联想起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式典型人物,他们身上散发的气味可以窥见社会各行各业中具有神圣感召力与原初性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全貌。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终结”的话题“甚嚣尘上”,危言耸听的批评之外是文学感觉的确在裂变、坍缩,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创作还会迸发出新的感觉吗?老藤用文学作品实践了嗅觉所具有的记忆感、欲望感、身份感、生命感乃至神圣感,用排列在瞳孔、唇齿、耳膜、发丝、肌肤、鼻腔和其他器官之上的感觉重建文学的、人本的风景。老藤的嗅景書写不仅召唤出暗藏在白山黑水、绿苇红滩中解构秩序感的膻腥味,也有心理地理、饮食滋味带来的本能的、属己的日常体验。此外,眼睛看到的活火山、嘴巴尝到的绿皮柿子、双手摸到的碑文……都让其文学故乡暗香疏影。也许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假如我们的嗅觉失去了感知那些味道从而创造出丰富而珍贵的词汇的能力,那么将无法用词语来把这些香气表达出来,它们也会因此变得模糊而又无法辨认。”[31]既然五感的钝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那我们如何具体把握感受?如果不用文字去记录火山喷发时弥散的气味、马匹舒张的鼻息、山羊厚重的膻气,我们何以认识人所生活的宽广无垠的世界?可行的方案是,作者不妨大胆地调动起所有的感官,去创造一篇呼吸、温度、声音与气味俱存,并且感性绵延、思想闪耀的小说[32]。
注释:
①“普鲁斯特效应”是研究界对“嗅觉引发回忆”现象的命名。
②基姆·杜布尼克《嗅觉文化读本》中收录了由道格拉斯·波尔图撰写的论文《嗅觉地景》(《smellscape》),第一次提出“嗅觉地景”的概念。为行文方便,后文将“嗅觉地景”简称为“嗅景”。
③在传统的感官意识研究中,视觉图像被认为是人观察和感受世界的主导性装置,但在人的感觉系统中,嗅觉与人内心纵深的私密感的通联,乃至于与外在世界的整合关系常常被忽视。实际上,嗅觉意象对人内心模糊甚至神秘感受的开掘能带来身体感官的充分释放,并形成一种“身体感意象”。关于“身体感意象”的论述,学者史言在《批评的召唤:文学启示与主题思考》中指出,嗅觉意象有别于“感官意象”“感觉意象”或“知觉意象”,对嗅觉意象的定位,应超越记忆层面的“再现性唤起”,而强调创造性或预见性的想象层面,视之为“身体感意象”。
参考文献:
[1]鲁枢元.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J].中州学刊,1997(5):88.
[2]刘军茹.新时期小说的嗅覺书写[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58.
[3][4][5]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J].小说评论,2021(1):63,61,63.
[6][24][32]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4,2,4.
[7][10][11][28][29][30]老藤.刀兵过[J].中国作家,2018(4):16,21,47,38,51,33.
[8][22][美]派特·瓦润,安东·范岸姆洛金,汉斯·迪佛里斯.嗅觉符码:记忆和欲望的语言[M].洪慧娟,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110,16.
[9]林喦,滕贞甫.一部气势恢弘《刀兵过》,一部辽南底层民间史——与作家滕贞甫的对话[J].渤海大学学报,2019(4):11.
[12]李建东.无限广阔的内在世界——论文艺创作的“内宇宙”[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1(1):14.
[13]王尧,牛煜.“东北—历史—故事”:《刀兵过》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9(1):119.
[14]史言.批评的召唤:文学启示与主题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7.
[15]林翠云,张箭飞.嗅景与个人记忆的重建:以《生死疲劳》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4):187.
[16][美]段义孚.恋地情结[M].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2.
[17][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3.
[18][英]纽拜.对于风景的一种理解[M]//美学译文(2).王至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81.
[19]老藤.北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20.
[20][27][31][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洲豹阳光下[M].魏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89,89,84.
[21]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39.
[23]老藤.国家羊汤[M]//熬鹰(辽西往事).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84.
[25]老藤.文学是映在故乡的影子[N].北京:光明日报,2023-03-08(15).
[26]林翠云.嗅觉地景与记忆——重思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D].武汉:武汉大学,2017:93.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