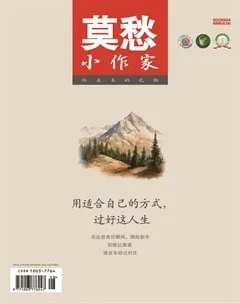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想,我得开始做点什么了。我28岁,几乎一事无成,写过一篇糟糕的论文,一部戏,还有诗。可太早动笔,写不出什么诗来。得等,一辈子都要去搜集意义和甜蜜,也许那会是漫长的一生,然后,在尽头,或许能写出十行好诗。
诗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不是感觉,而是经验。为写一句诗,得见过许多城市,许多人和物,要认识动物,要感受鸟儿如何飞翔,要知道小小的花朵以怎样的姿态在清晨开放。要能想起无名之地的路,想起未料到的相遇和眼见其缓缓而至的离别。要想起尚混沌的童年,想起受伤害的父母,他们想让你快乐,你却不理解他们。要想起孩子的病,它莫名地出现,有过那么多次深重而艰难的转变。要想起那些静寂、压抑的日子和海边的清晨,尤其是那片海。想起这一切,却还不够。还得有回忆,回忆许多个无与伦比的夜,回忆分娩的呼喊和睡着的产妇,她蜷缩着,轻柔而苍白。
有了回忆,却还不够。回忆太多,就得忘记,一定要有很大的耐心,等待它们再回来。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它。只有当回忆成为我们的血,成为眼神和表情,只有当它们无以名状、再无法与我们分开,唯有如此,一首诗的第一个字才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在回忆的中心出现,从那里走出来。
我所有的诗都不是这样写成的,故而也就不是诗。
我坐在这里,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开始了思考,他这样想着:有无可能,人们有过几千年的时间,去看,去想,去记录,卻让这几千年像课间休息那样流逝,只吃了点黄油面包和苹果?有无可能,虽然有发明和进步,虽然有文化、宗教和世间的智慧,人们却仍只是停留在生命的表面?有无可能,就连这本也该是些什么的表面,也被盖上了一层难以置信的无聊,让它看上去像暑假客厅里的沙发?有无可能,所有人们烂熟于心的过去,从未存在?有无可能,对于他们,一切真实都是虚无;他们的生命流逝着,与任何东西都不相干,就像空屋子里的钟?
如果这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么,为了这世上的一切,就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任何一个有这些不安想法的人,一定得从这被错过的开始做些什么:即使他并非最合适的,即使他只是随随便便的某个人:可再没有别人了。
这个年轻人,得坐下来,写作,日日夜夜:是的,他得写,这就是结局。
(摘自《布里格手记》,【奥】里尔克?著,陈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本文有删减)
——记者勇救被强迫卖淫少女背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