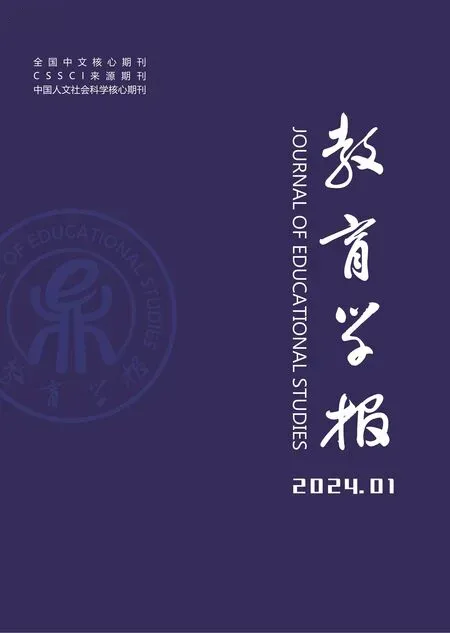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坚守与执着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阅读札记
李玉伟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在一月之内相继沦陷。为保存文脉,延续未竟之教育事业,一大批文化科研机构纷纷内迁,此时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奉中华民国教育部令,于长沙联合筹设分校,称“长沙临时大学”。未至年终,南京沦陷,震动武汉、长沙。面对时局巨变,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于1938年1月20日第43次会议作出迁校决议,决定西迁至云南昆明。[1]34大部教职员、学生在1938年2月离开长沙,经长途跋涉于4月底抵达昆明。此后长沙临时大学又于1938年4月2日奉教育部电令改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西南联合大学自此建立,校史也由此开始。
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相始终,它是全面抗战时规模最大、成就显著、中外闻名的高等学府,同时也树立了多校联合办学的典范,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璀璨的篇章。一部西南联大校史,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合作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更是近代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转型史。谈及西南联大,可谓“弦歌不辍”,为延续中国高等教育贡献颇深。它是“民主堡垒”“自由堡垒”,提倡学术独立和个人自由是联大的核心精神之一,正如冯友兰所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3]时至今日,西南联大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联大留下的精神遗产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回顾已有西南联大的相关研究,可总结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西南联大历史贡献的研究;其二,西南联大大学精神的研究;其三,西南联大教育教学的研究;其四,西南联大学生运动、学生活动的研究;其五,西南联大人物的研究。[4]相关成果十分丰硕。当下想要对西南联大校史或其中的人物进行新的探索,势必要从新史料入手。中华书局2018年整理出版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该日记始于1938年1月1日,讫于1946年7月14日,除1941年5月至12月缺失外,绝大部分日记保存完整。因该日记起讫时间与西南联合大学办学历程相始终,且详细记述了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的教学、科研、人事、行政、社交等情况,反映了他当时的办学思想、学术见解及对学校、教职员、政府和时局的看法,“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5],确乎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重要新史料。日记作为一种私人生活记载,其所具有的直接史料价值,早已广为人知,也成为研究者在研究某一历史人物或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参考。[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与西南联大关系密切的近代学人——郑天挺入手,发挥“探微”精神,从郑天挺与西南联大的互动中重新审视联大历史,剖析郑天挺在教学、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方面对西南联大作出的重要贡献,以郑天挺为个案剖析大学教授在抗战时期对于治学育人的坚守与执着,希望以此折射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变迁。
一、郑天挺与西南联大概述
郑天挺,又名郑庆甡,祖籍福建长乐,1899年8月9日生于北京。自1930年随蒋梦麟重返北大,任校长室秘书,并在预科讲授国文,此后长期在北大任教,直至“院系调整”。1930年夏,在周炳琳、胡适等北大院长的推荐下,郑天挺出任北大秘书长,一直任职到1950年5月。[7]370-405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因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均不在北平,加之法学院长周炳琳、课业(教务)长樊际昌等负责人纷纷南下,北京大学的各项事务均由郑天挺一人代理。因时局巨变,1937年11月郑天挺随罗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前往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已内定迁往昆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随命郑天挺先行前往昆明,负责驻滇办事处事宜。郑天挺2月15日从长沙出发,3月1日抵达昆明。[8]自此以后一直到1946年7月西南联大停办,郑天挺的生活、教学、科研、行政工作均与西南联大密切相关。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任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1)西南联合大学院系设置有调整,历史学系前期为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4月校务会议决定将历史社会学系分设历史学及社会学两系,并于6月呈报教育部,获准后于7月正式设立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揽卷》,第138-139页),长期开设隋唐五代史、明清史等选修课程。
1939年6月位于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后,他还长期担任文科研究所导师和副主任职务。行政工作方面一直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在1938年3月受委派前往云南蒙自筹设分校,还负责蒙自的北大办事处。1940年后郑天挺行政事务日趋繁忙,是年1月他代替沈履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之后相继担任迁校委员会、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等众多行政机构的负责人。[9]当时西南联大教职员所兼职务之多,无出郑天挺之右。就连联大学生都感慨,郑天挺是“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校内)”[10]。
二、“诲人不倦”: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教学
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任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因授课认真,颇受联大学子好评。兹将郑天挺历年授课情况进行统计,详见表1。

表1 郑天挺西南联大任课情况表[11]121-345
由上表可知,除1945年度至1946年度因北上筹备学校复原未开课外,郑天挺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每学年均承担一定量的教学工作,甚至在1940年担任总务长后仍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仅1944年至1945年一学年便负责14学分的课程。就开课内容看主要集中于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清史研究,这些授课科目与郑天挺的研究方向大体一致。
从日记中能够看出,面对繁重的教学任务,郑天挺并未敷衍塞责,相反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每学期的课程,并将教学与每日阅读、科研相结合,每堂课都是自出心裁、一丝不苟。在1937年至1938年下学期开设的隋唐史课程中,郑天挺在每天的日记中都详细记录了阅读、备课和授课的基本情况。1938年5月16日:“七时半起。上午读《唐书》《通鉴》,摘贞观中政事之要,以备讲述。下午授课一小时,讲述唐之平定群雄,分隋唐之际为三期:初期……中期……末期。”[12]615月29日:“上午读《唐书》本纪,参以《外夷传》,列为唐代用兵外族先后表,以备讲述。……饭后至西门,三时归。取《唐书·高宗纪》《武后纪》《张易之传》,戏拟一则天系年。”[12]65在授课过程中,郑天挺从《隋书》《唐书》《通典》《文献通考》等基本史籍入手,搜辑大量史料,在阅读中边思考边摘录卡片,最终形成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的讲稿,从隋末群雄蜂起一直讲至唐德宗时期杨炎两税法改革。不仅是隋唐五代史教学,明清史教学也是从基本史料入手,旁征博引,这是郑天挺备课的基本方法,也成为他的教学特色。1939年11月14日:“十一时至十二时讲述清史、清代之祖居,课毕归饭。午后小睡。读明人笔记,摘录并考订之,以备讲述之需,兼作《明史》札记初稿,此时但作卡片,尚未登之簿册也。”[12]209郑天挺在授课过程中留下大量史学教学的卡片,今人根据这些卡片整理出了“郑天挺断代史讲义丛书”(2)该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郑天挺元史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中华书局,2011年),《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17年),《郑天挺历史地理学讲义》(中华书局,2019年),《郑天挺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21年)。。
讲述历史时,基本模式为专题教学法。在明清史授课过程中,郑天挺将明末清初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分为六个专题,分别为《满洲的崛起和强大》《明清战役》《明末辽帅之数更与清太祖之对策》《清太宗之扰明与明清和议》《南明与满清入关》《明代灭亡的时代》。[13]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使得原本复杂的历史条理清晰,便于学生认知和理解。此外,郑天挺还重视历史基本典籍的介绍,在讲正课之前,照惯例先介绍这门课程的资料目录学,据学生回忆:“光用板书写出明史的史料和参考书刊,就足足花去两小时。”[14]
日记中常见的教学反思、自省,同样反映了郑天挺以教学为本的态度。1939年3月清史考试郑天挺共出三道题目(3)一、清以外族入主中夏,论者多咎吴三桂之请兵,清人亦自谓得天下于闯贼。试就史实论其当否。二、清太祖始创八旗,后世或谓为兵制,或谓为政制,或谓为户籍之制。三者以何说为长,试撮述其要。三、《清史稿》以蒙哥帖木儿为建州别系,而莫详其所出,孟心史先生以为即清肇祖孟特穆。能举其歧异之由,并推阐其世系否。(《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138页),其中一道竟没有学生能够作答,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昨夜归来及今晨车上仓卒拟定者,第三题竟无能对者。余授课时尝举其大要矣,岂世系记忆不清乎?”[12]138每到考试前夜,郑天挺均因担心失误而夜不能寐。1940年明清史考试的前一夜,郑天挺“惟恐有误,夜眠为之不安,警醒者屡”[12]236。1941年明清史考试前,郑天挺“一夜未敢熟睡”[12]380。此类内容在日记中十分常见。抗战时期,因经常要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跑警报便成了师生每日的“功课”,如遇上课,即使预先有警报郑天挺依旧会按时赶到教室,担负起保护学生的职责,其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可见一斑。1939年12月21日记:“忽传外间揭预行警报白旗,全所皇皇。余十一时须入校授课,或劝余勿往,婉谢之。入校,遇霖之于途,亦邀同出北门,复谢之。至校诸生均在,述松山战后之明清和议,迄下课而警报未鸣。归所途中白旗已撤,幸未他避,否则何以对诸生哉?”[12]222
学生对郑天挺所开课程的反馈如何呢?曾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很多学生都认为郑天挺授课逻辑清晰,注重讲解历史中的基本问题,每讲到关键处,则结合史源及有关研究,溯源探微,详论当世,考证同异,颇有创见。[15]正因为郑天挺对待教学一丝不苟,教学方法独到,且给分可观,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选课、听课。除历史学系外,连理学院和文法学院的学生也常来听课[16],选课人数常常超过百人,这在当时的西南联大较为罕见,郑天挺自己也感慨“本年选课者百四十馀人,不惟评阅为难,讲述亦为难也”[12]390。
此外,郑天挺还负责指导本科生论文的工作,间或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1939年2月22日记:“清华史学系四年级学生刘文雅,从余作毕业论文,研究湘军编制及训练。下午为之开参考书目,并检曾集有关系之书札奏稿,迄夜半始毕。今年从余作文者,尚有北大何鹏毓研究张居正之政治主张及政绩,清华孙文庆研究唐代田赋制度。”[12]1341939年12月14日:“四年级生刘熊祥(北大)、黄德全(联大)先后来谈作论文事,……刘研究戊戌政变前之学会,黄研究台湾与中日之关系,五时半去。”[12]220每当毕业季,日记中常见师生讨论毕业论文的记载。
除本科生教学,郑天挺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兼导师职务,为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贡献颇多。日记中常见郑天挺与研究生探讨学术问题、指导论文写作的记述。1939年11月8日:“晚研究生王明来谈。”[12]2071945年3月10日:“四时蒋相泽来,清华研究生也,原从心恒作贵州苗乱及改土归流论文,今日请改作雍正对政治制度之改革,请余指。”[17]1006除在上课时进城外,郑天挺长期居住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北大文科研究所驻地,与学生同吃、同住,不仅是学术导师,还言传身教,担任人生导师。当时,因文科研究所主任傅斯年的工作中心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事务繁多,故北大文科研究所实际事务多由郑天挺主持。研究所学生曾用对联戏谑道:“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院;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18]
总而言之,郑天挺为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人才培养贡献颇深,不仅为本科生开设多门选修课,而且认真备课、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所开设课程都深受学生好评。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方面郑天挺也都付出了很多心血,研究生入学笔试、面试、答辩、论文指导等都能见到他的身影。这种以教学为本的观念和做法,从侧面体现了一位大学教授在抗战时期对于教书育人的坚守。
三、“及时学人”: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治学
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并未因时局艰难和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而暂缓学术研究,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他广泛阅读,在西南边疆史地、明清史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写出一系列扎实而富有创见的文章,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也为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学术发展和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郑天挺仅是众多联大教授的缩影,透过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教书、研究和治学,能够感受到一代学人的风范。
全面抗战时期,郑天挺取得的学术成果无不建立在刻苦、勤奋阅读的基础上。郑天挺十分自律,几乎每日必抽时间读书,且不分时间、地点,凡是空闲皆会读自己的书或从他人处随手借来的书,其嗜读之精神时至今日依旧令人感慨。从日记中能够看到很多他读书时的记录:等候友人时读书,“六时半,金甫、佩弦、莘田约在办公处便饭,赴之。值开会未散,独坐金甫室,取架上《古文绪论》读之。”[12]118-119停电时也未敢放松读书,“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12]371躲警报时在读书,“饭后至公舍后防空洞,携《云南通志·俗祀》一册读之。”[12]383病中亦在读书,“病中不敢看书,仅读《三国·蜀志》数卷。起床后,或劝少用心,今日始读陈寅老文两篇馀,略写日记,看碑帖而已。”[17]647郑天挺还常常读书到深夜,曾在西南联大求学的任继愈回忆道:“无论怎么忙,他一直坚持研究和教学。老师们当中,天天在十二点钟以后才熄灯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郑毅生先生。”[19]如若多日未读书,郑天挺还会在日记中自我反省和鞭策,1938年3月30日自省:“自移居校中,终日栖栖遑遑,未读一书,未办一事。”[12]455月3日记道:“余自往昆明,十二日未读一字。所谓日课,荒嬉未理,可愧之至。”[12]57
为自我激励,郑天挺在日记中记录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1938年3月30日载:“每日读:史书,五叶至十叶;杂书,五叶至十叶;习字,一百;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12]45,并随后写道“此课程可谓少之又少矣,望能持之有恒”[12]45。郑天挺还会根据变化适当调整阅读计划,1938年5月3日记:“自明日始,参酌前定日课,改如下表: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读传记;《汉书》《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读杂书。以上多则三小时,少则一小时,最少须各读五页。”[12]571938年7月19日,因校中停课,无需再备课,所以郑天挺又改订读书计划:《唐书》《汉书》:一卷或二卷。《通鉴》:一卷或二卷。杂书:十叶至二十叶。写作:五百字至千字,专题或读书札记。月课:月初定之,月终检结。”[12]77虽然这些计划因时局变动并未完全执行,但这种有计划、有规律的读书和写作,对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不失为一种鞭策。
遍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能够大致归纳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读书特点。其一,阅读与教学相结合。阅读过程中郑天挺会随手札记,将与教学相关的内容整理成卡片或记录于簿册,以方便后来的教学。1939年5月至12月间持续阅读《明史》,并摘录讲述札记,以备上课之用。其二,阅读过程中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将心得、疑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记于日记之中,以备后来查看、研究。其三,阅读范围十分广泛,不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史学书籍之外,还涉猎语言学、民俗学、方志学、金石学、诗文集、小说等诸多领域,粗略统计郑天挺在西南联大阅读的书籍有二百余种。
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郑天挺进行史学研究和论文写作,阅读中有感触便记录在日记中,并拟定写作计划,形成了“阅读—发现问题—深入阅读—论文写作”的研究模式。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一文即是如此。1938年6月9日记:“余前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近日思之,觉其理颇长,因拟参考群书,作为论文。”[12]68在阅读中发现“发羌”为“Bod”一词的对音,继而深入阅读,五天时间便完成初稿,随后又将文稿送罗常培、邵循正、陈寅恪等人审阅,根据建议作出修改,最终该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此后,郑天挺又用同样的方法写成《〈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两篇文章。凭借《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三篇“以古音证地理”的论文,郑天挺获得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度(1943)第三届“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社会科学类三等奖。(4)西南联大教师中同时获奖的作品还有朱光潜《诗论》(文学类二等奖)、高华年《昆明核桃等村土语研究》(文学类三等奖)、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哲学类一等奖)、闻一多《楚辞校补》(古代经籍研究类二等奖)、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社会科学类一等奖)、罗廷光《教育行政》(社会科学类三等奖)等。(参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68-869页)另据《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记事(1939年至1945年)》记录,西南联大期间文科研究所编辑委员会印行的油印论文共二十种,郑天挺一人独占两篇,研究所其他成员均只有一篇。[11]574-575
以上所举几篇文章,皆关涉边疆史地和古地理学范畴,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古音证地理(或称以音韵证地望),对边疆史地的关注和重视反映了郑天挺史学研究的转向,这与西南联大所在之地——云南历史上为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无关系。在赴滇之前,同侪也提醒郑天挺留意南诏史料,他“闻之欣然”,在宴席上便“默拟一目”,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礼俗第三,语文第四,典制第五,传记第六,命名为《南诏书》。[12]8郑天挺学术研究的转向是西南联大众多教授的缩影,当时的南开大学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联大理学院教授也开始重视西南地质、地层和大气的研究[11]552-588。以上学术转型均有效推动了西南边疆人文、地理的研究,也是西南联大为西南地区学术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除研究领域的拓展,郑天挺延续了他研究明清史的传统,并将研究成果结集汇总,推出《清史探微》一书,奠定了他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坚实地位。1945年郑天挺将12篇有关清史研究的文章结集,命名为《清史探微》(5)《清史探微》一书最初由重庆独立出版社1946年出版。该书所收12篇文章分别为:一、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二、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三、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该书目录少一“度”字);四、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五、墨勒根王考;六、释“阿玛王”(该书目录误作“玛阿王”);七、多尔衮与九王爷;八、释“土黑勒威勒”;九、释“扎尔固齐”;十、释“巴牙喇”;十一、释“巴图鲁”;十二、释“巴克什”。,于1946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年6月初稿)、《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1943年9月初稿)、《清史语解》(1943年9月终稿)、《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1945年3月终稿)四篇文章均在西南联大时期写成。这本扎实的学术论著既是郑天挺多年明清史研究的学术总结,也集中反映了郑天挺的史学思想。“探微”一词,指探索微妙的事理,表现了郑天挺以实证释疑求真的学术追求,这是他治史的重要特点。考察《清史探微》中的文章,都是“小题目”,但却能用丰富的材料以微见著,以小见大,考证扎实、严谨。小题目中凸显了大的历史问题,展现了宏阔的历史视野,这反映了郑天挺对史学考据的重视。
西南联大时期,受时局巨变的影响郑天挺还自觉借史学以经世,通过史学研究为抗战服务。1943年6月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后,他在日记中感叹:“此文随作随辍且两月,此可见余之栖栖终日不遑笔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对抗战之大时代及国家民族也。”[17]711可见郑天挺写作此文有所寄托,此时,身处北平沦陷区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同样强调“有意义之史学”,其《〈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便旨在挖掘胡三省的民族气节,以此来彰显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20]陈垣与郑天挺两位学人一南一北,相互映照,这是面对民族危亡时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境。
综合来看,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正处于学术生命最旺盛的阶段,除在明清史研究领域继续耕耘,出版《清史探微》一书,他还实现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开拓和转向,在边疆史地和古地理考证方向也有不少创获,并结合时局以史学为抗战大局和国家做贡献。
四、“斯人不出,如苍生何?”(6)“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语出自郑天挺1940年1月17日日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第235页)。是日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人前来拜访,旨在劝说郑天挺担任联大总务长一职,未晤,遂留一字条,上书“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八字,同人亦签上姓名。:郑天挺就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在行政工作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1940年1月后担任总务长一职。(7)1940年1月9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132次会议决定“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122-123页)随后于1940年2月26日发布布告“兹经第一三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议: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等语;记录在卷,合行布告,希各知照。此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23页)任职期间兢兢业业,肩负整个西南联大的后勤事务,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此外还调和三校矛盾,对三校之间的合作贡献很大。
联大总务长向来被认为是任务最重、费力最多、最出力不讨好的职位之一,因此也成为西南联大诸多行政岗位中人员变动最频繁的。 任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受到最广泛认可的还是郑天挺,前后长达五年零四个月。在接任总务长之前郑天挺就开始处理联大校务,身为北京大学秘书长,他在1938年初就被派往云南蒙自负责筹划分校和北大驻滇办事处的事务。[12]9因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经常去重庆开会,连西南联大常委会也常由郑天挺代为出席,日记中常见此类记载:“师前得教育部电,嘱到重庆一行,迟之又久,始以今日成行。师离滇期中,命余代表出席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12]129
虽然郑天挺尽职尽责并受到三校师生一致好评,但考察《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难看出,就任总务长并非其本愿,在就职前经过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出于维持三校合作、顾全大局的考量才正式就任。
郑天挺为何不愿出任?其实,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时郑天挺就明确表示不想担任行政职务。1938年1月24日北京大学召开临时校务会议,报告迁滇并设驻滇办事处事宜,会议决定由郑天挺管理总务。郑天挺在日记中感慨:“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12]91939年12月19日,时任联大总务长沈履因前往四川大学任教务长,打算辞去联大总务长一职,并力荐郑天挺出任,但他“力辞之”,并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呜呼!吾日夜继晷,读犹不足,安有馀暇事此哉?”[12]222可见,南渡之后郑天挺的主要计划是读书治学,并不想为行政职务耗费精力,这是他坚决不就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重要原因。
此外,郑天挺不就任总务长一职,与其北大教授的身份密切关系,这牵涉西南联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北大与清华之间的分歧。虽在1939年底郑天挺明确表示拒绝,但1940年初学校依旧让郑天挺任总务长,“近日校中仍欲以余继任总务长,余虽示辞意,其事未止,且未经提出会议发表,余亦不能固辞。”[12]2311月8日北大教授汤用彤询问郑天挺对就任总务长的看法,并支持他不担任该职务,“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12]231汤用彤认为联大各院系学术领导皆由清华和南开教授出任,而行政领导则多是北大领导,出于北大未来发展之考量,承担行政职务会招来怨恨,出力不讨好,故不主张郑天挺出任。郑天挺听后表示:“此语确有远见,佩服之至。”[12]231第二天,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仍决定“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1]122-123。1月17日,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人前来拜访,旨在劝说郑天挺担任联大总务长一职,未晤,遂留一字条,上书“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八字,同人亦签上姓名。[12]235之后,陈雪屏来劝说郑天挺,并向郑天挺带来联大理学院中北大教授的意见,谓“均不愿余为此无代价之牺牲,……事务组不改组绝不可任也。”并进而说,“清华大学同人莫不深厌痛恶于事务组,谓其弊窦甚多”。事实上这句关于清华大学的评价真正刺激了郑天挺,“余得此为之辞意甚坚”[12]236。
1月20日,傅斯年在下乡前又拜访郑天挺并转述钱端生意见,谓:“恐余若不就总务长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12]237加之后来清华大学梅贻琦力劝,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建议他任总务长“至本年暑假,以免发生误会。”[12]243郑天挺就任总务长一事才基本尘埃落定。
联大诸多教职员之所以力劝郑天挺就任,全在于郑天挺处事公断、秉公执法,办事能力强。傅斯年在物色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时曾评价郑天挺“虽刊布之著作不多,然任事精干”[21]。何炳棣在多年后回忆道:“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22]郑天挺出任总务长可谓众望所归,但因担任总务长而极大挤压娱乐、读书、治学的时间,却是不争的事实。
以1940年担任联大总务长为界,日记中反映的郑天挺的生活轨迹差异明显。1940年前的日记还能经常看到郑天挺随友人外出逛夜市、玩升官图、看电影的记录。1939年1月29日载:“七时胡子安约在海棠春晚饭,饭后至夜市,得李苾园对联一副、张香涛条一张,大爨碑一张。”[12]1284月26日:“午建功约在家食饺子。下午在建功家作升官图戏。”[12]1419月31日:“九时谒孟邻师。携燕华师妹看电影五彩武侠戏片,极热闹。十一时归。”[12]184而1940年之后则多记录每日的工作、会议、教学和处理学校纠纷,有时甚至整日都在为学校事务奔走。1942年6月24日记:“七时起。八时入校治事。定发给市民身份证明书办法。十二时归。饭后小睡。二时入校,召集重要职员开会,讨论发身份证手续。三时半至文化巷开聘任委员会。六时半开常务委员会。晚饭后八时半开附属学校整理委员会,十时散,归。半日四会,事多不记。十二时就寝。”[12]570如此内容不胜枚举。
不仅是生活,读书治学也受影响。1940年3月13日记:“午饭后小睡。入校。杂事猬集。五时半归。遂不出。检阅群书,自就行政职务,读书甚少。此虽昔所料及而不意少至此也。家书友书亦久不作,谁之过欤?自讼无及矣。”[12]2531943年1月23日载:“十时半就寝。山上极静,夜中几不闻声响,诸同学之潜心专学,真可佩。余惜为才名所误,日牵俗务,否则上山与诸公共读,所进所得必不限于此也。”[17]653
即使繁忙如此,郑天挺依旧牺牲小我,长期担任总务长一职,直至抗战结束学校北上复原。在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期间,郑天挺为人处世,谨言慎行,奉公执法,待人接物,虚怀若谷,凡有益于校务、有益于学生者,皆尽力而为,从不推诿[23],为保障西南联大各项工作正常开展,消除三校之间矛盾和摩擦任劳任怨,其贡献被西南联大师生广泛认可。1948年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日,北大学子感念郑天挺一直以来对北京大学的关心爱护,在战火中坚守岗位、兢兢业业,遂以全体学生名义给时任秘书长的郑天挺献上“北大舵手”锦旗,以表敬重和感激,这是北京大学建校以来唯一获此殊荣之人。读完日记不难看出,郑天挺不仅为“北大舵手”,更称得上是“联大舵手”。
五、结 语
“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24]这是1983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时,王力先生所作《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王力先生用一首律诗简练地概括了西南联大的校史,并激励后世学人要让西南联大在历史中有一席之地。本文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及回忆、纪念郑天挺的文章入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郑天挺与西南联合大学的关系,着重论述他为西南联大发展所做的贡献。在教学方面,郑天挺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开设的明清史等选修课程颇受好评,为西南联大本科生、研究生人才培养贡献巨大;在读书和治学方面,郑天挺更是矢志不渝,不暇亦学,以读书带动史学研究,其代表作《清史探微》便成书于此时,由此奠定了他在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根据地利之便他还实现了学术研究的转型,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有关西南边疆史地的文章;在行政工作方面,虽就任总务长并非郑天挺本愿,但他为维持三校合作,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选择却为后人所称道,堪得“联大舵手”的称号。从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对治学育人的坚守与选择不难看出,面对时局巨变,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继续选择坚持教学科研,通过教书育人延续中国文脉,以学术研究而经世致用,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默默贡献,郑天挺如此,西南联大众多其他教授亦是如此,本文为认识近代学人提供了一重微观视角。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诸多教职员践行“刚毅坚卓”校训、顾全大局的结果。读毕《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可从一位历史学家的视角感受到西南联大的独特魅力,这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从中亦可窥探全面抗战时期近代学人对治学育人的默默坚守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