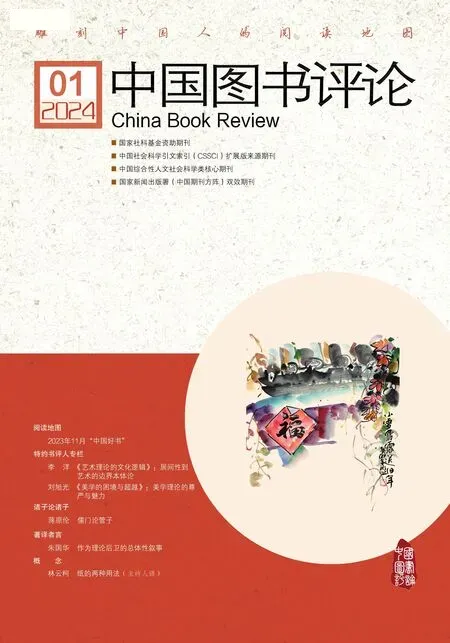作为理论后卫的总体性叙事
□朱国华
【导 读】 作为《文学与权力: 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 英文版的自序, 作者试图在向英语世界的假设读者来解释本书的学术意义时, 也在进行一种自我理解。 作者承认, 本书并未刷新既有文学理论的概念系统, 它不能归入理论旅行中的创造性误读那一类伟大故事的类别下, 甚至有点老派地维护了某种宏大叙事的立场, 但相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日渐艰涩化、 碎片化、 去文学化亦即精英化或非人性化, 这样的论说策略依然提供了一种另类可能。
《文学与权力: 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 的雏形是2000 年年底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 2006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印行的时候,我添加了附录二和附录三; 2014 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的时候, 我添加了附录四, 其余部分并未进行重大修改。 在20 世纪末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同时, 我在痛并快乐地学习近世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 尤其是福柯、 布迪厄、 鲍德里亚、 詹明信这些人的论著。 之所以痛, 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晦涩难懂; 之所以快乐, 是因为他们不断给我带来了获得新知的惊喜。 事实上, 吸收他们的思想养分, 构成了我确立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基本前提。 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20 多年后, 会有这样的一种幸运, 也就是享有盛名的罗特利奇出版社会出版本书的英文版。我的印象里, 西方主流出版社选择中文学术著作加以欧洲语言翻译的似乎以讨论中国论域为主, 对中国学者讨论中国问题, 可能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信任; 但对讨论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的汉语学术著作欧洲语言的翻译, 则似乎热情并不太高。 这是可以理解的, 其原因与其说源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倒不如说, 这反映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际情况是, 我们对解决本土问题尚且有点自顾不暇, 在大的方面来看, 恐怕还腾不出精力来思考诸多普世性的事实或实践。 我不知道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是否存在政治不正确的嫌疑。 不过, 既然西方出版社终于对一名中国学者的西方理论论著产生了兴趣, 这似乎便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进入本书之中, 对其进行重读并对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而这项工作首先可以从我对本书的“自我叩问” 出发。

我这里丝毫无意暗示, 本书获得的某种殊荣证明了它的重要学术价值, 它有多大程度的价值显然需要得到英语读者们的检验。 不幸的是, 本书显然并不太符合萨义德理论旅行理论的某种概括, 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并没有通过对西哲们的创造性误读, 构建一个具有结构复杂性的精致理论系统——萨义德脑子原本想的理论旅行, 是从一个理论系统中衍生出另一种多少带有变异性的理论系统的演化过程, 而本书至多只是通过对诸多精致理论系统的挪用、 折中和改编, 会聚成一个唯物主义或者多少带点实证主义倾向的视角, 重新回应黑格尔提出的艺术终结论的老问题。 那么, 作为一个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诸多理论旅行故事中的一个非典型个案, 我必须应对的解释压力是, 要阐述它有何必要译为英文出版。 我可能需要做个自问自答: 这个似乎老套的学术工作在英语世界还有意义吗?
我的回答方式可能同样老套,也就是既否又是。 “否”, 是指试图通过阅读本书, 刷新对文学理论的看法, 或者发现某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批评方法, 可能是徒劳的。 本书的基本内容, 其实在附录四的第三部分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交代, 概言之, 黑格尔艺术终结论凸显了文学合法性的命题, 而文学合法性依赖于对真理的辩护, 这就涉及到权力:权力一方面是文学的一兴盛的原因,因为文学构成了一种符号资本或话语权力、 意识形态权力; 另一方面又是它走向终结或失去合法性的结果, 因为伴随着它在表征领域里位置的急剧下降, 文学被挤压到权力的边缘。 当然, 附录四旨在以历史化、 语境化和本土化的立场反思和批判本书主要部分的宏大叙事和本质主义倾向, 这是多年后我对自己的批判。 但毋庸置疑, 它只能构成某种纠偏的效果, 不能影响全书的基本架构。 实际上, 从后结构主义在20 世纪下半叶兴起之后, 这样的写作风格早已经被宣判过时了。 因此,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偏离西方人文学科的传统学术轨道, 尽管它采用了许多来自中国的经验材料, 而且在叙事风格上, 它也许甚至比大部分西方文学理论著作更加清通明晰, 虽然其实对一些中国读者而言, 它运用的范畴和概念太多,读起来让人气闷——我们中国人更喜欢明快通透、 言近旨远可以诉诸直接的自然理解的语言, 对抽象术语在文章中的狂轰滥炸常常会感到无法耐受。 我必须无奈地承认, 如果再过50 年, 罗特利奇出版社再编一本 《五十位主要文学理论家》(Fiftykeyliterarytheorists), 我会不会因为本书的表现而能成功入选该书, 我缺乏信心。
我必须要花费更多的笔墨谈“是”。 首先, 我猜想罗特利奇选择本书加以英译, 很可能是因为它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本书分成13 篇独立论文, 曾经在一些学术杂志中刊出, 在知网所收录的文章中获得了广泛引用。 截至2022 年6 月21 日, 引用总数为321 次。 作为一本独立的著作, 在读秀所收录的著作中被引用67 次, 在知网所收录论文中被引用64 次。 考虑到中国人文学科的著作总体上的引用率比较低, 这应该算是一个较好的成绩。当然, 数据不能说明一切。 本书也得到了一些学者更显性的关注。 在一些重要杂志上, 刊发了4 篇针对本书的长篇书评。 本书也算获得过一些荣誉。 本书的一个章节曾经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后来整本书又获得上海市二等奖。 本书在许多大学的中文系被指定为参考读物, 也曾经出现过一些读书会, 来讨论本书的内容。就以上情形而言,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不谦虚地说, 本书在中国文学理论或文学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可见性。假如这个说法成立, 那么, 对关心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状的西方读者来说, 本书就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样本。 窥一斑而知全豹,他们可以通过对本书的阅读而初步认识到, 在中国得到某种认可的文学社会学的著作, 大概呈现为什么样的状貌。 其次, 如前所述, 本书可以理解为西方理论中国化的一个产物, 它显然经历了一个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或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社会语境双重压力下加以塑形的过程,就此而言, 它不仅同样配得上采用萨义德理论旅行的分析技术, 当然也许需要对该技术进行某些调整;而且, 对本书的理解, 还可以连接20 世纪文学共和国视域下中国与西方人文学科的对话关系。 最后, 本书尽管挪用了后结构主义或晚近媒介理论家的理论资源, 但是它主要遵循了看上去已经落伍的总体性的叙事原则。 不过, 正如现实主义文学似乎相对于各种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写作已经属于明日黄花,但是依然是一种吸引着许多读者的文学风格一样, 某种对文学的宏大叙事也可能还是一种值得留意或者尊重的观察文学的方法。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的志向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尽管他的后继者们大部分谨慎地采取了断代史的写作策略, 但是他贯通古今的雄心, 即便在今天来看, 也具有振奋人心的崇高风格和表征力量。在今天, 西方文学理论进入了更新的演化阶段, 实际上, 我主编了多卷本的一套书, 几百万余言, 期待对最近几十年来涌现的各种流行的、前沿的、 新颖的西方文论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介绍, 它已然出版。 我对它们的学习在感到收益颇丰的同时,感到存在若干流弊。 例如, 实证主义路线的理论往往对文学进行支离破碎的理解, 分析得过于琐屑而忘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批判理论往往只把文学视为实现政治目标的一个趁手工具, 对文学经验本身有所遗忘; 各种主义所附加的文学解说,采用艰深晦涩的词语和跳跃的逻辑,让人迷失在语言的迷宫之中无法自拔, 如此等等。 就此而言, 本书的结构与表达也许显出了某种时代的滞后, 但毕竟还是提供了一种另类选择的可能性。
综合否与是, 正如我在题目中所说的, 本书只能作为一个“理论后卫”, 而无法作为足球场上冲锋在前破门得分的“前锋”。 我不敢肯定这本书能否获得英文读者的青睐。重复我在一本书自序中的一段话:在学术著作数量越来越大的同时,它得到阅读的概率也越来越小。 我必须沮丧地承认, 这本小书也可能会死在它印行的那一刻, 所谓方生方死。 所以我要在最后把我的感谢赠送给本书每一位未来的读者——谢谢你, 正如王子之吻唤醒了睡美人一样, 正是你的阅读, 小书的生命之灿烂, 才为你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