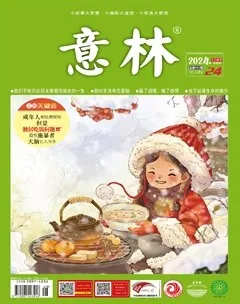消失的钓鱼佬
“喂,该起床了!”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刻意压低的声音,睁开眼,是我爸。猛然想起我们今天要去钓鱼。
此时差不多凌晨五点,外面天还没完全亮,家里其他人都没醒。我们蹑手蹑脚洗漱完,带上渔具就出发了。肩上斜挎着能充当小板凳的椭圆形木箱,里面装着自制饵料,清香扑鼻,这是打窝用的。一盒活蚯蚓,用泥土养着,鲫鱼、昂刺鱼、鳊鱼、翘嘴鱼等都爱吃。鱼竿是从山上砍的毛竹做的,制作工序复杂,胜在轻便,且韧性不输碳素竿。
目的地很远,在清晨的阳光开始照耀时,我们终于抵达一条两岸长满杂草的河流,略微查看河面情况,就各自找到树荫坐下,开始打窝、下竿。
河边特别安静,只有偶尔窜出的蚊虫鸣叫。浮标在水面上完全不动,时间几乎凝固了。这样的静默,要持续很久很久。
刚开始,我耐不住性子,会反复调整下竿的位置。我爸坐在不远处,眼睛片刻不离水面,意识到我的动静后,投来谜之微笑。我焦躁一阵,重新把自己按回原位。

浮标终于开始细碎地动,那是鱼群来了的信号,但不能急于起竿。河里的鱼种混杂,每一种都有不同的上钩特性。有些杂鱼特别小,只围着饵小口慢尝,很难钓起它们,是钓鱼佬最讨厌的类型;鲫鱼和鳙鱼胆小且磨叽,竿起早了会吓跑它们,要等很久才可能重新回来;彪悍的是黑鱼和较大的草鱼,它们能很快把饵掠夺精光。因此,从浮标动的态势判断鱼种,从而抓住时机,特别重要。
我攥紧鱼竿,隔着浑浊的河水,想象鱼儿们的吃相,心跳逐渐加速。一条鲫鱼被拉出水面,落在草地上,活蹦乱跳。虽然鱼只比巴掌略长,但足以为这一天鼓舞士气。我爸在这方面老谋深算,天黑回家前常常能搞条大的。我暗中想要超过他,从来未遂。
以上,是很多年前的场景了。后来我离开乡村,再难有闲暇去钓鱼。于是,野钓的日子就变成珍贵的片段,在我脑海中反复重映。虽然对优哉游哉的钓鱼生活念念不忘,但我后来变成了一个特别着急的人。吃饭很快,走路很快,看剧看书很快,再休闲的活动也手动二倍速。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因为要散完步、看完书。一字之差,却跟散步、看书的含义完全不一样。我也想慢下来,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的生活变异了。
钓鱼没办法变成一个简单的动作,还要求完全沉浸——钓鱼佬不掏手机。准备一支趁手的鱼竿,找到合适的野塘,水下是未知世界,钓鱼佬只能略施伎俩,然后耐心等待,再着急的人也要把自己按在那里。
有次我找人打听,上海哪里有可以钓鱼的地方,对方告诉我,在各种桥洞底下钓是上海特色。我说,可是有些河看起来有点脏,而且桥洞下有很多蚊子吧?会不会很晒?他说钓鱼佬嘛,只管钓鱼,哪讲那么多条件。 那一刻,我悲哀地发现,哪怕再怀念钓鱼的闲适,即使现在就回到少年时期的那条河边,我也没法做个真正的钓鱼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