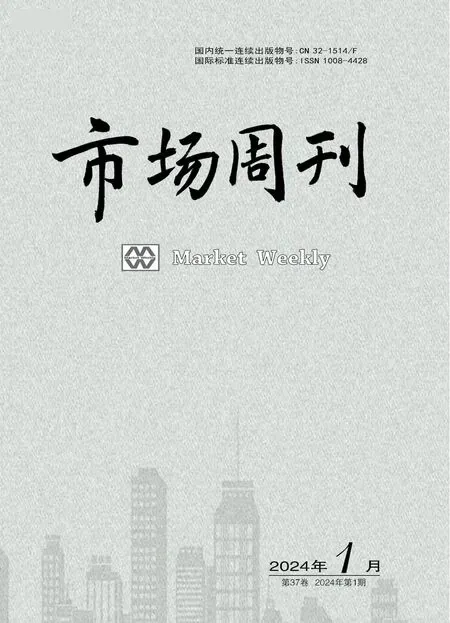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保护探析
白传振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6)
0 引言
随着大数据与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变,人工智能已经可以独立学习并制作“作品”。 2017 年5 月,由“作者”微软小冰创写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的出版,更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水平已经达到可以独立完成作品的新高度。 我国版权保护是以激励创作自然人为目的,以保护自然人版权为目标,但随着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不断出现,已经大幅度影响当前以自然人为中心的版权保护体系。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创作能力远超人类,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保护有必要并刻不容缓[1]。 但根据目前我国的立法状况以及司法实践,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保护存在众多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深入探析。
1 人工智能创作物定性探析
1.1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为版权保护客体
在我国版权保护的八种作品形式中,并没有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一席之地,在兜底规定中所规定的其他创作是否涵盖人工智能创作物,则要具体分析。首先是要明确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内涵,并非所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都可以称为人工智能创作物,它是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以及神经网络技术,通过对数据计算、分析、重组等方式,最终形成的智力成果,其本质就是人工智能对数据进行充分“学习”后再次进行“创作”而形成的成果[2]。
现阶段,人工智能创作物呈现以下几大特征:首先,人工智能生成创作物的效率极高,已经远远超过人类,这也是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快速冲击传统版权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创作作品往往会受到知识面窄、生理、心理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无法保持高强度持续创作,而人工智能可不受外界影响,并具有强大运算能力、高效数据整合能力以及深度学习能力,创作效率极高,如新华社智能员工“小新”可以在几秒之内便完成一篇15 ~30 分钟的演讲稿。 其次,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种类丰富多元,涉猎面极广,不仅涉及诗集、新闻稿、论文等文学领域,还涉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2016 年谷歌便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创作的90 秒钢琴音乐。 再次,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形式与人类作品无异,传统版权保护体系上的作品实质要件为独创性、可复制性、智慧成果,而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人工智能经过对大数据的“学习”然后进行“创作”的成果,如果抛开创作主体,仅从成果享受者角度观察,人工智能创作物与人类作品难以辨别。
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成为版权保护客体“作品”,在学术界存在争议。 一是以王迁与刘影为代表的“否定论”,王迁指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使用者将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最终得到的成果,人工智能无疑是人的智能,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虽然在形式上符合作品的特质,但始终缺乏独立且具有个性的独创性[3]。 刘影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人工智能依靠神经网络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从而加工输出形成的结果,人工智能无法进行情感表达,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有独创性[4]。 持“否定论”学者大体认为,人工智能所谓的“创作”无疑是人工智能单纯地按使用者提前选定的数据以及算法设计而进行的,完全体现不出人工智能的思想,人工智能是不能进行创作的。 二是以梁志文和吴汉东为代表的“肯定论”,肯定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作品”地位,梁志文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已具有人类独有的创造力,人工智能创作只需使用者提前设定目标,无须指令便可独立创作,人工智能已经有了发现规律、进行创作的可能性[5]。 吴汉东还指出只要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独创性,便是作品,不能在版权保护上搞歧视主义[6]。 持“肯定论”学者普遍认为,只要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独创性,就应当在不受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影响下,对人工智能创作物采取版权保护,相比较两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在不考虑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地位,只要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独创性,就赋予人工智能创作物可版权性,纳入版权保护。 这不仅符合版权保护目标,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人工智能创作物相关主体,从而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可以弥补我国版权保护领域人工智能创造物的空白,促进我国版权保护的与时俱进。
1.2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有版权性,则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作品性质,传统版权保护作品的实质要件便是独创性、可复制性、智力成果。 其中可复制性在当今信息网络时代已经不成问题,且人工智能创作物本身就是在强智能状态下形成的成果,是一项智力成果。 那么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具有可版权性便取决于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这一本质要件,这也是目前学术争议中最为激烈的一点。
独创性在版权研究与保护中作为实质性要素,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独创性进行内核研究,也体现对版权制度丰富性与深内涵性的无限追求[7]。有学者认为,独创性从文义解释上分为两部分:其一,独立完成,不存在抄袭、复制他人作品现象;其二,具有独特性,所生成的内容具有一定创造性,只要人工智能创造物具备这两项,便认定其有独创性[8]。 也有学者认为,独创性具体体现为作者精神与思想的表达,是作者精神与思想相融合的升华,人工智能明显不具有精神与思想,从此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创造物不具有独创性。 经过上述对独创性的证成,笔者认为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具有独创性,需综合分析。 首先,从独创性内涵出发,独创性是指作品与已经发表的同类作品或相似作品存在差异,且具有一定创造性,能够对本领域内产生一定影响,如人工智能的创作行为不存在摘抄、复制、抄袭等行为,且其最后的创作物也具有创造性,那么该人工智能创造物便存在具有可版权性的前提。 其次,判断独创性的标准应当从“作者中心主义”向“受众中心主义”转变,有部分学者认为,独创性是作者思想与精神的表达,但依据思想、表达二分原则,应当明确版权保护的是作品的创新表达而非思想,应当抛弃作品只能由人类创作的理念,在判断独创性标准时淡化创作主体,由作品创作者以外的受众判断独创性,这也符合作品的审美理论与作品需公布才受版权保护的本质。
综上所述,在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具有独创性时,应当从独创性最深层次的含义出发,弱化作品创作主体对独创性判断的影响,由作品受众对作品进行独创性判断,判断标准应当由主观色彩的“作者的个性情感表达”转变为“作品与类似作品的差异性”。 当人工智能创作物符合独创性条件时,就应赋予其可版权性,进行版权保护,如果直接否认其可版权性,尽管一定程度上可确保原版权体系免受冲击,降低执法成本,但会导致可预见性的大量人工智能生成物进入作品市场,从而对以人类为作者的作品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2 人工智能主体探析
2.1 人工智能主体不明确
在科技未发达时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由作者经过算法程序设计,完全表达作者思想,其版权应由作者享有并处分,但发展到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已可以在未有使用者的情形下独立创作作品,只要作品具有一定独创性,那么其是具有可版权性的,那么人工智能能否成为版权主体便成为一个问题,这也是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保护问题中最源头、最核心的问题,但目前此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
2.2 人工智能不具有主体地位
有学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保护问题,就要构建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主体体系,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具体可以借鉴法人人格体系进行构建,不过鉴于人工智能的特点,其民事权利可由其所有人代为行使,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根据激励理论,也可以为人类利用人工智能之创作力提供激励手段。 对此观点,笔者则有不同看法,人工智能非权利主体地位,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版权一直都是赋予人类作品的,现阶段赋予人工智能版权无现实意义,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负有民事义务,相辅相成,在侵权的情形下还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现阶段人工智能无法自主承担义务与责任,赋予其地位只会混乱法律体系。 其次,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还会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事上主客体混同以及交叉,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的智力成果,其本身就可作为版权保护的客体,如若再赋予其主体资格,那么便会形成人工智能的尴尬地位,会导致人工智能的主客体颠倒,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混乱现行法律体系。 再次,从著作权法与民法典的关系来看,著作权法与民法典可谓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果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便需要对民事主体制度进行一次重构,这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立法与执法成本。
综上所述,目前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过于前沿,人工智能享有版权无任何现实意义,只有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下,对版权权利进行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
3 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权利归属探析
3.1 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归属不明晰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于何人现行法律并没有具体明文规定,这便形成了一个争议性话题。我国目前学术界中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权利归属模式,我国目前版权赋予究竟采取何种模式,便需要对这几种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种版权权利归属模式便是公有领域模式,即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置于社会公共领域之下,使之成为公共财产,此模式无疑会短时间内促进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传播与利用,使作品市场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也可使现行法律免于修改,降低立法与修法成本。 但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置于公共领域,这就意味着其不能受到版权保护,从长远来看,这无疑存在重大弊端,首先会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不能给予投资者足够的利益,便会打击其积极性,从而使人工智能发展陷入阻滞。 其次会严重打击人类作者的积极性,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种种特征决定了其在与人类作品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若大量人工智能创作物进入公共领域,可能会导致人类作者版权产业的严重缩水。
第二种归属模式便是法律拟制模式,即为人工智能法律拟制版权主体人格,消灭人工智能不能成为权利主体这一障碍,这样便能直接解决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归属问题。 经上所述,现阶段赋予其主体资格并无现实意义,也没有必要性,只会徒增版权归属制度的复杂性。
第三种归属模式便是属人模式,与以上两种模式相比,具有更大的法理意义与现实意义,在学术界呼声极高。 但是在人工智能生成创造物的过程中,按照时间的先后,共有三类人发挥了不同作用:首先是投资人,其花费大量财力、物力来研发人工智能;第二类便是设计者,设计者将人工智能从虚无变成现实;第三类便是所有者,其在人工智能生成创作物的过程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究竟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赋予三类中的哪一主体,目前存在着争议。
3.2 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应归属投资人
在上述介绍的三种模式中,笔者赞同第三种版权权利归属模式即属人模式,这也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第一种与第二种模式或存在极大弊端,或没有现实意义。 属人说的优势便在于,首先能够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版权赋予相关人,能够激励相关人加大投资,从而推动人工智能的再进步。其次,符合版权保护法律制度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人工智能并不具有自主性,不能行使权利与承担义务和责任,而自然人在行使权利、承担义务、承担责任方面具有不二性。
那么在第三种模式中,版权赋予哪一主体,便又成为一个争议点。 有学者认为应将版权赋予人工智能所有者,认为其为取得人工智能支付了相当大的成本,并且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受所有者委托形成的,理所当然应当赋予所有者。 笔者认为,版权确立归属原则需要对相关主体权益进行最大利益化考量,虽然每个主体在不同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但投资者的作用是无法被替代的,可以说,没有投资者,便没有人工智能,也就没有人工智能创作物,此外,投资者在创造人工智能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人工智能成为现实,将版权赋予投资者,可以激励其再扩大投资,促进人工智能发展[9]。
4 结语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产物,其版权保护应受到重视,对人工智能创作物定性是对其进行版权保护的前提,若认定其具有独创性,就应当认定其为版权保护的客体,具有可版权性。 否定人工智能主体是必然的,人工智能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若贸然将其法律拟制、赋予其人格,必然导致法律体系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