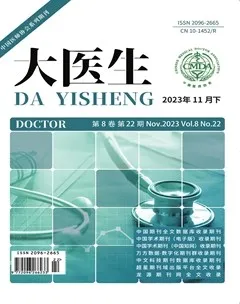李智教授“卫气营血”理论治疗外感发热类疾病经验
赵 轩,李 智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北京 100103)
1 “卫气营血”理论概述
1.1 理论渊源 “卫气营血”的概念最早由《内经》提出,至元代理论逐渐形成,至明清辨治体系正式确立。卫气营血辨证来源于《温热论》,是由清代医学家叶天士首创,在伤寒六经辨证的基础上发展,用于论治外感温热病的辨证方法[1]。四时温热邪气侵袭人体,造成卫气营血生理功能的失常、人体动态平衡的破坏,从而导致温热类疾病的发生。因此,将这类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临床表现概括为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证四个证候,可以反映外感温热病不同传变阶段的证型、邪正斗争的形势,揭示外感温热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一般规律,对后代临床诊治疾病具有较大意义。
1.2 临证发挥 现如今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随之而来的是与日俱增的压力,饮食起居生活方式等的改变。各种压力会造成气、血、津液输布不畅,经络不通,使现今人群多发内生郁热、内生血热、内生湿热等疾病,成为温病学新疾病谱的“培养基”[1]。因此,卫气营血的理论可应用于内伤诸疾病中,可涉及心血管、呼吸、消化、皮肤、妇儿等多科疾病。本篇主要阐述李智老师在外感发热类疾病中运用该理论诊治疾病的验例。现举例如下。
2 验案举隅
2.1 外伤感冒 感冒俗称伤风,是指感触四时风邪或时行病毒,引发肺卫功能失调的外感病,主要临床表现为鼻塞、流涕、喷嚏、头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脉浮等[2]。病变部位主要在肺卫。肺主皮毛,若皮毛受邪,宣发温润不足,则肺卫功能失调,发为感冒。冬、春季节多发病,引发咳嗽、鼻炎及慢性咳喘,甚至心悸、水肿等,对小儿及老年体弱者危害最大。时行感冒常暴发流行,传染迅速,起病急,症状重,若不积极防治或可导致死亡。夹湿感冒、虚人感冒是感冒中的特殊类型,不在本篇讨论的范围之内。
“风为百病之长”,风邪侵袭人体肺卫发病,常夹有其他当令之气相合致病,表现为风寒、风热、风燥、暑湿或疫毒、湿热等证型,李智老师认为,传统教材中将外伤感冒的证型仅归为风寒、风热、暑湿几大证型,分类单一,不太符合病变传变规律,造成临证困难。如遇时行病毒感染,高热持续不退,应已传到了气分,甚至营分或血分。对于外感风邪或病毒的感冒,治疗建议遵循叶天士《温热论》中提到的“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治疗原则[3]。感冒早期病变在肺卫,“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应发汗以祛除表邪,宣通肺气。但要注意其传变,现代人内热较盛,几个小时传变就可能发生。
李智老师认为,外伤感冒的传变,一般经过风寒表证(卫分证)、寒包火证、风热表证(卫分证)、半表半里证、气分证、气营两燔证、营分证、血分证等基本证型。风寒表证主要运用荆防败毒散,寒包火证主要运用防风通圣散,风热表证主要运用银翘散,半表半里证主要运用小柴胡汤,气分证主要运用白虎汤,气营两燔证主要运用清瘟败毒散,营分证主要运用清营汤,血分证主要运用犀角地黄汤加减。
2.1.1 案例一 男,57岁。患者因不慎摔伤导致左股骨颈骨折。于2000年2月1日收入望京医院骨伤综合科,于2月23日行左股骨颈闭合复位、中空螺丝钉内固定术,术后当晚出现发热37.8℃,之后每天下午发热37.4~38.4 ℃,有时晚8点体温达39.2℃。患者有糖尿病及脑梗死后遗症病史。患者发热期间,白细胞始终在正常范围,6月1日红细胞沉降率85 mm/h,结核菌素试验弱阳性,未找到肿瘤、结缔组织病等证据。先后经多位院内专家会诊,曾用中药汤剂,配合多种抗生素(包括青霉素、磷霉素、丁胺卡那霉素、环丙沙星等),体温未见下降。2000年6月15日,医务处组织全院病例讨论,专家意见仍倾向关节感染。2000年6月23日,请院外专家会诊,认为左髋关节腔内感染。李智老师于2000年6月16日第一次应邀会诊,建议甲硝唑、氨苄青霉素、奥复星静脉点滴,配合益气解毒汤药和紫雪散。6月28日,发热仍未好转,李智老师再次会诊,建议停用所有抗生素观察1周。1周后患者仍发热,建议用三联抗痨药试验性治疗。7月28日体温仍未下降,李智老师第3次会诊,予小柴胡汤合蒿芩清胆汤加减3剂。2000年8月21日,李智老师第4次会诊意见:经过6周的较系统的正规抗痨,体温无明显变化,结核基本排除,故停抗痨药,同时停用所有针对发热的西药。查看患者,形体消瘦,精神很差,午后夜间发热,8月20日体温最高仍达38℃,舌质红绛无苔,脉细数。此时患者已连续发热6个月,考虑热入营血,阴血耗伤,予犀角地黄汤合青蒿鳖甲汤加减,处方:水牛角12 g,生地15 g,丹皮12 g,玄参15 g,麦冬12 g,白芍12 g,竹叶12 g,银花12 g,连翘12 g,地骨皮12 g,龟板15 g,鳖甲15 g,白薇10 g,青蒿10 g。3付,水煎服,2次/d,嘱服药忌口。患者服药1剂后,白天体温在37~37.3 ℃,偶尔到37.6 ℃,继服该方9剂,体温恢复正常,于2000年10月9日出院。
2.1.2 案例辨析 该患者发热半年多来,先后使用多种抗生素,又经过系统抗痨6周,先后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会诊,几乎用遍了西医可能有效的办法,体温均未下降。最后单纯用中药,体温下降,病情才出现转机,这是证明中药疗效的很好证据。吴鞠通《温热条辨·下焦篇》云:“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热自阴来者,青蒿鳖甲汤主之。”[4]患者有中风后遗症,说明素有肝肾阴虚,感受外邪,热入营血,更易造成阴血耗伤,同时又有余邪未清,形成了阴虚热伏的青蒿鳖甲汤证。对于中风患者,发热久治不愈,应首选此证型。
2.2 外感咳嗽 外感咳嗽是以咳嗽、咯痰为主要临床表现,由六淫外邪侵袭肺系,或脏腑功能失调,内伤及肺,肺失宣肃所成。《素问·咳论》中指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2]。现代中医对肺咳认识较多,对肝咳、脾咳、肾咳容易忽视;治疗应该是多途径、多方面的,单纯使用抗生素难以取得良好的疗效。本篇主要阐释外感原因导致的咳嗽。
六淫之邪,从口鼻或皮毛而入,侵袭肺系,肺气被郁,肺失宣肃,迫气上逆。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云:“肺体属金,譬若钟然,钟非叩不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自外击之则鸣。”[5]外感咳嗽常以风为先导,兼夹六淫之邪,表现为风寒、风热等相合为病。李智老师认为,传统教材中将外感咳嗽的证型归为风寒、风热、风燥等几大类型,亦不太符合病变传变规律。外感咳嗽的传变主要经过的基本证型及所运用的方剂如下:风寒表证(卫分)主要运用杏苏散,风热表证(卫分)主要运用桑菊饮,痰热阻肺(卫气同病)主要运用麻杏三子汤,痰热郁肺(气分)主要运用清金化痰汤,肺热炽盛伤及营血(营血分)主要运用羚羊清肺汤加减。
2.2.1 案例二 男,54岁,感冒后连续咳嗽4月余,咳吐大量白稠黏痰,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工作。做过各项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使用多种抗生素和止咳化痰药,以及请名中医专家会诊,咳嗽咳痰不见好转。于2006年4月底请李智老师会诊,此时患者已静脉点滴抗生素10余天,仍咳嗽频频、咳大量白稠黏痰。李智老师望其舌质红、苔薄白腻,脉滑,观其胸片、肺部CT、肺功能均正常,无明显基础疾病。予麻杏三子汤3付,处方:炙麻黄6 g,生石膏(先下)30 g,杏仁9 g,炙甘草6 g,苏子10 g,莱菔子10 g,白芥子10 g,鱼腥草30 g,芦根30 g,旋覆花(包)15 g,白芍15 g,辛夷6 g,苍耳子9 g,拳参10 g。3付,水煎服,每日2次,嘱忌鱼虾海鲜、辣椒、烟酒,3天后咳嗽明显好转,痰量明显减少,再予4付巩固疗效,同时嘱其到空气好的地方练习深呼吸。半个月后,咳嗽完全痊愈。
2.2.2 案例辨析 此患者外感咳嗽4月余,咳嗽咳痰症状仍明显,表证未除,属于卫气同病。舌脉痰湿之象明显,予清热化痰,宣肺止咳的麻杏三子汤加减,对外感咳嗽、肺炎咳嗽均有效,对感冒后期发热已退,咳嗽咳痰迁延不愈的患者疗效尤其明显。
2.3 发热伴淋巴结肿大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cleosis,IM)是一种主要由EB(epsteinbarr EB),又称人类疱疹病毒4型(human herpesvirus 4,HHV-4)病毒感染,典型特征是发热(38.5~40℃)、咽峡炎、淋巴结及肝脾肿大、皮疹,以及周围血常规中出现大量异常淋巴细胞,属急性增生性传染病。病理特征是淋巴组织的良性增生、无化脓,具有自限性,多数预后良好[6]。EB病毒核酸检测对本病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少数病例迁延不愈,出现淋巴结组织凝固性坏死,可合并发展为坏死性淋巴结炎(菊池病)、噬血细胞综合征、淋巴瘤等,易漏诊误诊,主要表现为发热、淋巴结及肝脾肿大、全血细胞减少,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皮疹、肝功能损害,乃淋巴-单核巨噬细胞的过度活化增生,引发机体过度炎症反应,并伴有明显吞噬血细胞现象。该病起病很急,病情进展很快,如不进行及时有效医治,生存率低于10%,多数死于发病8周内[7]。现代医学对本病无特异性疗法,主要运用糖皮质激素对症支持治疗,或使用更昔洛韦、伐昔洛韦、干扰素、免疫球蛋白等抗病毒或免疫调节治疗[8],疗程较长、价格昂贵、毒副作用较明显。
在教材中,将本病归属于中医学“大头瘟”“喉痹”“痰核”“瘰疬”等范畴,辨证分为早中期、后期、恢复期等7大证型[9]。李智老师认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是由于疫厉邪气侵入机体肺卫,循三焦传变,导致气血、脏腑、津液功能失司而发病,其发病与感邪过重及正虚抗邪无力密切相关。该病邪气易感气分,亦可深入血分,燔灼津液,少数可发生邪闭脏腑,出现高热、神昏等症状。厉邪内阻经络,气机升降失常,邪气内闭,郁而化热;邪热外蒸肌肤,故热势持续不退,扪之灼手;厉邪痰饮留于体表产生赘生物,表现为淋巴结肿大,阻于肝经、脾经,则有肝脏及脾脏肿大,并伴有触痛;邪热中阻,耗伤胃阴,故见口疮、咽痛、咽肿;若邪热不退,热入血分,则可发为疹。少数正气极虚不能抗邪,或久病施治,或早期过用寒凉,均可导致正气过度亏耗,致使邪热内陷脏腑,而表现为邪盛正衰之危症。
2.3.1 案例三 女,36岁,2015年7月初诊。主诉:间断发热伴淋巴结肿大1年余。现病史:患者2014年6月无明显原因出现发热伴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以下颌淋巴结肿大为著。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查血常规示异型淋巴细胞>30%,EB病毒核酸检测提示EB病毒感染,诊断“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予抗病毒治疗3个月后复查EB病毒核酸转阴,全身仍有多处淋巴结肿大伴触痛。此后患者间断发热,并伴乏力,肝转氨酶升高。半年后患者于北京协和医院复查EB病毒DNA(+),血常规示异型淋巴细胞41.3%,辗转多家医院仅建议休息调养。期间怀孕不幸流产,体质逐渐虚弱已不能承担日常工作。患者于李智老师处就诊,老师察其舌脉,辨证:邪热入营,上焦毒聚。治则:清营透热,解毒利咽。予传单散结退热方,处方组成:牛蒡子12 g,黄芩10 g,黄连9 g,板蓝根12 g,白花蛇舌草15 g,半枝莲15 g,山豆根10 g,重楼15 g,连翘10 g,玄参12 g,升麻6 g,柴胡10 g,桔梗6 g,薄荷6 g,陈皮6 g,生甘草6 g。7付,冲服,2次/d,嘱服药忌口。1月后复查患者肿大的淋巴结减小,乏力感好转。继续予传单散结退热方治疗1月余,未触及肿大的淋巴结,患者精力体力也恢复正常,可正常参加工作。2015年8月18日于协和医院复查EB病毒DNA(-),检查未触及肿大淋巴结。后随访5年期间,病情无复发,并成功生育。
2.3.2 病例辨析 本案患者确诊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已2年,辗转多家三甲医院均仅建议休息调养,日常工作不能完全胜任,病症较典型。李智老师四诊合参,判断病机为热毒雍盛,予传单散结退热方连续治疗1月余,患者淋巴结逐渐减小,乏力感消失,精力体力逐渐恢复正常。由此可见中医药对本病具有确切的疗效。
3 经验总结
因四时六气之不同,人体素质之差异,外感疾病在临床上有风寒、风热和暑湿等不同的证候分型,在病程中还可见寒与热的转化或兼夹。感受时行病毒者,病邪从表入里,传变迅速,病情危重急骤。李智老师认为,临床上对于外感感冒、咳嗽、发热伴淋巴结肿大等类病症的诊治,传统划分风寒、风热、风湿、风燥等证型单一固守,若遵循“卫、气、营、血”辨证传变规律诊治,能起到较好疗效,反映疾病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传变发展过程。案例一辨证为热入营血,予犀角地黄汤合青蒿鳖甲汤加减,清热解毒、凉血散瘀、养阴透热,对高热持续不退、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有良好疗效;案例二辨证为卫气同病,予麻杏三子汤加减,清热化痰,宣肺止咳,方含麻杏石甘汤、三子养亲汤、金沸草散、芍药甘草汤等,对外感咳嗽、肺炎咳嗽均有良好疗效。此类咳嗽治疗中,应避免过早使用养阴益气或清血热入里之品,如贝母、麦冬、沙参、枇杷叶、生地黄、桑白皮等,否则会引邪入里,使咳嗽缠绵难愈,“如油入面”;案例三辨证邪热入营,上焦毒聚,予传单散结退热方清营透热、解毒利咽,即普济消毒饮加减重用重楼、山豆根,增强清热解毒、利咽消肿止痛之功效。若发热重、淋巴结肿大明显则需加用牛黄0.3 g冲服,防止发热持续不退,或病毒间断复阳,不能根治,乃临床经验用药。
综上所述,中医药治疗外感感冒、咳嗽、发热伴淋巴结肿大等外感发热类疾病疗效确切、较西药副作用小,并且如果干预及时,可阻止部分病例传变发展为重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