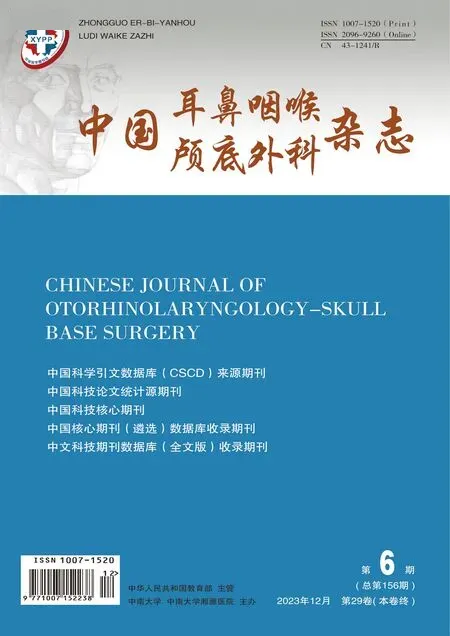脂肪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研究进展
杨佩宣,周威邦,张小兵
(1.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2.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耳鼻咽喉科,甘肃 兰州 730000)
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在全球的发病率非常高,尤其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全球20%~30%的人群患有AR[1-3],约5%患有哮喘[4],且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AR患者表现出来的喷嚏、流涕、眼痒等临床症状对患者的社交生活、学习和工作效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重者甚至会影响患者的精神状况,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5-6]。广泛认为,AR是一种由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介导的Ⅰ型变态反应性的非感染炎症。在临床医学实践中,不规范的药物混用和不合理的治疗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原有症状加重甚至全身的过敏和低血压等[5]。近年来,有关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的各项实验研究表明,MSCs本身具有低免疫原性及免疫调节功能,同时具有营养和促进组织修复的能力,其抗炎抗过敏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多个实验结果的支持[7-8]。利用MSCs自身的特点,进行细胞移植,理论上来说是治疗AR的新希望。脂肪来源的MSCs具有来源广泛,制备较易,组织修复功能和免疫调节能力明显等优点,本文就脂肪来源MSCs治疗AR的实验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AR的发生发展
普遍认为,1型辅助性T细胞(type 1 T helper cells, Th1)和2型辅助性T细胞(type 2 T helper cells, Th2)的免疫失衡是AR发生的免疫学基础[9],主要是指Th2在免疫反应中占优,而Th1不足,导致体内多种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的释放,最后表现为外在的鼻部过敏症状。
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变应原的种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引起国内变应原谱系的改变[10]。机体接触到外界变应原后,经抗原呈递细胞的处理,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和T细胞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T细胞结合,诱导T细胞分化为Th2。Th2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IL-4、IL-5、IL-13等[11],通过信号转导,从而诱导B细胞分化为产生IgE的浆细胞,同时参与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炎症反应。第2组先天淋巴细胞(group 2 innate lymphoid cells,ILC2)也参与免疫应答过程,其产生的IL-5、IL-13因子加剧了炎症反应[12]。除此之外,滤泡辅助性T细胞在诱导血清IgE水平上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3]。血清中,IgE与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表面的高亲和力受体结合[14-15],使其致敏,致使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释放包括组胺、类胰蛋白酶和趋化因子在内的生物活性介质,外在机体则表现为一系列典型的过敏症状[16]。
AR并不仅仅是上呼吸道疾病,它还可能导致下呼吸道的炎症发生,在AR患者身上,经常存在鼻炎与哮喘并存的现象[17]。
2019年底新冠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出现及其大流行的发生,对全世界人口的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截至2022年12月1日,全球已确诊超过6亿人,已有超过660万人的死亡被归因于COVID-19的大流行。AR和哮喘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病毒性呼吸道感染会导致其病情恶化[18-20]。部分回顾性分析研究结果表示,AR及哮喘是COVID-19的危险因素,但同时也有队列研究表示其不存在相关性[19, 21-23]。中度及重度哮喘目前被美国疾控中心列为COVID-19重病的危险因素[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gov)],同时还有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吸系统疾病被列入。结合上述资料,笔者认为,AR的治疗和控制是十分必要的,寻找新的有效的、疗效更好的治疗方式,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2 MSCs的特点
MSCs由干细胞分化而来,同时其仍然保留了干细胞的普遍特性,包括自我更新、自我增殖(克隆)和分化潜能[24-25]。MSCs最初由 Friedenstein等[26]发现,目前一直是各方向研究的中心。MSCs来源广泛,可从脐带血、子宫内膜、骨髓、脂肪、肝脏多种组织器官中提取[27],理论上,MSCs甚至可以从全身任何组织获得[28],通过体外培养,可以获得呈现出贴壁生长时具有成纤维细胞形态的细胞[29]。最开始,MSCs多指骨髓来源的祖细胞,直到2001年,Zuk等[30]才提出了脂肪来源的MSCs这一概念。脂肪来源的MSCs具有获取方便、提取简便、丰度大和多谱系化分化潜力的优点[31],且极少存在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因此在生物医学实验中,常采用脂肪来源的MSCs作为实验材料。
MSCs主要具有以下5项生物学功能[7,32]:①增殖功能;②多能分化功能;③归巢和迁移功能;④营养功能;⑤免疫抑制功能。
作为干细胞的一种,MSCs能进行增殖达成自我更新和细胞扩增,这与细胞本身具有的“干性”有关[33]。干细胞能在细胞周期中快速移动,较少在G1期停留,S期较普通细胞延长[34],且能长时间地保持在G1或者G0期的静止状态,在需要时再次进入细胞周期。体外培养时,MSCs的增殖功能仍然存在,并且能在一定的刺激下分化为脂肪细胞、成软骨细胞和成骨细胞[7, 35-36],也有部分研究表明[37-39],MSCs也能分化为内皮祖细胞、肌母细胞和神经母细胞。这样的分化能力,使得其在生物材料领域和组织再生领域大放异彩。MSCs可以沿着血管,穿过内皮壁,回到自然驻留地或者迁移到受损及患病组织中[7]。Fu等[40]研究表示MSCs能通过定向分化和旁分泌进行迁移和组织修复,促进受损组织和伤口的愈合。Cucarián 等[41]研究也表示人脂肪来源的MSCs和体育锻炼,能有效改善帕金森大鼠模型的运动障碍。但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42]。MSCs可通过细胞间接触产生修复环境的能力,伴随着多种生物活性大分子的旁分泌过程,这些生物活性大分子促进参与组织修复的炎症细胞的免疫调节和内源性祖细胞的分化[32,43-44]。MSCs的免疫调节特性能抑制局部免疫反应和纤维化组织形成,同时调节血管生成,细胞凋亡和细胞增殖。MSCs典型的体外调节能力是抑制T细胞[45]和B细胞[46]的增殖,以及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s)的分化,上调Treg细胞的数量来调节免疫反应[47]。在体内和体外比较不同来源的MSCs研究很多,但基本都产生了一致的结果,提示MSCs为免疫学应用中最有希望的细胞[48]。
3 脂肪来源MSCs的低免疫原性与免疫调节功能
脂肪来源的MSCs拥有MSCs的一系列生物学特性,自然也拥有免疫抑制功能。实验证明,脂肪来源的MSCs在体外扩增时,具有低免疫原性的特点[7]。其不表达Ⅰ类人类白细胞抗原及包括白细胞分化抗原40(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0,CD40)、CD80、CD83、CD86和CD154在内的共刺激分子,仅表达Ⅰ类人类白细胞抗原类分子。同时,MSCs还可通过调节DC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 NK)[49-50],间接抑制效应T细胞的启动,通过移植MSCs可以有效改善几种炎症性疾病[51],如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
脂肪来源的MSCs具有抗炎作用。不同来源的MSCs的免疫特性不完全相同,且来自脂肪组织的MSCs往往有更强的免疫抑制能力[52-53]。有学者认为[54-55],MSCs可以通过对T细胞的有丝分裂进行干扰,一定程度上阻止其增殖,达到抑制免疫应答的目的。这种抑制并不需要直接接触,但当两者进行直接接触时,抑制效应增强。在γ-干扰素(interferon 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IL-1等炎症因子的刺激下,MSCs会上调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和环氧合酶的表达水平,以致免疫抑制分子一氧化氮和前列腺素E2大量产生,进行免疫调节[51, 56]。值得注意的是,一氧化氮的调节作用,目前仅在小鼠系统中被证实[57],具有物种依赖性,在人体内,对应的是吲哚胺双加氧酶,在一些模型实验里,人MSCs也可发挥相应作用,但并不总是能抑制T细胞的效应[50-51]。MSCs能产生前列腺素E2,减少T细胞的增殖,抑制TNF-α和IL-12的产生,下调肥大细胞表面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类的表达,减轻炎症反应[58]。在Najar 等[59]的实验研究中,人脂肪来源的MSCs在体外共培养时,对淋巴细胞的增殖有剂量依赖性的抑制作用,且高于骨髓来源的MSCs。同时,其扩增速度也高于骨髓来源的MSCs,范围也更广。Quaedackers等[60]报道,人脂肪来源的MSCs可以与活化的T细胞、B细胞和NK细胞亚群结合。这些观察的结果表明,脂肪来源的MSCs具有很好的免疫调节能力,在细胞治疗和组织工程方面十分有益,且移植环境也很好。同时,MSCs产生多种趋化因子和黏附分子,将相应的T淋巴细胞募集到损伤部位,发挥免疫抑制作用。MSCs还可以通过抑制IFN-γ、IL-17的分泌,拮抗Th1和Th17的分化,促进IL-10的产生,诱导Treg细胞的产生[61-62]。Kavanagh的实验证明,MSCs能诱导CD4(+)FOXP3(+)T细胞,降低IL-4、IL-13水平,增加了IL-10的水平,说明MSCs能诱导Treg细胞参与调节气道的免疫反应。在人和鼠的体内,MSCs都能抑制B细胞的增殖、分化及活化,在体外共同培养时,B细胞表现出周期停滞、浆细胞生成受损,免疫球蛋白分泌能力受损的倾向[63-64]。有相应研究表明,这可能与MSCs胞外囊泡的分泌有关[65]。另外,Ivanova-Todorova 等[52]的研究表示,脂肪来源的MSCs能通过分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和IL-10控制DC的发育,特别是单核细胞衍生的DC,抑制了共刺激分子CD80和CD86的表达,从而抑制了DC有效刺激T淋巴细胞的能力,间接地导致免疫反应的降低或消失。脂肪来源MSCs的以上特点,说明了其能很好地调节Th1/Th2的平衡,从而缓解气道的炎症反应。
MSCs的免疫调节功能极其复杂,它涉及对T细胞、B细胞、DC细胞、巨噬细胞、Treg细胞等多种细胞的调节[66],形成了密密麻麻的调节网络,有助于免疫相关疾病的治疗。目前,在人体内,已经进行了克罗恩病(美国Mayo医生诊所),急性移植物抗宿主反应(Osiris Therapeutics)和严重成骨不全(St. Jude 儿童研究所)的临床实验。AR暂时没有相关的临床试验,但值得期待。
4 脂肪来源的MSCs治疗AR的相关实验研究
因脂肪来源的MSCs的上述特性,现已经成为AR治疗研究的新方向,有许多人对其治疗AR进行了相应的实验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结果。
Cho 等[67]通过动物实验,向AR模型小鼠(指人工造模的AR小鼠,一般采用卵清蛋白和氢氧化铝联合基础致敏,并使用卵清蛋白进行鼻腔激发)尾静脉注射脂肪来源的MSCs,光镜下比较发现MSCs可以改善AR模型小鼠鼻黏膜部位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且能降低血清中特异性IgE的水平。并对脾脏进行了IL-4、IL-5、IFN-γ的检测,研究人员发现与Th1相关的IFN-γ水平上升,与Th2相关的IL-4、IL-5水平下降,这说明了MSCs可能促进了Th1向Th2转化,调节了AR的免疫失衡。肖二彬等[68]重复了上述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同年,李冠雪等[69]也进行了相似的实验,向AR模型小鼠尾静脉注射不同浓度的脂肪来源的MSCs后,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中IL-4、IL-6、IL-10和IFN-γ的水平,发现IL-4、IL-6水平下调,IL-10和IFN-γ水平上调,荧光显微镜下CM-Dil标记的脂肪来源的MSCs可向鼻黏膜迁移,且高浓度MSCs注射组表现出比低浓度组更明显的迁移修复倾向,这说明MSCs对鼻黏膜的修复作用与剂量也有一定的关系。此实验一定程度上验证了MSCs具有迁移和促进受损组织修复的能力。Ebrahim等[70]则通过向AR模型小鼠腹腔注射脂肪来源的MSCs来进行实验研究。与口服孟鲁斯特钠的AR模型小鼠组相同,注射了脂肪来源的MSCs的小鼠,在行为学上,打喷嚏、流涕等过敏症状明显减轻,血清学分析结果则表示特异性IgE、IgG1、IgG2a和组胺水平也均有降低。对比注射了MSCs的小鼠和孟鲁斯特钠组的小鼠,光镜下发现腹腔注射脂肪来源的MSCs的AR模型小鼠鼻黏膜部位修复更为明显,表现出了MSCs修复作用。此实验也说明了脂肪来源的MSCs对AR小鼠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戴伟丹等[71]将脂肪来源的MSCs通过腹腔注射,注入哮喘模型小鼠体内,比较发现,干细胞治疗组小鼠的肺部炎症较模型组明显减轻,血清学实验也表示,治疗组体内IL-5、IL-13表达较哮喘模型组明显下调,且随着时间的变化,治疗组小鼠体内IL-25、IL-33等细胞因子的表达也逐步下降,上述因子均为ILC2的前炎症因子。此实验证明了静脉注射脂肪来源的MSCs能减轻哮喘的气道炎症,缓解临床症状,具体可能是因为MSCs抑制了ILC2的增殖。前文我们提过,ILC2也同样参与了AR的发生。去年,Trombitas 等[72]对慢性鼻-鼻窦炎小鼠进行了类似实验,通过向慢性鼻-鼻窦炎小鼠进行框周静脉注射脂肪来源的MSCs,在注射后比较对照组,模型组和MSCs治疗组的小鼠鼻黏膜,发现MSCs向鼻黏膜进行了迁移和修复。
综合上述实验结果,我们认为脂肪来源的MSCs能一定程度上降低气道的炎症反应,并且能一定程度上进行受损组织的修复,具有非常好的疗效,这是基于MSCs本身的特性实现的,尤其是MSCs本身的免疫调节能力。在致敏的微环境中, IL-2、IL-4、IL-5、IL-13因子上升,MSCs表面的IL-4细胞因子受体与IL-4结合,通过相应的细胞通路,产生TGF-β,与相应的免疫细胞结合,导致IL-4的含量下调,恢复免疫平衡。同样的,MSCs还能上调Th1型细胞免疫应答,使IL-10和IFN-γ水平上调,产生拮抗作用。并且,其组织修复、迁移以及免疫调节功能在实验中都得到了相当正面的反馈。
5 小结与展望
尽管脂肪来源的MSCs治疗AR已经在动物实验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被证实为有效的治疗方式,但至今仍然没有临床实验研究结果。现阶段,MSCs几乎都是在体外环境下培养增殖的,而不是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这可能会在实际应用时产生不同的影响,MSCs的生物学特性或许也会发生改变[73]。脂肪是属于个体比较容易获取的来源,培养方法和繁殖水平也相对容易,提取也较骨髓更为方便,细胞丰度也更大,将来在临床实验上可能获得更多的考虑和关注。
本文收集的数据主要是使用脂肪来源的MSCs在动物体内进行的实验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从理论上来说,对难以治愈的AR患者来说,这可能是新的治疗方向,是新的治愈希望。从治疗的安全性上来说,脂肪组织中存在大量的间充质细胞,并且在体外培养时,能迅速增殖,这就减少了染色质变异的可能性。在实验研究上,也暂时没有发现其导致肿瘤发生的现象,但是人体内相关的实验研究仍然匮乏,并不能因此认为脂肪来源的MSCs不会导致肿瘤的发生。Neri等[74]的研究表示,脂肪来源的MSCs具有一定的遗传稳定性,比骨髓来源的MSCs更安全。
近年来,有关MSCs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的研究越来越多,有相当的文献研究表明,EVs可能具有与MSCs类似的免疫调节特性。外泌体是由质膜直接向外发芽产生的,其产生微囊泡、微颗粒和直径约为50 nm至1 μm的尺寸范围的大囊泡,外泌体起源于内体,直径为40~160 nm(平均约100 nm)[75-76]。MSCs衍生的外泌体于2010年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小鼠模型中首次进行了研究[77],后续在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癌症和免疫系统疾病中都有相应的应用[78]。Zhao等[79]的研究提示脂肪来源的MSC-EVs可从脂肪来源MSCs内转移至巨噬细胞,与其结合,诱导M2型巨噬细胞极化,从而缓解炎症反应的发生。Dong等[80]的发现则证明,对类固醇抵抗的哮喘小鼠使用MSC-EVs,可以逆转气道的高反应性,减轻炎症反应。郭瑞敏等[81]对MSC-EVs治疗呼吸系统相关疾病的研究中,提出雾化、滴鼻使用,能更直接让MSC-EVs到达呼吸道,发挥归巢、免疫调节功能。应用EVs治疗AR的实验研究现在极少,但这不失为更进一步的选择,EVs的制备比起MSCs更复杂,但它的使用也更为安全和简单,无需考虑MSCs异常增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而且EVs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相对较少,也无法直接形成肿瘤[78],最近的研究表明[82],MSCs衍生的外泌体正是诱导外周耐受和调节免疫反应的有效细胞器。将其作为AR治疗的新策略,则需要更多的实验支持。
在各种呼吸道病毒传播的流行中,控制AR患者的症状,能减少呼吸道病毒的传播。Gani等[83-84]表明,虽然过敏不是新冠病毒发病的危险因素,但仍建议在COVID-19的流行期间,对AR患者加强管理,以降低传播感染的风险。应对儿童AR患者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接种,构建群体免疫屏障[85]。控制AR患者的发病症状,甚至治愈AR,在现在,在未来,都是迫切的。希望有更多更细致的实验,能为AR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笔者认为,使用脂肪来源的MSCs来干预,是治疗AR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