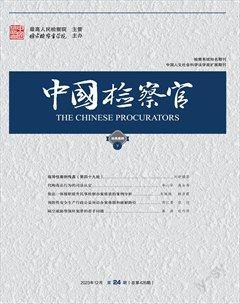盗骗交织案件中处分意识的认定思路
李璐 刘通 马殿峰
一、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某古玩店购买银元。被害人孙某先后取出5枚民国三年和3枚民国七年的银元放在柜台上供张某挑选。店主介绍,民国三年银元每枚价格为1100元起,民国七年银元每枚价格为3400元起。犯罪嫌疑人张某挑选了2枚民国三年的银元,与店主商定交易价格为2300元,并支付给店主2300元。后犯罪嫌疑人趁店主不注意,迅速将2枚民国三年的银元调换成2枚民国七年的银元,并向店主展示后放入口袋。因民国三年、民国七年银元外观相似,不仔细甄别无法辨出,店主对放在柜台上剩余银元特征未在意,在查看柜台上剩余银元数量无误后,将剩余银元放回柜台内。犯罪嫌疑人得手借故离开。后被害人在向下一位顾客展示银元时,发现银元被调包,遂报案。
犯罪嫌疑人张某于次日被抓获归案,被调包的2枚银元被追回。经查,张某曾犯诈骗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经价格认定,被调包的2枚民国七年银元价值人民币7200元。
二、分歧意见
本案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以张某涉嫌盗窃罪移送审查起诉。公安机关认定的盗窃数额为4900元(被调包的银元价值减去已支付的钱款)。在审查起诉期间,办案组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但对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产生分歧。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构成盗窃罪。该意见认为,本案虽然存在“骗”的成分,但被害人并没有基于错误认识而产生交付意思。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主要是“偷”,而不是“骗”。因此,应认定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因犯罪数额未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1],不构成犯罪。一是被害人具有处分意识。本案被害人仅在被处分银元的年份上有错误认识,不影响其处分意识的认定。二是被害人陷入了认识错误。行为人利用先支付低价银元价款,后调包为高价银元的方式,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物。
三、评析意见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针对同类商品的调包行为,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意识,处分意识如何认定。在本案处理意见上,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一)本案被害人缺少与行为人之间的意志交互
本案属于典型的盗骗交织案件。笔者认为,只有从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上加以区分,才能准确定性。盗窃罪是行为人不经过被害人同意,单方违背被害人意志获取财物的行为,惯常作案手段是秘密窃取。诈骗罪是行为人通过与被害人言语沟通交流获取财物,行为方式是对被害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意识。处分意识是指处分人认识到将自己占有的财物或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给对方占有或享有[2]。笔者认为,在理解处分意识时,可以通过行为人与被害人是否有“意志交互”或“意思互动”(本文统称“意志交互”)加以判断。
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经由与被害人的意思互动,促使其产生针对财产决策的认识错误,在优势认知的支配下取得被害人交付的财产[3]。因此,意志交互是被害人产生处分意识的前提。通过有无意志交互,可以形成易于判断的区分标准:在盗窃罪的情形下,被害人的意志不在场,犯罪由行为人单方面完成;在诈骗罪的情形下,双方形成了意志交互,被害人在行為人的诱导下“自愿”向行为人转移财物,从外观看是一种“合意”行为[4]。
结合本案,行为人在购买银元过程中,一直有与被害人语言沟通交流行为,甚至在调包银元后还向被害人展示,这些行为是否可以认定被害人具有处分意识呢?答案是否定的。实践中,并非只要行为人与被害人有沟通,就认定为有意志交互,还要从沟通行为能否影响或加深被害人处分意识上加以区别。本案中,行为人虽与被害人有沟通行为,但其沟通目的是通过向被害人支付低价值的银元价款,让被害人降低防范意识,通过掩饰以达到其窃取高价值银元的目的。因此,本案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欠缺意志交互,被害人没有处分意识。
(二)本案被害人对被处置的特定财物没有认识
通过考察意志交互,有利于判断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意识,同时,也有利于从处分意识的构成要素上对本案的定性加以判断。认识因素是处分意识的核心构成要素。但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认识因素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尤其对被处分财物的种类、数量、价值是否需要具有完全认识,观点不一。本案中被害人认识到处分的是同类商品,是否具有处分意识?
有观点认为,只要认识到将某种财产转移给行为人,不要求对财产的数量、价格等具有完全认识。[5] 处分人对所处分的财物数量或价值评估错误,不会影响其实施处分行为。[6]上述观点在相机调包案的2个案例中得以体现。案例一:行为人在一个照相机的盒子里装入两个照相机,店员只收取了一个照相机货款的,认为店员对照相机的数量有错误认识,不影响处分意识。案例二:行为人将照相机放入方便面箱子里,店员只收了方便面货款,认为店员没有认识到处分财物中有照相机,不具有处分意识。[7]
通过上述观点及案例指引,本案被害人认识到处分的是同类银元商品,似乎具有处分意识。但笔者对上述处分意识的审查思路并不认同。首先,从意志交互上看,行为人无论将相机装在另一台相机盒子里,还是放在方便面箱子里,都是通过物理操控实施,其付款时并未通过意志交互使营业员产生交付意识。其次,从被害人认识因素上看,上述两个案例中的营业员对行为人调包后的相机都没有认识。我们不能因相机被放入盒子或箱子的外观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难免会陷入了逻辑不能自恰的境地。笔者认为,针对同类商品调包行为仍要坚持客观主义立场,对处分意识中的认识因素作限缩解释:
第一,对被处分财物的“量”产生错误认识,阻却处分意识。即被害人只有认识到被处分同类财物的具体数量时,才具有处分意识。在此,不能将认识因素人为扩大化,对于被害人压根没有认识到的同类财物,强加解释为有处分意识。最高人民法院27号指导案例也持相同观点[8]。回到本案,行为人将2枚低价银元调包为2枚高价银元,被害人在处分财物的“量”上没有错误认识,是否具有处分意识,还要进一步在处分财物“质”上加以判断。
第二,对被处分财物的“质”产生错误认识,也阻却处分意识。即在判断认识因素时,将认识对象限缩为特定物,认识到处分的是此物而非彼物,这样才能符合司法期待。本案被害人虽然对处分银元的数量没有错误认识,但由于行为人的调包行为,对被调包后的高价银元没有认识。无认识,则无意识。因此,本案被害人没有处分意识。
综上,本案被害人既未与行为人产生意志交互,亦未认识到被处分的是高价银元。因此,本案被害人不具有处分意识,行为人应认定为盗窃罪。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三)建议建立递进式的处分意识类案审查思路
前文所述,针对本案的定性认识,应从处分意识有无上加以区分。本案对处分意识的审查思路,可为盗骗交织类案提供借鉴。笔者主张针对盗骗交织案件中的处分意识构建递进式的审查思路:
首先,要看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有沟通交流行为。诈骗罪通过与被害人意志交互,“说服”其主动交付财物。因此,通过行为人与被害人是否有沟通,可将大部分调包案件准确定性。例如,本院辦理的另一起调包案件,王某某系某加油站“汽车之家”的厨师,趁工作便利,多次将摆放在货架上的白酒饮用,事后将灌满自来水的空酒瓶重新放回货架。该案行为人也采用了以水换酒的调包行为,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沟通行为,被害人也不可能产生错误认识,应直接认定为盗窃罪。
其次,要看被害人是否因意志交互而陷入交付财物的认识错误。盗骗交织的案件,事后被害人都感觉被骗了,似乎都产生了认识错误,但有些认识错误并非因行为人意志交互引起的。比如,做法调包案中,行为人为被害人做法,让被害人将现金放入倒扣的乌盆内,待次日才可打开。被害人等次日打开乌盆后,发现钱款早在做法时被行为人调包为白纸。这个案件中,行为人也与被害人沟通了,但取财时显然是在被害人意志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并未对被害人交付财物的意识产生影响。因此,应认定为盗窃罪。
最后,通过认识因素的客观标准对处分意识检验回溯。某些盗骗交织案件中的欺骗性要素较强,通过意志交互无法简单区分,需要进一步通过认识因素对处分意识是否存在进行检验。如前文所述,认识因素应坚持客观立场,即将认识对象限缩为特定财物。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客观判断标准,会导致实践中通过技术手段改变过磅重量的案件统一认定为盗窃罪,与以往司法实践判例认定的诈骗罪不符。其实不然,在通过技术手段改变过磅重量的案件中,被害人虽对交付货物的重量产生错误认识,但这种错误认识不属于交付意识的错误认识,被害人知道交付货物的全貌,知道处分的是哪些财物,对处分“量”上没有认识错误,仍然具有交付意识,应认定诈骗罪。
由此,对盗骗交织案件审查判断思路是:第一步,要看行为人获取财物是通过与被害人沟通交流,还是通过物理操控转移实现;第二步,要看被害人是否因意志交互而陷入交付财物的认识错误;第三步,通过认识因素的客观标准对是否存在处分意识检验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