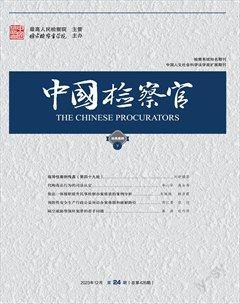人身检查措施的违法性认定与适用原则
李继华 王兴周 杜同舟
摘 要:人身检查是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刑事案件证人是否可以作为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以及男工作人员能否作为检查妇女身体的适格主体,是侦查监督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证人可以成为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从保护妇女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将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3款规定的“妇女的身体”限缩解释为妇女身体的隐私部位,因而男工作人员对妇女的非隐私部位进行人身检查不具有违法性,但应遵循关联性原则、有限同意原则与身份区分原则。
关键词:人身检查 目的性限缩解释 主体对象 适用原则
人身检查对查清案件的性质、犯罪的手段和方法,作案所用的工具及犯罪的情节,从而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查明犯罪人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法要求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检查,即贯彻同性别保护原则。然而实务中由男侦查人员对妇女进行人身检查的情况并不鲜见,从而产生其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的违法性认定问题。
一、人身检查措施的违法性认定争议
[基本案情]2023年3月某日凌晨,犯罪嫌疑人王某与情人陈某乙(女)的哥哥陈某甲因琐事发生纠纷,持菜刀将陈某甲砍伤致死,陈某乙系现场目击证人。两名民警在案发现场楼道处用棉签提取陈某乙面部他人溅射血迹一处,在陈某乙手指甲提取拭子一枚,用采血卡在陈某乙手指提取血迹一份。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发现对陈某乙进行人身检查的两名民警均为男性。
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本案中,两名男性民警在陈某乙的面部、手部提取生物样本的行为是否违法存在争议。争议焦点可概况为两点:其一,证人是否可以作为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其二,男工作人员能否在特定情形下成为妇女人身检查的适格主体。
二、证人可以成为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
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外,证人能否作为人身检查措施的适格对象,是本案中侦查行为是否违法的争议问题之一。有观点认为人身检查的适用对象应限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不得对其他人采取[1];亦有观点赞同人身检查的对象包括证人[2]。笔者认为,证人亦应属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
(一)符合条文目的
就刑事诉讼法第132条作字面理解,“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系不包括对象限定语的目的性表述。换言之,即凡利于该目的实现,证人亦不为法律所排除适用。本案中因陈某乙的体表留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生物样本而对其进行身体检查即为适例。
(二)符合条文逻辑
刑事诉讼法第128条为“勘验、检查的范围”,该条规定了检查的范围涵盖“与犯罪有关的……人身”,并未限定人身的主体范围。刑事诉讼法第128条与第132条属于“总-分”逻辑关系,前条文效力及于后条文,将证人作为人身检查的对象,符合刑事诉讼法条文逻辑。
(三)符合客观需求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实务中,侦查机关对目击证人进行身体检查的现象并不鲜见,其目的在于通过人身检查全面收集证据,迅速侦破案件。立法者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选择中持动态平衡的观点。证人对于侦查机关发现客观真实意义重大,同样负有接受人身检查等侦查措施在内的容忍义务,只是对其可采取的人身检查种类与强制程度均明显低于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从陈某乙体表提取的生物样本能够帮助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伤情、生理特征及状态,故对其采取人身检查措施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1款之规定,陈某乙系人身检查措施的适格对象。
三、男工作人员特定情形下可作为妇女人身检查的适格主体
从立法目的和司法实际出发,男工作人员在一定条件下应当被允许作为妇女人身检查的适格主体,但应限缩解释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3款中“身体”概念的外延,补充隐私部位的界定,从而准确贯彻刑事诉讼人身检查过程中的同性别保护原则。
(一)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3款作目的性限缩解释的合理性
法律实施离不开法律解释。面对丰富多彩的司法实践,对法律条文作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作处理结果符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解释,是司法机关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应然选择。目的性限缩解释作为一种法律漏洞补充方法,指依法条之文义已涵盖某一事实类型,但依立法目的,该类型本不应包括在内,于是将该类型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积极地将不合规范意旨部分予以剔除。[3]换言之,目的性限缩的适用前提是法律条文可预测的理解范围过广、涵摄面过大而形成法律漏洞,导致对个案判断违背常理。在前述案例中,立足司法实际和常理常情,将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3款中“妇女的身体”限缩解释为妇女身体的隐私部位,并进一步将概念外延界定为阴部、胸部、臀部、腰部、大腿等人们通常认为的隐私部位符合本法条保护妇女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立法目的。
在法律适用技术层面,司法机关在个案中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具有实务可行性,且有其先例可循。在2020年王某非法交易费氏牡丹鹦鹉一案中,交易标的虽为禁止交易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涉案30只鹦鹉系由人工繁育,总价不过几百元,若对法律进行字面的文义解释,预期刑罚将高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悖于立法目的。經审慎调研论证,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认为王某等的行为未实际侵害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或造成濒危野生动物被侵害的风险,决定对王某等人作不起诉处理。[4]检察机关在该案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出罪处理,正是运用了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即在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过程中排除了已被广泛人工繁育的费氏鹦鹉。案件处理结果顺应了民众对法律的朴素认知与期待,真正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实质价值层面,通过目的性限缩解释对男工作人员检查妇女身体非隐私部位的行为作出合法认定符合比例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3款体现了对妇女人身权利、人格尊严等法益的特殊保护,其实现路径是以降低侦查效率为代价,对男工作人员实施人身检查的职权范围作出额外限制。依据通说,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与相称性[5],而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亦不外于比例原则之调整范畴。笔者认为,在人身检查制度现有规范基础上作“身体”表述的目的性限缩解释,可以兼顾妇女人身权益与侦查效率:其一,从实然法角度考察,现有人身检查制度中已有相当数量的程序性规范,制约机制较为完善。譬如人身检查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侦查部门负责,检查人员必须持有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强制检查应当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检查的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检查的侦查人员、检查人员、被检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被检查人员拒绝签名的,侦查人员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等等。其二,依照社会通常观念,在履行充分告知、说明并取得妇女同意后,依照流程检查其日常裸露的非隐私身体部位,即使由男工作人员实施,也不存在妇女性自主权等权益受损的风险,因而不具有违法性。其三,以触碰、目视妇女身体隐私部位为手段的人身检查措施,不论是否系强制检查,其实施主体一律排除男工作人员,能够最大限度避免男工作人员介入引发的妇女人身权利风险。本案中,两名男工作人员从女性面部和手指采集标本的行为,如果机械地认定为违法,则有违立法目的,也难以被社会公众所接受。
(二)男工作人员特定情形下作为适格主体系客观需要
在侦查实务中,男工作人员对妇女身体进行人身检查多系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变通措施。公安机关作为采取人身检查的首要主体,女性工作人员比例长期偏低。截至2021年初,全国200万公安民警中,女性人数不足29万,仅占队伍总数的14.3%。[6]加上女性更易被分配于行政或内勤类岗位上的现实情况,可资调配于实施人身检查的女工作人员更是寥寥无几。譬如在深夜时段、地点偏远的时空环境下,若现场情形具有立即检查妇女身体的紧急必要性,安排女工作人员可能存在现实困难。因此,有必要重新划分人身检查中男工作人员的职权边界。
应当注意的是,人身检查主体的职权边界划分应当始终以同性别保护为原则,男工作人员介入应被视为紧急必要性情形下的例外做法。即凡具备女工作人员或医师能够参与的客观条件,则应由其实施,从而最大限度尊重妇女意愿、争取积极配合。从刑事诉讼法第132条释义看,“必要性”可与该条第2款强制检查“必要的时候”做类似理解,即若不进行人身检查,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紧急性”则应主要指两种情况,其一是涉及可能对被检查人或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危险物品,如体腔内部的爆炸物、毒物等;其二是人身检查所涉及的证据可能由于时间推移、被检查人行为等情况而存在灭失风险。综上,紧急必要原则能够在同性别保护女性权利的基础上兼顾侦查便利需求,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四、准确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32条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为确保刑事诉讼法第132条关于人身检查措施的法律正确实施,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侦查机关采取人身检查措施应当确立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关联性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的关联性应当理解为与案件事实的关系。证据具备关联性是其具有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人身检查措施同样应当秉持关联性原则。《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2条规定,证据是否相关,取决于以下两个标准:“(a)该证据具有与没有该证据相比,使得某事实更可能存在或者更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趋向;并且(b)该事实对于确定诉讼具有重要意义。”[7]该规定对于我国人身检查制度贯彻关联性原则、明确具体适用标准而言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遵循关联性原则,人身检查措施的检查主体、受检对象、检查目的及必要手段等问题,均可得到妥善回应。
(二)有限同意原则
从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2款规定来看,“犯罪嫌疑人拒绝检查”以及“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为采取强制检查的条件,而依照相关释义,侦查人员在此之前必须首先问明原因,向其讲明检查的目的、意义,让其接受检查,如果犯罪嫌疑人经教育仍拒绝检查的,侦查人员才可适用强制手段。此外,本款规定的“必要的时候”是指不进行强制检查,人身检查的任务无法完成,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而经教育,犯罪嫌疑人仍拒不接受检查等。[8]因此,不论作为人身检查对象的妇女在案件中居于何种身份地位,侦查人员均应当事先向其告知检查目的、部位与手段。不论是否采取强制手段,人身检查均应当以取得妇女同意为原则,这是妇女权利特别保护在立法层面的直接体现。
但是,有限同意原则也应当在人身检查中得到遵循,即妇女接受人身检查的容忍授权必须具有客观限度。一方面,侦查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进行强制检查;另一方面,即使妇女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也不得作为男工作人员检查其隐私部位的正当性理由。原因有二:其一,侦查活动不得有伤风化、违背公序良俗。由于医师普遍在长期医学教育中建立起了“去性化”的人体抽象认知,其自身性别不为职业所考量,因此我国并未在人身检查措施中限制医师性别。然而,无医学专业背景的普通男性侦查人员检查妇女隐私部位,不论是否得到婦女本人授权,均有悖于社会基本伦理之嫌,其行为本身足以在客观上构成《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99条所禁止的“贬低其名誉、人格的方法”或第200条同样禁止的“有伤风化的行为”,遑论其间存在个别不法分子通过诱骗、恐吓取得妇女同意,假借职权行为二次侵犯人身权利的潜在风险。其二,男工作人员检查妇女身体隐私部位有损社会公众对公权力行为的合理信赖。若允许男性工作人员对妇女采取直接涉及身体隐私部位的职权行为,一旦面临相关控告、申诉将难以自证清白,公权力机关将同样面临舆论压力,由此得出的检查结论亦难免面临“毒树之果”之质疑。综上,在人身检查过程中遵循有限同意原则,不仅是对妇女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侦查机关公信力的保护,更是对在案证据合法性的保护。
(三)身份区分原则
依据被检查人在案件中的身份地位不同,以全面性、层次性的梯度化规范分别明确各自的容忍义务,以及所对应的可采取手段类型与强制程度,是检察机关准确认定人身检查措施是否具有违法性的必要前提。考察现行法律法规文义,犯罪嫌疑人为明确可以强制检查的对象;被害人的容忍义务仅见于部分实务界观点;证人的容忍义务则归于空白。域外立法多较为详备,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1c条第2款规定,“对被指控人以外的其他人员,如果对健康无不利之虞且措施为查清真相不可避免,准许不经受检查者同意,进行确定血统的检查和抽取血样”[9]。可见,德国不仅严格区分被检查人的身份,还对被指控人以外的其他人员设定了明确具体的人身检查容忍义务。因此,我们可立足本土国情,参照域外立法,在制定法层面增加被检查人身份的区分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