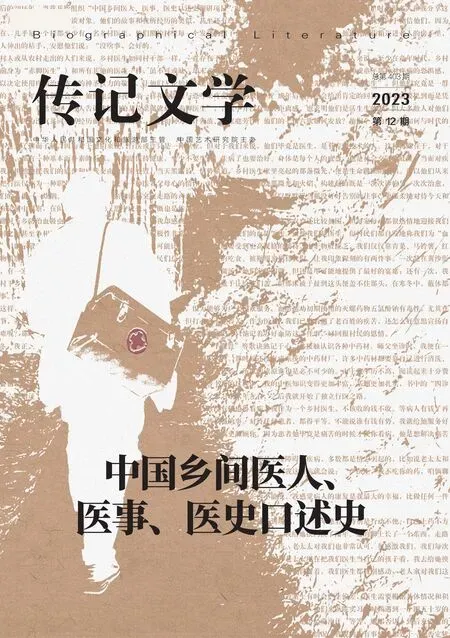我的西南联大研究
李光荣

我研究西南联大四十余年,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有人要我交流一下经验,我也有一些能够认识到的不足,归结一下,或许对己对人都有些好处。虽然我的研究仍在继续,所说并不是经验的全部,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若有方家见此指点迷津,不是求之不得吗?于是写下这些文字——
蒙自时期
1977 年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机,也使我站在了学术跑道的预备区。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考上了昆明师范学院即今云南师范大学。1978 年2 月报到,在入学教育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新名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师院的前身是西南联大,1946 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为北大、清华、南开大学,把所属师范学院留给了云南,独立为昆明师范学院,院址即在原西南联大新校舍。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上学时,校园仍保留着西南联大的格局。在学校里我们时常听到西南联大的故事,有时还会去故事的发生地玄想一番。我们的宿舍在校园东北角当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办公室的位置,记得曾任西南联大助教的陈晓华教授跟我们住在一层楼,我们每天都会从他家门前走过。下楼往西,路北是“四烈士”陵园,路南是西南联大的教室,再往前路北的食堂仍在西南联大学生食堂原来的位置。过了食堂就是那条贯通学校南北的大路,南头是师生出入学校必经的大门,北头是跑警报到后山去躲避的后门。汪曾祺写《新校舍》就是沿着这条路写两边的。路西当年的运动场和学生宿舍变成了我们的教室、系办公室、图书馆、篮排球场之类。我们天天行走在西南联大师生曾经走过的路上,沐浴在西南联大的文化氛围里。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多位老师曾是西南联大人:王彦铭、陈晓华、彭允中、母履和、熊朝隽等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前两位还曾做过西南联大的助教。其他老师或多或少也都与西南联大有关,如刘正强老师是西南联大学生王瑶先生的硕士。刚从“文革”过来的老师们,在课堂上绝口不谈自己的经历,不谈西南联大,但他们的精神气质、言谈举止、学问态度、讲课风格等都透露出西南联大的品质,每堂课下来,同学都有一种餍足感。文化的传承大概就是这样,观摩也是一种教育,即梅贻琦提倡的“从游”法。学生在与老师的接触中能够感受到西南联大的学风。
此外,我们小组的卫生区域是“四烈士”陵园,闻一多衣冠冢也在其中。我们每周末打扫这个区域,用流行的话说,是与闻一多、“四烈士”对话,是致敬“一二·一”运动。这也是西南联大的文化熏染。四年下来,打扫了多少次却没有统计过。
西南联大曾掩埋于历史尘埃许多年,但西南联大已深深印在我的心上,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或许也是学术研究的源泉。
1982 年1 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蒙自师范专科学校即今红河学院任教。蒙自师专在南湖北岸,紧邻老城南门。中文系老师吴敏、杨显川了解蒙自历史,我听他们说起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便去探访故迹。又听外语系老师鲍秉全说美国学者易社强先生(John Israel)来考察过蒙自分校故址,这给我较大刺激。我那时认为,中国的历史自己没弄清,却由外国人来搞有伤自尊。于是,我更为自觉地寻找蒙自分校事迹,考察了海关大院、东方汇理银行、哥胪士洋行、周家大院等,这些地方有的已经荒废破败,有的依然在为人所用。
1984 年我讲“中国现代文学”和“大学语文”课程,开始组织学生参观蒙自分校旧址,讲述有关故事,同时继续调查分校事迹,上图书馆查找资料。几年间,蒙自、个旧、建水、石屏、开远的图书馆,我都访了个遍。
1992 年编辑《西南联大在蒙自》一书,是我西南联大研究的一个重要历程。蒙自老人卜兴纯先生约请分校师生写纪念文章,收到稿件后,却因年高体弱不能操觚,于是委托我全权编辑。我仔细研读全部书稿,对蒙自分校获得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提升了原有的一些认知。同时,我补充了一些材料,如《陈寅恪诗》三首和《刘兆吉采风诗》六首等,撰写了史料文章《关于今天的报告》向分校师生说明当时的情况,其他还做了编辑的工作。
《关于今天的报告》是我研究西南联大的第一篇文章,也是研究蒙自分校较早的文章之一,除分校师生的回忆文章述及蒙自分校外,作为研究者的文章,是王云、易社强之后的第三篇。无疑,在蒙自分校和西南联大研究史上,已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1993 年3 月发表的《陈寅恪南湖诗》是我的第一篇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的小文。别人回忆文章提到的多为陈寅恪“崧岛上作”、刘文典书帖的《蒙自南湖诗》,小文则讨论了陈寅恪的一组南湖诗,视界较宽,认识独立,标志着我专论西南联大文学的开端。还有几篇文章刊登于《云南日报》《云南民族报》上,署名为“李光嵘”。
我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3 期上的《南湖诗社》一文更具学术性。文章考察南湖诗社的历史面貌,评价其诗歌成就,肯定其培养人才的功绩,指出其文学史位置,基本说清了南湖诗社的历史、贡献与地位,是最早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论文,在西南联大校友中引起一定反响。文章奠定了我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的基础,开创了我从文学社团入手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的道路。
1995 年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文艺报》举行征文活动,我写了《“听风楼”情思》投去,刊登于该报5月27日。这是最早以“听风楼”为题讲蒙自分校故事的文章,把蒙自分校听风楼传得更远。如今听风楼已是参观蒙自分校的一个景点。
1993 年5 月至1994 年5 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樊骏老师门下访学。之前我曾拜访了钱理群老师,他鼓励我研究西南联大文学。樊老师去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会,他俩谈起我的研究方向,樊老师曾看过我包括《南湖诗社》的几篇习作,也有这个意向。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只能等我访学回去再开始研究,在这里一时找不到资料,他同意了。蒙自的资料我已摸清,要开拓研究只有到西南联大校本部所在地昆明才能进行。因此,回到蒙自后,我经过两年的努力,于1996 年8 月调入云南师范大学。
昆明时期
到一个新的单位,首先得适应环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写其他论文,在西南联大研究方面无所建树。大约2000 年前我开始作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方面,以闻一多为突破口。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此前没做过。研究必须从资料做起,且全面的资料建设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学术机制不允许我慢慢地做。我觉得必须找到一个口子进去,逐步扩大方能收效,于是决定从闻一多研究入手。闻一多是西南联大师生中得到最多研究的人。虽然研究者多取革命政治角度,但有的材料可以通用,或者可以从中获得研究文学的线索。我入手不久就发现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价值,并由此拓展到闻一多的戏剧活动研究。学者都是带着自己的学养与审美眼光进行研究的。我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曹禺戏剧和哈尼族文学,在文学、戏剧和民族文化方面有些知识积累,所以能在别人不太注意的地方看出价值、产生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我写出《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春天》一文,分析了闻一多在昆明从事戏剧活动的原因、作出的贡献,描述了闻一多的戏剧家形象。接着,我发表了《彝族歌舞与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彝族歌舞与闻一多〈悬解〉的诞生》,前一篇主要考证“彝族音乐舞踊会”对《〈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创作的影响,揭示闻一多歌舞剧本的独特性,用的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后一篇说明《〈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创作动因来自彝族民间歌舞,主要用历史方法,仅三千字。接着,我又写了《闻一多在昆明的戏剧活动》《闻一多的戏剧活动对当今戏剧创作的启示》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开拓意义得到学界的重视,《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春天》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舞台艺术》2002 年第2 期全文转载;《彝族歌舞与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一文2004 年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闻一多基金会于2009 年奖励了我在闻一多戏剧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
文化的存在状态盘根错节,必须掌握多个方面才能写出局部甚或某一点。我在闻一多的戏剧方面有点突破,是以研究闻一多性格为前提的。《闻一多的艺术家气质及其兼政经历》《闻一多的人性救国思想及其实践》《蛮性:救治现代柔弱人性的灵丹——论曹禺和闻一多戏剧合作的基点》等文章就是在研究闻一多思想和性格方面的努力。不过,这类文章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大注意。
第二方面,从闻一多拓展开去。闻一多以外,由于没有材料的支撑,仍然只有小感触,我发表短文作为学术积累。这些小文章中,《西南联大的五月四日》较为重要。文章通过西南联大在每年5 月4 日这一天的活动考察,说明“五四”精神是西南联大的文化血统。本文奠定了我研究西南联大的一个基本思想,坚持至今。文章发表后得到西南联大校友们的肯定,2008 年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庆祝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收入了本文,而该书较少收研究者的文章。影响较大的还有一篇《西南联大的南湖倩影》,把蒙自南湖给予师生的温暖和师生为南湖增添的文化内涵揭示了出来。文章发表后,受到读者尤其蒙自文化界的热评。后来,关于蒙自文化的多本图书收录了本文,有部电视片以本文为结构主干,解说语言则照搬本文的文字,蒙自分校师生的诗被写上南湖湖心亭内壁,也与本文提供的认识作用分不开。
如果说我在蒙自时期的研究路线是由小到大(由小题材写短文到大题材写长文)的话,这时则是大小结合,根据材料决定文章的容量与篇幅。此后CSSCI 评价体系得以推行,大块文章成为趋势,我也走在这条道路上。了解西南联大的人都知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很重要,其文言语句和所用典故却难以读懂,于是我边学边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评注》,对《碑文》逐字逐词逐句作解析,又对其主旨内容、思想感情作了评述,发表后成为年轻人理解《碑文》的助手。沿着《西南联大的五月四日》的思路,我写了《西南联大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传统》,考察西南联大文学的精神渊源,论说西南联大文学是“‘五四’文化血统”在文学中的显现。
这时学界对外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评价较高,我把论文投往韩国,从2005 年开始在《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第9、11、13 辑先后发表了《抗战文学的别一种风姿——论西南联大文学》《联大剧团及其戏剧演出》《西南联大剧艺社始末》三文,都是两万字以上的长文,把西南联大文学艺术推向国外。
第三方面,争取项目支持。没有项目,就没有资金;没有项目和资金,就没有时间保障;项目、资金、时间联系在一起,没有它们,研究就会困难重重。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后,我开始申报项目。
2003 年,我申请到项目“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这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我把已经准备好的其他论题写完后,便投入课题研究。首先是上图书馆,把昆明各大图书馆的目录查阅一遍,然后按照线索借报刊图书来阅读。由于不知道查找目标及其所在刊物,进度缓慢,收效甚微。我苦涩地戏称这种方法为“大海捞针法”,但也别无他法。而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不知笔名,无法判断某篇文章是谁写的,有的从内容上看应属西南联大人所写,却不敢断定,读了一份报纸没发现几篇西南联大的作品。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找到文学当事人和知情者。
2004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在徐州召开,主题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我参加了这组的讨论,从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一些教益。理事会结束,我立即北上北京,主要目的是拜访西南联大校友。两个多月,我访问了几十位校友和校友子女,获得了许多东西,如作品、笔名、线索、他人的联系方式、报刊未载的情况等,我收获巨大,喜出望外。这又一次证明了西南联大研究从民间做起的规律。回来后,我一方面根据校友提供的联系方式,扩大对外地校友的咨询;另一方面再次扎进图书馆,把以前读过的报刊读一遍。图书馆闭馆,则整理材料,准备写论文。
这时,我已有了总体认识,我把西南联大文学史分为早中后三期,写成《西南联大的早期文学社团》《西南联大的中期文学社团》《西南联大的后期文学社团》三文,投《新文学史料》,后刊于2005 年第3 期、第4 期和2006 年第1 期,一家刊物连续三期刊发同一作者的系列论文,实属不易。我将论文寄北京和云南的西南联大校友会,他们找了十几位专家校友审阅,都给予肯定,我十分高兴。王景山的鉴定写道:“我反复拜读了李光荣先生的三篇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文章,深感这不仅是有关史料搜索、整理的可喜成果,同时也是对之进行分析、评论的学术性著作,我非常佩服……”鉴定意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写作的底气更足了。这组文章是我研究的“纲领性”成果,阐述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基本面貌、历史分期、成就地位等问题,写各文学社团便是按照这组文章的思想和路子进行的。
这组文章的成功和校友会的肯定与帮助,使我产生出把结项形式由系列论文改为专著,以全面系统地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想法,便向国家社科办提出申请,而没要求增加经费,同时延长结项时间。当然获批了。有朋友不理解,而对于我来说,不是为了完成项目,而是真正作西南联大的研究,希望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成果,回报西南联大。
成都时期
2005 年,我调到西南民族大学工作。成都离西南联大所在地远了,查阅资料不便,关注西南联大的人少,西南联大研究的气氛也冷清了。这是我研究的不利条件,可以说是我离开昆明失去的东西。但成都是一个包容的城市,研究者自由选择研究对象,不但不限制,而且都给予支持,西南民大的学术空气浓厚,大家都干着自己的事情,对工作有一种积极热情的态度,能相互鼓励肯定。就这样,我在成都研究西南联大心情是愉快的。由于我有较足够的资料准备,思考问题较为成熟,成果产出较多。
我一边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一边作研究。我沿着昆明的路子,主要作了三方面的研究:文学项目、闻一多、文学创作。这个分类不合逻辑,只是为了集中内容表达方便罢了。
第一方面,文学项目研究。国家项目“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随我转来成都。结项的阶段性成果有《高原文艺社始末及其意义》《〈凯旋〉:影响最大的反内战广场剧》《冬青文艺社及其史事辨正》《穆旦在文聚社的散文创作》《冬青社的小说创作》等。结项时间是2008 年6 月,可临到时间,汶川发生了强烈地震,成都受到严重影响,余震不断,这期间大家都不敢待在家中,而我却整天坐在屋里改书稿。我不是不怕,而是为了守时。有时被余震惊吓,跑出去舒缓一下再回屋。我体验了一个多月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的紧张生活。我曾把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写入结项书的“后记”,由于不想以此博取评审专家的同情,最终删去了。
结项不是我研究的终点,终点是弄清西南联大的成就。结项后,我还继续发表了《南荒文艺社:一个被历史遗落的社团》《中国现代文学的劲旅——文聚社》《〈文聚〉封面、目录和版权页》等一些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论文。
2015 年我再次获批国家项目“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编目索引与综合研究”,发表了阶段性成果《杜运燮:“飞虎”翻译与“机场诗歌”》《作家汪曾祺的由来》《论穆旦的诗体贡献》《冯至〈招魂〉诗的创作、发表与版本考》《陈铨在西南联大的剧作及〈野玫瑰〉的演出与争论》《汪曾祺的大学生活与西南联大书写》。项目于2020 年顺利通过结项。
之后,我协助闻黎明先生申请到国家重大项目“西南联大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并承担一个子课题。此外,我还作过一些校级、省级和部级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项目。我把爱好与项目挂钩,把项目当学术来作,因此,快乐大于艰辛。这也是我的一点项目经验吧。
第二方面,闻一多研究。继续昆明的闻一多戏剧研究,我发表了《西南戏剧劲旅——论抗战时期的联大剧团》《闻一多昆明时期的戏剧思想》等文章,保持着创新性。
我在成都开发的是闻一多的诗歌研究。诗歌本是闻一多研究的热门话题,但集中于他的新格律诗及其理论,而对他后来的诗歌活动与思想却有所疏漏。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探讨:1.《闻一多南京时期的诗歌贡献》认为闻一多南京时期的诗歌没显示出独特性,可以看作他北京时期的继续;2.《西南联大与我国朗诵诗的中兴》涉及闻一多对昆明的朗诵诗运动所作贡献:培育了西南联大朗诵诗,推动形成昆明的朗诵诗规模,中兴了我国的朗诵诗运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8 年第1 期作了摘录;3.《何谓“全新的诗”?——闻一多的朗诵诗理论试探》首次把闻一多的朗诵诗理论概括为态度上的人民立场、功能上的团结战斗、艺术上的综合运用、风格上的雅俗共赏四个方面,认为这是闻一多对朗诵诗理论的独特贡献;4.《西南联大的朗诵诗观念——从闻一多到朱自清和李广田》把西南联大的朗诵诗观念归纳为新体的诗、今天的诗、“我们”的诗、综合的诗、有力的诗、行动的诗,认为这是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共同完成的朗诵诗理论,具有自足性,这套理论是中国朗诵诗理论的精髓,达到了40 年代的理论高点,可以代表中国朗诵诗理论的最高成就。
第三方面,文学创作研究。在当今的学术体制下,开拓一个新领域,不可能全部弄明白了再动笔,往往是边进入边认识,研究成果由零碎开始,凑少成多,逐渐积累,达到整体认识,再由整体回望局部,这时就相对从容一些了。我那时仍然没有整体的写作计划,只知道朝着研究目标前进,但也可以分为作家作品和综合两个方面。
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我发表的文章相对多些,最初是介绍湘黔滇旅行收获的《刘兆吉及其〈西南采风录〉》,接着是一组写汪曾祺小说佚文的文章《〈钓〉:汪曾祺的文学开端》《汪曾祺初期小说四篇》《当年习作不寻常——汪曾祺初期小说校读札记》,然后是讨论穆旦书写亲历缅甸抗战的《“化入树干而滋生”——论穆旦的抗战》,最后是研究朱自清、沈从文的长篇论文《朱自清先生在昆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还有一篇对非作家梅贻琦的研究《论梅贻琦的美育思想》,意在从校方的层面认识西南联大文艺为何取得辉煌业绩,论述了梅贻琦对西南联大文艺活动与创作的重视,此前发表的《民族原生态歌舞首登中国现代大舞台》就已涉及他支持闻一多、王松声等举办彝族音乐舞踊会,由此说明西南联大文艺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取得的成就卓著,是师生苦心孤诣的创造与努力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校方与师生的“共谋”。可见,文学研究还需注意文学之外的因素。
综合的研究如考察地方文化与学院文学双向互动的《西南联大文学与云南地方文化》、讨论西南联大文学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提供因素的《试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论述西南联大文学地位的《中国校园文学的一座高峰——论西南联大学生创作》、提出研究西南联大文学新思路的《民国文学观念与西南联大研究新视角》、指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特色的《文学抗战的艺术呈现——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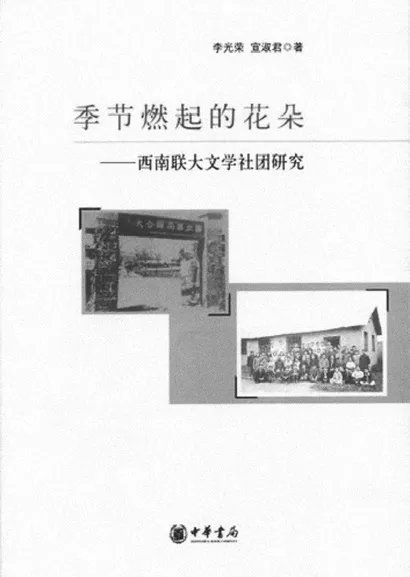
李光荣、宣淑君:《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在综合研究中,不能不提到我的七本专著和两本作品编辑:1.《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与宣淑君合著;2.《语言文学大师风采》,与宣淑君合著;3.《民国校园文学高峰——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及其创作初论》,与宣淑君合著;4.《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5.《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6.《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季节燃起的花朵》增订本);7.《西南联大艺术历程》。还编辑了两本作品集:《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汪曾祺全集·小说卷(一)》。我还在《云南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文艺报》《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

李光荣:《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西南联大艺术历程》
我的不足主要是无法组织研究团队,因此无法完成大的选题;研究进度越来越慢,设想的著作没全部实现。
综上所述,我的西南联大研究奠基于昆明,开始于蒙自,发展于昆明,成熟于成都。现在,云南师大聘我为特聘教授,我以另一种形式回昆明继续研究西南联大,为的是回馈母校和故乡云南。
我四十岁时曾对西南联大前辈表示:“把后半生献给西南联大。”二十五年来,我排除困难、不畏险阻,孜孜以求地追求,出版了九本书,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五十多岁时,我警告自己:非西南联大的文章不写。我以弘扬西南联大精神为目的,写的都是严肃的论文,且多有创新开拓,从未想过以西南联大故事扬名赚钱。现在可以向西南联大前辈汇报:我没辜负你们的希望与重托。在总结研究过程的此刻,我要感谢樊骏和钱理群老师,张中良和李怡学友,周锦荪、王景山、刘晶雯、卜兴纯等前辈,需感谢的人太多,恕不一一列名。我仍在继续努力,为彰显西南联大业绩,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