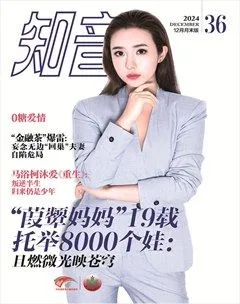匪夷所思:我不能参加姥姥的葬礼?
最亲的姥姥去世了,父亲却禁止她参加葬礼,只因父亲认为,姥姥对她而言是外人。以下,是杨弃知的自述……
不该来的葬礼
三月六日下午,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医生说,你姥姥……你姥姥快不行了。”电话那头,她泣不成声,“我们正准备把她送回老家,你要不要来见最后一面?”
“我要去。”
母亲的问题有些奇怪,但我来不及思考,便毫不犹豫地回答。
挂了电话,我立刻开始收拾东西,搭上姨夫的车准备回家。在这期间,父亲发来一条消息,嘱咐我不要回去。
我追问一句为什么,他却没有回复。我心想,或许他是和母亲一样,担心影响我学习。然而这是最后一面,无论如何,我一定得回去。
回老家的路程并不遥远,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姥爷颤颤巍巍地下了车,急急地就要往村口赶,我们扶住他,站在路边等候。不一会儿,救护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姥爷喃喃地说了一句:“来了。”
屋内的灵床已经布置好了,我们把姥姥推进去,舅舅将她连同着床铺一起抱到灵床上。不知过了多久,长辈们叫我们进去“喊魂”。众人乌泱泱地在床前跪下,我跪在人群中间,听着四周哭声渐起,泪水突然就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姥姥真的走了。
无意间,我瞥到父亲也到了,站在人群后面做完了仪式。结束后,舅母招呼着我们先吃点东西垫肚子,我走过去问他要不要盛一碗粥。
他面色不佳,但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就扭过头去了。我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在这种场合,大家心情都不太好。
然而过了一个小时,父亲突然把我叫出去,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
“你为什么要来呢?明明都跟你说了不要来。”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为什么不能来呢?姥姥去世了呀。”
“那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擅自来到这里,奶奶很生气?”
父亲说:“你来见姥姥最后一面,后面就得跟着参加葬礼,把姥姥送走。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这里都是讲究内外区分的,姥姥就是我们的外家人。你来参加葬礼,第一,对你不吉利;第二,对奶奶很不尊敬。”
尽管他没有详细解释,但我还是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作为“外人”,我来参加葬礼不仅容易招致不吉利的事情,还伤害了“自家”奶奶的面子。
可这种观念本来就是错误的,我气血上涌,想也不想便顶撞道:“姥姥也是我们的亲人,这种观念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父亲冷静地看着我,说:“别管它平不平等,大家都是这么讲究的,如果不遵守,就会惹上一身麻烦。”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这并不是我们家第一次在“内外区分”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了。
早在去年年底,姥姥就住院了,母亲经常去医院照顾她。然而父亲却对此感到不满,每次母亲从医院回来,他都冷着一张脸,不说话也不看她,自顾自地把碗筷撞得乒乒乓乓响,两人没少因此吵架。
父亲不允许我和弟弟去医院探视,理由是“快过年了,老跑医院不吉利”。
有一次,父亲直接挑明了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照顾姥姥应该是几个舅舅的责任,不关母亲的事情。
母亲气急了,撂下狠话,说:“你最好保佑自己的父母永远不要生病。”
由于畏惧父亲生气,也担心加剧家里紧张的气氛,后来我真的不怎么再去医院。一直到姥姥转院,我才去探望了她三次。
这样的父亲令我有些陌生。因为在我的认知里,父母关系很好。我没料到在这件事情上,父亲会这么敏感。
被排除的女人们
虽然母亲觉得,是父亲把她的父母当作外人,但在我看来,母亲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有些举棋不定。
姥姥得的是肺炎,为了方便,在离家最近的社区医院里治疗。母亲好几次忧虑地跟我说,这家医院比较小,病房都是空的,也没给姥姥做什么治疗,就是挂水而已,她担心医生的水平不行。
我便向医生朋友咨询,得到的回复是:“老人家年纪太大了,县城医院医生的临床经验不一定够,建议转至上级医院。”
然而母亲却有些犹豫,不是说“太远了”,就是说“没有认识的人”。在我三番五次追问下,她终于说出了真实的想法。
“我是没权力做决定的,要让他们(舅舅们)做决定。”
我不太认同。这么多年来,都是母亲带姥姥和姥爷做体检的,按理来说,她应该最了解姥姥的身体状况。况且,在治病这件事上,舅舅们明显不太愿意管。
小舅舅比较依赖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很少自己下决定。大舅舅当惯了甩手掌柜,之前办理住院时,母亲忙着帮姥姥收拾东西,要他先去医院办理。然而她敲了许久的门,大舅舅才走出来,说自己不懂怎么做,要母亲收拾完带着姥姥一起去办。
我向母亲建议:“既然你意识到了医院这个问题,就应该主动提出来。”
“这不行。”母亲辩解道,“换医院是大事,我去提意见,别人会说我嫁出去了还指手画脚,不行不行。”
后来我趁探望姥姥的时候,鼓起勇气和舅舅们说过几次,但他们没有太在意我的话,“如果这个医院治不了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转院的。”
我那时也深受“内外区分”观念的影响,担心作为外孙女,给太多意见会令人不喜,渐渐地也闭口不谈了。
直到最后一段时间,姥姥的病情突然恶化,舅舅和母亲才连夜将她送到市里的医院,姥姥立马就被转到重症监护室里。
医生责怪我们送得太晚了,县里的医疗技术太落后,没有足够的资源给姥姥上监护设备,当地的医生也过于疏忽,最终延误了病情。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逐渐发现,连母亲也被姥姥的葬礼排斥在外。按照当地的风俗,参加葬礼的宾客在离开之前,必须用柳叶沾水轻点全身各个部位,以驱逐“不详的气息”。我原以为只有外来的宾客才需要如此,后来才发现母亲和我也要这样做,而母亲的堂哥,也就是姥爷的侄子却不用遵循这种规矩。
“不是说,姥爷的侄子已经很多年没有和家里联系了吗?”我悄悄地问母亲。
她含糊地说:“那也是姥姥的侄子,不管过了多少年,都可以算是他们的自家人。”
“但你是她的女儿呀。”我在心里替母亲不平,明明是至亲的血脉,却还比不上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亲戚。
在头七出殡的时候,这种排斥更加明显。按照传统,出殡当天,逝者的子孙后辈需要守在灵堂里。我却被告知需要像其他宾客一样,在旁边的会客厅里等候主家邀请,才能进入灵堂。
时辰就要到了,有人来“请”我们过去。
我抢先站起来,走在队伍的前头。到了灵堂,水晶棺摆在正中央,两位舅舅和表哥们披着麻衣,一脸肃容地跪在旁边,后面跟着哭红了双眼的表妹。我心里有些酸涩,找了一个不被人遮挡的位置,端端正正地对着姥姥的遗照磕头。
“主家”很快向我们回礼,大舅舅跪下来磕头,其他人跟着跪下来。一磕一叩之间,主和客的身份被划分得清清楚楚。
复杂的滋味从我的心底漫上来。
一直以来,姥姥都很照顾我。小时候,爸妈忙不过来,她也曾带过我一段时间。长大了,我去外地上学,每学期开学之前,她都会塞一千块钱给我,让我好好读书。
有段时间我的身体比较虚弱,她总去药店买药,要我带到学校里。她是母亲的血脉至亲,是我们的家人,到最后我却只能以客人的身份与她道别。
让女儿仍然是女儿
从葬礼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会胃疼到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为什么当初我没有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无数次地假想过,假如我没有听父亲的,坚持去医院探望姥姥,是不是最后的离别就没有那么仓促;假如我再大胆一点,向舅舅们多提醒几次,姥姥的病情需要重视,是不是结果会有所不同?
我试图给自己找理由,什么没有经验啦、与舅舅们不亲近啦、他们觉得你还小啦等等,都无法完全说服自己。
最终,我不得不承认,那时的我过于懦弱,屈服在“内外区分”观念之下。
我不敢挑战父亲的权威,不敢打破“姥姥姥爷是你的外人”这个观念,甚至用它来麻痹自己:毕竟你只是外孙女,你的话他们也不会太在意。
上大学之后,很多人半开玩笑地对我父母说:“养女儿最没用了,学历这么高,以后不还是别人家的人。”
这种话像是调侃,但折射出来的观念却不得不让我警惕:似乎每个人都默认了我会与原生家庭切除联系,成为一个“外人”。
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天我的父母生病了,我却不能出钱带他们看病,又或者我也做不了主,只能听从弟弟的决定,不敢针对父母的病情发表一点意见……类似的悲剧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我绝不想让它再次重演。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获得原生家庭的支持。考虑到父亲以往的固执,我想先争取母亲的同意,从小的问题开始探探她的态度。我以为经历姥姥的事情,她会更理解我,没想到她意料之外地表示了反对。
我们坐在床上闲聊时,我状似轻松地问她,结婚后能不能回家过年。母亲一下子坐直了,瞪大了眼睛着急地说:“不行啊,不行。”
我有些震惊,脱口而出问:“为什么呢?”
“你这样不给男人留面子。”她苦口婆心地劝道,“在我们这里,过年回娘家是会被嘲笑的,大家会说你们的感情不好。”
第一次试探不欢而散。我没有放弃,变着法子表明我的态度。
有天晚上,一位亲戚来我家做客,开玩笑地说我以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母亲还笑着点头附和。
放在以往,我可能低头笑笑就过去了。但那天我没打算顺从,便抱住母亲的手臂,大声说:“现在都不流行这种说法了,即使结婚也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小家庭。”
众人哈哈大笑,也就把这个话题揭过去了。事后,我对母亲说,要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平等的观念,不要把我让给别人。母亲不以为意,嗤笑道:“等你结婚就明白了,到时候你就做不了主了。”
父亲的态度同样复杂,他自然不会希望我与他们切断联系,但他似乎有些不确定。有一次,当我提起“别人家的人”这个话题时,他没有直接表明态度,而是说:“关键得看你立不立得住,能不能自己拿捏主意。”
从他们的话语里,我提炼出了两个字:能力。我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所以他们不确定我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确定我有没有做主的能力。
可是为什么,我需要这么努力,才能维持我和父母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呢?
我最终没能说服他们。
姥姥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看到奶奶板着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客厅里的灯光很暗,她的下巴紧绷着。听到声响,她抬起眼看着我,问我为什么要去葬礼。
进家门之前,父亲叮嘱我要道歉,但我原本就做好了硬碰硬的准备,于是直截了当地说:“姥姥去世了,这是我能见的最后一面了。”
奶奶沉默了一会,没有我预料中的激烈反应,而是说:“我会准备一些仪式,保佑你不受侵扰,平平安安地生活。”
她放软了声音,问道:“饿了吗,我煮了面,要不要吃一点。”
那一刻,我真切地意识到,站在我面前和我观念相悖的,是朴素爱着我的亲人,只是几十年来形成的认知实在难以改变。
我一时有些怔愣,感到心情复杂。他们不是我真正的敌人,糟粕观念才是。我放弃硬碰硬的想法,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能找到温和而坚定的解决方法。
让女儿仍然是父母的女儿,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编辑/杨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