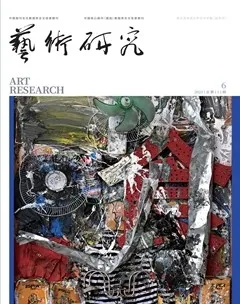浅析达玛鼓的渊源及其文化属性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刘浩世
达玛鼓是我国青藏高原地区藏族传统音乐中的一种演奏乐器,是作为一种有别于古代地方宫廷、藏传佛教寺院和民间其他鼓器乐形式的,具有中亚地区器乐艺术风格的棰击膜鸣乐器。本文通过浅析达玛鼓的渊源及其文化属性,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达玛鼓的多元文化语境。
一、达玛鼓的形制及其演奏
达玛鼓,也被称为噶阿,是流传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种多棰击膜鸣的打击乐器,流行于我国西藏的拉萨、日喀则、昌都,以及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巴塘等藏族文化圈内,多被使用在地方宫廷歌舞乐队和藏传佛教寺院仪式音乐中,并且是作为一种特殊乐器而使用。
(一)形制
达玛鼓整体形状呈圆锥状,上大下小,像一个口小肚子大的罐子。从外观来看,达玛鼓的上部分是鼓体直径的最大部分,口沿顶部鼓口的位置部分是向内收的一个状态,呈现出鼓碗口部分小于鼓的上半部身。其上端鼓面蒙以牦牛皮,鼓面蒙皮的时间一般选择的是藏历九月(公历十月),这个时间段的牦牛长得最为肥壮,身上的皮质状态也是最好的。
达玛鼓一般有两种规格,一大一小:大的达玛鼓被称为达玛切,或者也被称为雄达玛,按照音域也被称为低音达玛;小的达玛鼓被称为达玛穷,或者也被称为雌达玛,按照音域也被称为高音达玛。达玛鼓属于无固定音的高膜鸣乐器,音量洪大,音色明亮,穿透力非常强,大小两鼓的音高一般保持在五度的关系。
(二)演奏场域
达玛鼓在藏族文化圈内,其演奏场域比较特殊,主要是用于在古代宫廷噶尔巴乐队伴奏宫廷歌舞,或者是在迎送达赖喇嘛的时候演奏,还有就是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举行传召大法会、迎请强巴佛等礼仪、寺院仪式歌舞羌姆中被使用,在藏戏中也有达玛鼓的伴奏,但一般的藏族民间传统歌舞中看不到达玛鼓的伴奏。
(三)演奏姿势

达玛鼓的演奏姿势分为两种:坐着演奏和边走边演奏。坐着演奏时,一般是在室内或者园林中,演奏者大多席地而坐,或者是坐在卡垫上,随着乐曲的进行,需要伴奏时击棰鼓面;边走边演奏是在户外行奏,这种演奏情况一般是达赖喇嘛远巡举行迎送仪式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演奏姿势有多种,比如将一对大小达玛鼓分别放在马背的左右两侧,演奏者可以选择骑在马上击棰敲击,也可以选择一个人背着两个大小达玛鼓走在前,演奏者在其身后击棰敲击演奏。
二、达玛鼓的渊源
(一)达玛鼓的考古渊源辨析
在青藏高原地区,鼓是作为承载着具有古老而历史的一种象征性符号意义而使用的,达玛鼓不同于青藏高原地区本土的其他鼓形式,其外形与形式(锥形高低音的一对对鼓)更像是一种外来文化在本土碰撞、融合、新生后的产物。举例来说,其在“寺院乐器所含佛法内涵和象征性意义以及音乐性程度”①上,是作为一种具有一般象征性意义而言的演奏乐器,而不是作为一种法器使用而言,这代表达玛鼓并非是属于传统意义中的一种附有文化隐喻的符号而言,而是一种新生的外来者,虽然这个外来者是已经扎根在本土了,但是其相比作为一种本土宇宙体系的文化价值的载体——法器而言,更适宜作为一种实际演奏的具有功能性的乐器。
作为一种锥形高低音的对鼓,达玛鼓从外形、音色、形制等方面来看,与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的代表乐器纳格拉(Nagela)鼓相似度很高,并且达玛鼓所使用的鼓棒不同于西藏传统乐器的那些鼓所使用的鼓槌弓形状,其鼓槌是直棒形的。据了解,纳格拉鼓是从古代中亚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新疆的伊斯兰乐器,约在公元9 世纪之后成为维吾尔族的打击乐器。青藏高原地处中亚、南亚、东亚等各路文化的交接点,古代文明的几个发源地均处在西藏的周边地带,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西藏传统音乐文化受到周边地区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可知纳格拉鼓最早出现在古波斯,“随着伊斯兰教‘圣教’广为流传,在各地形成不同的变化,与当地文化结合形成各自的特点”。②
在公元7—9世纪之间,吐蕃与大食存在一定的交流,且当时处于伊斯兰教的兴起与东传,纳格拉鼓作为伊斯兰文化中的军乐器乐被吐蕃认识和推测是极有可能的。但9 世纪中叶后,吐蕃王朝在内外矛盾中崩溃,从公元869年到1239年的370年中,处于史籍中被称为分裂割据时期的混乱时代,吐蕃与大食的正常交流都存在状况,在此时间内纳格拉鼓的传播至西藏地区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二)达玛鼓的名称渊源辨析
达玛鼓这个名称,是根据音译而来的,藏语中也被称为“噶阿”。在藏语中鼓被称为“阿”,所以按照这个逻辑,达玛鼓应该是“达玛阿”,但是其被称为“噶阿”,所以“噶”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根据《藏汉大词典》中对“噶”的解释“噶”字在藏语中作为单独一个字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和别的词组在一起时才具有意义:“基本字义:1.〔~伦〕中国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2.〔~厦〕藏语“发布命令的机关”,即中国原西藏地方政府,由噶伦四人组成,1959年后解散;3.译音字。详细字义:译音用字。如:噶布伦,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萨噶达娃节(藏族地区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噶厦(xià)(原西藏地方政府,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解散)。”③
从“噶”的字义中可以推出一个浅显的结论,达玛鼓被称为“噶阿”,是作为译音用字组合而成的一种特定指代词,是特指,具有特定指代物体。“噶阿”作为达玛鼓的特指代词,可以简单的推论出几点:
1.“噶阿”是在短时间内被单独赋予的一种称谓,这种称谓并不是指的考释、隶定和叙述它本意的字母意思,而是说它已被吸纳到藏族本土宇宙观的视野中来,被组织到本土化的文化叙述中去,从而剥离出它原有的知识背景,被重新认识、观察、构想和阐释。而这种“采撷的过程”并非“约定俗成”,多由具有强制性力量的上层建筑操作的意味。
2.“噶阿”这种称谓在当时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背景中处于精英阶层,一般的普通大众对于这种带有政治性的价值观念的产物还处在迟滞状态,对于其中经过观察、剪裁和修饰后的阐释有种陌生感。但不熟悉并不代表无意义,任何经由人工的称谓本身就携带了人的想法,从17 世纪至今延续下来的称谓,既是历史话语的重构,也是从对这个称谓陌生到熟悉、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样态。
另一方面,达玛,在藏语中意为“跑马射箭”,并且也是西藏江孜地区独有的一种节日,这种节日是17 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统辖全藏后,西藏地方政府委派僧俗官员在江孜宗本主持的节日活动。而达玛鼓的演奏形式中的一种是被放置在马背的左右两侧,演奏者骑在马上击槌演奏。据悉“纳格拉鼓曾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军乐”④,是随军在马背上演奏的乐器,达玛鼓作为纳格拉鼓的变体形式的乐器,与流传在新疆地区的纳格拉鼓形式相比,更接近于伊斯兰细密画中的形制。
一般而言,文化的交流和互渗是缓慢和零星的,但一旦本土宇宙观的世界视野拓宽必然引起文化交融与冲突,而在这种文化交融和冲突下则必然导致思想世界的变化,其中各种外来资源变成了本土宇宙世界观自我调整的契机。以一种鼓的名字为节日名,并且这种乐器是马背上可携带演奏的乐器,其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同,那么可以从某一方面推测出,达玛鼓是通过等级或者秩序来作为一种权力的基本结构的携带载体。从中可以推测出达玛鼓传入西藏地区并非是从下而上,而是从上而下的一种较为“垂直”的传播方式。达玛鼓作为古代地方宫廷乐舞的伴奏总领乐器,是在17 世纪之后的时候才被称为“噶阿”,作为一种进入到藏文化当中,以一种平等权力的物质力量在等级社会层面上的一种表现,体现这种异域文化体系所代表的上层建筑对于当时的藏族文化体系而言,是平级,甚至是处于一种威胁的等级体系的表达:

1.14世纪的时候,与西藏地区相邻的克什米尔伊斯兰化;
2.16世纪末或17 世纪初的时候,伊斯兰化的巴尔蒂王入侵西藏阿里地区的拉达克王国,俘虏了拉达克王并娶了拉达克王的女儿,此时的拉达克王国成为了巴尔蒂(汉书史籍称为“大勃律”)王的附属国;
3.“17 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时期拉萨再度复兴为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⑤
4.“伊斯兰教在卫藏地区的可考历史是从五世达赖喇嘛(17世纪)开始的”。⑥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粗浅地推出以下结论:
1.西藏地区在9世纪末经历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其地方稳定性、经济水平、军事力量等都不复以往,与此同时,伊斯兰文化东扩逼近西藏地区甚至内部思想世界,对于本土宇宙世界观的固有思想世界形成一种交流、渗透或者说是威胁的程度,其中的某些资源具有超越本土性功能权力的时候,本土宇宙世界观会将其进行吸纳、吞噬甚至解构后再度阐释,瓦解其中的外来文化的意识形态,削弱其中的异域思想,将其“话语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来摄取、融解。
2.“达玛”意为“跑马射箭”,作为鼓的前缀形容语代表着这种鼓极有可能原本是使用在马上的,并且这种鼓本体的应用空间的特殊性与其代表的一种攻击性。这种空间性与攻击性混合形成的“视觉”冲击了西藏本土宇宙世界的观念和思想的领域,以致在进入西藏本土宇宙文化之后其原本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的观念仍残留些许,从中可以窥见其原本的叙述背景。
3.达玛鼓从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文化传入西藏的途径是由克什米尔地区至阿里地区,然后至卫藏地区,并不是从新疆地区或者印度地区传入的。
4.达玛鼓作为纳格拉鼓的一种伊斯兰文化载体的乐器,传入西藏地区成为一种较为熟悉的器乐推测约为16 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

三、达玛鼓的文化属性
“纳格拉鼓广泛地分布于西亚、中亚、北非等非伊斯兰地区,被众多的穆斯林民族所使用”。⑦达玛鼓作为纳格拉鼓的一种变体,却被使用在古代西藏地方宫廷歌舞、藏传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等非伊斯兰属性中,文化决定属性,达玛鼓作为一种遵照藏族文化逻辑并被本土化的伊斯兰文化载体,从某一侧面证明了文化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外来的物品,发现原本从未想象过的满足需要的多种可能性,并且进行“修正”,以适应不同的现存观念和社会体系。
(一)鼓面制作
达玛鼓这类膜鸣乐器主要是以膜震动的方式来作为发声,鼓身只起到共鸣作用,所以对于鼓面蒙皮的制作会比乐器其他部分更为讲究,这种制作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文化属性的“构拟”或“重建”。
从远古时代的高原西部岩画中的牦牛图像到民族创世神话中的牦牛化世界,再到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希荣仲孜(牦牛舞)”,无不显示出牦牛是独属于生活于这片高原地区人们的动物崇拜。从古代藏族先民的心灵世界的物化,到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离不开牦牛全身的物质化利用,对于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来说,牦牛是无可取代的。所以从达玛鼓的制作来看,采用牦牛皮而不是其他动物皮作为达玛鼓最重要的鼓面,反映的是藏民族的这个游牧文化,是青藏高原牧民们对自身生存环境、自然现象的关注和认识,不仅记录其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种踪迹,表达其思想感情的产物,并且也是对其民族文化有偏向的价值确认。
(二)演奏姿势及场合
1.姿势
从某一程度上来说文化属性是赋予每种生活方式来作为它的特征的某些属性。相似的物质生产方式对于文化的认同与思考在某些方面会趋于一致性,纳格拉鼓作为一种应用在马上的“军乐”乐器,其到了经济形态是游牧生活为主要之一的青藏高原地区,相似的物质生产下的这种实体化了的精神生产保留部分程度上的共鸣,使得达玛鼓演奏姿式中也有在马上演奏。与此同时,达玛鼓除去静坐演奏外还有人背着达玛鼓走在前,演奏者在其身后击棰敲击演奏的姿势,这种演奏姿势是古代封建社会时期“政教合一”僧侣集团意识形态的统治标志的一个侧面,它历经明清,达到极盛时期,最后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中走向灭亡,是特定时代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生产关系的缩影。
2.场合
与纳格拉格演奏场域还有婚庆、娱乐场合伴奏所不同的是,达玛鼓在藏族文化中多被使用在较为严肃或正式的场合,例如应用在古代地方宫廷歌舞“噶尔”乐舞场合中,利用其乐器本身的宏大声响和极强的穿透力,来作为王权的非壮丽无以重威形式,并且以伴奏为总领,负责总领与其他乐器联接唱句,使“噶尔”宫廷乐舞在整体形式上结构严谨,华丽工整。这种演奏场合的变化,表明了达玛鼓这种人世间的欢快心音成为了礼仪性的典重主调,成为一种存在于藏文化秩序设定的尺度和形式之中的“噶阿”。
(三)音乐本体
达玛鼓在西藏本土宇宙世界观中的结构位置,就像文化秩序一样,会对其的认知与重构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是因为这种再生产使其形成于另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关系之中,这种生产使其改变了文化“语言”,造成新的交流形式、使用语境、价值需求和诠释语言,形成一种适应本土宇宙世界观的分化。其音乐本体在这种分化下形成一种三维合成结构:声音—概念—行为。
1.声音
达玛鼓的声音相对西藏传统乐器中的其他鼓来说略不同,其音色主要来自于膜振动,使用高原独有的牦牛皮所蒙的鼓面在直鼓槌的敲击下泛音很密,筒体共鸣使得音色清晰明丽,借助筒腔内空气反作用能够传至很远。这种声音不同于其他鼓的声音,是外显与内隐的秩序和文化的替代性概念所形成的具有“异域的想象”的视觉印象、听觉联想与象征意味。
2.概念
达玛鼓使用的鼓槌非西藏传统乐器中的弓形鼓槌,而是直鼓槌。弓形鼓槌因自身材料和形状等原因使得弹性较好,敲击鼓面时会有类似二次敲击声的微弱回响。达玛鼓使用直鼓槌这种“音乐事象”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人们来说,是另一种音乐语言概念,造成了新的交流形式、使用语境、价值需求和诠释概念形态。
3.行为
从前述演奏场合可知,达玛鼓是作为具有仪式宫廷“噶尔”乐舞引导的音乐行为,负责伴奏乐队中总领其他乐器,在曲式的承转或者舞段变动时,以悠扬平和的鼓声作为提示;在伴宴时,与竖笛配合合奏,则倒握鼓槌清奏鼓面,一来控制鼓自身的音色,二来也是控制乐队整体的音量,使伴宴气氛肃穆柔和,轻奏音乐抒情柔美。并且负责敲击达玛鼓的乐手身份多为管理处秘书或财务处总管等,这种总领其他乐器的音乐行为和乐手具有的社会阶级文化含义的身份代表了达玛鼓在西藏本土宇宙世界观中的结构位置,代表了一种思想、政治要求的音乐行为,是阶级制度规范的艺术表现。
透过达玛鼓鼓面制作、演奏姿势及场合、音乐本体等文化属性的内容,可以窥见在历史演变中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性的西藏社会系统的运作框架与生产方式,并且在这个生产实践过程中,达玛鼓被赋予某种特定的话语权力地位,具有“多价的”或“多功能的”,成为了藏文化体系中“声为律”“身为度”的一种象征属性。
四、结语
他性从阿拉伯半岛途径丝绸之路并行至青藏高原,跨越欧非亚大陆,存在他者自我的聚合体将彼此之间的文化紧密关联,并且这种文化间的高度互动化流变过程也反映了青藏高原古代人民与其他地区跨文化圈的交流,远超过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的想象。达玛鼓作为具有双重属性的符号和标志,即传达了对事物的认知、描述、记叙、表达和理解,也积淀了历史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使得这种具有伊斯兰异域文化“话语”的权力在西藏宇宙世界观中被转构、重新阐释,所形成的文化共识建构出一种知识领域,并且有了超感觉的客观形象和主观感受,而这又使其成为具有精神生产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源泉。
注释:
①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3):10.
②崔斌,杨叶青.纳格拉鼓及其伊斯兰文化渊源[J].西非亚洲,2009(7):71.
③张怡荪.藏汉大词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④张欢,谢万章.丝绸之路上的膜鸣乐器——纳格拉[J].中国音乐(季刊),2014(1):51.
⑤拉萨市情调查组.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⑥周传斌,陈波.伊斯兰教传入西藏考[J].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0(11):110.
⑦崔斌,杨叶青.纳格拉鼓及其伊斯兰文化渊源[J].西非亚洲,2009(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