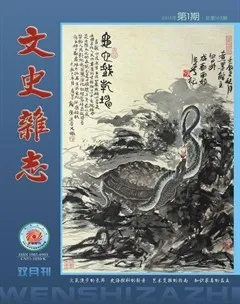真情岁月
陶利辉
摘 要:宋蜀华先生是一位有海归背景、具有深厚人类学素养的知名学者。他的研究方法充满辩证思维,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其精力较多地投放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上,以助力于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他为人宽厚、低调、谦逊,深得同事尊重、学生喜爱。
关键词:中国化;语言天赋;农村公社
1923年6月19日这天,家住成都皇城东侧皮房街的英语教师宋诚之先生的夫人刘芷君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为了让孩子走好未来的路,宋诚之给他取了一个儒雅而不失大气的名字——宋蜀华,期冀孩子长大后能承继巴山蜀水的灵气,在华夏复兴中有所作为。
相识于独到的文章
我与宋蜀华先生(1923—2004)的相识,缘于先生的一篇文章。那是40年前的一个秋天,作为有幸通过高考独木桥踏入大学校园的一分子,对身份变换的激动、对未来前景的期盼、对专业知识的渴求,伴随着满校园《外婆的澎湖湾》歌曲韵律,童年的幻境渐渐远去,青春的梦想在内心疯长,促使自己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除学习必修课外,还开始关注学校的学术动态。因所在的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包含中国史、民族史两个专业,民族研究是特色,我和我的同学们更多关注民族研究方面的动态。也正是这个时候,中国民族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民族学研究》第一至第四集。这些文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短短数年理论研究的精华,里面既有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的力作,也有民族学、人类学界部分青年学者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和历史学紧密结合》的文章引起我的注意。作者不仅阐述了国外民族学研究的各种流派,还通过丰富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国民族志的活化资料,论证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篇署名宋蜀华的文章,置于论文集不太显眼的位置。就当时而言,自己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历史学专业本身——史学情节较重的缘故,对这篇文章情有独钟;到后来才渐渐悟出这篇文章是作者对民族学中国化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国外民族学历史学派研究方法的强力推荐。当然,最初我还不知道作者是学校一位主管科研的副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同时还是一位有海归背景并具有深厚人类学素养的知名学者。
受教于精心的培育
在我上本科阶段,宋先生一直都在校领导任上,同时还受国家推荐应邀担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每年出国参加相关会议较多。虽然从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政策伊始,先生就开始领衔招收研究生,但因没有时间培养,同时用他的话说更怕耽误了学生,故而所招研究生名额都很少,每次只招1—2名。直到1987年,也是我本科毕业那年,先生领衔的导师组才决定招5名研究生。我们从招生简章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奔走相告,决心努力准备,尽量不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跟随先生学习的机会。
尽管招生名额有所增加,但当时报考研究生的难度仍很大。一是我们考先生的研究生属跨系考试,虽然平时历史系的老师都说民族史与民族学差不多,民族学系最早还是从历史系分出去的,但我们学生知晓,两者的研究方法是有差异的;二是先生是很有名气的大家,在民族学、人类学、中国民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史研究领域都受到同行高度尊重,慕名报考的人数不会少,竞争压力会很大。但要就此放弃机会转报其他专业,自己还是不愿意的。我们几位同学于是相互鼓励,相约努力战胜其他竞争者,在导师的研究生团队里胜利会师。结果我们都如愿以偿,成功上岸。当我们在复试环节,介绍我们本科都来自同一个班,并提出先生是否在民族学研究领域特别推崇美国民族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的历史学派时,先生的脸上洋溢出会心的微笑。我想我们当时在场的人都读懂了先生微笑背后的深意,这是在鼓励学生们勇于探索,坚定前行。
大约从1987年开始,宋先生不再兼管学校行政事务,但参与校外的学术活动仍较多。即使这样,先生总要挤出时间给我们上专题课,希望我们在知识结构上能更优秀。他给我们上《社会学调查定量定性分析》,结合自己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滇西的调查,讲解调查方法和调查报告的撰写;给我们讲授古代越人从长江流域出海口到云贵高原再到东南亚的迁徙和文化流变;给我们讲授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农村公社问题以及傣族村社对马克思、恩格斯农村公社理论的实证价值。他还协调王晓义研究员给我们讲授《民族社会学》、陈克进教授讲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语言学家张公谨教授为我们开设傣语,支持我们去听蒙古史专家贾敬颜教授的古典文献学课。
有一次,贾敬颜先生授课讲到高兴处还讲了宋先生一段趣事,说北大教授洪煨莲与我校张锡彤教授当年在北大办了一个专题班,要找一位古文功底深厚的老师去上课。两位老先生权衡后,直接点名让宋先生去上课。当时宋先生还比较年轻,圆满完成了两位老前辈交办的任务,并在多个场合提及洪煨蓮先生点名让他去上课一事,对老前辈的肯定表示感谢。宋先生不仅古文功底好,英语也非常棒,在所参加的国际会议上都能流利地使用英语。记得有一次给我们上课前,他给我们聊起早上外台报道广州一名劫机犯手持木柄手榴弹胁迫飞机改变航向一节。当时我们只能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囫囵吞枣听个大概,而先生却能辨析出木柄手榴弹。先生具有如此高的英语水平除了拥有多年留学背景外,按其爱人黄璞老师的话说,“他特别有语言天赋”。
得益于学养的浸润
1947年至1949年期间,宋先生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厄尔金(A·P·Elkin)教授,对人类学进行了系统研学。按常理,回国后他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人类学开设课程比较完整的高校,从事本专业的教学与科研,而且可把研究点选在东部或中部汉民族居住区,对材料获取和实地考察都会方便很多。但是,宋先生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几起中国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后,毅然将自己的精力比较多地投放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上。他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残存的社会发展形态中,能发现并找到人类社会演进的案例,对研究人类社会早期发展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同时还认为,一个优秀的人类学工作者应当以研究对象的发展为使命,帮助这些研究对象群体发展繁荣进而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这些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由他执笔发表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上的《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制度的初步研究》一文中。
不仅如此,他还十分热衷于向国外介绍中国民族现状和民族研究个案的价值,引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广泛兴趣。1983年,当他在墨西哥大学开展学术交流结束后,该校立即以西班牙文出版他的讲义,给予定名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以此表达对中国民族研究成效的肯定和对宋先生研究观点的赞誉。
宋先生的研究方法充满了辩证思维。他总是立足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内在机理,在观察、分析中注重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实践到理论,引人思考,发人深省。在他参与调研和起草的几个滇西民族社会调查报告中,我们总能读到通过实证揭示的理论方面的内容,让人耳目一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林耀华先生主编并获得中国高等教育教材一等奖的《原始社会史》一书中,宋先生执笔撰写的“农村公社”相关章节,运用大量国内外资料,将人类社会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阶段的农村公社演绎得惟妙惟肖,俨然一幅村社形成、发展、蜕变的生动画卷。宋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文笔洗练,思维缜密,逻辑清晰。他的《百越》一书,论及古代越人的活动时间长、范围广,而全书却不到20万字。他的每篇文章读后都会给人以启迪,但很多文章都控制在数千字。
宋先生虽然学术造诣很高,但为人始终进退有度,谦逊低调。他的一位同事(即曾任翦伯赞秘书的吴恒教授,也是《原始社会史》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常与之搭档组成导师组招研究生)在一次闲聊中非常感慨地对我说:“这么多年,我与老宋没有红过一次脸!”中山大学的人类学老前辈梁钊韬先生去世后,该校人类学方面一时难以物色到比较合适的博士生导师。梁先生的几位博士生经校方推荐来中央民族学院联系指导教师。吴先生在指导其中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时,认为该文涉及荆楚文化,让该生呈宋先生把一下关。事后吴先生碰见宋先生问及此事,宋先生谦虚而风趣地说:“老吴,我已经看过了,我只是把你用铅笔改过的地方用圆珠笔描了一遍。”由此可见,他们作为民族学的老前辈,彼此间是十分尊重和友好的。
宋先生不仅对同事真诚相待,对学生也是严管厚爱,要求学生诚实做人,公道正派,低调谦虚,踏实做事。因此,在他领衔招收的研究生中,无论博士还是硕士,无论后来为省部级干部还是专家教授,大都能从先生的学问和为人中汲取滋养,点亮自己多彩的人生。
宋先生有生之年连续三届担任中国民族学会会长,连续三届担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为推进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进程,为国际社会消除种族歧视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谨以拙作,兹以纪念!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杨筑慧《宋蜀华:师德生辉》一文,部分圖片来源于作者珍藏)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