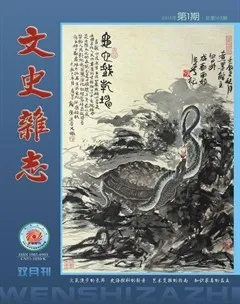试论梁启超的“革命观”
赵栩
摘 要:梁启超通过《释革》完整地建构起他独特的“革命”价值体系,又通过此后多篇文章不断调整其“革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迂回地阐述他的政治理想。他的“革命观”虽然没有落地成为国家和人民最终的选择,但也是晚清“革命”思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改革;变革;暴力革命;政治改良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是胡适为梁启超写的挽联。胡适将梁启超“神州革命”置于其“维新”功绩之前,其意可供深思,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学界、思想界对梁启超在推动“革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之作用的认证。哈佛大学文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教授陈建华是研究梁启超的大家,他这样评价梁氏:“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并使之在中土普及的第一人”[1]。梁启超非常擅长利用逻辑上的论述策略来达到其自身表达核心观点的目的。梁启超发表于戊戌政变失败后的《释革》[2]是其最早诠释“革命”语义的文章,他的“革命观”比较集中体现于这个文本中。所以本文以《释革》为考察中心,兼及《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1913年)等文本,作为突破口,尝试从变与不变的角度对梁氏“革命”观进行考察。
一、“革命”语义在《释革》中生成背景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受到清廷顽固派的血腥镇压,六君子血洒刑场。梁启超逃往日本,继续宣扬其主张。丁文江等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的不少激烈言论,如“中国实舍革命外无法”“所以唤起民族精神,势不得不攻满洲”[3]等。此时期梁启超的思想是比较激进的,他提出的“排满”革命也就是要实行“以种族革命为本位”的彻底改革。此时的梁启超一方面承受“吸国民之膏,吮国民之血”的骂名直面维新变法失败的事实,一腔爱国救国之心不被大众理解;另一方面,梁启超虽接受了日本的许多政治理念,但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感到不满,并迁怒于清廷无能。这时的梁启超感知到“反满”已成大势,内外因交加,令他短暂地站在了“暴力”的一边,希望实行种族革命,彻底地推翻满洲贵族治下的清王朝。此时梁启超的“非理性”因素更占上风;而通观相关史料,当时他在该时期所说的“革命”也只是在“喊口号”,并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
这种激进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很久。作为维新领袖,梁启超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是深远的。他有自身的政治理想和广阔的世界视野。法国大革命的血流成河才不过百年,“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惨烈不是梁氏所愿意看到的。情绪平和之后,梁启超仍要回到他“变革”的路子上来。但是,“变法”的路子在维新时期就已经宣告落败,那如何变更路线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呢?我们知道,梁启超擅长通过论述逻辑和文字策略来表达他的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借势”。当时人逐渐接触到西方历史和文化,看到了英美国家“revolution”的胜利。国内学界、政界、思想界受到日本翻译家的影响,纷纷以“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革命话语成为一时风尚。徐勤(康有为弟子,维新派学人)与康有为通信的函件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虽用语夸张,却也能反映出当时“革命”话语的流行颇盛。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无法抢占阐释“革命”话语的先机,他能做的只有打碎既有阐释逻辑体系,从根本上重塑一套新的“革命”话语,借“革命”之势来阐述自身观点。
于是就有了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释革》一文。文本约三千字,字字有深意。学者羽戈在研究梁启超革命观问题时,曾说《释革》的论述逻辑“有些缠绕不清”[4]。其实不然。文章全文都紧扣“revolution”这个关键词展开论述,草蛇灰线万变不离其宗。同时,梁启超提到在中国文化元典中“革”属于同一个词义领域,无论是“改革”“变革”还是下一步要論述的“革命”都是归属于“革”这个语义场的。在这个语义场当中的各个语词既有着共同的方向,又有着微妙差距。而这微妙差距间,大有可供灵活解读的空间。
二、“革命”语义在《释革》中的衍变过程
要正确认知梁启超的“革命”观,必须看到“革命”语义在梁启超逻辑体系中的衍变过程,通过把握梁氏在《释革》中对“革命”语义的阐释逻辑来把握梁氏对于“革命”的理解和他尝试将“革命”融入自身政治思想体系的深层意义。
《释革》开宗明义,先对“revolution”原有翻译进行推翻。梁氏认为,日本学者将“revolution”翻译成“革命”,“非确译也”。其推翻过程有理有据,条分缕析,设置了顺承递进两个层次的结构对比项。
梁启超对比的第一组语词是“revolution”和“reform”。他认为,“reform”译为“改革”是没有问题的,针对“事物本善”的对象,“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也就是说“改革”意为在原本的基础上后期进行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动作是很温和的,对事物本体不形成伤害。而“revolution”则与之相反,梁启超将其定义为“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是全面改弦更张之举。对应到中文的翻译上,梁启超认为“revolution”应被翻译为“变革”。与“改革”不同,面对事物已经“有害于群、有窒于化”的情况,就要通过更增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今人”(当时的仁人志士)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内部已然产生不可回旋之害的中国。迫于世界大势,梁启超满怀斗志地振臂一呼:“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然后梁氏顺理成章的开始第二层对比,即将“革命”(中文本义)、“revolution”(泰西本义)从意义上区分开来,并论证“revolution”应译作“变革”。
《释革》中提到,在西方的历史中,1688年英国革命、1775年美国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王朝更易从未用“revolution”这一语汇。直到19世纪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之后,“revolution”才被广泛应用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影响。所以可见,“revolution”的泰西本义并不是指王朝更易。而在中国,“革命”一词自封建社会开始就被用于形容以暴易暴的战争,即“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是一种以暴力为形式的政治活动,其目的只是“王朝易姓”,最终不能改变封建王朝的本质。这样的“革命”属于王朝革命,是狭隘而局限的。梁启超认为,19世纪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是将“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囊括入内,并最终改变了英美法德等国的社会性质,使其国力增强——只有这种形式的“revolution”才是其时中国应该效法学习的“别创一新世界”的政治运动;所以将“revolution”翻译为“革命”是错误的。梁启超在解构了“revolution=革命”的陈说之后,终于打出了“变革”的大旗,开始论证其终极命题:“revolution=变革”的逻辑话语体系。
一方面,他通过论证“revolution”并非暴力革命,以劝慰那些正在忧惧“革命”的“仁人君子”(既得利益的统治阶级)。他同时也说,如果“仁人君子”们助推“变革”,国民也应该对统治阶级“优而容之”。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扩大“revolution”(变革)的内容,依托进化论和“优胜劣汰”的原则理论,将社会各个领域包含到他“变革”的事业中去。在《释革》最末一段,梁启超慨然疾呼,中国的国民和君主在国家即将面临“天然淘汰之祸”之时是命运共生的关系,应当同心同德“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
如何实现他所说的这种“变革”?梁啟超并没有给出脉络清晰的路径规划,但通观全文可以总结一二。其《释革》云: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
“变革云者,一国之民,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之,……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
“中国之当大变革者岂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变不得革,又遑论其余哉!”[5]
行文包含了梁启超对他自己建立的“大变革”理论体系的关键解说。他在强调了社会全面革命之后,又将政治领域的革命提了出来,划分清楚了主次关系。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国民在这场“大变革”中的作用,甚至提出“国民革命”的概念来与“王朝革命”的概念相抗衡。这说明此时的梁启超一改维新时期从上而下的“改革思路”,开始重视国民在国家政治变革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他早期的纯粹精英治国、精英救国理念的松动,其对后来“国民革命”思潮全面兴起,当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所体现的“革命观”(实际为“变革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其一,清王朝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这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其二,这个“变革”是循序渐进的,以政界为先,但不能囿于政界,要贯彻到“一切万事万物中”;其三,“变革”不是推翻某姓某族的暴力血腥行动,统治者应当借助国民的力量推动变革,而顺势而为的统治者可以得到国民的宽容和优待。这一系列的“变革”观念共同构建起梁启超中后期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至此,无论梁氏明面上的说法如何变幻,立场如何来回跳转,他的政治观念都可以归纳到《释革》的核心思想中。
三、《释革》与梁启超革命话语体系的生成
在《释革》中,梁启超曾极力论证“revolution”的翻译错误,认为应将“revolution”的中文翻译用“变革”取代“革命”。但此后梁启超的许多文章却采用了“革命”的表述。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年)、《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5年)、《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1906年)、《现政府与革命党》(1907年)、《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1913年)等文。当然,他在不同时期的撰文中所表达的“革命”语义是有变化的。梁启超在变化和反复论证中,最终生成了其“温良渐进”的“革命”话语体系。
在1904年《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梁启超对“革命”进行了重新阐述,用更广义的“革命”来包裹、囊括《释革》中提到的“变革”。文中提到“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表达出他对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革命语义”(指武装及暴力革命)的担忧。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革命语义”将革命指向暴力事件,这在梁启超看来是过于极端的。梁启超觉察到呼吁暴力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宣传鼓励的革命方式极有可能打破平和自由的社会秩序,这与他温良的改革立场是相悖的。他认为,这不仅有害于社会的稳定,甚至有可能使中国陷入另一种维度的混乱中去。
梁启超在1913年《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中,提出了“革命复产革命”这一论断,力陈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成果,并认为暴力革命建立的政体其后也必定会被另一场暴力革命所推翻。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完全放弃通过重塑“革命”语义表达自身政治观念这一路径了。他因为在“革命”和“保皇”之间一度语焉不详,而受到老师康有为的批评。梁启超自己也感觉到其阐述方式在面对社会上已然定型的“革命”语义时显得十分单薄无力。他察觉到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变革观”对扩大其“君主立宪”政治理想效果并不明显。此时他便果断调转枪头,退回到他“改良立宪”的原初立场上来。梁启超重新站到改良派阵前,高呼“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力图引领社会思潮摆脱“革命复革命”的循环怪圈,回到“政治改良”的道路上来。
四、结语
梁启超通过《释革》完整地建构起他独特的“革命”价值体系,又通过此后多篇文章不断调整其“革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迂回地阐述他的政治理想。他的“革命观”虽然没有落地成为国家和人民最终的选择,但也是晚清“革命”思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顾晚清“革命”思潮,我们应当对作为“改良派”梁启超所提出的“革命观”进行重新的反思和价值重估,看到他在推动“革命”现代语义生成方面提供的客观价值。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们对梁启超“革命”观的问题,应当在客观认同其“革命”思想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回到历史现场和相关论述文本,重新认识他的“革命”观所体现的内涵,并对其所显示的现代意义予以重新审视。
注释:
[1]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2000年版。
[2][5]梁启超:《释革》,载于《新民丛报》1902年,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369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页,参见第226页。
[4]羽戈:《梁启超的革命话语》,《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第9期,第123—124页。
作者: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