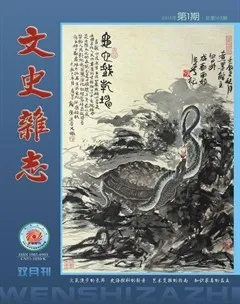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读史方舆纪要》对重庆大足县河流的误载
方珂
摘 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有一些细节错误,如于重庆府大足县河流的记载上。这些错误,当然有迹可溯,顾祖禹采撷前人志书时,未予深究。
关键词:《大足县志》;赤水溪;长桥河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下文简称《纪要》)作为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其山川地理的记载备为详细。但由于历史环境下人们对地理认识的限制,细节上也存在不少脱漏错误之处,后人当不断加以完善。笔者发现其中对重庆府大足县的河流记载有误。
一、问题所在
《纪要》对四川省重庆府大足县的河流记载原文如下:
赤水溪县东六十里。源出安岳县界,流入县境,又东入于涪江[1]。
据大足县方志办编的《大足县志》记载,大足境内有三条主要的河流,一是濑溪河,二是怀(淮)远河,三是窟窿河。[2]而窟窿河在县境西南与濑溪河汇流,实际上是濑溪河的支流(见图一)。濑溪河又称长桥河。据《大足县志》记载,“长桥河”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其自四川安岳县石羊场流入大足县境,自珠溪镇长滩出大足县进入荣昌县,最后在泸州汇入沱江。长桥河上源确在安岳县境,但是其入境后穿县廓而过,并未在“县东六十里”,而且并未“东入于涪江”,因此和《纪要》中“赤水溪”记载不符。那么在“县东六十里”的是哪条河流呢?对比现今的大足县地图[3],在县境东标明有两条较大河流,一条是流沙河,一条是怀远河,两河在雍溪镇汇流,流出县境入铜梁。《民国重修大足县志》中将此两河皆称为沙河,指认为赤水溪,其记载摘略如下:
沙河 旧志一名赤水。源二:一导自玉龙乡,……至雍溪场口与另源之泥河汇。……二导源于石马乡之染房沟名泥河,至雍溪场口汇沙河。以上沙河泥河二水汇流后,至石岭坳入铜梁境,注涪江。[4]
笔者看到《纪要》和民国县志的记载,互有矛盾,若“赤水溪”是“沙河”,那确实符合“在县东六十里”和“入于涪江”,但其不符合“源出安岳县界,流入县境”;若“赤水溪”是指长桥河(现称濑溪河),又不符合在“县东六十里”和“入于涪江”。
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四川通志》和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大足县志》中,“沙河溪”和“赤水溪”都是单独列出,并未并称。那么到底哪条河流是赤水溪呢?雍正《四川通志》下“赤水溪”条的记载如下:
《寰宇记》:赤水源自普州安壁县界来始龙溪,在静南县东七十里。《舆地纪胜》:“赤水溪有马石膏滩,又有玉滩”,《旧志》:“在县东六十里,一名马滩。河源出铜梁六瀛山,南流四十里至普安场,又十五里至沙河溪。其沙河溪在县东南七十五里,源出玉口山石谷,流十五里合赤水溪,又五里至旧州坝,仍北入铜梁县界,盖即始龙溪也”。
清乾隆《大足县志》中的记载与此相同。这样的记载很混乱,天南地北,让人摸不着头脑。既然无法从较近年代的记载中辨明,笔者认为往年代更前的资料继续追溯,将更早的各种舆地记录并列出来,这样或有助进一步分析。
二、资料辨析
那么将各种记载中涉及大足“赤水溪”(包括“长桥河”与“濑溪河”)的记载罗列如下:“赤水溪,经县南,去县九十步”,后文又有“濑波溪,在县南五十步”[5];“赤水溪,源从普州安居县界来”[6];“赤水溪在大足县,其水源自普州安溪县界来”,后文又有“赖婆溪,在县南五十步。源自静南县来,多有石碛,不通舟行。因赖婆村为名,旧为州所理”[7];“玉溪,在大足县赤水……马滩,在大足县赤水溪”[8]。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大多数记载的共同点是赤水溪源头都在普州,即今四川安岳县。那么从地图上追溯自安岳县境内流至大足的河流,可以看出稍具规模,并流经县廓的乃是长桥河(今名濑溪河,参见图一)。
而且清雍正《四川通志》中所载的“长桥河……至县东郭长桥”与1996年编纂的今《大足县志》中记载的“东关大桥位于县城东,原名东郭长桥……跨越濑溪河”[9]是完全对应的。再从另一点看,在今《大足县志》中,记载有“濑溪河据历代史志记载和老船工口碑资料,有马滩、石膏滩(白泥滩)……、玉滩、小滩等滩名”[10],这与上列材料中《舆地纪胜》记载的“赤水溪有马石膏滩,又有玉滩”及《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多有石碛”也是完全能对应的。至此,笔者认为清初以前所称的大足“赤水溪”应当就是清初以后所称的“长桥河”,即穿县城而过而最终进入沱江的现今所称的濑溪河。
为寻找更确凿的证据,在翻阅各种县志的过程中,笔者正巧看到一则材料,即《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所载于乾隆六年(1741年)上任的大足知縣李德的《重修尊经阁记》,其文记载:“学之左,有旧砌而圮,询司铎杨君,曰:‘此昔尊经阁也,自明季而墟矣’。……遂相与即地规制倡修,工不逾年而落成。……肩桂楼、赤水、营山夹辅”[11]。桂楼应是宋明代以来的五桂楼,《舆地纪胜》中记载“五桂楼在正街西”[12];明正德《四川志》亦记载:“(大足)五桂楼在治西。宋乾道间,邑中五人同奏名,太守曹岍建楼以旌之”[13]。这样桂楼无疑是在县治附近,营山是在县城西面;[14]那么“桂楼、赤水、营山夹辅”,可以证实赤水绝不是“县东六十里”的河流,而是县城内的长桥河。
至于县城东六十里的河流,明代以前地理书中未见明确记载,在明代后才出现。其一支称为沙溪(河),另一分支在现地图和志书上称淮远河(民国县志上也称泥河);在大足县雍溪镇两流合并后入铜梁县境,最后进入涪江。《纪要》上的“铜梁县”条下载“涪江。马滩河,在县南五十里。源出大足县界,东流经合滩,有楼滩河来会焉,经县南,而东注于涪江”[15],即为此河。
既然赤水溪就是长桥河,那么《纪要》中的这条关于赤水溪的记载就有几处错误。原文:“赤水溪县东六十里。源出安岳县界,流入县境,又东入于涪江”。首先,赤水溪并未在县东六十里,而是直接穿城而过,出大足后,流向西南入荣昌境,最后在今泸州市龙马潭区胡市镇入沱江;其次,赤水溪并未进入涪江,进入涪江的是县东六十里入铜梁县的那条河流(大足境内称沙溪或淮远河,铜梁境内称马滩河)。
三、本源追溯
这里可追溯一下前人如何对“赤水溪”的地理认知产生错误的。建州之初(唐乾元年间),昌州州治在昌元县(今重庆市荣昌区),而《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昌元县,中。乾元元年与州同置。○濑波溪,在县南五十步”[16],说明昌元县治(昌州州治同在)是在赤水溪(因前文认定赤水溪即为濑溪河)边的,而后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州治迁至大足,[17]当也是紧邻赤水溪。《舆地纪胜》载:“县旧治在虎头大足坝,徙今治”,旧县治很可能在赤水溪的西面,所以《元和志》中“大足县,东临赤水,西枕营山”,这样的说法应是无误的。到了宋代,由于地名更迭极为频繁,许多地理志已经混淆不清,如《寰宇记》载:“赤水溪,源从普州安居县界来”[18],安居县实际上没有河流入大足。《方舆胜览》载:“赤水溪。在大足县,其水源自普州安溪县界来”[19],而普州根本没有安溪县,《舆地纪胜》则更是直接引用前人之书的内容:“○岳阳溪,《舆地广记》在安岳县。○赤水溪在大足县东。《寰宇记》云源自普州安居县界来。《元和志》在故静南县”[20],作者已不知道岳阳溪就是赤水溪的上游。明正德《四川志》所载:“赤水溪,其水自普安州溪发源”[21],则更为离谱,把发源于云南镇雄的赤水河和发源于四川安岳的赤水溪都混为一谈了。清嘉庆年间的《四川通志》虽然明确写道:“长桥河在(大足)县西,上流即岳阳溪”[22],即安岳的岳阳溪是现今大足濑溪河的上游,但是该志的编者仍然搞不清赤水溪是何指,遂在后文中又东西麾指:“赤水溪在县东六十里。《寰宇记》:‘溪源自普州安岳县界。来始龙溪在静南县东七十里’。《舆地纪胜》:‘赤水溪有马石膏滩又有玉滩’。《旧志》:‘一名马滩河,源出铜梁六瀛山,南流四十里至普安场,又十五里合沙河溪,其沙河溪在县东南七十五里,源出玉口山石谷,流十五里合赤水溪,又五里至旧州坝,仍东北入铜梁县界为淮远洞河,又六十里入县城与巴川河合流出城东……至铜梁城,环绕县治如巴字。穿城至平滩与淮远洞河合’”[23]。其颠倒混乱,难以取信。
若要论之,唐代的地志,因为建置还不太复杂,昌州又所立不久,所以线索不太纷繁,出错可能性小。宋代的地志,多为江南人所撰,对于西南的状况不太熟悉,出错倒也情有可原。而明清的方志,多为在当地为官的官员或者本地士宦参与而纂,为何在地志中出现了将“赤水溪”指为县东六十里的“沙河”的错误?笔者思索,认为应是与赤水溪改名有关。早期的“赤水溪”的名字应该一直沿用到明末,明末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其作为在大足县的记载中出现的惟一河流名,应该可以为证。但是,清代可能起了变化,在嘉庆年间任大足县令的张澍所作的《重修东郭虹桥碑记》中这样记载:“今来署斯邑,有监生刘增前请曰:‘东关之有桥尚矣’。父若言建自明末,厥制甚庳狭……今上嘉庆十八年,秋水洪发,沦于波。臣往来裹足,目者心恻,增等身金修桥,因以立计。桥高二丈六尺有奇,亭上数楼祀神,以视巩固。费钱四千余缗,经始于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春,乃蒇事”,这是说在明末就在赤水溪上修建了长桥,清代重修后更为壮观,时人于是称赤水溪为“长桥河”,一直到民国年间仍为此名。“赤水溪”的名字被逐渐淡忘,后之修志者只从前人志书上知道此名,而不知所指,更不知道所谓的“东临赤水”是指以前而不是现在的县治,于是错误嫁接到了现在县东的淮远河上,以致前后志书读来不一,引人疑惑。《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更是从前人书中仅作了采撷,未予深究。
四、结语
因此,《读史方舆纪要》中关于大足“赤水溪”的此条或可改为“赤水溪,穿县廓过。源出安岳县界,流入县境,南流入于荣昌,又南流,于泸州入沱江”,在其后可增加一句“沙河,县东六十里,源出玉口山,并淮远河入铜梁,为马滩河,入于涪江”,或许较为妥当。
明清间人对西南的地理认识与前代相比,有较大的跃进,但其中也夹杂了不少错误,《读史方舆纪要》也不例外。直至民国年间,这些混淆的认知还依然存在。在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可以为前人的成就剔除瑕疵,以求继承并继续获得正确的认知。
注释:
[1](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四川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78页。
[2]大足县志编修委员会编《大足县志》第2篇第2章《河流》,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3]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勘测院编制《大足县地图》,西安地图出版社2004年版。
[4]大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点校》卷一《方舆上·河流》,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206页。
[5](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昌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8页。
[6](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昌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47页。
[7](宋)祝穆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六十四《潼川府路·昌州》,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22页。
[8](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一《潼川府路·昌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1149页。
[9]《大足县志》第11篇第13章《公路桥》,第425页。
[10]《大足县志》第2篇第2章《河流》,第96页。
[11]《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点校》卷八《文征上》,第645页。
[12](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一《潼川府路·昌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1150页。
[13](明)熊相纂修正德《四川志》卷十三《重庆府·台榭》。
[14]《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四川四·重庆府·大足县》下“赤水溪”条下注“《图经》:县东临赤水,西枕营山,北倚长岩,最为险固”,第3278页。
[15]《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四川四·重庆府·铜梁县》下“涪江”条,第3289页。
[16]“濑波溪”当是后来所称“濑婆溪”,《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昌州》中“昌元县”条下载:“○昌元县,与州同置,东接赖婆溪”,后文又有“○赖婆溪,在县南五十步,源自静南县来,多有石碛,不通舟行。因赖婆村为名,旧为州所理”。“濑波”与“赖婆”,或语音相近而讹误,或书写错误导致。
[17]唐光启元年即公元885年州治才向东迁至大足,已是《元和志》成书以后的事了。
[18](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昌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47页。
[19](宋)祝穆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六十四《潼川府路·昌州》,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22页。
[20](宋)王象之著《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一《潼川府路·昌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1150页。
[21]正德《四川志》卷十三《重慶府·山川》。
[22](清)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一《舆地·山川·重庆府》,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764页。
[23]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一《舆地·山川·重庆府》,第764—765页。
作者单位:大足石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