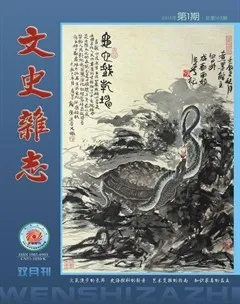从“宋伯姬之死”谈起
马文增
摘 要:《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述宋伯姬之死乃因火灾中等待“姆之至”时发生意外,孔子因其“有情有义”而褒之;经文总体而言讲了六件事,有褒有贬,体现了孔子以“礼义爱信忠”为判断是非善恶的衡量标准;“襄公三十年”是“微言大义”和“属辞比事”手法的范例;孔子于“澶渊会盟”一段详列十二国之名而讳言鲁,乃效法周史官讳言两周之际史事的权变之举,非出于惧上或私亲。
关键词:宋伯姬;褒善贬恶;阙文;澶渊会盟
《左传·襄公三十年》经文曰: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罢来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天王杀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晋。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子、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
于此段经文之理解,历史上多有歧义,笔者敷陈己见如下。
一、关于“宋伯姬之死”
如何看待宋伯姬之死,“《春秋》三传”的看法不同。《穀梁传》曰:“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公羊传》曰:“其称谥何?贤也。何贤尔?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左传》曰:“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
笔者认为,《公羊传》之“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云云乃出自杜撰——全城大火,慌乱嘈杂之中,宋伯姬如何可能和有司文绉绉地谈论“妇人之礼”?史官又如何可能绘声绘色地记录下这一场景?更关键的是,《公羊传》所谓的宋伯姬之“守礼”,按照礼的标准来衡量,恰恰是违背了礼——一个老妇人不按照正常的老年人的行为规范行事,而要按照少女的行为规范行事,这怎么会是守礼?这是不理智,是头脑僵化、思维不正常的表现,因此《左传》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同样,《穀梁传》所谓“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云云亦无道理。“贞”者,正也,端方、正直,《穀梁传》以思想僵化、行为走极端为“贞”、为“妇道”,实属曲解,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恶劣。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义”是面临选择时所应依据的标准,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所以孔子作《襄公三十年》时选取宋伯姬死于火之事,断非出自所谓褒扬“宋伯姬守礼”之考虑。
鲁国国史中关于宋伯姬之死的记载非史官实录,而是出自二手资料。笔者判断,宋都城深夜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平时负责为宋伯姬处理杂事的“傅”年纪小,反应灵敏、动作快,在有司通报的时候,已经起身来在宋伯姬的身边,而贴身照顾宋伯姬的“姆”则由于年纪大、反应慢,或其他原因,尚未至宋伯姬处。宋伯姬与姆常年相处,危急时刻,不愿抛下姆不顾,故坚持等待姆之至,所以“姆未至”的真实意思是“姆还未至,我要等她来了再一起走”;而随后发生意外,宋伯姬最终没有跑出来,被大火吞噬。宋伯姬下葬时,参加葬礼的鲁国使臣叔弓询问宋伯姬的死因,有人就给叔弓提供了当时的大致情况和有司复述的宋伯姬所说的“姆未至”三字,但叔弓并未理解是什么意思。查阅文献可知,叔弓是擅长于礼仪的人,多次作为鲁国外交使臣出使。因此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叔弓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想当然的把“姆未至”三字和“礼”联系起来,想象出了宋伯姬在大火及门的情况下,“宁愿被烧死也不愿违背礼”这样一个场景,并在返回鲁国后讲给了鲁史官。鲁史官遂将叔弓的讲述笔之于国史。
《诗·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所谓“则”者,“礼、义、爱、信、忠”,即清华简《五纪》所谓之“五德”。[1]孔子對作为人伦标准的“五德”有深刻的理解,所以面对鲁国史中关于“宋伯姬之死”的这段记载,一眼就看出了真相,而左丘明则只是看出鲁史所记的这件事可疑,但想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
二、关于“褒善贬恶”
孔子删述《春秋》以褒善贬恶。何为善?符合“礼义爱信忠”的;何为恶?违背“礼义爱信忠”的。善,褒之;恶,贬之。
概括而言,《襄公三十年》讲了六件事,以“五德”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整体上描述了“襄公三十年”这一年天下人的道德状况。其中,“楚子使薳罢来聘”,楚君守聘礼,楚使臣薳罢坚决不答穆公探问之辞,恪守臣子之职,君有“礼”,使臣有“义”,留其名以褒之。“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天王杀其弟佞夫”“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三件事属同类,为色、为权、为气,而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不“义”无“爱”,留诸名以警后世;宋伯姬因不忍抛下姆而独自逃生,死于火灾,有“爱”有“义”,故以“卒”称其死。“卒”者,“大夫死曰卒”(《礼记·曲礼上》)。老妇人而有大夫之德,褒之。晋、齐、鲁、宋等国之使臣代表国君会盟,商议救济遭大火之灾的宋国,结果除了滕国之君表现出了应有的君子品质,如约给予了宋国援助,其余各国君主的表现则全部爽约,故用“子”称滕国国君而用“人”泛称其他国君,盖名实相符。有君德则尊称其爵,无则不用,是即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的体现——直指晋、齐等国国君“不信”;而宋君在国家遭受大灾、国民急需救援的时刻,面对各国的言而无信,不敢据理力争,不能为国人争取应有的援助,怯懦无勇,亦属“无义”,故亦不称其爵。[2]
三、关于“微言大义”与“属辞比事”
在表现手法上,“襄公三十年”中孔子“属辞”以言“大义”,以“比事”明是非对错,可谓《春秋》之典型:边远之楚国、小弱之滕国君主有德,以其爵称之,而晋、齐等大国、中原之君失德,则以“人”称之;王子瑕奔晋逃生,在周王不顾及亲情、刀剑相向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奔大国晋以求庇护,理智清醒;而郑良霄则在因犯众怒被逐的情况下,暂以小国许为落脚点,稍后即潜回郑,图谋报复而终被杀,乃属不知反省,妄自尊大而自寻死路。按《礼记·王制》所载,“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宋伯姬有德,故专门言及鲁叔弓如宋参加葬礼,以示宋伯姬卒后按时下葬,葬礼庄重,尽享哀荣;蔡景公失德,遭砍杀而死,死后七个月才入土,不合礼,且“冬十月葬蔡景公”七字外再无一句,暗示葬礼之匆忙与简陋——所谓“葬”者,遗骨残骸,草草埋了而已。
四、关于“阙文”
按照《左传》之记载,鲁大夫叔孙豹也参与了澶渊会盟,但孔子并未将其人写入《襄公三十年》,其中原因,左丘明谓之“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若按左丘明的说法,言而无信则“不书其人”,则与会之国当全部“不书”,甚至会盟之事也当“不书”;而事实上孔子恰恰是不厌其烦地将十二国一一罗列,所以左丘明的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
笔者认为,孔子之“为鲁国讳”乃出于不得已,其原因孔子曾委婉地做过说明:《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据《论语歧解辑录》一书的记载,历史上诸注家皆断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3],笔者认为如此断句不对,各家之注亦皆非。
“犹”:犹豫,再三考虑,再三权衡。
“及”:随从,引申为效法。
“史之阙文”:此指周史档案中自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至惠王三年(公元前674年),两周之际近百年周史记原始档案缺失之事。
“有马者借人乘之”:“有马者”,有马匹者,结合“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之说,“有马者”代指有权势者,主要是指国君;借,凭借,倚靠;人,人力,此指驭夫;“乘”,读shèng,四声,古称四匹马拉的车为“乘”,“乘之”指使普通的马匹成为能驾车的“乘马”。
“今亡矣夫”:今,如今;亡,通“无”。
国君有马,但马需要经过驭夫的调驯才能用。驭夫之如何调驯马匹,自有其一套技能,“有马者”完全不干涉其工作;所以孔子这里实际上是用“有马者”不干涉驭夫之职的例子来说历史上的君主是不干涉国史之职责的。按许兆昌教授所言,“史掌记事,遂得以将所记之事进一步编成史著。”[4]“马”者,史料也;“乘之”,史著之成也。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国史秉笔直书,君主所为之善恶是非一如其实,不受外力干涉。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这一传统已经遭到破坏,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书·大禹谟》)之说,国君的“道心”愈发微弱,而“人心”则愈发膨胀。在人心的作用下,君主就会对国史之记载加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如实记录鲁君之非,那么第一种可能是鲁哀公直接不再允许孔子整理鲁国国史;第二种可能则是孔子删述而成的《春秋》被鲁哀公或者鲁哀公之后的鲁君禁毁,导致孔子所阐发的义理留传不下去。为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发生,孔子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效法周史官的先例,“为尊者讳”,列出“澶渊会盟”之十二个与会国,而独不言鲁。
所谓“史之阙文”,笔者认为是有确切所指的,即两周之际的史事记载缺失,表现之一是出于曾同孔子一同去东周观史记的左丘明之手的《国语·周语》中关于两周之际的记载,由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直接跳到了惠王三年(公元前674年),曰:“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惠王三年,边伯、石速、为国出王而立子颓……”,中间约百年的史事完全缺失。從清华简《系年》的相关记载看,周代史载中最大的“讳言”即是这段历史,即,镐京陷落后周幽王杀褒姒母子后被杀,随后虢石父在其封地虢国立幽王之弟余臣为周王,称惠王,虢石父挟惠王而朝诸侯二十一年。其间,晋文侯自称王,诸侯皆不予承认,晋文侯出于嫉恨之心出兵灭虢而杀惠王,而后将平王立于镐京,在镐京挟持平王而朝诸侯三年;三年后晋文侯死,周平王才得以东迁至洛邑建都,时间在公元前747年左右。[5]而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记载王子朝以告诸侯之辞“……至于幽王,……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中看,显然,两周之际从虢石父挟持幽王之弟(惠王)直至晋文侯挟持平王之诸多史事在周王室中历代流传,但史书上则见不到文字记载。
两周之际的史记何以缺失?笔者认为非史官之失职,而是因为若干种原因,如不载虢石父挟持周王之事,以免后世有人效仿;不载晋文侯挟持平王之事,或因受到晋国的压力,等等。在情形复杂的情况下,周史官对两周之际的史事最终采取了“阙文”的处理方式。“阙文”实际上是“曲笔”的一种形式。许兆昌说:“曲笔并非孔子的专利与首创,它实际上是对上古史官记事之传统目的与功能的一种继承与发扬。”[6]笔者认为此恰可为“史之阙文”的注脚。当然这种“阙文”的情况在史书中并不多见,“中国传统史学中,既有直书,也有曲笔,但直书一直是传统史学的主流原则”[7]。
《襄公三十年》中体现的这种“阙文”的做法,即详列参与“澶渊会盟”的十二国之名,而不言鲁,孔子知道后人会产生误解,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笔者以为,孔子所谓“知我者”,是指读者通过《春秋》的“微言大义”,能知孔子以“礼义爱信忠”为准则来断天下人之善与恶、天下事之是与非;而孔子所谓“罪我者”,盖有人会因《春秋》中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现象而误以为身为鲁国人的孔子惧上且私亲,不能秉笔直书而区别对待,因而会指责孔子。
注释:
[1]参见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中西书局2021年版。原释文“礼义爱仁忠”,陈民镇认为其中“仁”应释为“信”(陈民镇:《试论清华简〈五纪〉的德目》,《江淮论坛》2022年第3期),从之。
[2]《左传》曰:“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笔者认为,左丘明围绕“信”做传,近孔子意,惟“归”或“不归”在君而不在使臣,故孔子所谓“人”者实指会盟各国之君,“不书鲁大夫”云云可商榷;《公羊传》曰:“宋灾故者何?诸侯会于澶渊,凡为宋灾故也。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所为何?录伯姬也。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丧,曰:‘死者不可复生,尔财复矣!’此大事也,曷为使微者?卿也。卿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卿不得忧诸侯也。”《穀梁传》曰:“会不言其所为,其曰宋灾故何也?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灾以众。何救焉?更宋之所丧财也。”二者敷衍搪塞,不可取。
[3]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36—839页。
[4]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284页、187页。
[5]详见拙作:《两周间史事新研——以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为依据》,《管子学刊》2019年第2期。
[6][7]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第284页,第187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