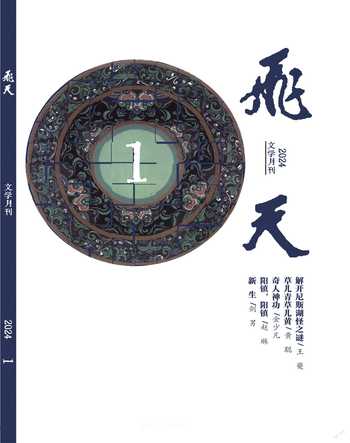梦游
厂刀
当我回到梅溪河的时候,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全回来了,好似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他们亲切地叫我:“克顺,克顺!”
我本以为,我再也不会回去了。但年龄大了,长期给人打工也不是个事儿,还是得自己搞点事业。
黄丽丽跟我说,要不然回鄉创业吧。那时,众筹经济盛行,我们便想到了认养一头猪的项目。
在梅溪河建一个养猪厂,然后给每一头猪编号,顾客可以提前预订猪的部位,比如有人要买A2号猪的猪头,有人要买A2号猪身上的梅肉,到了某一个时间点,杀了猪,再分别卖给不同的客户。
也可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有客户想要走动的猪,就放猪在地上跑,还给客户直播。现在大家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越来越注重健康和安全,吃看得见的肉,才放心,我们都确定养成系的猪会大受欢迎。
我决定回梅溪河的时候,黄丽丽却后悔了。她说,你回家了没人照顾你,而且你又经常梦游,真害怕你出事。
前一段时间,我梦游过一次,把黄丽丽吓坏了。黄丽丽告诉我,当时我把窗户当成了门,一条腿已经迈了过去。好在黄丽丽及时抱住我,才没出意外。
我安慰黄丽丽,放心吧,不会的,我是在梅溪河的时候开始梦游的,有可能这次回去了就好了。
她说,那好吧。
就这样,我带着创业的决心,雄心勃勃地回到了梅溪河。梅溪河唯一一家商务宾馆正在装修,我只好到我的同学大G家暂住一段时间。大G这些年在外务工,挣上钱了,房子装修得特别豪华,客房布置得像酒店。
大G以前在外面做建筑,孩子大了,要回来上学,再加上建筑行业萎靡,所以大G不再去外面工作,而是承包一些诸如修路、打涵洞的政府工程。
大G说,你还记得李国清吗?我说,知道,小学数学老师。
“对对对。”大G说,“当时他打你的时候,可把我们吓得不行,他双手合十,对你拜了拜。后又拦腰抱住你,说要把你从二楼扔下去。”
我对大G说,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大G说,可不记得清楚么,童年阴影,也打过我好多回,回答不上问题,就要挨打,我现在偶尔还做噩梦。
大G告诉我:“你知道吗?李国清已经不当老师了,混成了镇长,每次我找他办事,心里都打鼓。”
我说,真是恭喜他,当镇长可比当校长好多了。
大G说,还是老关好,从来不打人,你记得不,以前还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一个官儿,我是窗户管理员,我最喜欢的老师就是他了。
经由大G提醒,我也想起了老关。大G愣愣地盯住我,他问我:“你笑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想起当年,尿过老关一头。小学五年级,我寄宿在学校。同学们晚上睡不着,都说一些骇人的鬼怪故事,我们的学校建在一片坟场上,他们说,晚上有鬼,鬼没有脚,到处飘。晚上走路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我有了尿意,想上厕所,又太远,就劝自己,算了,直接睡吧,但被尿憋着,怎么也睡不着。内耗了很久,最终决定强打起精神,出宿舍后,一想到会出现鬼,心里敲起了鼓点,背脊处发冷,心脏也剧烈跳动。
但实在忍不住,纠结了半天,最后决定去上厕所,一开门就飞也似地跑起来,顺着宿舍旁边的坡道,往厕所而去。厕所是旱厕,氨气刺鼻,一排排的蹲坑,仅有半米高的水泥墙壁略微挡一下。我一进门,两眼一抹黑,根本看不清,心下惶恐,为速战速决,就近找了个坑位,开始撒尿,一开闸,轰轰烈烈,正享受时,忽闻有声。
“是谁?”我压根没想到坑位居然蹲着人。
一束手电筒光朝我射过来,我吓得一哆嗦,边将工具往裤裆里塞,边往外跑,有几滴尿没抖干净,洒进裤腿里了,湿漉漉的。我仓皇不已,慌忙往宿舍跑。躺在床上,惊魂未定,我确信那不是鬼,而是人。那声音很熟悉,像是老关,教师宿舍没有卫生间,只能和我们一起方便。老关被我淋了一头,他肯定要收拾我。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也有可能睡着了,但梦见自己没睡着。
第二天上语文课,我不敢抬头看老关,生怕他知道昨晚是我尿的。当时他拿着手电筒,肯定认出了我,我心里使劲儿念叨,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同桌黄丽丽用胳膊肘拐了一下,我不快地说,你别推我。黄丽丽又拐了我一下,我告诉她,都说了,叫你别推我。她说,老师叫你。
我惶恐地站起来,心想,老关肯定知道了,我两股战战。
老关向我提了一个问题,黄丽丽悄悄传递答案,我照着念了一遍。老关用手示意我坐下,我如释重负,看来老关压根没认出是我。
直到那一年春节,我爸回来,他跟我一起走路。他说,好小子,听说你尿了关煌卿一脸。
我说,没有的事。我爸说,关煌卿都给我说了,他还说你尿得真准,就是味儿有点臊,可能是水喝少了。
我心想,老关人真是太好了,知道是我,也没有收拾我。
对老关,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老关的事,连我们这些孩子都知道。老关本来是可以考上大学的,那年头包分配,考上大学就可能当官儿了,当官就是当管,是管别人的人。但老关没考大学,甚至连考试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大人拿老关的事教育我们,一辈子别犯法,小偷小摸也搞不得。
奶奶说,当时老关在读高中,就在要考试的当口,有人偷了老关的米,他心有不甘,然后想到了一个昏招,也去偷别人的。他没有什么经验,鬼鬼祟祟偷东西时,被发现了。
老师不让老关参加考试。老关觉得委屈,他是被迫之下才效仿的,但没人关心这,谁叫他被抓住了呢。
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意大利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时,我登时就想到了老关,不过那已经是我得上梦游症很多年后的事了。
被学校清退,老关去北京打了几年工,碌碌无为,没有成事。最后回到学校,做了代课教师。梅溪河上的人对关老师很信任,都说关煌卿教得好。我奶奶说出她用几十年总结出的人生道理:人教人是教不会的,事教人一次就够了。当年老关吃了苦,才会更爱惜现在。
下午,我让大G开车送我到政府,去问问要办些什么材料。大G开着本田思域,把我送到政府楼外。我说:“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大G说,我就不去了,省得看见李国清。
我只好自己一个人进去,问了好几个工作人员,才找到李国清。我记忆中的李国清,一向冷酷,不太好说话。但这会儿见他,很难和以前的李国清对上,胖了,手上戴着一块腕表,又戴上了一副金丝框边眼镜,因为长胖的缘故,又有了柔和的感觉。
我喊了一声:“镇长。”
李国清说:“别那么喊,就喊李老师好了。”
他撇过头去,跟同行的人说,他是我以前的学生。我要办厂的事情,政府早就知道了,李国清也很高兴,他说这是振兴乡村,好事。直播这些年很火,而我又是一个比较新的商业模式,打出了差异化战略,或许真的有前途,能带领大家致富。
他对我说:“只要按照正规的方程序法来,手续一律放宽,还问我,有没有什么难题。”
我告诉李国清,就是选址的问题,成本有点高。
“以前的中心校行不行?可以去看看。”李国清说。
我说,没有学生了吗?他们说,大家都把孩子送到了县城,家长们以孩子的學业为重,在县城陪读,顺便打零工。人口也往城镇迁徙,所以学校废弃了。
晚上,我请领导们吃饭,李国清说,要是关煌卿在就好了,当年他挺看好你的,说你灵性,未来有出息,他没看错人。
席间,喝了大酒,都放得开了。李国清拍着我的肩膀,跟众人说:“别看这小子是个老板,小时候调皮,还扒女学生裤子。”
我没想到,当年我的那点糊涂事,人们居然还没有完全忘掉。
李国清也醉醺醺的,要不然不会说那种唐突的话。他说,当年要不是我拦住关煌卿,他都能打死你。
虽然我心有不悦,但我还是装作受教地说:“小时候犯错,确实是该教育,要不然路都走歪了。”
但当年被老关打,我都恨死他了。
那时,表哥从广州回来,带回了影碟机。村里的小青年,几乎隔三差五都来找表哥玩,他们用床单把窗户堵上,在屋子里看片,我是表哥的马弁,被允许加入其中。每天看了黄片,从屋子里出去的时候,都神采奕奕的,眼睛里冒出热乎乎的光芒。
我跟他们在一块儿,我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燥热得可怕。好像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很容易被控制。
我的表哥被控制了,天天缠着我姑姑,说要结婚。至此,表哥也开始了他相亲的漫长生涯,整整持续了十四五年。
表哥可以找姑姑要女朋友,而我无法要,我还太小。但我盯上了黄丽丽,以前我觉得黄丽丽不好看,嘴巴翘得像鱼嘴,个子矮小,结果在影碟机里活泼好动的女人的熏陶下,我发现其实黄丽丽也不错,原来的鱼嘴,陡然变得性感。
黄丽丽性格外向,经常和男生打打闹闹。一个郁热的傍晚,我们和黄丽丽打闹,她捏我的脸,我就抓住了她的手,然后我就搂抱住黄丽丽了。她又咬了我一口,我变成了表哥这样的男青年,身体发热,澎湃的生命力溢出了体表,后来黄丽丽嫁给我,一起在北京工作时,她告诉我说,当时你的眼睛炽热,宛如一头发疯的野兽。
那一天,我抱住黄丽丽的腰,她用脚抵住墙壁,又用手扒住阳台。但她力气不如我的大,我生拖硬拽,把她拉到宿舍,插上插销,开始扒黄丽丽裤子。
黄丽丽两只手拽住自己的裤腰带,我们两个人都很忙碌,但最后是我失败了,黄丽丽扒开插销,跑了出去。
无数的同学看见黄丽丽捂着嘴奔跑。同学们都说杜克顺把黄丽丽的裤子扒了。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男同学问我,她下面长什么样。我不屑理他们。他们又说,黄丽丽找老关去告状了。
老关问黄丽丽怎么了,黄丽丽哭。老关问黄丽丽,有人欺负你了?黄丽丽还是哭。老关又问,是谁?有人说是杜克顺。老关问,是杜克顺?黄丽丽哭得更大声了。
大G慌慌张张跑来告诉我,他说,老关知道了,你躲起来吧。我浑不在意,我又没有扒下来。而且老关和我的交情非同一般,去年我的腿被摩托车撞了,是老关天天带我去看腿的。
后来大G说,老关冲进宿舍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老关狠狠踹了我一脚,明明把我踹倒了,结果一个箭步,又将我拽了起来,神乎其技。
老关让我站在空旷的操场上,烈日当空,同学们都在睡午觉,但他们都听见了荆条拍在皮肉上的声音。老关把荆条抽打在我身上,发出脆响。我疼得跳脚,这时,我才害怕起来。老关真是想打死我。我往外跑,腿脚没有老关快,又被老关扑倒,这下他打得更用力了。
我没想到,老关下手这么狠。更没想到,最后还是我讨厌的李国清救下了我。李国清拦住老关时,老关已经打断了三根荆条,我把裤子搂上来一看,大腿、小腿上,全是凸起的血红的棱,一碰就疼。
老关勒令我坐上他的摩托车,他把我送回了家。我们到家的时候,奶奶正在劈柴。她头昏眼花,但还是一眼就看见了我们。
奶奶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关老师。她问关煌卿,他又调皮了?
老关推了我一把,你自己说吧。
我垂着头,不敢言语。
老关说,这么小的年纪就知道扒女生的裤子,这怎么得了,读书好又有什么用。他把别人对他说的话,沿用在了我的身上。老关又交代几句,骑着摩托车,突突开走了。
老关走后,我抬头,看见奶奶正颤颤巍巍地,小碎步地朝向我走来,就像在大海上随海浪摇晃的一叶舟,浪大一点,就得被淹没在浪里。奶奶最后还是挺住了,她的嘴角开始哆嗦,用布满老年斑的手,结结实实抽了我一巴掌。
第二天,奶奶背了几块腊肉和半背篓土豆,把我领到了学校。奶奶对老关说,还是请您管管他,他的父母不在家,我也管不了。如果再不听话,关老师就打吧,别怕打坏了。老关没有要东西,但让我留下了。
经此一事,我的名声尽毁,梅溪河上的人都知道我跟着表哥学坏了,扒了女生的裤子。我对老关恨得牙痒痒,寻思着怎么报复他。
酒至正酣,见我一直没说话,李国清突然看着我,他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和关煌卿还有点亲戚关系吧?
我说,他是我堂姐夫。
关煌卿和我堂姐结婚,正是我报复他的开始。
我上六年级时,老关到处托人说媒。老关的母亲晾衣服的时候摔断了尾巴骨,瘫在了床上,如果没有人照顾,那老关就没法工作。
老关条件不好,即便是当教师,负担也过重,所以比较难找,谁愿意嫁过去就伺候人?
奶奶觉得我犯的错,让她丢了脸面,更让她亏欠关煌卿,所以奶奶对老关的事比较上心。奶奶说,关煌卿没有老婆,他妈又瘫在床上,太命苦了。
我想到了房族里的堂姐,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嫁出去。走亲戚,看见堂姐时,我每次都紧张。她的脸上有大块红斑,而且脖子像一颗树瘤。上初中学了生物课,才知道那是得了大脖子病,缺碘。
我说,堂姐不是还没有嫁人么。我启发了奶奶,她开始奔走。老关的工作迫在眉睫,想找好的又找不到,最后老关同意了奶奶的游说。
知道老关和堂姐要结婚,我表哥跟我说:“老关真是病了,如果是我的话,还不如不娶。”
老关结婚那天,他把我的堂姐背在背上,有人往他的脸上抹锅底灰,他的脸像花猫。慌乱中,老关挤掉了一只鞋,老关就一只脚穿着皮鞋,另外一只脚穿着袜子,背着我堂姐进门。人们互相推搡着,欢欣鼓舞地前进。
回到家,大家又一窝蜂涌上去,找新郎要红包,我也混在里面。我就像个钻头,扒开人,不断往里拱,我终于站在最里面那一圈了,悄悄朝老关的肚子闷了一拳。
老关捂住肚子,叫了一声,但不知道是谁打的。人们推搡老关进洞房,他就更不知道是谁打的了。
老关结婚没多久,我就毕了业,要去镇上读中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有新的老师,有新的同学,一切都是新的,满是憧憬。
上中学后,我的成绩也还不错,学校为了升学率,把我们这一些成绩相对拔尖的人归拢在一起,叫做火箭班,集中辅导,目的是让我们考上普高。我们县是贫困县,教育条件也比较落后,我们乡更差,能考上普高的人,向来稀少。
我们一个月只回家一次,偶尔会听到人们说起老关。老关没了后顾之忧,一心扑在工作上。老关带班讲课依然卓有成效,因教学质量突出,而且又是资历最老的人,老关被提拔为主任,后来又听说老关当上了校长。
我心想,这狗日的,因祸得福了。
后来,我们经常在公路上看见老关,老关骑着一辆太子摩托车,背后,一个年轻女人紧紧地贴着老关,老关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
大G告诉我,那是学校新来的音乐老师,你看老关那样子,肯定和女老师搞在了一起。我想,如果我是老关的话,我也愿意跟这个女老师搞在一起。
我知道,当时好多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代入老关的角色,都替老关鸣不平,年纪轻轻的,本来有很好的前途,结果却溃败了,最后又套上了新的枷锁。人即便再强大,也强大不过命运。
最后堂姐听到了风言风语,堂姐去学校闹,没兴起多大的波澜。每一次去学校,她都碰不到那位女老师。有人说,女老师调走了。堂姐认为,大家都在包庇这一对狗男女。她去得更勤了,但去的次数越来越多,她自己反倒像一个笑话。
不同的人给她出不同的主意,让她愈加迷茫。后来她去了教委,堂姐请求领导批评那位女教师,最好让她永远也教不了书。领导不胜其扰,停了老关的职务,让老关配合调查。处理结果超过了堂姐的愿望,她又去教委,人说,你怎么又来了。她说,只要开除那个女人就好了,怎么还把我男人的工作给停了?领导你搞错了。
领导吹着保温杯里的热茶,吸溜一口,看也不看她,然后说,你把机关当什么了?
堂姐乞求地看着领导,领导不为所动,她又在教委的大门口站了一天,最后还是没有打动领导,她只好原路返回去。她真是搞不懂,事情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人们又开始同情起关煌卿,历经磨难,好不容易才当上校长,结果又把帽子弄丢了,也够悲苦的。他们打心眼里相信,老关不是无辜的。
不过转念一想,那也是关煌卿咎由自取,他的老婆虽然配不上他,也是他自己选择的,堂姐耐烦地伺候走了他的母亲,老关怎么能跟学校的老师鬼混?人们总是在背后叩问老关的灵魂。
从接到通知,老关就再也没有从屋里出来过。人们都指望,老关能重新站起来,再差也不过是丢了工作。老关当年也遇到了挫折,结果挺过来了,还发展得这么好。人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没个准数。遗憾的是,老关再也没爬起来。
我的奶奶告诉我,关煌卿喝老鼠药的那天,突生异象。
下午三点光景,太阳还悬挂在天空的一侧,像磨得光光的铜镜。风云变幻,不多时,乌云如蛇一般,从不同的角度,朝那淡薄的日头而去,云一层又一层,不断游移,合谋噬日。
最终,太阳被包裹住了,天昏暗得要命。沉悶了一会儿,都快黑得看不见了,一道闪电劈开浑浊的天空,又消失不见,惊雷震得耳朵疼,雷落在地上,劈断了长了三十多年的黄桷树。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暴雨。奶奶双手撑着下巴,专注地看着滴水。
奶奶看见堂姐正垂着头跑,喊她躲雨,堂姐看见了亲人,她跑过来,搂住奶奶就一顿哭。
堂姐又跟关煌卿吵了一架,关煌卿说,堂姐毁了他,听信这些子虚乌有的事。堂姐见关煌卿死不承认,气不过。
奶奶也安慰她,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样,要想宽绰一些。
堂姐哭得愈加厉害了,她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受了委屈。她的眼泪和外面的大雨联系在一起,她哭得大声,雨也就越大,粗壮的雨线自天际砸下来,涵洞被堵,路面淌满积水,雨落在瓦上、铁皮上,发出噼啪的声响,拨乱了人心。
堂姐对奶奶说,我得回去了。奶奶看看外面,雨势还没住,让堂姐再等一等吧。堂姐等不及了,她想要回去。
奶奶借给堂姐蓑衣,看着她回去了。雨足足下了好几个钟头,这场暴雨的痕迹很重,把田地冲出了一条条沟壑,梅溪河上涨了洪水,卷走了很多东西,河面浑浊,汹涌向前。
堂姐后来告诉梅溪河上的人,说那天关煌卿吃下老鼠药后,嘴里的污秽浸湿了三床棉絮,又打湿了铺盖下的稻草。他扑倒在床上,面目扭曲,沉如麻条石。
一个女人回忆起这一天,她说,下毛毛雨的时候,她正在给猪喂食,她恍然发现远方有一个人晃动,一抬头,看见是老关,她打算喂完猪,再跟老关说话。她忙完了,却发现老关人不见了。人说,那是老关的魂魄在游走。
奶奶跟我说,她早就意识到不对了,堂姐刚从家里离开,原本好端端立在街沿墙壁上的锑盆滑了下来,在地上旋转翻滚了好几圈,还发出刺耳的金石之声。
我打断奶奶,你别瞎说,世间无鬼神。奶奶欲言又止,她为我跟她说不到一块儿去而失落。
老关没有等来那一纸通知,上面调查结果认为,女教师和老关只有上下级关系,女老师听见流言蜚语,为了声誉,早已主动调任。堂姐不相信调查结果,女教师就是不想被牵连,撇得一干二净,她还哂笑说,老关看错了人,居然和这样的人搞在一起。
自打老关去世后,我有了梦游症。有好几次,奶奶发现我半夜起来穿衣服。在一个盛夏,我半夜爬起来,走向了漫漫黑夜。被奶奶发现时,我正蹲在一个草垛后面。第二天,奶奶向我讲述这一切,我浑然不知。没有想到,我的梦游伴随着我很多年,我到市里,到北京,都发过病。
上次和李国清一起吃饭后,就开始着手办厂。建厂的工作包给了大G。自从表哥结婚后,他对他的婚姻生活感到厌倦,看他无所事事,我也就雇佣他当我的司机。尽管有人帮忙,但还有很多事要我操心,要卡成本,也要保证质量,太忙太累了。我原本想去老关的坟前看看,缅怀一下,但老是忘。只是偶尔放空的时候,会想到老关。
事情还在继续着,过去了六个多月,等到了养猪厂竣工,当然后面还需要建设一系列的辅助设施,要引入各类设备,并且要铺供应链,还要去找客户等等,离成功还很遥远。
李国清说,养猪厂建好,要剪个彩,庆祝一下阶段性胜利,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能鼓励到别人。
我本不喜排场,李国清又劝,这是镇上第一家由政府扶持的大型企业,而且是用数字化把传统企业重新做了一遍,还打算当成示范点,让更多的人返乡创业。所以不能过于低调,剪彩仪式还会邀请县里的领导莅临指导。
他这么说,我也不好拒绝了。真没想到,会搞出这么大的排场。梅溪河上的人都来了,有些人一大早就来等着,工作人员派发拍手器和充气棒,一派繁荣气象。
我忙前忙后,迎来送往,倒也有一个乡镇企业家的风范。我已经在展望,过不了多久,我的养猪厂里,将关满一头又一头的猪,隔几个月出栏一次,到时候我的银行账户里会出现一串长长的数字。
等送走了领导,我的亲戚朋友们还没有散去,他们对我说,克顺,你出息了,办了这么大的事业。怎么也得表示一下,但你不缺钱,就送点土特产吧,你寄到北京去,给你媳妇和孩子吃。
我再三推脱,然而盛情难却,只得收下。大家又在养猪厂逛逛,尽兴后陆续离开,这时人群散开,我见到了一个矮小佝偻的女人,她脸上的红斑变成了紫色,脖子似乎更肿大了,这些年我刻意回避她,故意错过她的一切消息。再见时,她还是印象中的那个样子,我怯生生的,想装作不认识她,巧妙地走开。
但她率先喊了我一声:“克顺,你还认识我不?”
堂姐比以前更老了。她提着一个包袱,跟我说:“这是我养的鸡下的鸡蛋,这土鸡蛋是很好的,你收下吧。”
然后她不由分说地塞在我的手里,堂姐朝我摆摆手,她对我说,我走了。刚走两步,她又跟我说:“谢谢你呀,克顺,如果当时不是你的话,我会被蒙在鼓里一辈子,那样我就真的委屈死了。如果是别人,我还不会信。我们是亲戚,你又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你的话肯定是不会假的。”
“克顺,等你空了,来我家玩,来吃饭。”堂姐晃着瘦削的肩膀,慢慢走了,我也迷失在她的背影里。
那次闷了老关两拳,但还不够,看到女老师搂住老关的腰,我就意识到自己等来了机会。我站在老关家的门前,我想了想,然后告诉堂姐,老关已经和一个漂亮的女老师搞在了一起。在摩托车上,她紧紧抱住老关,就像两个人长在了一起。
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很激动,身体颤动,我感觉连每一个音节都在跳舞。说谎话,会让我兴奋。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般走向,所以多年来,我都没法坦然地面对堂姐,更无法心安理得地接纳她的雞蛋。她孤身一人,要她的东西太不合适了。
乡亲们送的鸡蛋,我都装在了一个大筐里,我捡出一部分。等要装时,却找不到她的包袱,只好另找一个盒子。我告诉表哥,让他开车送到老关的家,把鸡蛋还给堂姐。
表哥惊诧地看着我,他说,你的堂姐早就去世了。我说,怎么可能,剪彩的那天,我还看见了她。
表哥则信誓旦旦地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剪彩的那天,我们都不知道你躲哪里去了。我们动员了好多人来找你,最后发现你就站在老关家颓废的旧屋前,捏住拳头,指节被你挤压得发白,仿佛正在下一个巨大的决心。
我不信,又问大G:“真的假的?”
大G点头,跟我说:“克顺,你又梦游了。”
责任编辑 晨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