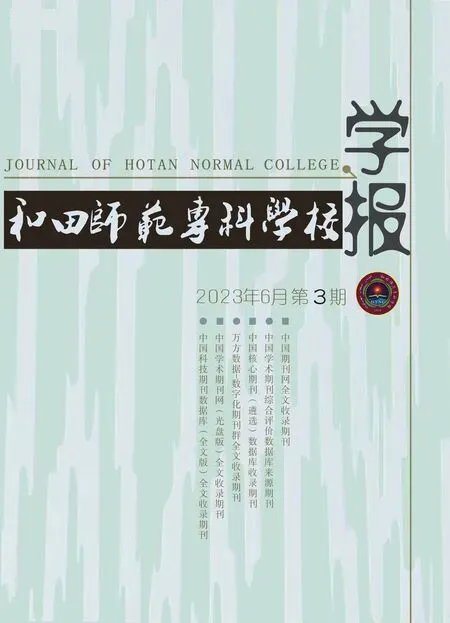西域生态书写的美学研究
杨 波 李佳珈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无论广义和狭义的西域,从世界历史、地理情况看,西域在欧亚大陆板块中具有重要的地理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西域生态与环境书写构成了历史上西域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有文字记录以来西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描述。 西域生态书写不仅是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后的人类生态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人类生态文明互相交流、交融的结果。 以人类生态共同体的视野审视西域生态文化、西域生态书写,探究西域生态书写的美学意义和审美内涵,将是西域生态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起点。 作为生态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西域生态书写应该从哪里入手? 如何梳理这些文献? 根据历代文献对西域的记录,可以将西域生态书写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历史地理文献中关于西域生态与环境的书写
中国早期的历史地理文献主要在先秦之前。《禹贡》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是研究先秦时期地理环境的重要著作。 其成书时间估计在公元前三百多年的战国时代,《禹贡》分为:九州、导山(山岳)、导水(水文)、水工、五服五个部分,共一千一百多字,对中国古代的地理进行了描述。正如《〈禹贡〉释地》中所说:“《禹贡》是一篇综合性的地理志,内容包括行政区域,山岳(导山)、水文(导水)、土壤、物产(贡物)、交通(贡近)、民族(夷、戎)等。 文字简明,体系完整,内容翔实。 与同时期的地理文献相较,它不像《山海经》那样渗杂神话,也不像《尔雅·释地》、《周礼 职方》那样仅仅罗列地名,而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地理著作,是研究我国上古时期地理环境最重要的文献。”[1]其中“雍州”所在大概指现在的东起黄河,秦岭以北,西至甘肃省以西,包括后世所指西域个别地区。 书中说:“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2],杜预作注时认为,“三危”就是今天的敦煌,这种说法为后世所认可。 对“西戎”的书写,也说明在战国时代,人们对西域一带的居民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然,从现代地理学的眼光看,《禹贡》中必然有很多错误。 如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对陕西、甘肃、四川一带的地理最明白,山西、河北、河南次之,到东部则相对模糊,至长江下游出现明显错误,并由此推断《禹贡》的作者可能是西北地区人氏。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禹贡》中已经有了很多涉及后人所谓“西域”的情况。
另一个重要的古代地理学著作《管子》是托名管仲而写的著作,其中的《地员》、《度地》、《地图》三篇总结了当时人们地理知识,是我国先秦时期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学文献之一。
《管子·地员》篇是我国先秦时期关于土壤分类的地学代表作,同时还讨论了土壤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也是一篇有关古代生态地理植物学的较早的论述,体现了战国时期农业土壤科学的发展。 如《管子·地员》中将土壤分为上、中、下三类,选择相应36 种植物进行种植。 以土壤特点区分垦殖的作物,中华民族早期的土壤生态观在其中已经有所体现了。
《管子·地图》篇是为了古代战争便利而做的地形描述,对于何处地理环境利于掩藏、何处地理环境可为作战依托做了详细描述。 文中主要论述了战争指挥者了解地理形势、军队形貌对于带兵打仗的重要性,以及地图记录地形,兵家常备地图的必要性。
《管子·度地》篇是我国最早关于水利建设的文献,中国是农业大国,灌溉工程对于农田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中根据水的发源地与流向进行分类,分为:经水、枝水、川水、谷水、渊水,详细论述了修建堤坝、疏通河道、改变水流方向对于减少水灾的重要性。 《度地》中将四季与修建堤坝相对应,提出春季是进行土石工程的适当时节,修建堤坝不应影响农业生产,在修建好堤坝后还要派专人管理,定期巡视并进行修补,保证堤坝正常发挥作用。
《管子》中没有直接提出西域生态状况、也没有关于西域生态的书写,但是关于土壤、环境等自然生态的认知却代表了当时人们在这方面的基本认识。
其他重要历史地理著作常见的还有《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水经注》。 尤其是《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传》等资料一直是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学习、了解西域生态情况的重要参考、学习资料。 到清代时期,历经几朝,在乾隆时代对西域的统治达到高峰,为了歌颂自己的文治武功,也是由于管辖的需要,由清代皇帝组织一些学者对西域舆地进行详细的考察、记录。 史地之说由此盛行,再加上乾嘉朴学考据之风大盛,西北舆地研究一时成为显学,出现了以祁韵士、张穆、洪亮吉、徐松、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的西北舆地专家,对西域生态与环境书写愈发详实,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对西域地区自然、地理、人文等情况书写最为全面的时代。
清代关于新疆的史地研究成果丰富,不完全统计约有200 余部著作,清代西域生态、环境书写的地理类著作主要有:祁韵士《藩部要略》22卷、《西域释地》、徐松著《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为代表性著作。清人的著作的大多数作者都亲临西域(新疆),著作中对西域的山川、河流、荒漠、人口等情况都有记录,也有很多人对前人的著作进行校勘,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学著作中对西域生态、地理环境记录最为详实的著作类别。
二、神话时代对西域的想象
《山海经》是我国神话时代的代表作品。 《山海经》的作者不详,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地理著作,记录了早期人们对古代中国四方地理的认识,也有人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神话之作,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昆仑神话”的一个重要源头,对后来的“蓬莱神话”体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内容,包括大山大川、地理位置、民族分布、地域物产、原始宗教等,保存了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历史上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最早整理《山海经》的是汉代的刘歆。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 个邦国,550 座山,300 条水道,100 多位历史人物,400 多个怪兽。 《山海经》的记载中也保留下来了古代时期人们对西域的想象。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3]在司马迁看来《山海经》记录了太多的怪物,他不信,所以不说。 其中《西山经》与《海内西经》对于昆仑山的地理位置、河流情况、形状样貌等有所描写,同时指出昆仑山是万山之首,百神所在。
《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 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泛天之水。 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 墨水出焉,而四海流注于大杆。 是多怪鸟兽。”“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4]
《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 昆仑之虚,方圆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 面有九井,以玉为槛。 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 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5]
《山海经》中对昆仑山的书写其实是对西域地区重要文化地理环境的书写,昆仑作为神话想象的创造,其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古人对未知地区的“想象”,所以《山海经》中对西域地区地理、河流、气候等情况的书写与今天的地理情况有较大差异,导致很多学者对《山海经》真实性存疑。 事实上,《山海经》中对西域生态的集体想象性书写也蕴含着早期人们的生态审美态度。 如对“方位”的认知体现着早期人们的宇宙观、对珍禽怪兽的想象体现了对自然理解的创造。
三、历代西域行记、日记中对西域生态、环境的描写
行记,是旅行途中用来记录游历所见所闻的一种纪实性文学体裁,其中前往新疆、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的行记被学者通称为西北行记或西域行记。 最早的记录西域情况的可以追溯至《山海经》与《穆天子传》。 公元281 年(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出土的《竹书纪年》中有六卷本的《穆天子传》,记录了周穆王西巡之事,这个发现将中原地区与西域交流的时间大大往前推进,在当时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两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就注释了《穆天子传》,后世学者也有多人对此进行研究,《穆天子传》也成为我们了解古代西域生态状况、生态观的一个重要文献。 在《穆天子传》研究中学者产生较大分歧的一个问题是周穆王西巡线路的考证,而西巡路线的考证其实是对西域地理位置的和生态状况的考查。 近代学者中顾实、丁谦、刘师培、岑仲勉、顾颉刚、小川琢治、常征等围绕这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穆天子传》中有多处涉及西域的地理内容,尤其是对“昆仑”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如: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皇帝之宫……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珠泽之人乃献白玉石……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 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庚辰,济于洋水。 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车。 天子使逢固受之。 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黄金之鹿,白银之麕,贝带四十,朱四百裹。 戏乃膜拜而受。”[6]
虽然对舂山、洋水等地的地理考证有多种说法,但有很多学者依然认同舂山大致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也就是葱岭附近,《穆天子传》中记录的周穆王到达舂山、洋水的活动可以说是对周穆王到达昆仑山、帕米尔高原一带,主动与当地部落首领“戏”交往交流的记录,从周边地理和当地部落献上的礼物可以看出当地很可能还是以畜牧业为主。 穆天子一路西巡,可以说是汉文文献中比较早地对西域环境的记录。
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史记》中其实也包含着早期的行记内容,而司马迁自己也说:“大宛之迹,见于张骞。”[7]相传张骞西域归来后曾经撰有《出关记》一卷,专门记录了西域之行的所见所闻,可以说是第一部汉文记载西域的专著,遗憾的是已经失传。 从司马迁的自述中可以判断《史记》中关于西域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来自张骞的行记内容。
另一种重要的西域行记类型是历代求法僧人记录的行记、各类人员,包括遣员、流人到达西域途中或在西域行程中所记日记对西域生态、环境进行的书写。
后秦、东晋时期法显的《佛国记》、北魏时期的《宋云行记》可以说是较早的西行求法行记代表。 唐代时期是僧人行记发展的高潮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玄奘、辩机的《大唐西域记》以及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 其后代表性的有唐代杜环的《经行记》,五代高居诲的《使于阗记》,宋代王延德《使高昌记》,敦煌残卷《西天路竟》。 之后代表性的西域行记有元代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明代陈诚著有《西域行程记》、《西域蕃国志》等。 在这些行记中对西域生态描写更具个性化和人性化,已经不同于《山海经》的神话想象,也不同于历史舆地之作中的稍显呆板。
如现存有《宋云行记》的《洛阳伽蓝记》中对葱岭地区环境的书写:
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 西行六日,登葱岭山。 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 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 山中有池,毒龙居之。 昔有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泛杀商人。 盘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乌场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尽得其术。 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悔过向王。 王即徙之葱岭山,去此池二千余里。 今日国王十三世祖也[8]。 再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帕米尔高原地区的环境书写:
波谜罗川,国境东北,踰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 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踰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飃风。 地鹹卤。 多砾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绝无人止。
波谜罗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馀里,南北五十馀里,据大葱岭内,当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 水乃澄清皎镜,莫测其深,色带青黑,味甚甘美。 潜居则鲛、螭、鱼、龙、黿、鼉、龟、鳖浮,游乃鸳鸯、鸿雁、鴐鹅、鹔、鸨。 诸鸟大卵,遗 荒野,或草泽间,或沙渚上。 池西派一大流,西至达摩悉铁帝国东界,与缚刍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 池东派一大流,束北至佉沙国西界,与徙多河合而东流,故此已左,水皆东流。
波谜耀川南,越山有钵露罗国,多金银,金色如火。
自此川中东南,登山履险,路无人里,唯多冰雪。 行五百馀里,至朅盤陁国[9]。 同样是旅行者的记录,二者同样是对帕米尔高原地区的自然生态进行书写,写法上却有区别。 《宋云行记》不仅记录了葱岭的自然环境,还将当地关于毒龙的传说记录了下来,而毒龙对路过商人的伤害显然是人们对恶劣自然环境产生原因的一种想象。 《大唐西域记》中则是据实记录,将波谜罗川的地理、气候、土壤、植被一一书写下来。 而这些西行求法之人留下的行记对后世的行记写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域行记最繁荣的时代是清代。 清朝中期国家统一,康熙、乾隆雄才大略,西部防边、戍边、屯田需要更多的官员和军队,大量官员、流人或遣员从内地出发前往伊犁、乌鲁木齐、塔城、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万里行程中留下了各种行记。 如洪亮吉的《遣戍伊犁日记》、王廷襄的《叶柝纪程》、倭仁的《莎车行记》、袁大化的《抚新日记》、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裴景福《河海昆仑录》、温世霖《昆仑旅行记》、林则徐的《荷戈纪程》和《乙巳日记》、吴恢傑的《西行日记》、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以及宋伯鲁的《西辕琐记》等。 这些行记几乎贯穿整个清代,并延续至民国。 吴丰培先生曾经将所见清代新疆行记36种,编成《甘新游踪汇编》。 当代还有胡大浚先生主编的“西北游行记丛萃”第一辑(2002 年)、第二辑(2003 年)属于比较权威的选本。 这两套丛书选录了19 世纪以来西北行记中的著名之作共37 种,辑为20 册。
如林则徐的《荷戈纪程》记录从西安到伊犁123 天的行程,详细记录沿途道里交通、气候环境、民族关系、民风物产,如路过玛纳斯河:“二十二日,丁酉(11 月24 日)。 晴。 辰刻行,过西关,十里有玛纳斯河,车马涉过。 是河本极宽深,今值冬令水弱,河流隔为三道,其深处犹及马腹,夏令不知如何浩瀚矣。”[10]路过果子沟(塔尔奇沟):“今值冬令,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沿山松树重叠千层,不可计数;雪后山白松苍,天然画景;且山径幽折,泉溜清冷,二十余里中步步引人入胜。 若夏秋过此,诚不仅作山阴道上观也。”[11]到南疆之后,林则徐记有《乙巳日记》,其中记录了南疆现巴楚现周边的生态环境:“此数程皆树木薪郁,枯苇犹高于人;沿途皆野兽出没之所,道中每有虎迹,因此次随从人多,兽亦潜踪而避耳。”[12]《乙巳日记》写于1845 年,从林则徐的记录看,至少在当时现在新疆境内已经灭绝的“新疆虎”在十九世纪中期在南疆还可以看见,不得不说林则徐的这段记录是记录南疆地区生态历史的重要证据。
一般来说,很多行记都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这使得西域行记中的西域生态书写更具审美评价的价值。
四、历代西域文学作品在对西域的“集体记忆”“集体想象”中的生态环境想象
边塞诗作为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很早就出现。 《诗经》中的早期边塞诗,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边防、戍边战争活动及战争中的人的活动的真实面貌。 如《小雅·出车》、《小雅·采薇》、《王风 君子于役》、《召南·殷其雷》等。 但《诗经》中的边塞诗主要体现的是戍边的艰苦、征夫的怀乡等。 《诗经》之后,边塞诗逐渐成为重要的诗歌题材,但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真正涉及西域的诗歌和诗人并不多,到了唐代,由于疆域的快速扩大,东西交流日益频繁,唐朝以宏阔的气魄与胸襟包容着世界各地的文化与艺术。 军人、诗人、艺术家陆续到达西域边关,亲历西域的山水、地理、气候、民族,西域的生态与环境开始真正渗入诗歌描写中。
唐代是中国古代边塞诗繁荣的一个高峰,唐代边塞诗人之多、边塞诗作数量之大都大大超过了前朝,也为后代的诗歌创作树立了一个典范。唐代边塞诗的创作贯穿整个有唐一代,边塞诗创作在唐代一时蔚为风气。 唐代边塞诗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而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诗歌则是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作。 除高适、岑参这样的典型边塞诗人以外,唐代很多大诗人都写过边塞诗,如李白、杜甫、王维等。 在唐代的边塞诗中,有的诗人的人生轨迹中虽然没有到过西域,但根据西域形象历史书写中形成的套话或文化记忆也对西域的黄沙白云、冰川雪山等自然景观进行了想象描写,西域独有的意象也成为唐代边塞诗的特点,如塞外、雁门、漠北、玉关、黄河、羌笛、胡笳、琵琶、战马。 这种写法也成为后代边塞诗的模仿对象。
以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为例,此诗写在诗人二次出塞任封常清幕府期间,时间大约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44 年)或十四年(公元745 年),诗歌标题中的“走马川”为唐轮台。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轮台,一个是汉轮台,一个是唐轮台。 汉轮台在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轮台县策大雅附近,唐轮台的位置较多的学者认为应该是今天乌鲁木齐市南郊的乌拉泊附近(也有说在阜康或昌吉周边)。 本诗是为即将出征的掌管北庭都护的封常清壮行而作,这首诗集中描写了部队在走马川中顶风冒雪夜行军的紧张、壮烈的场面。 诗歌的第一部分,“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平沙莽莽,狂风夜吼,碎石乱飞,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唐军艰难前行。 诗歌的第二部分,“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顶着狂风,冒雪暗夜行军的边防战士斗志昂扬,和恶劣的环境形成反衬,夜不卸甲,行军中矛戈碰撞的声音彰显出军纪严明。诗的最后部分,“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饯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东师西门伫献捷”[13]。 诗歌当中的场景如:黄沙漫天、风吹石走、风刀割面,风雪中马汗成水,寒风中砚水成冰,但讨敌檄文依然振奋人心,这样的壮烈场面独特且洋溢着豪壮之情,是对西域的生态环境的具体的记录和描写。
但是唐代的边塞诗人中只有个别人,比如岑参,真正到过西域,并跟随高仙芝、封常清两次在西域戍边,随军六年,见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 其他边塞题材诗人如杜甫等人并没有到过西部边陲。 这也是“边塞诗”的一个特点,边塞诗,包括书写西域的边塞题材诗歌,其作者可能并没有到过西域,但是他们可以根据他人的书写和记录,以西域边塞的意象入诗。 究其根本,这类诗歌其实是诗人对西域边陲的想象,是建立在文学史基础上的“集体记忆”或“集体想象”。
元代耶律楚材西域诗著作颇丰,留有诗文集《湛然居士文集》,明代陈诚到访西域,并留有诗歌集成《进呈御览奉使西域往回纪行诗》一百多首。
中国诗歌史上另一个西域诗的高峰是清代。当代学者王星汉在《清代西域诗辑注》中说:“历代西域诗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首推清代。”[14]早期的清代西域诗研究者吴蔼宸先生在《历代西域诗抄》中搜集得清代22 位诗人,904 首西域诗。 当代学者王星汉作《清代西域诗辑注》,收录清代诗人58 人,诗作1111 首。 清代西域诗,与前代相比,有时间长、地域广、数量大、作者多、题材富、体式全等特点。 清代社会政治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在西域诗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可以说清代西域诗一方面成为清代诗歌的独特风景,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也以“史诗”的形式记录了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清代的各种现实与矛盾。 代表性的诗人及作品有: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洪亮吉谪戍伊犁期间留有《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诗;祁韵士《西陲竹枝词》、《新疆赋》;李銮宣《坚白石斋诗集》、施补华《泽雅堂诗集》、史善长《味根山房诗钞》、左宗棠《左文襄公诗集》、景廉《度岭吟》、萧雄《西疆杂述诗》、宋伯鲁《海棠仙馆诗集》、张荫桓《铁画楼诗钞》等。
五、历代类书中对西域生态、环境的书写记忆
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以信息时代的视角看,古代类书就是古代社会的一个个“数据库”,他们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历史地形成了一套编纂方法,以便于检索、征引的一种工具书。 常见的有“通典”“会要”类的书籍,其中记录了西域生态与环境。 重要的代表有《唐会要》、《宋会要》、《册府元龟》等。 如《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 外臣部(五)土风第二,记载了关于古代的龟兹国:
龟兹国,在白山之南,能铸冶,有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折其臂,并刖一足。 赋税准地微租,无田者则税银钱。 婚姻、丧葬、风俗、物产与焉耆略同,惟气候少温为异。 又出细毡、鹿皮、氍毹,饶沙盐绿、雄雌黄、胡粉及良马、犁牛等。 一说有城郭屋宇,耕田产牧为业。 男女皆翦髪,垂与项齐,惟王不翦髪。 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 尤重佛法。 其王以锦蒙项,着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床。 土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安息香、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15]。
这段记录中涉及了古代龟兹国的气候特点、物产情况,是关于古代西域生态情况的一种记录。 类似书写在古代类书中非常多见。
六、历代志书也是研究西域地理、历史、环境的重要文本
志书是综合记录某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也称地方志,一般来说,综合全国情况的称为“总志”或“一统志”,地方性的如省志、州志、县志、厅志、乡土志等;专志如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方面的志书。 中国历史上凡遇太平盛世,朝廷便有大规模修志之举。 当代学者高健曾经统计历代有关新疆的方志多达165种,分为通志、区域志、府县志、乡土志、兵要地志和国外所编新疆方志六大类。
比较早的记录西域的志书,如东汉时期班超之子班勇著有《西域风土记》。 此后,清代以前的西域方志类记录并不多见,唐代有敦煌残卷《西州图经》、《沙州伊州地志》、《新唐书·艺文志》录有许敬宗的《西域图志》六十卷,但已经失传。明代陈诚著有《西域蕃国志》、马理等编纂的《陕西通志》卷之十地十《河套西域》志的西域部分、张雨《边政考》(十二卷)中所见《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土地人物图》。
清代以后,有关西域的方志著作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被称为西域第一部方志的《西域图志》。 永贵等编纂的《新疆回部志》、七十一(椿园)《西域闻见录》、徐松参与的《钦定新疆识略》、和宁编纂的《回疆通志》、《三州辑略》、钟方撰《哈密志》,当代学者马大正整理出版还有《新疆乡土志稿》包含新疆四十三种乡土志。 光绪年间终成《新疆图志》。
《新疆图志》卷十六 蕃部一 中详细记载了哈萨克族分布的地理位置、生活习惯、地形地貌:
“哈萨克有左、右、西三部。 左部为汉坚昆地,右中部、右西部则汉康居地也。 隋时属西突厥,唐五德中,统叶护徙都千泉。 《西域传》云:‘碎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南,雪山三垂,平陆多泉池。 突厥可汗避暑其中。 西赢百里,至怛罗斯城。’《汉书》所云:‘王冬徙乐越匿地,至夏所居蕃内,马行七日’者也。”[16]
以上所列各类当然不是西域生态、环境记录的所有文献。 西域生态与环境研究离不开历史文献,同时,由于新疆地区,或者所称西域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不仅汉文文献史料中可以看到历代西域生态与环境的变迁,在国外一些史料中也可以看到对于新疆、西域地区的生态环境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西域生态书写审美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