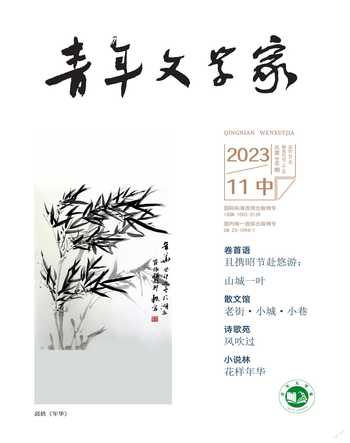十万亩槐林的美丽与忧伤
潘京
“十万亩槐林/加上十万亩沙土/再加上十万亩阳光/十万匹军马,十万吨海水/就是我的大孤岛。”这是诗人马行长诗《大孤岛》的开篇。诗人笔下的大孤岛雄浑、辽阔、神秘,有着恢宏的气象。这首诗是诗人继《从黄河入海口到塔克拉玛干》《海拔3650米之上》两部诗集之后,创作的又一首有相当影响力的力作。在我的感受中,马行是在行走中完成诗集《从黄河入海口到塔克拉玛干》的,是以鹰一样的目光俯视着大漠与雪山写下他的西藏组诗《海拔3650米之上》的,而这一次,他静坐在落英缤纷的槐林里,在参悟中构思了他的《大孤岛》。马行以十万亩槐林、十万亩沙土、十万亩阳光、十万匹军马、十万吨海水的叠加意象,勾勒出了“大孤岛”给予他的遐想与轮廓、恢宏与苍茫。
马行曾对我说过:“孤岛—那儿是我的家,那里的一切都是我熟悉的。”在这组诗里,你看不到诗人他行色匆匆的不安与焦灼,也看不到他居高临下神祇式的凝视。在这近乎禅境的静观下,大孤岛缓缓走入他的心灵世界,成为他灵魂的一部分。
马行出生在黄河北岸一个叫大马村的地方,小时候的他曾无数次向往过大孤岛。那片辽阔的土地与他们狭小的村庄相毗邻,它开阔、神秘。每到春天,大荒原在阳光下泛出耀眼的光芒,远方的田野生出浩浩荡荡的劲草。在散步的时候,他总能遇到从大孤岛方向飞奔而来的一群群骏马,它们经过他的面前向着更遥远的地方飞奔。那里的土地一望无际,那里的人澎湃着青春的面孔,那里就是传说中的大孤岛,一个令他神往的地方。后来,他离开了村庄,走进了大孤岛。再后来,他离开曾向往过的大孤岛,跟随着勘探队走遍了大漠、戈壁、雪山,从黄河入海口到塔克拉玛干,从大漠无人区到青藏高原。但是,他依旧会在某个时刻返回他的大孤岛,在这里追忆,在这里沉思。
诗人笔下的大孤岛,地处黄河尾闾,这里曾经是一片浩瀚的大海。当源自巴颜喀拉雪山湍流不息的河水将黄土高原的泥沙裹挟到这里时,在河海交汇处以气势磅礴的填海造陆运动,形成一片新生的土地。诗人用荒原特有的意象描绘他的大孤岛,用他曾经领略过的戈壁、高原,以及大漠中的气象,勾勒他的大孤岛。他的大孤岛既是荒原的大孤岛,又是天下的大孤岛;既是现实的大孤岛,又是他心中的大孤岛。
长诗《大孤岛》保持了诗人一贯开阔豪放的诗风,开篇所运用的意象分割法,是他在诗歌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手法,如他的获奖短诗《大风》:“塔里木,大风分两路/一路吹我/另一路跃过轮台,吹天下黄沙。”此诗把大风一分为二,一分给人,一分给景,而其核心在人,在人的力量与大风力量的对峙,在“我”行走于天地之间的勇气。意象分割法古已有之,如唐人徐凝的《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特点在于,用数字分配意象,《大风》中的“两路”大风;《忆扬州》中的“三分”明月夜;《大孤岛》中的“十万亩”槐林、沙土、阳光,“十万匹”军马,“十万吨”海水,在人们心中,成为大孤岛最富诗意的代名词。
“因为我来/那么多的槐花都在落/那么多的忧伤,那么多的美/我该接住哪一朵,又该安慰哪一朵。”五月,是槐花盛开的季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孤岛都会举行槐花节。第一次参加槐花节,我曾与马行同行。走在槐林里,漫天的槐花瓣雪片似的随着初夏的长风飘洒,那情境美得令人炫目。起初我以为是错过了槐花盛开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在大河吞吐泥沙而成的这片土地上,因为含碱量巨大,任何树木的根系都无法深植于地层深处。因此,槐树在这里是长不高也长不大的,它的花期十分短暂。尽管这样,槐林依旧在这里扎下根,它们缓慢地生长,渐渐地融入这辽阔的荒原与苍茫,它的花朵以顽强的生命力绽放着。五月,槐林,在诗人的眼里是美丽的,更是忧伤的。
“大孤岛再高一点就好了/最好比槐树还高一点/如果那样/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大海,一低头就能看到黄河的流淌。”生活在荒原的人都知道,曾经的大孤岛,还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大洼地。大孤岛经过亿万万年大海的洗礼来到世间,新淤地之上遗落着大海的诗意。走在这片低于海平面的土地上,你依然能够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看到散落在其中的海底贝壳。“高”在这里似乎不只是一个物理的尺度,而是马行心灵的一个期许,是大孤岛留在他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让他义无反顾地走出少年时代心中的“大”孤岛,行走天涯,找寻诗意的远方,找寻心中的方向。大孤岛上十万亩沙,不能成丘,不能成高山。它不能生长更高的树,不能有更持久的花。那缤纷的落花不是因为我们错过了花开的季节,而是它生于斯长于斯的命运。如果大孤岛再高一点呢,这浩瀚葱郁的槐树林的根是否可以扎得再深一点?它的身姿是否可以再挺拔一些?他更希望大孤岛的人,目光看得远一点。大孤岛是否可以再高一些?高到在这里能看见远方的河流和大海,看到河海交汇的壮丽与苍茫,看到一朵朵洁白的花在更高的地方盛开。马行徘徊在槐林,心中滋长着对大孤岛的幻象。
大孤岛是马行生命启航的地方。他属于它,却一次次离开它;他不属于它,却一次次回归它。他每一次走近它,都想把眼前的风景看得更清楚;他每次离开它,都想在记忆中把它记得更清楚!他忘不了那些“牧馬的,放蜂的,种树的,割苇的,开着卡车寻找石油的/再就是,与神交往的人,写诗的人”。
当午后槐林被浓郁的黄昏包裹得越来越深,马行迟疑过,要不要再往密林的深处探寻。那里随处都是他熟知的枝枝蔓蔓,熟悉的鸟鸣与虫鸣,但它们是孤独的,因为很少有人进入那里。那里有的是寂静的槐木,无声的昏暗,或许还有曾经陪伴过他许多个夜晚的孤独月光。
他想过,“我想安一个家/就在大孤岛,就在大孤岛无边无际的槐树林里”。他想像屈子诗中描写的那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做个世外的超脱者,但敏感、脆弱的心胀满不尽的忧伤。“一场风,能够吹起多少尘沙/一场风,能够吹落多少槐花”,就“坐一会儿/像棵槐树一样,而布谷鸟,却在林间鸣叫/布谷鸟/是不是在叫我?”一颗年轻的心,如何能停得下远行的脚步,又如何能停止对故土的回眸!人生又需得经历多少苦辣酸甜,才能进入静美饱满的季节。无论离开大孤岛多久,它依旧搅动着一颗心的波澜。而这或许是每一个离开或是离不开荒原的人的最真实的写照。
往深处走,去看看那些更孤独的槐树。槐树不仅仅是树,那是马行的伙伴,那是曾经的他—诗人任真,他是一个和马行一样孤独的诗人。他对马行说过,他不会离开荒原,如果荒原上只剩下最后一个诗人,那就是他。马行怎么能遗忘这些“章节”呢?槐树还是小镇那位身高足足1.9米,长得像某个领袖的镇长,是那些知青、牧马人、养蜂人……还是为孤岛献出青春的老人袁础。
“那天,袁础在槐林里/像棵槐树一样/一动不动/他的头上/不时有槐花落下/槐花落在他的头上,也落在大地上。”这一节诗的意象,让我联想到王维的《鸟鸣涧》中“人闲桂花落”的意境。尽管描写的情态、景物有别,且一为有我之境,一为无我之境,使用的句式也不一样,但槐林幽静的景色让二者在呼应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打通了古今的审美空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化古为今的可能。在这节诗中,诗人着笔老人“一动不动”,一如古诗中写春山之“静”,皆以“落”花之动景衬托。无言的落花,无言的触动。这种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而且,这里的“静”,并非古人空山澄怀之静,而是暴风雨之前的静,蕴含了极大波澜的静。从字面上看,诗人似乎没有任何抒情的成分,连浪漫的笔触都感觉不到,仿佛仅仅陈述了一个真实的场景而已。但如果你是一个有禅意的人,就会感悟到这段描写里的深意,感受到蕴含其中的“大音希声”之力。“大”孤岛,可否如它的名,能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承载,承载起我们一生的悲欢与梦想。
诗人“举着酒杯,试图找一个蝴蝶一样的人,或蝴蝶一样的一颗星”。“蝴蝶”的美丽在于它能够破茧而出,蝴蝶在这里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蝴蝶一样的人”是能够突破自身的局限,精神指向更开阔、更自由的人。可是,大孤岛是有“边界”的,它难以逾越的自闭气质,囚禁了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离开它的人,因为失去了这个怀抱而感到孤独;没离开它的人,因为背负着它的苍凉,更感到孤独。面对大孤岛,有时,你能感到一种终生不能彻底破茧的疼痛。有意象的分割就有意象的聚合,大孤岛无数意象的指向都是“我”。忧伤的是“我”,多情的是“我”,超然的是“我”,惆怅的是“我”,静坐在槐林的袁础是“我”,留在大孤岛的任真是“我”,行走于落英缤纷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
诗人品味出大孤岛所含有的“孤”的味道,直到这孤独的味道把整个槐林都染透。“槐树林/静寂如月光/仔细地听,有鸟鸣,有风吹动树叶/仔细地听,尘世是虚幻的,孤独是真实的。”刹那间,他对孤独的感受似乎有理由,又似乎不需要任何理由。孤岛在这一节有了鲜明的象征意味。他说出了它灵魂深处的孤独,那是大孤岛与他相生相契的部分。无论它多么美,在经历过它的空阔与苍凉的一代人的心中,永远都摆脱不掉那个孤独的灵魂。透过诗人对自我精神的呈现,想象力是《大孤岛》颇为显著的艺术特色,随处可见的想象与夸张,使大孤岛带上童话般的色彩:“我担心,终有一天/大孤岛会长大的,会晃荡着双腿,摇摇摆摆地/走到大海里去/如果那样,也很好嘛/大海的幸福并不比我们少/我希望大孤岛把十万亩槐林也带到大海里去/如果那样,每逢到了春天/大海上就会开满槐花。”
大孤岛会长大,会用自己的腿走入大海吗?行走的大孤岛如果把十万亩槐林也带到大海里去,十万亩槐林在春天的大海上盛开,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而隐喻,需要审美者用心去看、去想、去悟。陈超在《诗艺清话》中说,对诗人而言,整个宇宙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外界事象与人的内心能够发生神秘的感应与契合。因此,“象征”等不是一般的“修辞”“技巧”,而是内外现实的“相遇”“相融合”。诗中的形象绝不是从属的工具,它自身拥有自足的价值。至此,主客体不再区分,不是诗人外在地描写世间,而是他自身就是世间一条柔韧的神经纤维。这是诗人自始至终都在感知的大孤岛,让他充满惆怅又充满爱意,它是他心灵独享的一杯酒,他要细细地品味它,细细地感悟它。
“槐树开花时节/那个坐在槐树下的人/要么等来蜜蜂/要么等来多情的女子/要么就只能等来一阵又一阵的大风。”这一节的“等”令人浮想联翩。等待与期待,是享受孤独的最好境界。大孤岛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在这里停留是幸福,抑或悲伤?袁础,一个像槐树一样扎根在荒原的老人,他能给诗人答案吗?或许,这里本无路可走,并无答案可寻。
“我是第一百零八次来大孤岛/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爱上了这里的偏远/第二次来的时候,我爱上了这里的骏马/第三次来的时候,我爱上了这里的芦苇/第四次来的时候,我爱上了这里的飞鸟……/现在,我退隐江湖,不再说爱,我独坐大孤岛十万亩槐树林,看花开花落。”即使有一天大孤岛在地理意义上彻底消失,它也不会从一代人的心灵上消失!因为这里曾经留下人们刻骨铭心的青春与孤独。在这里长不大的岂止槐树,还有我们的情感;这里未老就已衰败的岂止槐花,还有我们未曾爱过就已逝去的人生。诗人彻头彻尾自始至终的感伤暗合了荒原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忧伤。感伤与孤独,美丽与忧愁,是我从这些章节中读到并体味到的。只是有着阳光一样面孔的诗人,能否真的修炼到“现在,我退隐江湖,不再说爱”,是否真的能“独坐大孤岛十万亩槐树林”,平静地“看花开花落”。我只看到他把荒原特有的孤独气质带到了每一个他到达的地方,带到他的戈壁滩,带到他的雪域、冰川、大漠、无人区,把他的悲悯与祈祷带到了能抵达的每一个地方,并把它们化作一首首动人的诗篇。
这首让人脱口吟咏出开篇的诗,因为众多的意象而耐人寻味,但是多年以后却被诗人自己否定了,他说《大孤岛》算不上一首好诗,他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在我看来,这首诗呈现了荒原人的心灵历程,在为数不多的描写大孤岛的诗篇里,颇有张若虚“孤篇盖全唐”的气势。这首诗中美得令人耳目一新的忧愁,透视出整整一代荒原人的精神特征。马行对荒原人命运的哲思,对荒原物象、人文诗性的表达,以及他敏锐地对美的感受力,都通過这样一次颇富灵性的书写定格在荒原的文字史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