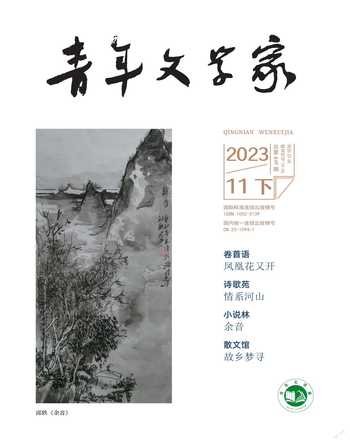屋上瓦
季大相

住有所居,它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如果连个简易的栖身之处都没有,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即使不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生活境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屋上有瓦,则是乡村人家安居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0年以前的乡村房屋,大多屋无片瓦。这不是一户人家、一个村庄的现象,而是那时乡村的普遍境况。那时农家住的都是土坯墙、草苫屋面的土草房,因经受不住雨水长期的反复冲刷,三五年过后,大多土墙便开始起裂,常常见到房子四周竖立着一根根木棒用以支撑,防止墙体歪斜倒塌。屋面上的草同样也经受不住风吹日晒、雨淋雪打的摧残,由金黄色逐渐变成灰褐色,开始发霉腐烂,用手一碰甚至成了一堆灰烬。日光或月光射入室内,呈直或斜的细线交替变幻着,看得人心里拔凉拔凉的,这并不是什么独特的美景,而是意味着未来的雨雪天要遭罪了。这种房屋的人家只能趁着晴好天气,弄点儿新草插上去,或者铺上块塑料薄膜布遮盖一下,但这种方法只是应应急而已,治标不治本。遭逢雨雪天气,屋外大下,屋内小下是常事,家里的桶、盆、碗,甚至连锅都派上了用场,一排排地摆放好用来盛接雨水,总不能眼睜睁地看着家里被淹成小河。雨水滴落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伴随着大人的叹息声、婴幼儿的啼哭声,似在演奏一曲嘈杂的交响乐,在这难挨的日子里,自是引得人愁上加愁。若遇上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时,一些人家的室内既无干燥之地容身,又破屋歪墙的险象环生,只能拜托邻居、亲朋接过去暂住,或者直接在家门前搭个棚子落脚,条件虽简陋,心头却多了份踏实。那时的村里,一年四季都能见到有人家在翻盖房子,结构还是土坯墙、草苫屋面。危房拆了建新房,待新房住成危房又得拆建,几年的微薄积累,拆建一次房屋又被花个精光,却又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我是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农家子弟,住过土草房,也和过稀泥,脱过土坯,也曾一边端着脸盆、木桶等容器来接雨水,一边口中喋喋不休地咒骂天气无常。母亲听了,便会生气地责备我,不要抱怨老天,骂老天会遭天谴的。此刻,沉默是最好的应对之策,如果出言顶撞,她甚至还会点炷香,跟随着袅袅升腾的青烟,双膝跪地,双掌合拢,不停地磕头祈祷,“菩萨原谅,小孩子不懂事,要怪罪就责罚到我头上……”后来,我不再说这些被母亲认为“大逆不道”的话,她也不再因我而烧香跪拜菩萨了。
我的父亲是名老革命军人,曾在南京等大城市待过,经常给我们讲述他当年的一些见闻,包括大城市里的楼房瓦房、电灯电话之类的事物,让我小小的心灵为之神往,满怀憧憬。一次,父亲带我去县城,所到之处满目新奇,见到了楼房、砖瓦房。那时的楼房、砖瓦房均是清一色的青砖墙体,苫顶则大多是小瓦一排排铺就的,不知是什么年月盖的,有着一股年代久远、古老陈旧的视觉冲击。也有少量青瓦苫顶,隐隐地透出现代气息。在我那时的认知观念中,它们无疑是空中楼阁,是水中花、镜中月,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年幼的我在羡慕之余,也生发出了一个梦想:哪一天我也能住上这样的大瓦房就好了。当然,这是一个埋藏在我心底的秘密,从来没有与人说过,因为那个年月,谁要在乡村里说自己将来要像城里人一样住上楼房、瓦房之类的话,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也就是说,这个念头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疑是痴人说梦,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穷”字在作怪,那时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这一代不可能把“穷”字甩掉,过上富足安身的好日子。
1980年左右,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土地的自主权,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渐渐地有了积余。正在小学念书的我,也不再受到饥饿的困扰,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于是,一些人家开始翻盖房子,这时候的房子不叫土草房了,而是叫土瓦房,墙还是土坯墙,屋面改用苫瓦,不再担心房顶因烂草而漏雨了。即使瓦坏了,插补一块上去替换也方便多了。
一天,有人上门通知父亲去公社民政办一趟,父亲问他有什么事?来人只回答说是有好事。次日一大早,父亲带着满腹疑问前往公社,中午时分才回来,没等母亲相问,他已先自开口说道:“政府下拨到公社一批质量稍逊的瓦,公社安排给我们这批老复员军人改善住房条件,每家一千块,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当兵人的一片心意。”父亲的言辞语气间颇有几分自豪感。过后不久,父亲借了两台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请了驾驶员,奔波二十多公里到指定砖瓦厂将这批瓦运回。瓦体上的裂缝、缺角等破损处灌滴水泥浆抹补,原本就凹凸不平的瓦面,又多了些疙疙瘩瘩,像人体伤愈过后肌肉上扭曲的疤痕,醒目且刺眼,可见它在打样、烧制过程中的创伤也是显而易见的。父母一合计,家里的土草房虽然墙体依旧牢固,但屋面已开始漏雨了,干脆将草顶揭掉,换苫上瓦。第二天,父亲就忙着去请帮工和瓦匠。几天过后,土草房成了土瓦房,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了金凤凰。可没过多久,屋面又出现漏雨的现象,原来,水泥浆抹补瓦缝的地方发生酥化,裂缝出现二次裸露,导致雨水顺着缝隙淋落下来。屋内虽不像外面那样哗哗地大下,滴答、滴答的断线般小水帘却也困扰人,就连吃顿饭都得不停地挪动桌凳来避雨。
母亲埋怨道:“不花钱就是不行,才几天啊?又漏雨了。”
“好孬是瓦,不比草苫强多了,以前下大雨,屋内都能养鱼了。”父亲并不认同母亲的说法,看似理直气壮,其实也显得底气不足。天晴的日子,父亲会架梯爬上屋面,查找漏雨的地方,插块新瓦换下破瓦,或铺上塑料薄膜布,隔断瓦的缝隙,再下雨也就不漏了,但是治标不治本,塑料薄膜布禁不住风吹日晒,不久就会风化,过段时间就得更换一次,挺麻烦的。
哪个庄上如果有一两家冒尖户(意指富裕户)能盖上砖瓦结构的房子,很快就传遍十里八乡,名头在外,响亮得很。庄上的人在外与人拉呱(方言,闲聊),常有人问:“听说你们庄上某某人家盖了新瓦房,是真的吗?”提问者难掩内心油然而生的惊讶、羡慕之情,回答的人脸上也倍感荣光:“这还能有假?瓦房亮堂呢!”
经过几年时间筹备建筑材料,我家于1985年秋季兴建了三间砖瓦结构的房子,在庄上算是冒尖户之一。记得我家搬入新房那天,我异常兴奋,直到黎明时分才入睡,还做了个美梦,梦到许多人在我面前竖起大拇指,夸赞道:“了不起啊!你家住新瓦房了。”我不停地点头,脸庞绽开成一朵花。
在家家户户搭建土瓦房的初期,瓦的实际需求量并不大,但市场竞争力很强。生产厂家除了在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广告宣传,加大推销力度外,还苦练内功,敢于在产品质量上“亮剑”,直接将生产厂家的名称刻在瓦体上面,用户拿起瓦一看,就知道是哪里出产的,这是走以质量赢用户、求生存的倒逼发展之路。除了本地产品外,还有来自山东、安徽等地的外来瓦,它们显著的特征是瓦体上无一例外地印刻着厂家的名称,与瓦融为一体,字迹清晰,一目了然。
“人家的瓦抓在手里重沉沉的,结实周正,不易破损漏雨。”经一些见多识广的瓦匠推荐,加上用户之间相互打听,起到了口口相传的传播效应,时间稍久,产品优劣已在大众心目中有了定位。一些产品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另有一些产品则被淘汰出局,失去市场。
早年间,乡村人家住上土瓦房,就能被人高看一眼,主家的儿子找媳妇也不是难事,自会有媒婆主动登门,牵线搭桥当“红娘”。若男方自身条件差点儿,如有跛脚之类的小缺陷,托个媒人说亲,媒人也会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向女方家介绍男方家条件如何如何的好,并拍胸脯保证嫁过去有福享,不会受罪,很容易就能促成一桩姻缘。后来,三间砖瓦房成了标配,如果谁家没有三间砖瓦房,儿子谈对象绝对是老大难,因为仅从外面一看,瓦房都住不上,说明这家穷啊!有几个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吃苦呢?事实亦然,自1985年以后,农村翻建新房基本上以砖瓦房为主,瓦的用量由此大增。当时的道路路况差,且车辆物流成本高,如果走公路运输的话,产品则因成本原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我的家乡洪泽因洪泽湖而得名,水路交通便捷。由此引发一个有趣的现象,家乡的农户建房用的砖头几乎全部为县内砖瓦厂生产,而瓦则是清一色的外来产品,本地的砖瓦厂只产砖而再无片瓦出厂,所以提起本地砖瓦厂实则是有砖无瓦,浪得虚名了。
那些外来厂家卖瓦的营销方式很单一,却很实用,现在回过头去看,无非就是立足一个“抢”字。这个“抢”字可以理解为抢时间、抢市场,不是有“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吗?用最短的时间把产品卖出去,才能达到节约人工等成本,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庄前有一条叫浔河的河道,它开凿于京杭大运河同一时期,是大运河的一条支线,上游连通洪泽湖,下游直达白马湖,綿延数十公里,是一条横亘东西的黄金水道,运输船只来回穿梭,热闹繁荣。这源于水运除了节约成本外,还能使产品免受长途颠簸(当年多为砂石路,崎岖不平),损耗率很低。往来船只中有部分就是瓦的运输船,船停靠到码头,一块长木板搭在船头和码头上当桥板,由挑夫从船上将瓦挑上岸,按一摞五十块或八十块不等的数目码放好。我很钦佩挑夫,他们走在桥板上,桥板像弹簧一样上下起伏、晃荡,有一种随时可以将行走其上的人颠下河的架势。我看着就胆寒,脚下不由自主地打起战来,可那些挑夫一点儿也不在乎,脚底像粘连在桥板上一样,随着它的节奏起伏迈步前行,有的打着号子,有的哼唱着小曲,哪里是在卖苦力,简直就是来享受快乐的。事实亦然,那个年代有力气没地方打工挣钱的强劳力多得是,壮劳力不稀罕,但不易得到这份挑夫的工作,它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挑夫都是码头附近的人,外面的人想插一杠,任你通天本领也没门儿。毕竟,谁也不愿从自己的饭碗里分出一杯羹。
从船上将瓦搬运上岸,接下来就是卖瓦了。大多船主也是卖瓦的商贩,卖瓦也和其他生意一样,需要一个交易过程,通常与当地当前建房户多少等因素直接关联,需求量大的话十天半月卖完一船货,慢一点儿的一个月也难清仓。对货主来说,根本耗不起这么长的时间。于是,卖瓦这个行业也衍生出中间商,就是通过批发的方式,从货主那里拿货,然后以零售价格卖出赚取中间差价。记得浔河码头边住着一户与我同姓的本家兄弟,人们都习惯叫他“阿三”,因他在自家兄弟五人中排名第三。他因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瘫痪多年,出行只能依靠双手撑着两只小板凳挪动身体,但他凭借毅力自学了小学课程,在乡亲们的眼里他又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他虽然没有娶上媳妇,靠做柴席、编竹篮为生,倒也是衣食无忧。对了,瓦堆放的位置属阿三家的地皮,他说了算。
初时,货主与阿三达成协议,瓦堆放在他家的地皮上,按月支付一定的租金。接触久了,彼此处出了感情,货主与阿三商议,“干脆你也来做卖瓦的生意,多赚点儿钱。”二人一拍即合,就这么简单地达成了合作关系,原本瓦上岸堆放的是阿三家地皮,现在的瓦则成了他手里的货,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老板。当然,他手头没有余钱当本钱,都是先卖瓦,后付货主的货款。一来二去,阿三的手头也逐渐宽裕起来。周边人羡慕地说:“他家住了个风水宝地,给他带来了福气。”
卖一块瓦到底能赚多少钱,这始终是个谜,阿三至死也没有透露。也许是暴利吧!他怕被人咒骂自己没良心、黑心肠。不过,卖瓦时他那张嘴很有迷惑性,天花乱坠,适时地掺杂些奉承、吉利的言辞,也不失为“生意经”。比如,有人家为了儿子找媳妇而盖新房的,他张口就来,“大瓦房,亮堂堂,小媳妇进门喜洋洋,老板你快发喜糖……”他这一番即兴说辞,直入买家心窝,既让人家觉得舒坦、受用,同时也让这单生意站住了脚,之后就是直接搬瓦过数,付钱装车,往往是在说笑中轻松地完成一笔交易,让买家连出门盘算,货比三家的计划也随之抛置脑后。又如,“都是前后庄的,我还能多赚你钱啊,糊个口就行,每块瓦少收你一分钱”,遇到村邻或亲友,他又会把人叫到一旁,悄悄地说,“你们买的瓦,每块比别人再少五厘钱(0.5分),我保个本就行,还能真赚你们钱啊!”熟悉的人都说他是蜜獾,甜死人的嘴,辣死人的心,赚你钱还让你感激他,认可他对你好。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谈论一番后,又下一个结论,卖给我们的瓦总归比别人便宜了点儿,还能随便挑,阿三对大伙儿还是不错的。
阿三卖瓦的生意一直维持到1998年前后,随着公路运输日益发达,大量的外来瓦涌入,加之市面上出现了琉璃瓦,他的瓦销量日衰。阿三本是个重度残疾人,长期与病魔作斗争,最终还是在跨入2000年世纪大门后不久离去。他留下一个本子,记下了一些人赊欠瓦款的账目,有的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旁边还会留几个字:某某家太困难,免去;给就收下,不还也免了……名单上的人家大多是困难户。阿三与瓦,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是人们闲暇聊天儿时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诸如,有女人看上他善经营的头脑,想嫁给他,结果因他身体原因而不了了之,他终究未能脱单。还有他自食其力的精神品质,一直是庄上人家教育后辈的身边励志人物的鲜活教材。这也许是人们怀念他的特殊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