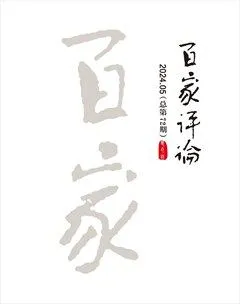历史转折中的启蒙神话及其限度
内容提要:在《长征》一诗中,骆一禾对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和赞颂,凸显了其与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某种错位。但是,骆一禾将革命高度美学化的思路又显现出其间的强烈共振,而在这种复杂关系当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骆一禾的“中国视野”。通过对其诗学理念的梳理和阐释,分析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出:骆一禾既承接和转化了20世纪的革命资源,又将其表述为“绝对的现代”神话,二者之间的连接点则是强烈的“民族新生”意识。这暗示了80年代含混、暧昧、充满歧义的过渡性特征,也体现了骆一禾作为80年代诗人的典型性。
关键词:骆一禾 新启蒙 革命 中国视野
引言
重读骆一禾的诗歌与诗论,不难发现其宏大的文明视野、世界想象和对现代文化、线性进化论思维的批判性立场,对浪漫主义诗学的提倡与80年代诗歌主潮的某种“不合时宜”a,但其所携带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激情又深深契合80年代的文化氛围b。同时,其在诗中对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的强烈肯定却又似乎与“告别革命”的时代诉求并不相称c。由此,并非仅作为一个诗人(狭义的诗歌创作者),更是作为“新启蒙”知识分子的一员、作为“正反社会主义经验和现代文明的产物”d,骆一禾在何种意义上想象中国;或者说,经由与80年代种种思潮的相悖或契合,骆一禾提请着何种文化资源、达成了怎样的自我认同,又与历史和现实建构了怎样的想象性关系,其间蕴含着怎样的时代信息?本文试图从其《长征》一诗e及其他文本切入,对上述问题做出简要回应f,并希望由此勾勒、反思其“历史与文化意识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视角所造就的阐释世界方式的独特性”g和局限性。
一、对革命的启蒙式书写
对于“长征”这一在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骆一禾在诗中称其为伟大的“历史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心脏”,既区别于“军阀和绅士们”和“1840年——1940年”“所有的对外战争”,也区别于“农民”历来的生存状态,标志着“一种新生”,“写在亚洲中部”和“世纪的内心”。而在该诗的表述中,“长征”之伟大首先即在于“把历史教给了农民”。如果说“由于无产阶级的出现才使人们意识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h,那么也正是由于把握了“历史”的“农民”主体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的独特性与有效性。如果参照李泽厚在其影响深远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将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与“政治救亡”相对立的二分法,骆一禾的这种表述无疑显现出了与8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思潮的明显错位。而从这样的历史体认出发,骆一禾对世界的想象也就不同于现代化视野中的“先进—落后”想象,而是被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启发/表征的“第三世界”,并写道:“望着那些久已去世的领袖/第三世界的英雄/在这个年头我还能说什么呢”。由此,骆一禾颇有意味地区分了两类人:一是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中作为中心和理想镜像、在冷战结构中作为世界另一极乃至参与左翼革命的人,二是与中国当下“在和平里待腻了”而“不懂历史”的“才子们”,骆一禾甚至将其类比为“军阀和绅士”“土财主的军绅政权”。或许可以说,骆一禾在此展现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想象,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这首诗的表述,骆一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强烈的关于“中国新生”的意识,并在与中国当下现实的对比和批判中明确地提请着革命的精神资源。但复杂之处在于,这一“中国”既非所谓“封建历史”的中国,也并不是以美国为范本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中落后的中国和“文革”这一社会主义道路极端化的中国,而是以“长征”作为标识的、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初期的“中国”。
由此,骆一禾相对于“新启蒙”思潮的独特性似乎渐次显露,但联系上文所提及的“长征”“把历史教给了农民”的表述,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说法凸显的首先是革命的启蒙与乌托邦的面向,而非以暴力破坏与重建秩序的现实面向i。同时,谈到“启蒙”势必涉及谁启蒙谁的问题,而在骆一禾的诗中,充当这一启蒙者角色的是“长征”而非具体的革命者或革命知识分子。如果参照毛泽东在农民落后的、封建性的一面和进步的、革命性的一面之间做出的著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二者在主语和主体想象的微妙错位之间所蕴含的丰富意味就更为明显。也就是说,这一对“长征”的人格化、主体化和本质化想象所内含的问题意识,已然不再是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必须完成的革命动员和政治询唤、进而建构“人民—国家”的历史任务,而是经由对革命历史的重新叙述与评判,在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再次启动某种整体性的中国想象、并确认这一想象的坐标系的方式。
进而,我们可以引出骆一禾赋予“长征”的另一层内涵,即“中国的心脏”这一身体性修辞所携带的“生命——中国——长征”同构的意味。“处在长征的影响中/不等于了解长征/正像知道苦难/不等于了解苦难/——这种不同是绝对的/哲学的和血肉的”。显然,经由这种“绝对的/哲学的和血肉的”区分,“长征”在此进一步占据了某种世界观的地位,而它所天然地呼唤的一个重要概念“人民”,则被骆一禾描述为一个“经历了频繁的战争与革命”却“未完全兑现”的“历史地发展的灵魂”j。由此,一个“继续革命”的主体诉求似乎呼之欲出,也可以说:在“中国新生”的强烈意识中,骆一禾将由“长征”所标识的革命视为一次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世行动,这与其将写诗视为“创世”k之举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诉求则在于重建对于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人”。其间值得关注之处在于,80年代的“革命”已然成为一种体制性话语,而如何经由对这一话语的重返与重估,将内含其中的乌托邦目标从体制化的权力机器中剥离,进而重新确立革命的可能性与有效性,或许也正是骆一禾的诗与诗论所蕴含的某种想象。这与丁玲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有相通之处,即“尝试通过自我改造和主体修养从内部克服这种裂痕,并将自我提升到另一个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她始终将‘革命者的自我’视为一个未完成的、展开中的过程。”l
具体到骆一禾这里,这一未完成、或曰持续生成的状态同时被赋予“人民”和“我”,也正展现出其“中国视野”,而这一论述源于其诗论中一个先在的规定,即个人、进而是抽象的人的生命必然处于不间断的生成状态,逐渐走向“滋长、壮大和完美”m。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生成当然具有丰富的可能性,进而包含深广的历史容量。而在骆一禾的论述中,这一抽象的“新人”诉求,其实最终落实在了“新诗”、进一步说是“中国新诗”的身上,由此,骆一禾强调诗歌的文明价值,并认为其应该也能够如古希腊史诗、神话或希伯来神话般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奠基性的价值准则与力量n,而这种诗歌将刷新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并“伴生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进而塑造“中国大地”所需要的新人o。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骆一禾提出“新诗意识”的说法:在80年代后期“后浪推前浪”的诗歌现场,“古典之美和现代之美同样经受着新诗意识的转化和锤炼”p。“新诗意识”显然是这一表述中的主体,那么,何谓“新诗意识”?参照骆一禾的相关论述,或许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于新生和杰出的中国诗歌的呼唤”,并致力于“使民族的灵魂舒张发展”q。在这里,民族意识的自觉被同构于诗歌意识的自觉,同时,借助这一“生命——诗歌——中国”的坐标系,骆一禾也同样对五四进行了某种重述。
如果说80年代通过“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建构了自身最大的神话,即把自己讲述为又一个五四,并以此在所谓“现代性”的脉络中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r,骆一禾也部分地借用了这一话语策略。具体来说,骆一禾借用鲁迅的表述,将80年代指认为与五四同样充满紧迫感的、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s。由此,骆一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事实上“阐扬的是对于文字、语言的精神看待的态度”t,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标志的新诗之所以确立,则“是由于它隶属于白话文运动而成为伟大的开端。也就是说,新诗由一个伟大的文化运动(也是救亡运动)作为标志而立极”u。显然,五四这一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在此种表述中被高度诗歌化、美学化了,而“隶属于”这一行动的新诗所携带的能量,则不仅是“艺术”的,同时也是“政治”的,即“它替代自己的批判对象而成为新的政治理想的化身”v。与其说,这种生命本体论式的历史观与诗歌观,超越了将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理解方式,将纯粹的审美原则扩大到社会与历史中去,并以此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重塑和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进而重新想象、设计中国的未来,毋宁说,这种与激进的美学理念相伴生的“历史感”,通过“诗歌——中国——新人”的同构而试图作用于“普遍”的个人生命及其感性w,进而召唤着那些漂浮于特定时空中、携带着乌托邦冲动的个体。这种美学化、审美式的解放方案中或许携带着80年代“诗化哲学”的身影x,暴露出骆一禾作为“新启蒙”知识分子的重要侧面,同时,这一“内面的人”与文学(诗歌/审美)和“中国”的同构,也清晰地展现出了骆一禾的诗及诗论作为典型的现代文学的特征y。
因此,正如上所述,与其说骆一禾所召唤的是中国革命,不如说是对整体性的民族启蒙的想象(两者也正是在塑造新人、改造民族的层面保有历史逻辑上的契合),而诗人、诗歌则在其中被赋予了结构性的重要位置。但问题在于,骆一禾将革命重新命名为对民族的启蒙,一方面遮蔽了革命和民族的复杂性,简化了革命对革命者/革命知识分子与民众、社会在不断变动的历史语境中彼此纠缠的张力,也抹去了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对新的伦理关系、社会组织的探索与困境;另一方面,其将革命书写为对民族和人民的启蒙,认为民族、人民和“我”都始终处于持续生成的状态,但却并没有回应这种生成的条件、路径和方式究竟是什么,而是将之描绘为想象性的乌托邦,也因此,这一想象在理论层面充满了不稳定性。所以,骆一禾才需要塑造一个绝对、本质的关于“生命”的神话,来支撑这一论述,即其所谓“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z。
二、“生命诗学”与神话式的启蒙主体
骆一禾将自己的思想体系称为“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而一个关于此的简单描述是:借用弗洛伊德对人类意识结构的分析与荣格对“原型”的相关论述,骆一禾提出:在生命的整体构造当中,“自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定点”,而是“‘本我——自我——超我’及‘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双重序列整一结构里的一项动势”,因此,历史由无数生命实体构成,而每一实体都存在着展现“全体意识”的潜能,即同时含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处于一种潜在的“集成状态”,并催动自我的“不断成长和发现”。进而,骆一禾提出了“博大生命”的命题:“指那些说出了大文化风格中主导精神的导师的总和”。也就是说,作为“复合体”的“博大生命”仍需经由个体来完成,而个体的不断成长则是孕育“博大生命”的唯一途径。具体到骆一禾在其诗学思考中提出的“诗歌共时体”概念,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即不同于一般线性文学史观中的代际更替图景,骆一禾认为诗人是“置身于具有不同创造力型态的,世世代代合唱的诗歌共时体之中的”。而组成这一“共时体”的,则是每一个真正的诗人所创造的独特的“诗歌心象”,即诗人将相同的词汇转变为“不同的语流和语境”和“有构造的诗歌语言”时,展现出的各不相同的艺术思维和对生命的感知。也就是说,文字和语言本身并无意义,而“诗必然完成在语言创造中”,只有通过“生命自明”/加速燃烧的生命的力量将语言置于诗歌的上下文中,“把经历、感触、印象、幻想、梦境和语词经沉思渴想凝聚,获得诗境与世界观的汇通”,语言方能重建与存在的联系而显现出自己,诗人亦由此完成自己对诗和生命的独特贡献,并在其间“生长着他的精神大势和辽阔胸怀”。
显然,与其说这是一种自成一脉的诗学表述,不如说是80年代流行的诸多理论语言的一次集中展示,而其间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的身影尤为明显,只是将其由马克思和康德而延伸出的关于“实践”与“积淀”的表述,改造为了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当然,也正如李泽厚将“人类总体—个体”这一对称结构的焦点移至“个体”,认为个体的“现实性早于和优于”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普遍性,从而将这一理论启蒙化;骆一禾同样将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的意识结构的分析,转换为了“个人”所具有的呈现生命“集成状态”的巨大潜能,同时也将《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对“传统”的理想秩序的强调,转换为只有“个人”发挥自己内在的生命力才有望加入的、有着各不相同的创造力型态的“诗歌共时体”,进而将上述理论启蒙化,在一个先验性的主体结构中,为个人话语预留了一个相当关键的功能性空位,并借此完成了关于“人”的本质论述,将这一具有完整主体性的个人放置于一个完满的想象性关系当中。
由此可见,骆一禾的诗学体系所关切的并不仅仅是诗学问题,而是有着回答“何为‘人’/‘人’何为”这一问题的冲动。在骆一禾的论述中,这一体系是对现代理性及其造就的原子式个人和后现代式碎片的超越:现代社会主客体的拆分使人脱离了“他的基本状态”,自我中心主义则进一步使内心由一个“世界”坍缩为“角落”,进而使人失去生命力,具体到诗歌层面,则是以比喻和意象的拼贴代替了真正的创造力;而生命的运动则是另一种状态,其间蕴含着以创造力为基点、超越现代主义思路展开写作的可能,并最终决定新诗的命运,当然也将刷新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由此而“伴生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塑造新人。
在此,“生命”既是意义的起源和动力,也是归结。这当然可以说是启蒙的加速度所带来的必然思路,然而,这种加速度如何与相对稳定的日常伦理对接,如何落实在切身的主体建设过程中,而不是单纯强调主体生成的潜能?骆一禾的“生命哲学”并未回答这样的追问,而是通过对一系列概念的辨析,悄然绕开了这一对20世纪中国革命构成过重大考验的问题。
譬如其将“文化”区分为两种面向:一是精神觉醒的生命历程,它的活动构成文化的“根性”,不同的文化乃是生命活动的不同途径;一是“习俗、知识”等文化形式,仅仅是文化的外壳和“僵死的制度”。通过这种区分,骆一禾将生命从文化中剥离出来,赋予其本体论的意义,由此得出结论:“文化之死并不注定生命之死,否则就将文化与生命这种命运的、人文的东西变成了逻辑的、自然遗传的东西。”从这种生命本体论的观点出发,骆一禾又将传统文化明确区分为:“本土生命”/“本土精神”和“传统文化”两类,前者蕴有创造力,而将前者归入后者则是传统文化的持有者即传统文人们被统治者奴化的逻辑。再譬如其区分“日常”与“现实”,而“现实”之所以不等于/大于消磨自我的“日常”,也正在于个人生命得以与其构成一体两面、互相参与和生成的状态,而如果说骆一禾由此经验着“非现实的日常”或想象着真正的现实、历史,那么,这种区分也并非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涉骆一禾对“何为现实”的想象和文化诉求;因此,在其对群体性的“人”展开书写时,也就将之区分为“庸众”和“人民”两副面孔,而“现代意识”的来源也从外部的启蒙转向了内部的觉醒。
显然,这已经不是“启蒙—被启蒙”的单向关系所能完全涵盖的一种生命意识。如果联系20世纪中国革命对新文化运动的超克来看,不同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单向输出与改造,前者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之间积极寻求一种良性的辩证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必须深度介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具体结构和现实经验,并召唤出其中大多数个体和群体的革命性,同时也会在不断的探索和缠斗中,校准自我的身心状态,磨合出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相对合理性的实践方式。可以说,这是一种双向的启蒙和改造,也正是这种辩证关系形塑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但是,骆一禾对革命的启蒙面向的强调,对这一点并没有充分的关注,而是如上文所述,在启蒙的思路中迅速将革命人格化、美学化了。
这种思路无疑过滤掉了对革命经验中诸多含混、幽微的历史遗产与债务的省思,当然,这也和骆一禾对“民族新生”的整体性构想有关。在这一构想中,与其说“生命”作为骆一禾的诗学体系当中释放批判能量、构造乌托邦的原点而存在,不如说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认知装置,并由此过于笼统地剔除了其辨析出的两极之间广大的灰色地带。也正因此,历史才能被化约为不断循环的“死局”,而这种化约在以循环论的叙述带来某种历史纵深和洞察力同时,事实上也预设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结论,进而受制于此,封闭了对历史细节的进一步考察与体认,更难以使骆一禾对塑造这一认知装置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机制产生充分的反思,也无助于对80年代何以呈现为如此面貌展开细致、切实的剖析。
进一步说,骆一禾经由这一特定的认知装置,将“立人”的要义聚焦在“生命”的生长、壮大之上,并由此讲述了一个关于“新人”和“生命”的神话,试图以此超越现代理性个人的局限,但悖谬之处在于,这一神话本身即是现代的发明。也就是说,在骆一禾的思想脉络中,存在一个真正、理想和绝对的现代,作为历史的远景和终极目的,经由诗歌及其所谓的“诗歌共时体”,被转化为了强烈的当下感性经验。依循这样的思路,主体可以经由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和汇入,直接完成自身的建构,而无需从自己的现实经验和具体处境出发,在反复磨砺中校对自身与现实的结构性关系。
在今天看来,这种高度美学化的思路当然并不如其自述的那样有充分的真理性,反而携带着在旧的价值观念退场、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历史过渡期,基于主体的不稳定状态的“有限”合理性,但在彼时的认知结构所带来的特定视域和对焦方式中,诗歌/诗人的建设性意义及其批判对象的不理想都被放大乃至绝对化了。无疑,这种神话式的叙事乃是基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动,那么必须追问的就是,当这一启蒙神话、生命神话被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其间真正的剩余物究竟是什么?
三、“中国视野”与“非政治的政治”
事实上,在骆一禾写于1981年的一首诗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表述,即“别离开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的土地”和“晨昏交替的时分”“来猜测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民族艰难造就英雄的混沌”,此时“一个新的社会刚刚被自然怀孕”,“每一个人……就是我们的整体”,而其间的抒情主体则是“用血液和体温”“织补”“残山剩水”的“我们这一代”。这种将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同构,经由全称代词的使用呼唤关于“祖国”的集体认同的修辞方式和使命感、代际意识、个人的主体意识,固然都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经典话语,但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其与新启蒙知识分子的一个极为有趣的错位:“我们这一代”的使命乃是“织补残山剩水”,而非告别“废墟”、迈向“新生”;同时,“织补”所联系的实践中的主体状态和具体社会构造中的身心体验,也有别于“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中高度神话式的“生命”。如果联系其对“五四”和“长征”的修辞化表述,似乎可以梳理出一个有趣的历史脉络,即“‘我们’织补残山剩水——‘中国文明’寻找新的合金——‘中国’新生”,其间的主语从“我们”到“中国”的微妙转变,或许也暗示出,随着80年代历史脉络的推进,对部分知识分子而言,整体性的启蒙冲动逐渐代替了切实、精微的实践和改造方案。
简言之,这种历史体认的逻辑在于,无论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织补”,还是以“长征”所标志的“新生”,都意味着一个坚实的主体位置已然存在,而“寻找新的合金”的命名,却将五四与80年代的中国主体标示为“未完成状态”。如果说“五四——长征”由此而存在某种连续性的话,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中,80年代被命名为五四,则意味着如《长征》一诗所表露的,对于后革命时代的到来和冷战的终结、“第三世界”的退场,骆一禾有着明确和不无痛切的体认,而当这一体认与在80年代末消费主义带来的震惊体验合围,将80年代命名为“五四”,也就包含着直面“告别革命”的现实经验和“朝向未来”进而重新打开革命所携带的乌托邦激情这一双重面向,而由于8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促使革命发生的历史结构已然消失/被压抑,作为另类现代性方案的革命在这里不得不作为幽灵而借助一个高度本质化和美学化的“现代意识”回返。当然,这一回返能够成立的前提依然在于,革命与现代共享着某种对于“新人”进而是新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也可以说,这一想象正是缝合“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之缝隙的入口之一,上文所涉及的骆一禾的一系列表述,未尝不可以在这样的逻辑中理解。这意味着80年代历史转折中的知识分子所携带的不仅仅是以西方/现代为参照系的、对于更理想的生活图景和社会结构的想象,更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变动中的某种整体性诉求,换言之,80年代的社会能量并不是一种抽象、无背景地朝向自由和开放,而是乌托邦式的个人解放冲动和国家社会的转轨相耦合的定向迸发,而在这一过程当中,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因素,其存在与民族国家本身息息相关。
具体到骆一禾这里,其在“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中,正如上文所述,事实上以抽象的“生命/精神”之名悬置了作为具体行为方式和历史经验的传统,进而既反对传统中国的神话,同时也通过对现代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后现代的碎片化的批判取消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史进化论的合法性,并由此抽空了“现代”本身的历史逻辑和内容,将塑造新人的所谓“现代意识”绝对化,或曰将解放的目标寄托于某种“绝对的现代”/“现代的神话”,并在基于此而组织对于现实的批判能量时,悬置了层叠于现实经验细节中的含混与复杂。这里蕴含着卡尔·曼海姆所批判的某种极端和片面倾向,即认为“只有在乌托邦中和革命中才有真正的生活,制度性的秩序总是不断衰落的乌托邦和革命所遗留的邪恶残余。”而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这一逻辑事实上无法回答“现代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如果可以借用“纯文学”的命名,将该逻辑指认为“纯现代”的话,那么,抵达“纯现代”乌托邦的路径,在这一脉络中正是由某种自足、完满的“纯文学”或曰审美想象所造就的。已经有论者指出,海子、骆一禾的美学理想和刘小枫的“诗化哲学”渊源颇深,但正如贺桂梅在将“诗化哲学”指认为“纯文学”的合法性得以建构的知识谱系之一时所说,“这种‘非政治化’的诉求本身即与现实世界处在一种紧张的‘张力关系’当中,而其政治性也因此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骆一禾而言,或许这种“非政治的政治”更富意味的地方在于,除了以诗歌想象浪漫主义的主体形象/以浪漫主义的主体形象想象诗歌,他也同时以这样的方式想象着中国乃至世界。
进而,如果说80年代确实存在关于“落后的中国”的叙述,并带来了某种处于历史和未来之间的焦虑的话,在上文论述的基础之上,骆一禾对于进化论历史观的批判和对“共时体”诗学的强调,就有着另一重意味,即“克服历史的时间差”从而走向、参与世界的一次想象。但反讽之处在于,这一由不同的“创造力型态”构成的、“世界诗歌”意义上的共时、多元的存在,事实上是有核心的,换言之,其内部是有秩序/等级的,而处于这一秩序顶点的是但丁、歌德、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西方文学大师,固然可以由此而指认骆一禾的文学资源,但更为重要的是,判定这种秩序/等级的理由和标准在于,这一“共时体”所指涉的从来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文体的诗歌,而是与诗歌同构的生命/精神世界,即其所谓“在这个层面里自我的价值隆起绝非自我中心主义、唯我论的隆起”,而是“生命自身”/“生命构造”,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和雅斯贝尔斯意义上的“大全”/本原。由此当然可以引出对骆一禾诗学的某种存在主义解读。但如果由此重审骆一禾的“共时体”诗学,更值得注意之处就在于,这其实是一种以“多元”“共时”为名的一元、本质化论述,而所谓“走向世界”,在此并非“平行移动”,而是意识到自己身处“共时体”当中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生长。其内在逻辑或许正是张旭东在讨论80年代现代派美学成就的历史特性时所指出的“双重的摹仿”,即“在空间维度上,具体讲在形式创新和审美游戏上,它摹仿了一个更‘现代’更‘世界’的艺术建制和哲学建制,但在自身‘政治无意识’的表达和叙述上,也就是说,在时间维度上,80年代文艺和文化思想讨论却在象征和‘自律性’层面摹仿了新中国前30年历史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创造性和内在韵律”,也就是说,在这一由审美话语开启的内部自律空间中,所填充的依然是民族、国家、文化甚至文明等集体意识和集体经验,而这一话语的操持者也往往“不假思索地把个人探索的主体性等同于集体行动的主体性”,由此,在骆一禾的表述中,这一不断发扬感性血肉的生命力同时也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感知,得以以诗歌/审美为媒介,将革命中国的宏大叙事与主体意识“解码”并“再编码”至一种以“现代”为名的意识形态之中,“配合完成了现代化国家和全社会的期待和目标。”
当然,也正是由于民族国家话语的始终在场,这种作为“非政治的政治”的审美想象,并不仅仅是所谓“内面的发现”的产物,正如姜涛所说,“新诗、新文学的起点”也从一开始就和“鲁迅思考的民族‘心声’问题、晚清以降仁人志士对于‘心之力’的强调,以及五四新文学对于情感的普遍性、真挚性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具有某种整体感和社会性,和20世纪的‘时代精神’有很强的内在同构和共鸣”,这当然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境遇和历史体认直接相关,而由于80年代将自身建构为另一个五四,也就内在地继承了这一感知。这或许也是骆一禾再次提请革命资源的原因之一,而革命精神所携带的“不断寻求‘远方’的精神动力、为了崇高事业‘献身’的激情、对于更广大人群的关切等”面向,和被革命塑造的“中国道路”“中国形象”,既被骆一禾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所继承,也间或是对“‘纯文学’的知识谱系”的梳理与批判并不能完全涵盖的、80年代中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在精神结构之一种。
注释:
a有论者指出:“如果考虑到80年代的中国诗坛对‘现代主义’一边倒的热潮这重背景,骆一禾、海子的诗学理念和文学史观念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下颇有“逆流而动”的意味。骆一禾、海子都提倡浪漫主义并质疑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诗学,这是80年代中国作家较早地从文学本身——而不是意识形态——角度反抗现代主义的主张之一。”李章斌:《“新浪漫主义”的短暂重现——简谈骆一禾、海子的浪漫主义诗学与文学史观》,载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1年第1期,第1页;“毋庸讳言,骆一禾、海子的诗歌趣味迥异于当时乃至而今的文学风尚,他们的写作也与习见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直接构成一种对峙。似乎可以说,他们所要掀起的是一场‘新浪漫主义’运动,这样说也大致不差。”姜涛:《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重读骆一禾的诗论》,载于《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第59页,收入姜涛:《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另收入陈东东编《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86页。
b如王东东经由对骆一禾诗学的存在主义阐释,认为“为民族生存甚至民族精神提供一幅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图景,而这一点也契合了1980年代的启蒙和浪漫的思想潮流。”王东东:《“与闻于世界之创造”:骆一禾诗学建构的存在主义路径》,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第137页。
c如冷霜引用骆一禾写于1987年的《长征》一诗,指出“后革命”语境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与80年代以来诗歌在认识与研究上的“断裂”,而近年来,虽然骆一禾“诗歌中的文明视野,他的诗歌观与浪漫主义诗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被越来越多地讨论,但他的另一些面向”,在这种“断裂”论的遮蔽下却难以被充分挖掘。此外,骆一禾在诗中“对中国革命的强烈肯定和赞颂”与“新启蒙”思潮的距离,和他在诗歌观念上与“第三代诗歌”主潮的距离之间,或许也存在某种相关性。冷霜进而认为,骆一禾“在1980年代后期诗歌中展现出来的宏大的文明想象与他从革命传统顺承而来的世界眼光之间的关系,他对浪漫主义诗学的倾心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艺术资源的革命能量之间的关系,也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参见冷霜:《“后革命”语境与当代诗歌研究的“断裂”》,载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26页。
d西川:《答马铃薯兄弟问:学会欣赏思想之美》,收入《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243页。
e骆一禾:《长征》,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7—303页。本文下引诗句如无标注,均出自该诗。
f目前对骆一禾诗歌文本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从其诗歌的部分核心意象、重要主题或经典作品入手展开细读与分析、讨论其诗歌理想,如何清:《骆一禾诗歌意象问题探寻》,载于《名作欣赏》2022年第15期,第49—51页;钟世华:《文学精神与历史理性——以骆一禾诗中“黄昏”色彩的分析为中心》,载于《当代文坛》2021年第5期,第166—171页;胡书庆:《碧绿的十字:骆一禾诗歌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等,但此类研究集中于麦地、黄昏、水等意象或爱、牺牲等主题,论者的注意力也往往被其两部长诗和《桨,有一个圣者》《黄昏》《壮烈风景》等代表性的短诗吸引,重复性过高。经由诗歌理念分析其诗人形象,如雷前虎:《骆一禾:客死人间的圣徒诗人》,载于《名作欣赏》2019年第2期,第145—146页。而由于骆一禾在诗歌与诗论中有着大量的自我阐释,此类研究也多易于滑向对骆一禾观点的复述。对骆一禾诗歌不同版本的考证,如于慈江:《骆一禾〈先锋〉〈为美而想〉二诗的版本及其他》,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期,第204—211页,但除比较不同版本间的异同并作出相应的简要分析外,并未提供更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和观点。
gr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第21页。
h[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9页。
i毛泽东在《讲话》中亦曾强调革命作为“普遍的启蒙运动”的意义,而“文艺”则在其间扮演着“普及”“提高”乃至塑造新人的重要使命。详细论述参见张旭东:《“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与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第3—17页;收入张旭东:《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273—292页。
jmz骆一禾:《美神》,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3页,第832页,第833页,第832—846页,第836—842页。
k参见骆一禾:《火光》,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7—854页。
l贺桂梅:《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03页。
n骆一禾:《致阎月君》,收入陈东东编《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60页。
opq“十月的诗”引言,载于《十月》1987年第4期。
s骆一禾:《水上的弦子》,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29页。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的位置在此由“被启蒙”转变为主动“寻找”。或许可以说,这一转变也在不经意间标示出骆一禾在历史的变动中确认“中国”主体的努力。
tu骆一禾:《论昌耀》,收入陈东东编《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47页,第462页,第453页,第453页,第453页。
v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文化研究(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5页。与此相参照的是,骆一禾强调诗歌的文明价值,并认为其应该也能够如古希腊史诗、神话或希伯来神话般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奠基性的价值准则与力量,参见骆一禾:《致阎月君》,收入陈东东编《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60页。
w这一点从骆一禾对鲁迅的评价中也能看出。林贤治就曾提及骆一禾“强调鲁迅哲学的独创性、现代性,人格的深度,因而是中国情感本体论哲学的思想者,而不是逻各斯理性哲学的思想者”,而骆一禾做出这种判断的“着眼点在中国。”参见林贤治:《悼一禾》,收入陈东东编《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9页。
x详细论述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文化研究(第2版)》,第五章“‘文学性’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思潮’”第一部分“美学谱系:诗化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348页。
y参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另参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结语“当代文学难题与中国经验的历史自觉”第三部分“从‘中国’思考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16—526页。
转引自张玞:《大生命——论〈屋宇〉和〈飞行〉》,收入陈东东编《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9页。
“十月的诗”引言,载于《十月》1987年第1期。
本段观点参见骆一禾:《美神》《火光》,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2—854页。
参见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 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参见[英]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收入陆建德编《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参见骆一禾:《一封新发现的骆一禾的遗信》,载于《广西文学》2010年第5期。
即骆一禾诗《残忍论定:告别——访莱蒙托夫》,在对混乱的庸俗市井和“弄臣世界”展开批判时所写“现实不再出现/现实已被日常围歼……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日常主义”。该诗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6—501页。
此处也可以参照竹内好对历史的理解:“历史并不是被作为结果来理解的”,而是“以可能性的状态存在于主体内部……对于主体来说历史就是每一个现在,如果主体放弃了判断、决定以及行动,也就失去了他的历史”,由此,竹内好得以“超克”进化论视野中以先进与否衡量历史与历史人物的标准,而是将主体与历史同构,“以介入历史的深度,和是否具有真正的主体性来衡量历史人物”,同时将历史产生的时刻指认为“主体为了自我形成而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参见唐宏峰:《作为方法的竹内好——以〈何谓近代〉和〈近代的超克〉为中心》,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第88页;另参见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代译序)》,收入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6页。
前者参见骆一禾:《市井狭邪——论一种性格及其惯性思维》《残忍论定:告别——访莱蒙托夫》,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3—310页、第496—501页。后者如《长征》中所书写的“农民”。
参见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载于《读书》2016年第2期,第13—24页。
骆一禾曾在诗中将80年代中后期的北京市井生活,与由军阀、庸众、“黑幕小说、通俗演义”等构成的晚清和“黑暗”民国,以及明王朝由盛而衰的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同构。参见骆一禾:《市井狭邪——论一种性格及其惯性思维》,《残忍论定:告别——访莱蒙托夫》,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3—310页、第496—501页。
骆一禾:《致后人》,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14页。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李步楼、尚伟、祁阿红、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0页。
参见王东东:《追寻美神:1980年代中国的新浪漫主义与审美教化——以骆一禾、海子为中心》,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期。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5页。
洪子诚:《1954年的一份书目——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载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第10页;收入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参见骆一禾:《一封新发现的骆一禾的遗信》,载于《广西文学》2010年第5期。
骆一禾:《火光》,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51页。
“雅斯贝尔斯借谢林‘与闻于世界之创造’(Mitwissenschaft mit der Schöpfung)的隽语来论述进入大全或本原的努力:‘在我们的根源里我们曾经参与或知道万物的本原,而在我们的世界这个窄狭范围里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从事哲学思维活动,就在于唤醒我们的回忆,从而让我们返回本原。’”引自王东东:《“与闻于世界之创造”——骆一禾诗学建构的存在主义路径》,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参见骆一禾:《火光》,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7—850页。
张旭东:《文艺文化思想领域40年回顾(1979——2019)》,收入张旭东:《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0—321页。
姜涛:《怎样重新领会“革命诗歌”的传统》,载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这一点从其诗中强烈的自我主体与牺牲意识、“居天下之正 行天下之志 处天下之危”的主体位置与“生为弱者”“为我成为一个赤子/也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人”的自我想象、“修远”使命的提出等方面,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来。相关诗作/诗句参见骆一禾:《世界的血·第四章:曙光三女神》《生为弱者》《漫游时代》《修远》,收入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1页,第115—116页,第526页,第483—487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