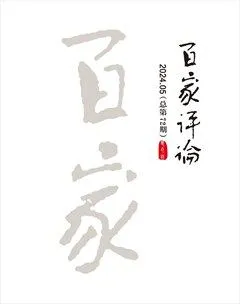儿童视角与“60后”作家创作
内容提要:儿童视角是60年代出生作家进行历史书写时采用的一个重要叙事策略。这一创作群体以儿童视角的不同叙事形态和固有特征为基点,展开了对多维历史图景的童化观察与再现。在纯真童眸的烛照下,儿童开启了个体成长之困的真切自我言说,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创痛也得以客观呈示和深入剖析。60年代出生作家以儿童视角对历史的多重透视,既表现出对儿童本体情感世界的深切关怀,也指向对特定历史与驳杂人性的别样审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叙事开拓出一个新的空间。
关键词:60年代出生作家 儿童视角 创伤书写
60年代出生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坛中的一个重要创作群体,主要指出生于60年代或50年代末,在80、90年代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代表人物有苏童、余华、格非、毕飞宇、艾伟、邱华栋等。因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相似的成长经历,这一代作家在走上文坛后聚焦个体的生存苦难与心灵疼痛,对人类的伤痛性体验予以浓墨重彩的书写,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世代作家的独特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创伤书写时,这一创作群体不约而同地将儿童作为小说的视角人物来建构文本a。其中余华、苏童和毕飞宇对儿童视角的运用尤为广泛,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创作,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自传体小说,毕飞宇的《白夜》《怀念妹妹小青》《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或是局部或是全篇,均以儿童视角来描写人物的生存境遇,以此表现对个体、家庭与时代的多重关照。在儿童的观察和表达下,历史的褶皱与人性的幽微得到了丰饶的细腻书写。
叙述视角是叙事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昭示着“谁在看”的问题。其在文本中往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诚如学者所言,“叙事角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数,一个叙事谋略的枢纽,它错综复杂地联结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何物,看者和被看者的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和观览的‘文化扇面’。”b从这一角度而言,60年代出生作家对儿童视角的集体青睐就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因此,对小说中儿童视角的探察就成为阐释这一作家群体创作风貌的重要突破口。同时,儿童视角不仅是一种修辞,它还隐含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审美偏向与创作观念。加强对这一叙述视角的考察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文本与60年代出生作家的深层心理和文化心态之间的潜在关系。
一、成长之困的深切体验与自我言说
“成长”作为个体由青涩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成长叙事便成为众多作家所青睐的书写内容。60年代出生作家的童年大多在喧嚣的历史年代中度过,加之各自不尽相同却又共同指向“疼痛”的成长经历,使其童年生活在整体上浸润着一种难言的苦涩。在毕飞宇看来,“等待”“失望”和“忍受”就是他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词,“那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等待的时代。……我的童年与少年如此的漫长,全是因为等——在大部分时候,你其实等不到。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忍受力。我的早熟一定与我的等待和失望有关。”c从文本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童年时期的匮乏体验构成了60年代出生作家走向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开掘不尽的创作资源。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他们聚焦儿童的“成长”主题,展开了童年创伤的记忆反刍,力图在无声的回溯中寻求心灵的告慰。于是,在选择叙事策略时,他们便不假思索地以儿童视角观照儿童本体的内心世界,在深切体验成长之困的基础上展开了自我的真实言说。
从观察的内容来看,儿童视角可以分为“内省型”与“外审型”。“内省型”即儿童向内省察自己,“外审型”则是审视外界的人事物。在对个体成长创伤进行审察时,60年代出生作家充分发挥了“内省型”儿童视角在关照儿童本体、深入儿童内心方面的显著优势。在他们笔下,作为叙述视角的儿童往往在担任故事观察者与讲述者的同时,又构成了文本情感世界的体验者。他们常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亲口讲述自身及同伴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多重困境。《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将其自身从南门被送养到孙荡,最后又独自回到南门的漂泊历程向读者娓娓道来,“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d余华在此没有为孙光林的讲述寻找代言人,也正是因此,孙光林的真实心理得以完全敞开,使读者直接窥探到其内心的孤独感和弃绝感,进而生发出切身的怜悯和同情。成长叙事在苏童的创作中也占有重要比重,他的“童年与成长”系列小说的创作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在《城北地带》和《刺青时代》中,“我”目睹并亲口讲述了同伴小拐、红旗、达生等孩童和少年在缺少教育与关爱的环境下放纵自我原欲与野性,最终在迷惘中走向落寞的结局。在此,小说对个体成长的书写因具备儿童本体的亲历性而增强了文本叙述的真实感与可信度,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间接促发了读者情感的深入。
除了采用“内省型”儿童视角对个体艰涩的成长困境展开叙述外,60年代出生作家还注意到儿童天真乐观的性格特点,故而选择以儿童面对客观现实的落差来凸显其成长的艰辛。在整个社会群体中,不同于成年人的成熟理智,儿童因其年龄较小而往往具有天真懵懂,甚至是盲目乐观的一面。基于此,他们对外界的想象常常过于理想化,而客观的现实存在往往与他们原初的美好假想形成某种错位。这一乐观预期和失望结局之间的反差,恰恰构成了文本的叙事张力。《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在被送走之前,并不知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未知的领养生活,他以为这只是一次遥远的游玩。于是,面对祖父孙有元投来的忧虑目光,他颇为得意地以一句“我现在没工夫和你说话了”e进行回答。不仅如此,“我弱小的身体昂首阔步地从我祖父身旁走过,故意弄得尘土飞扬。”f天真的孙光林对自身的处境明显做出了错误估计,他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与此后被再次抛弃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鲁鲁亦是如此。在第一次踏上远行的汽车去寻找正在劳改农场改造的母亲时,七岁的他背起草席,提着书包,“对自己的行程充满了把握”g。然而,即便他学着大人的样子胸有成竹地用三根被汗水浸湿的香烟“贿赂”了司机,即便他在到达农场后诚恳地哀求工作人员把母亲还给他,终究也无法改变他即将成为一个孤儿的事实。在鲁鲁那近乎偏执的乐观和最后的失落之间,生出一种黑色幽默式的荒诞,儿童命运的飘零感随之生发,令人不免为之叹息。在毕飞宇的《怀念妹妹小青》中,同样存在着儿童美好愿景的现实破灭。在纯真无邪的妹妹看来,铁匠铺里的一切都过于美妙,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将双手伸向了鲜红的铁块,最终细嫩的小手被烫得面目全非。不同于儿童视域的纯真无瑕,现实世界往往是斑驳陆离的,其中自然有明媚的光影,但也不乏时而浮现的阴云。在这二者的参差对照中,儿童的世界显得美好又脆弱,其成长所经历的滞涩由此得到了细腻的刻画。
60年代出生作家对儿童的成长主题确实有着特别的偏爱。诚如学者所言,“他们才刚步入而立之年,却显得足够老成,旧事重提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许多作者都喜欢向读者诉说自己‘早年’的经历,于是乎匮乏的童年和少年成了小说叙述无尽的资源。”h但是不同于萧红、迟子建等乡土抒情派作家在《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麦穗》《北极村童话》等作品中以儿童视角对童年生活进行的诗意还原与温情呈现,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人将视点转向了易被人们忽视的僻暗角落,揭示出儿童成长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在此过程中,他们以“内省型”儿童视角来关照儿童的心灵世界,并在儿童的烂漫假想和客观现实的两相对照中,实现了对成长创伤的真切讲述与有力强化。
二、家庭伤痛的敏锐捕捉与真实复现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每个人赖以存在的最小单元。理想中的家庭往往呈现出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和兄弟和睦的温情景象。然而,当我们跟随儿童的视线进入6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世界时,看到的却是迥异于既有温情之景的家庭呈现。《河岸》中库文轩因失去“革命的母亲”而被妻子乔丽敏离弃的结局,余华笔下父爱的缺失给孙光林、国庆和鲁鲁带来的深重弃绝感,以及《刺青时代》中王天平、锦红、秋红和小拐之间错综复杂的手足冲突,都向我们传递出家庭生活中的些许“杂音”。在书写家庭创伤时,儿童的观察视点开始向外转,由对自身成长创伤的关注转向对家庭创痛的洞察,以“外审型”的视角敏锐捕捉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中的隔阂与矛盾,并凭借其视角的原初性将这一伤痛经历进行了客观的真实复现。
不同于成人感受力的日渐钝化,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长期保有敏锐的直觉和敏感的性格。因此,在向外观察时,面对成人无法感知或触碰的领域,儿童往往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其间,进而捕捉到他人难以察觉的隐秘创痛。余华笔下的孙有元在晚年摔伤腰后,开始变得唯唯诺诺,“在家中的日子里总是设法使自己消失。他长久地坐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无声无息地消磨着他所剩无几的生命。”i即便如此,孙光林还是以其敏锐的童眸观察到了祖父的尴尬处境。孙有元为了能够夹到饭菜而悄悄怂恿小孙子锯矮桌腿的狡黠,其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轮番寄宿于两个儿子家中的凄凉,以及去世前接连遭到儿子咒骂的哀伤,都没能逃过孙光林的眼睛。余华在此借助孙光林的犀利目光,对孙有元极力掩饰的这些窘境进行一一捕捉,让我们看到了本应温暖的父子亲情的另一重面影。苏童的《河岸》则借助少年库东亮敏感多思的性格,向读者呈现出库少轩的身世隐痛及其与乔丽敏夫妻情感的破裂。在库少轩结束审察归家后,库东亮机敏地关注到夜里突然出现的安静。因此,他悄悄爬上枣树,以少年偷窥的视角目睹了父亲向母亲卑微求和的窘态。然而库少轩的乞求并不能改变他与妻子分道扬镳的结局,多年来的夫妻情分在其被判定为不是烈士后代的那一刻便所剩无几了。在库东亮的偷窥中,我们仿佛也目睹到库少轩在夫妻关系中遭到的猜疑和离弃。可以说,无论是对父子亲情冲突的捕捉,还是对夫妻情感破裂的揭示,敏锐的儿童视角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优势。
此外,儿童的社会化程度较低,一般未受成人世界的浸染,儿童视角因此具备了原初性的呈示功能。于是,在面对隐秘难言的家庭伤痛时,儿童不仅可以凭借其敏锐的眼光和敏感的性格予以精准捕捉,还能以其原初性的童眸对这些伤痛进行贴合事实原貌的真实再现。在余华的《现实一种》中,从拧脸到打耳光再到卡喉管,直至不小心松手摔伤堂弟,四岁的皮皮在不自知的状态下对堂弟施加了深重的肉体暴力。而这看似无意的伤害背后,实为夫妻关系失范的延续。在此,余华借助皮皮的视角对堂弟被摔伤后从身体一动不动,到头部不断流血,再到蚂蚁沿着凝固的血迹一直爬进其头中的整个过程予以了自然主义式的真实复现。对于这令人目不忍视的场面,余华没有选择回避和快速勾勒,而是表现出极强的叙述耐心,将这一画面徐徐延展开来。在此,皮皮虽然能够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身边存在的被成人视为创痛的存在,但是受制于生理发育的不成熟和心理经验的欠缺,他终究不能切身体会,亦无法理解这种深巨的疼痛,于是可以在规避情感侵扰的前提下,对堂弟遭受的肉体伤害进行不动声色的耐心观察,进而使堂弟遭受的肉体伤害得到聚焦化的文学呈现。
6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中往往氤氲着缕缕挥之不去的悲凉。在表现家庭情感时,他们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家庭关系的剑拔弩张,理想中的温暖亲情在此销声匿迹而不见踪影。当然,其间也有温情之景的偶然闪现,但并不能完全化解那略显晦暗的情感基底。就小说的人物刻画和伦理书写而言,这其实妨碍了人物健全人格主体的建构和良性情感伦理的生成。在60年代出生作家以儿童视角敏锐捕捉隐秘亲情创痛的背后,是这一创作群体对家庭伦理失范和情感隔膜的正面拷问。从小说的深层叙事意图来看,这恰恰也从侧面反映出60年代出生作家对家庭温情的期冀与向往。
三、历史的多维呈示与深入剖析
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并未局限于个体成长与家庭关系的狭小天地,而是触及了更为广阔的时代内容,呈现出对历史的多维呈示与深入剖析。可以说,童年时期的种种经历在这一创作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深重的历史情结,因此在他们绘制的文学图景中,对历史的描摹占据了很大比重。正如余华所言,“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j面对不同世代作家所共同关注的历史书写对象,60年代出生作家以儿童视角的独特叙事方式参与了历史记忆的重构,由之实现了对特定历史与驳杂人性的别样审视。
60年代出生作家首先从儿童视角的叙事形态入手,运用“混合型”儿童视角对历史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呈现,揭示出伤痛的广泛性与深入性。具体来看,小说中儿童的视域兼顾内与外,将自身的成长遭遇与外部的家庭环境和时代浪潮等因素联系起来,在多种力量的交织互渗中传达出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刻思考。在《河岸》中,苏童以库东亮的儿童视角对后者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多维审察,成长的孤独与焦虑在亲历者的讲述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库东亮将观察视点向外转,洞察社会世相,捕捉到家庭关系的紧张和历史的残酷,使得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多重创痛在小说中一一呈现。不仅如此,苏童还进一步揭示出这些创痛之间的复杂关联,突出其中历史强力的统摄性和主宰性。“就像水跟着水流逝,草连着草生长,其实不是选择,是命运,正如我父亲的命运,与一个女烈士邓少香有关,我的命运,注定与父亲有关。”k在此,儿童的个体成长与家庭的现实命运都被紧紧嵌进历史浪潮之中。在余华的《兄弟》和毕飞宇的《那个男孩是我》等小说中,均可以看到历史的类似书写方式。可以说,在“混合型”儿童视角的全面洞察下,以特殊历史时期中个体的成长焦虑或家庭的分化瓦解来表现复杂的历史,已成为众多60年代出生作家共同的叙事选择。
在文本中,主体所视内容不仅与采用哪一个视角有关,更取决于视角人物所处的社会位置,因为这决定了主体观察世界的立场。就社会角色而言,儿童是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的,加之其思维发展的不完善性,故而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多重话语的裹挟,进而能够以旁观者的立场对眼前事物作出剔除政治干扰和道德判断的客观呈现。鉴于儿童视物的如是独特性,60年代出生作家便选取了儿童这一边缘性视角来探寻历史真相。在《地球上的王家庄》中,毕飞宇就选择以一个八岁男孩作为小说的视角人物。在男孩的冷眼旁观下,特定历史时期中王家庄民众的蒙昧状态得到了不动声色的客观呈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创作群体在此所采用的儿童视角多是作为一种限知性视角而存在的,其展开的是一种不追求广泛性和权威性的限知叙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儿童视角的采用在本质上是对成人理性的有意疏离,作者最终意欲呈现的是一个不同于成人经验的客观世界,这与宏大的公共历史记忆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艺术张力。
60年代出生作家之所以选择以儿童视角书写历史,除了出于叙事效果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他们既有的个人经验。因此,在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进行反思时,这一代作家很难超越其既有的童年经验,而代之以成人视角深入审视其中的悲欢。但是,历史是颇为复杂的,仅以儿童视角展开的相对浅显的个人记忆复现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小说家是民族记忆的生产者。一个成熟的作家,读者有权利要求他通过重述个人具体记忆而抵达对一种集体经验的召唤。”l针对这一问题,60年代出生作家便在小说中引入了成人视角,以成人的理性审察对儿童的客观呈示进行补充,进而实现对历史创痛的多重观照与深入剖析。毕飞宇的《怀念妹妹小青》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其间存在着童年经验自我与成人叙述自我的交织与叠合。在童年经验自我的视域下,历史的多个面向都得到了冷静的客观再现。但是,由于作为儿童的“我”缺乏批判时代暴力的能力,经验自我下儿童视角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止步于此了。于是,作者同时安排了具有理性判断力的成人叙述自我来对妹妹进行“怀念”,在回看中以妹妹的创伤境遇来表现历史强力下个体生命所遭到的伤害。在此,特殊年代的无序状态受到了来自不同主体的多重观照,尤其在成人视角的理性审视下,这一历史得到了进一步地深入挖掘和有力质询。
面对既有纷杂的历史,60年代出生作家需要着重思考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问题。在此,叙事视角的选择就成为这一代作家创作的突破口。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60年代出生作家摆脱了集体言说的主流叙述方式,而以“混合型”儿童视角揭示历史多重面向。同时,作家们依托个体的童年经验,以儿童这一远离意识形态的边缘性视角旁观历史,进而规避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那种司空见惯的情绪宣泄式的控诉模式。此外,针对单一儿童视角的有限性,他们以成人视角进行补充,二者叠合后所形成的复调结构有效地扩大了文本的时空容量和话语空间。与其他世代作家相比,60年代出生作家确实通过对儿童视角的多方运用表现出一种异质化的叙事姿态,大大丰富了新时期既有的历史创伤叙事。
结语
60年代出生作家以儿童视角书写历史,既受制于个体既有的童年经验,也与当下的社会思潮和儿童视角的独特叙事优势有关。视角的改变意味着审视世界的角度的变化,往往能够为文本带来崭新的叙事形态和别样的美学风貌。这一创作群体以儿童视角为依托,通过回忆与现实的交织、内视与外审的结合、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并置,构建起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促进了新时期历史书写的理论探索。然而,60年代出生作家在书写历史时也存在一些局限,譬如过于倚重童年记忆和历史记忆,而在呈现和剖析当下创痛方面却略显苍白乏力等。同时,本文虽重点考察了60年代出生作家以儿童视角书写不同创伤的具体路径和叙事效果,但所作论析同样存在很多不足,如从作家代际的角度对整个60年代出生作家进行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一创作群体内部存在的个体差异,这需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注释:
a本文论及的儿童视角指在叙事文本中以儿童作为观察角度,是成人小说中一种较为复杂的复合视角。在这一视角下,作为隐含读者的成人叙述者往往会对儿童视角的叙述进行干预和补充,与儿童文学中的单一儿童视角存在本质区别。
b杨义:《中国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61页。
c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defgi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第167页,第167页,第126页,第155页。
h郜元宝:《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60年代出生作家群印象》,《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j余华:《自序》,《黄昏里的男孩》,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k苏童:《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l张莉:《现实感与想象历史的可能——以苏童近年创作为例》,《文艺研究》2015年第8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