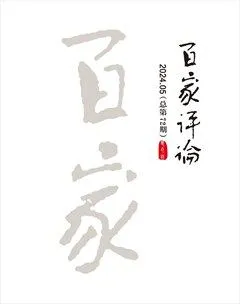新世纪西部小说的女性书写
内容提要:新世纪西部小说的女性书写取得重要发展。西部小说打破了女性作为映衬男性群像的创作局限,细致呈现女性与空间、女性与自我、女性与他者、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复杂关系,展现了西部女性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文化场域的行为实践和崭新面貌。尤其西部作家对少数民族女性自我觉醒和观念变化的书写,丰富了西部文学的女性话语体系。
关键词:新世纪 西部小说 女性书写 公共场域
卢卡奇认为:“小说是成熟男性的艺术形式”,即“小说的精神态度是男性的成熟,其素材的典型结构是离散、是内在性和冒险的分离”a。卢卡奇的论述强调了小说的雄性特质却忽略了小说的柔美特征。西部小说也一样,读者对它产生强烈的刻板印象,即他们普遍认为西部小说具有阳刚、雄壮的特点而忽略其柔美、温情的内容。进入新世纪,西部作家在女性书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打破读者对西部小说的刻板印象,也重构了西部小说的审美风貌。新世纪西部小说关于性别关系问题的书写发生重要的转变,譬如其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表达等层面重构并丰富了西部文学的女性话语体系。
一、西部小说的刻板印象与雄性气质
西部的自然环境影响小说的审美风格。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西部小说便以豪迈和阳刚的风格享誉文坛,譬如小说中的流浪汉、屠户、猎人、老兵、土匪等人物体现西部的文化气质,也奠定了西部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事实上,西部旷远、严酷、荒凉的自然环境影响作家的审美感受。相应地,小说的故事主人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顽强生活,他们身上张扬着原始生命力,残酷的环境也造就了他们坚韧和刚强的品格。红柯早年生活在新疆,新疆的自然风物完全融入其小说创作,因此红柯小说的男主人公总是展现英雄气质:“所有的人都听见群山上空滚动的吼声,雄狮团长跑遍了八百公里的塔尔哈山和巴儿鲁山,他给那些丧失斗志的人以勇气,他的声音令人振奋”b。红柯习惯性采用“雄狮”“战马”“苍狼”“火焰”等一系列词语形容男性,展现男性在西部自然环境的锻造下所形成得刚烈、韧性的品质。同时,他们纵情奔跑在西部的草原、森林、群山、沙漠之间,以一种自由洒脱的方式生活。郭雪波的《大漠魂》中的老双阳和干儿子狗蛋克服困难,不畏惧沙尘暴,在沙漠深处种出了红靡子,而老双阳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行为正是雄性气概的显现。雪漠的《猎原》中孟八爷智斗狼群和猎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坚守初心,他的生存意志和生命韧性在黄土高原上熠熠生辉。一定意义上,西部作家塑造了大量具有征服性特征的男性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性格的形成受到西部的沙漠戈壁、森林草原、雪山湖泊、暴雪沙尘的影响。
西部小说在两性关系中着重凸显雄性气质。西部小说集中描写男性英勇、威武的一面,却呈现出女性软弱、柔情的一面。这种两性关系的对比中,作家们有意识地凸显雄性气质而弱化女性力量。在红柯的作品中男性像险峻的高山、奔腾的河流、翱翔的雄鹰,他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昂扬的斗志和野蛮的干劲。例如,《古尔图荒原》中在新疆奋勇开垦冻结的土地的丈夫,《西去的骑手》中马仲英所率领的跨黄河、过沙漠的英勇骑兵队伍,《大河》中彪悍能干的父亲自由地穿梭于森林和山涧之间。同样,这些小说作品中的女性是柔弱、渺小和被动的存在,女性的懦弱衬托出男性的雄性特征。红柯的《大河》中,湖南籍女兵在阿尔泰意外怀孕,她受到老金的照顾并顺利渡过生活难关。老金的彪悍、粗犷衬托出女兵的单薄和柔弱。雪漠的《大漠祭》中,老顺的女儿兰兰以换亲的方式嫁给白福,她总是遭到丈夫的毒打,婚姻生活使其感到绝望而痛苦;莹儿同样以换亲的方式嫁给老顺有阳痿问题的二儿子憨头,他爱上丈夫的弟弟灵官,因为灵官的逃避感情和离家出走,她独自忍受情感折磨而痛苦地生活。郭雪波的《霜天苦荞红》中,瀚海科尔沁沙地自然环境恶劣,村民种植的苞谷没有收成,乡村的女性被迫靠出卖劳力维持家庭的生计。一方面这些女性的性格软弱使其无法逃离自己所处的生活绝境,一方面她们的被动性使其无法选择自己的理想生活和情感归属。受到西部传统文化的影响,西部作家有意识地塑造具有阳刚特征的男性形象,并通过柔弱和悲惨的女性衬托男性主人公,以此呈现了一种凸显男性气质却失衡的两性关系。
在传统的性别关系结构中,父权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男性逐渐成为一种“支配和压抑女性的性别角色”c。西部小说中的父亲或哥哥等男性总是决定女性的人生和命运。例如,《大漠祭》中的父亲不顾及女儿的感受而决定利用女儿为儿子换亲。《马兰花开》中的父亲为了缓解拮据的生活而匆匆嫁了大女儿马兰。《紫青稞》中的大姐桑吉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无奈地踏上进城为孩子寻父的道路。二姐达吉过继给阿叔次仁,为了让阿叔有一个体面的上门女婿,她听从其安排接受了普拉的感情。事实上,男性性别身份的确立反映社会大众对性别想象和性别观念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和东部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西部作家普遍产生文化焦虑,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自我性别身份的建构,以丰富的实践活动应对男性的性别危机,进而以此彰显西部文化在社会性别机制方面的影响。西部小说从社会语境和两性关系的层面呈现了西部的男性文化气质,深刻反映了西部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性别文化。
西部小说过度刻画男性角色往往导致女性的失声或消失。具体来说,西部小说内部存在一种显见的父权文化,这构成压抑和主导女性的主要因素。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们往往会记得红柯笔下英勇的军垦战士、郭雪波笔下机敏的猎人、雪漠笔下跋扈的父辈、董立勃笔下嚣张的基层干事、李学辉笔下乖张的紧皮手等等,而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往往是沉默的,她们或失声或没有存在感,这也说明女性在西部的历史发展中被遮蔽的问题。关于新疆兵团建设的书写中,红柯、董立勃等作家着重呈现男性在新疆建设过程中克服恶劣自然环境而英勇献身集体事业的行动及表现。关于西部大开发的书写中,贾平凹、雪漠、刘亮程、郭雪波等作家重点展现村长、书记、队长、村民等男性角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忽视了女性的贡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的书写中,叶尔克西、梅卓、马金莲、亮炯·萨朗等作家也强调少数民族男性的率先觉醒以及他们推动西部偏远地区改革发展的历程。作家们普遍忽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诉求,实则忽略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与女性命运的内在关联。正因为如此,西部小说的刻板印象是雄性的,其中女性的声音被忽视了,故而小说温柔、细腻的主题内容和情感表达也不为读者所注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西部作家们也逐渐作出改变,他们也听到了属于女性的声音,譬如一些西部作家立足现实生活和壮阔历史的女性书写,既展现了不同女性的风采,又以女性视角审视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使得西部小说的女性叙事呈现多重意蕴。
二、女性的浮出与性别视角的建立
西部作家开始注意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他们通过对女性生活遭际和命运轨迹的书写,反思了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女性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自我主体性的建构。谷运龙的《灿若桃花》中,丧夫的小姝不畏惧长辈的阻拦和世俗的眼光,克服重重困难嫁给自己的初恋地宝,自信坦然地开启新的生活。《春兰》中幺姑娘不满意家里的定亲对象,进城打工时与厨房工作的同事自由恋爱。同样,春兰的订亲对象秋生进城读书,她拒绝母亲介绍得其他结婚对象,决定进城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春兰和幺姑娘作为被羌族传统文化束缚的女性,反对包办婚姻、走出羌寨是她们自主性的选择,这种反叛与出逃主题的书写具有思想启蒙的意味。《日近长安远》中,农村女孩甄宝珠反复找“商品粮”d未果的情况下,嫁给了农村小伙秋生,宝珠决定同丈夫进城打工。她既吃苦耐劳又聪明伶俐,从卖袜子、开饭馆到停车收费,赚了不少钱,改善了原本贫困的生活。西部作家将女性的精神蜕变和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西部女性迸发的生命活力。现代化带来丰富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改变了西部的文化传统、情感结构和心理模式,处于失落状态的西部女性接受现代观念启蒙,摆脱外在的文化精神束缚。她们通过调整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他者的复杂关系,获得一种新的自我认同,并凭借顽强的信念寻找到更加可靠的精神寄托和生活方向。
新世纪西部小说也展现了女性在追逐自我过程中遭遇的自我沦陷问题。小说《日近长安远》中,罗锦衣原本是个普通的乡村女性,她通过跟孟建设交往,成功地转为民办老师,但她又不甘于一辈子当一个普通的乡村老师,再次通过交易成为一名县城的老师。罗锦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借助付良才的力量,一步步地从县城进入城市,由普通的民办老师成为城市一所设计院的院长。她懂得察言观色和拉拢关系,并通过外貌的收拾打扮,不断地包装自己。随着罗锦衣人老珠黄,付良才选择了年轻的卢双丽。故事的结局便是罗锦衣依靠男性得到的一切却同样毁于男性。作家这样的处理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但是也说明了罗锦衣凭借交易换来的一切终究是泡沫。王华的《花城》中花村的女性苕花、金钱草等女性进入城市当打工妹,从事搞传销、卖保健品、卖化妆品等工作,她们为了在城市谋生不惜出卖自己e。苕花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甚至嫁给年龄较大的城市男人。这些女性觉得花村的生活无聊,她们想要体验城市刺激的生活,然而城市中某些不良风气洗刷掉了她们身上的纯真和善良,苕花、金钱草等人在城市也前途渺茫。这些进城的乡村女性企图通过逃离家庭来释放个性和追求自我,但她们往往囿于性别身份最终陷入困境。西部小说展现女性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越轨危机”f,进而说明女性依靠性别红利获得的生存资源和社会资源终究会使得自己陷入深渊。
同时,新世纪西部小说展现女性在自我觉醒过程中的内心矛盾和情感冲突。尽管她们的思想有所觉醒,但是仍旧受到男性的观念主导或影响,故而她们思想和生活总是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小说《紫青稞》中,普村的藏族女孩达吉过继给叔叔次仁后进城生活。她进入城市积极适应新生活,学着售卖农副产品,从卖牛奶到卖奶渣、奶酪、油酥再到开酒馆,达吉实现了经济独立。但是,达吉为了让阿叔有一个体面的上门女婿,她听从叔叔的安排接受了自己原本不喜欢普拉。尼玛潘多的小说反映了已然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她们的精神仍旧未能独立,她们习惯性地接受长辈的安排,以致其长期处于情感压抑和精神孤独的状态。小说《野麦垛的春好》中,西部偏远山村的春好自幼跟同村的张生相好,两家也决定换亲,即春好嫁给梅子的哥哥张生,梅子嫁给春好的哥哥跟风。然而梅子因不满跟风不思进取,喜欢上其他人,导致两家的换亲没有成功。春好因为哥哥跟云的恶劣行迹又被迫为其换亲,嫁给自己不爱的郝家树,她的生活没有了指望。后来春好跟同村的东拴有了感情,被邻居撞破,东拴意外判刑,春好无奈只能进城寻找出路。进城后的春好为生活所迫,从事不光彩的行当,自此她变成家里的摇钱树。尽管生活艰难,但春好对陌生人也充满善意,如照顾打工少年小秦和其他的乞讨者。春好对生活充满信心,她从未想过放弃自己。在小说的最后,春好和失去双腿的张生走到了一起。季梁栋写出了西部女性的朴实和善良,她们总是以柔弱的身躯应对残酷的现实生活。这群女性无法在逃离家庭之后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精神空间,因为她们总是在回归家庭和寻找自我之间反复徘徊。
进入新世纪,西部女性经历了多种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她们面对感情变得更加地主动,体现了鲜明的现代精神与时代色彩。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对于自我的觉醒与拯救中必然伴随着种种苦难的历程”g。小说《拉萨红尘》中,玛雅穿梭于不同的男性之间寻找精神伴侣,并以此来反抗爱情的易逝以及麻木的婚姻生活。琼吉白玛总是陷入爱情或是婚姻的艰难抉择中,她遵从内心的情感需要而不惜违背婚姻法则和道德伦理的约束。藏族女性重视自己的情感需求和内心感受,她们也敢于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去追求理想生活,但是她们对于自己的生存处境、精神需求以及行为表现依旧充满困惑。这说明少数民族女性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而这种觉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小说《月焰》书写两代藏族女性的命运轨迹和情感纠葛。母亲琼芨白姆出生在藏族的贵族家庭,西藏解放的时候,琼芨白姆离开家庭去寻找刘军长,之后她学会汉语被推荐上大学。在上学的过程中,琼芨白姆跟自己的同学巴顿谈恋爱,在巴顿返回拉萨之后她又跟自己的老师雷产生感情,此后她嫁给巴顿,两人又迅速离婚。跟洛桑结婚多年后,琼芨白姆选择跟洛桑离婚,尔后她同丹竹仁波切的感情也无疾而终。女儿茜玛跟母亲琼芨白姆一样,她也无法正视自己的感情,总是游离在不同的情人之间。在新世纪阶段,西部小说对女性的呈现体现了日常生活中女性意识的外化,即女性通过彰显自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来确证自我的“性别角色”h和社会特征,例如她们习惯性地表述“我要怎么样”。西部作家在书写女性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分析女性与空间、女性与自我、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从而揭示女性主人公在放纵、颓废、倾听以及觉醒过程中对自我的发现和安顿。
三、走向公共文化场域
新世纪西部小说关于女性的书写取得重要的发展。在西部作家笔下的女性群体,“面对公认的差异和区分,她们承诺认识上的合作并寻求公共性”i。作家们开始关注长期被男性所遮蔽的女性声音,书写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情感问题中的困境,呈现女性丰盈的内心世界。在西部小说中,女性不仅自我意识觉醒,而且她们积极走入公共文化场域,展现自己的精神风采和职业能力。尽管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着女性群体的生活和选择,但进入新世纪阶段,女性群体的思想和观念发生变化,她们普遍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西部小说中女性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她们日渐从私人领域进入公众领域,譬如有意识的通过架空父权体现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南茜·弗雷泽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不受限制地理性讨论公共事务的理想”j。女性走向公共场域,即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场域。譬如政府机构、商业领域、文化传媒等领域都有女性活动的身影。女性有自由地表达自己和选择生活的权利,她们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和表现值得被尊重。
西部小说展现了女性逐渐走出做家务、照顾儿女的私人领域而相继成为医生、老师、厂长等公共文化场域的代表人物。她们打破了人生只能由男性决定的观念,找回了自己丢失的话语权。阿舍的《阿娜河畔》中,新疆某兵团农场的石昭美喜欢来自支边家庭的明中启,但是明中启喜欢上海的支边青年娄文君,后来石昭美与明中启因为误会而结婚。婚后的石昭美没有被家庭困住而是积极提升自己,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她经常深入基层,救治兵团的病人。正是在基层工作中,石昭美走出情感困境,也找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生活追求。马金莲的小说《马兰花开》中,因为父亲嗜好赌博,马兰高中辍学,用自己的彩礼换得弟弟妹妹的学费。她嫁入李家妥善地处理了婆媳关系、妯娌关系,当李家的大家庭分崩离析后,她兴办养鸡场,逐渐成为在家庭中拥有话语权的人。小说中的马兰是一个聪明、善良、勤劳的女性,她既能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小孩,也能积极谋求出路。贫困的生活并没有压垮她,反而激励她寻找脱贫致富的道路。她顶住来自家里公公、丈夫乃至小叔子的压力而兴办养鸡场,增加了家庭的收入,从而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情况。马兰也是西部小说中具有成长意义的女性形象。她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家庭话语权,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施展了自身的才能,也赢得家庭话语权。尽管西部小说中存在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性别关系,但是这种对于现实问题的回避恰恰揭示出阻碍女性发展的文化根源是复杂的,它不仅存在于单一的男女关系中,“也存在于家族集团男性成员与女性成员之间,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作为阶层的男女关系之间”k。因此,新世纪西部小说的时代意义在让女性进入公共文化场域,改变自己困窘的生活局面,进而追求理想或创造新的生活。
新世纪西部小说在历史长河中描摹女性的身影,反映她们在民族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和创造力,尤其展现了少数民族女性在现实生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风采。具体来说,西部小说从思想观念、行为表现、文化取向等多个方面展现西部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变化。肖勤的小说《好花红》写贵州黔北大娄山的故事。主人公花红的父亲是猎人,母亲曾因落难嫁给父亲但是不爱他。母亲与隔壁山里的年轻猎户相好而死在父亲的枪下。花红自幼跟父亲学得一手好枪法,在父亲失踪、新婚丈夫苦根失联的情况下,花红加入革命队伍,并凭借过硬的本领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尔后成长为一名部队指导员。花红为了让手上沾染老百姓鲜血的苦根绳之以法,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花红选择牺牲个人的情感维护群众和集体的利益,体现现代女性的精神自主和理性决绝。王华的《大娄山》中的娄娄是碧痕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她为了营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贫困青年,因为意外的车祸而丧生。娄娄活在碧痕村每一位村民的心里,她为脱贫致富所兴建的苗绣作坊没有停止运作,这也说明娄娄的精神影响着每一位村民和乡村干部。《紫青稞》中的阿佳天加是一个男性化打扮的女村长,“只有村长阿佳天加男人般的身材,浸透了阳光和青稞酒的黑红脸膛能一眼认出来……谁都知道村长生就一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l。普村阿妈曲宗家的老屋子被洪水冲垮,阿佳天加不畏惧藏族的“忌讳”,将即将撒手人寰的阿妈曲宗接到自己家暂住。阿佳天加的出现,是对藏族传统权威文化的解构。她既可以胜任原本男性负责的村长一职,又展现出超越男性的气魄和担当。女性乡村干部在当下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少数民族女性进入公共文化场域,她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在乡村基层做出一番事业,展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女性独特的精神面貌。
新世纪西部小说展现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公共领域”对于女性群体来说,是永远敞开的。在这个场域中,她们拥有了发掘自我潜能的机会和条件,同时她们在公共领域的表现也值得期待。贾平凹的《带灯》塑造了给乡村政治场域带来一丝明亮的基层乡村女干部带灯的形象。带灯是樱镇综治办的负责人,平日主要处理群众上访的日常事务。带灯是一个机智、聪明、能干的基层工作者,她机智应对村民的上访问题,妥善处理村民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尽管带灯身处综治办这样一个复杂的机构,但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团结了一批基层群众,将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女性基层干部竭心尽力地为人民群众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她们也在公共领域展现了自身的卓越才能。同样,尼玛潘多的《在高原》中,藏族姑娘白玛措吉毕业之后,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自己的故乡。白玛措吉回到塔金后成为一名乡镇干部,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她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她的很多改革思路和策略得不到周围人的响应。白玛措吉的一腔工作热情慢慢变得冷淡,她开始重新理解和认识自己的工作。小说的结尾,白玛措吉带着遗憾离开塔金走向了拉萨。在公共文化领域,西部小说中的女性基层工作者重视如何改善乡村基层管理以及如何调整乡民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不能忽视,带灯和白玛措吉的故事结局也反映女性在公共领域遭遇的客观难题,这亦说明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发展和成长之路任重而道远。
新世纪西部小说展现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表现不只是为了强调女性的觉醒和改变。在更深层次的方面,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发展也显示出她们在思想和行为表现上的智性精神,即一种充满正义感和生命赤诚的文化追求。例如,红柯的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中,新疆女孩吴丽梅具有纯粹的人文理想和知识追求。吴丽梅从渭北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繁华的城市,而是去到新疆偏远的大漠腹地塔里木军垦大学,从事有建设性意义的科研工作,诸如她常带着学术团队考察塔里木河下游的太阳墓地。吴丽梅最终献身学术事业,一场沙尘暴将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大漠深处。吴丽梅是新疆大漠和红柳文化的象征,即吴雪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拼搏精神。红柯将吴丽梅比作是“太阳”,“因为吴丽梅有生命活力、有信仰追求、有生活期待,她正像是一团火,太阳深处的火焰最终熔化人心的黑暗”m。与吴梅丽不同,她曾经的恋人徐济云浑身流露着“平庸之恶”n。徐济云在各种场合都穿着吴丽梅织的羊毛衫,他要从吴丽梅的身上汲取那股“火”的力量。唯利是图者利用一己之私扑灭学术圈和知识圈的火。徐济云深刻地知道吴丽梅离开他,离开渭北的原因是她厌恶知识分子圈子的污浊。小说中徐济云作为被现代物质文明腐蚀的个体,他所寻觅的救赎资源来自新疆姑娘吴梅丽。吴梅丽身上的自信、开朗、善良、正直等品质洗涤了徐济云内心的污浊,让其获得暂时的内心安宁。在公共文化场域,女性身上所体现的智性精神,代表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这也反映了女性个体独立睿智的精神品质和文化诉求。
在西部小说创作题材上,涵盖了从私人到公共的各种议题,既涉及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系、个体对自我身份、社会关系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现状的反思。在传统文化视阈下,西部女性一方面遭受着天灾人祸、疾病和死亡等带来的伤痛;一方面又遭遇着欺骗、不公和误解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尽管身处逆境或饱受挫折,女性依然挑起家庭重担,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女性的沉默背后是她们没有话语权和选择权。及至当下,西部作家们“努力撼动着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开辟出告别革命之后政治的新空间。正如所见,这些作家的作品体现出女性突破历史给定的角色,以主体之姿进行思考与创作的生命力”o。在新世纪的创作过程中,马金莲、肖勤、王华、阿舍、尼玛潘多等作家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强调普遍意义上的女性公共空间场域的重要性,呼吁建立女性表达自身和彰显自己的公共文化空间。同时,西部作家也强调充分地尊重女性的诉求和主张,关注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职业选择和工作成绩,彰显她们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由此也呈现西部作家在建构女性形象、推广性别文化以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多重探索。
进入新世纪,西部小说的女性书写打破了女性作为映衬男性雄性特质的窠臼。西部小说中的女性作为一群鲜活的生命存在,她们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情感需要,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且她们进入到公共文化场域后能在各行各业绽放自己的光彩。尤其西部作家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自我觉醒和观念蜕变的书写,丰富和重构了西部文学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体系。总之,新世纪西部小说展现了女性的性别自醒、性别反思以及性别经验的超越,体现对女性的精神诉求和文化主张的尊重,从而将性别平等与自足逐渐外化为一种朴素的日常生活书写。
注释:
a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b红柯:《古尔图荒原》,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c詹俊峰:《瑞文·康奈尔的男性理论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d周瑄璞:《日近长安远》,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e王华:《花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6期。
f萨拉·艾哈迈德:《过一种女性主义生活》,范语晨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86页。
g田泥:《走出塔的女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h露西·德拉普:《女性主义全球史》,朱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5页。
i米兰达·弗里克等编:《政治哲学中的女性主义——女性的差异》,选自《女性主义哲学指南》,肖巍、宋建丽、马晓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j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k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
l尼玛潘多:《紫青稞》,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m红柯:《太阳深处的火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01页。
n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o汪潇灏:《共域与私域之间——21世纪拉美女性导演作品观察》,《当代电影》2023年第5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