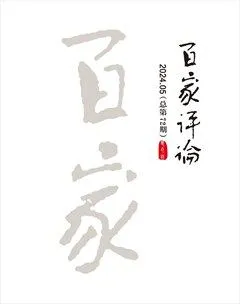从刘绍棠到徐则臣:运河文学书写范式的变迁
内容提要:运河独特的自然与文化价值赋予了文学书写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运河文学发展脉络中,刘绍棠和徐则臣各具特色的文学书写从各自时代中脱颖而出,展现出运河文学书写范式的变迁,赋予运河新的文学内涵。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时间、空间、象征等多个维度的对比,可以看出刘绍棠笔下的运河是千百年来“活”在生活中、带有浓厚的地域和乡土特征的京东运河,常作为衬托性的生活景观和精神底色出现在文本中。相比之下,徐则臣则更注重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主体性,书写其百年动荡的命运变化,彰显运河整体性和个体性的特征。时代语境的变迁是影响运河及其文学书写转变的关键,如何在运河申遗的热潮中,完成文学书写对文化遗产的反哺是当代作家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关键词:运河文学 刘绍棠 徐则臣 文化遗产书写 乡土文学
运河是自然景观与人类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条自然的文化之河。作为河流文化中的特殊存在,自古文人墨客都将深情的笔墨泼洒在大运河之上,由此孕育而生了专属于运河的文学书写。近年来,对于运河文学书写的研究不在少数,研究者们从多个方面剖析运河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特征,展现出运河的风情、历史和文化风貌。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全局,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究各时期的书写特征和运河风情;另一类注重研究典型的作家作品,从具体的作品入手,关注作家的创作手法和技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运河的命运浮浮沉沉,运河的文学书写也随之变化,书写范式的变迁对于运河文学的整体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内涵。
刘绍棠被称为“大运河之子”,他的一系列运河小说成为20世纪50—80年代当之无愧的运河文学书写典范。1982年,伦海在《刘绍棠的“运河文学”》一文中首次提出“运河文学”的概念,并通过对刘绍棠小说内容书写和选材视野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刘绍棠的“乡土文学”是地地道道的“运河文学”a。由此,运河文学作为独特的谱系而存在,一批作家陆续为运河文学的发展积淀力量。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家的创作大多与刘绍棠的运河文学书写有着一致的倾向,多注重描写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b。而随着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运河文学再次成为书写热潮,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北上》更是将运河文学书写上升到新的高度。徐则臣笔下的运河文学突破了原有的书写模式,从多个层面寻求突围和发展c,成为一种新的书写范式。因此,本文对刘绍棠和徐则臣的运河文学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当代运河书写范式的变迁,为文化遗产的文学书写提供参考。
一、时间维度下的运河书写之变
运河在中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开凿荆江沟通汉水的荆江运河、开凿巢湖沟通肥水的巢肥运河,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而到了隋代,隋炀帝开凿、梳竣运河,有了大运河之说d。隋唐时期运河的建设更是达到顶峰时期,贯通南北,统一全国。元代依托隋代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将运河裁弯取直,大大提高了运河的使用效率。后续朝代也对运河给予高度重视,进行疏浚、治理工作。总的来说,大运河的开掘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盛于唐代,取直于元代,治理于明清,贯穿中国古代的各朝代,积淀悠久沉重的历史文化。
与长江、黄河等河流横向分布相比,大运河贯通南北,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漕运体系,成为维护封建王朝经济和沿岸人民生活的保证。如果说运河是古代历史的见证,那么漕运则成为运河“活”的见证,并延绵至今。刘绍棠和徐则臣都关注到了运河的时间维度特征,但在文学书写中各有侧重。
刘绍棠的一系列小说选取了不同的时间节点来写运河,比如《蒲柳人家》《渔火》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运河,《运河的桨声》《夏天》描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运河等。在《蒲柳人家》中北运河上的帆船仍络绎不绝地往来,纤夫仍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文中也具体描写了运河上船夫的生活“刘罐斗每天黎明拂晓解缆,日落西山收船,往返两岸,迎送行人”“一支三丈大篙,握在手里,舞弄得十分轻巧。解开缆绳起了锚,大篙一抵河岸,大船便驯顺地直奔河心;然后他在河心一篙直刺到底,大船定住方位,在水流中不晃不转,平平稳稳向对岸靠拢。”e寥寥几笔船夫的行船技巧之熟练跃然纸上,同时凸显出两岸人民对运河的依赖,运河在奔流着,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而在《渔火》中“活”的运河描写更为明显,主人公之一的春柳嫂子生活在船上,一年到头都在河上打浆摇橹、行船撒网,“春柳嫂子这个小船帮,每天早起到通州东关的运河码头,载一船鲜鱼水菜,运送到北京东便门的菜市”f。
在这些典型时间维度下,运河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机,继承了隋唐以来的漕运功能。在刘绍棠笔下,人与运河融为一体,运河作为生活的底色默默地“活”着,奔涌着,“运河里响起一片行船的桨声”g。刘绍棠作为土生土长的“运河之子”,他对北运河有着深切的眷恋,北运河是童年的美好回忆,更是避难的港湾。运河在刘绍棠心灵中留下了美好的烙印,在对其描写时深受主观情感的影响,这也导致他的运河书写的片面化,缺少宏观历史深思,对运河发展、变化的历史描写不够深刻,没有关注到运河本身的价值与深度。反观徐则臣的运河书写,《北上》中的运河经历了“运河之殇”到“运河之活”的历史变化h,视野较为宏阔。
在时间选择上与刘绍棠不同的是,徐则臣并非一本书选择一个大的、相对固定的时间区间作为故事背景,而是选择了1901年、2012年、2014年三个小的、跨度大的时间节点,以点带面式地呈现不同年代的运河特征,追求“史诗化”的小说书写。而这种书写方式与当代文化大环境和大时代的熏染息息相关。以河流小说为例,作家们常常采用多卷本“大河”史诗叙事模式,书写江河流域一个或多个家族的生活、奋斗和家国情怀,为其立传、写史。i运河文学作为河流小说的分支,徐则臣在书写时也顺应了“大河”史诗叙事的传统,致力于为运河写史,所以在小说时间选择上更为精准,时间覆盖面更广,展现百年间的运河命运起伏。
《北上》选取1901年、2012年、2014年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展开叙述,同时在结构上选择交叉叙述的方式,不以时间顺序为依据,而是按照运河的命运来谋篇布局。在1901年的故事叙述中,小波罗一行人几乎是一路与运河为伴,真正与运河同呼吸,这时的运河看似“活”着,实则是日落西山,与晚清政府的命数一样垂死挣扎着,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其漕运功能的没落。1901年的故事结尾这样写道“并肩行使的一艘官船上有人在谈漕运。一个说:‘这怕是最后一趟了。’另一个说:‘果真要废?’‘宫里传出的消息’”。j小说中的北上之行与现实中光绪帝颁废漕令交叉重叠,虚构时间与现实事件在结尾重合,将对运河命运的思考推向高潮。漕运作为运河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千百年来运河“活”着的象征,而如今漕运被废除,也意味着运河的命数将尽,由活变死。而到了2012年,横跨百年时光,邵家跑船命运在新时代科技冲击下面临终结,“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k,船家人的“上岸”预示着运河命运的沉沦。这两个节点都展现出对“运河之殇”的深思:当运河漕运功能受到挑战,命运沉浮飘荡,运河该何去何从。但《北上》的出发点并非是要停留在运河之“殇”的缅怀层面,而在于揭露运河由“殇”到“活”的时代命运,探寻新时代运河发展前景。在第二部、第三部中,新一代的运河人面对殇之痛,迎难而上,利用时代的契机,让千年运河“活”起来。《大河谭》的起死回生和大运河申遗成功,再次将虚构时间与现实事件重叠,运河在遭遇了旧的漕运功能没落后,寻找到新的价值支撑,即运河独特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文化内涵的挖掘探索,运河再次以新的身份“活”在人们生活中,完成了身份蜕变和价值重构。徐则臣通过对“运河之殇”到“运河之活”转变的描写,将运河放置于时间与历史的维度中,给予深刻的反思,将运河的命运上升到百年间的世界、民族的命运,“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l。
简而言之,从时间维度角度来看运河书写之变,刘绍棠在乡土情怀影响下,偏重于描写生活中“活”的运河,是对千年历史的“不变”的继承;而徐则臣在时代史诗写作影响下,偏重于将运河的命运与世界、民族命运相联系,关注到百年间运河之“殇”到运河之“活”的“变”的创新。
二、空间维度下的运河书写之变
大运河横跨南北,蜿蜒3200公里,串联北京、济宁、扬州、杭州等18座城,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养育了沿岸子子孙孙,孕育了各具特色又包罗万象的风俗人情。
刘绍棠的“运河文学”是在“乡土文学”基础上孕育而生的。刘绍棠多以京东运河为写作背景,以北运河一代的农村生活作为创作主体进行细致描写。从空间维度来看,运河书写的地方性、区域性特征突出。相比于河床宽阔、水流和缓的南方运河,北运河地势高低起伏,在样貌上显得更为野性:水流较急,四季变化明显,时而碧波浩渺,时而汹涌澎湃。在《蒲柳人家》中,刘绍棠曾这样写道:“这片河滩方圆七八里,一条条河汊纵横交错,一片片水注星罗棋布,一道道沙冈连绵起伏。河汊里流水潺潺,春天只有脚面深,一进雨季,水深也只过膝,宽窄三五尺,也不搭桥,可以一跃而过;河汊两岸生长着浓荫蔽日的大树,枝枝丫丫搭满大大小小的鸟窝m”。进而,刘绍棠自然而然地将北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与独特的运河滩风貌相融合,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水乡风光。在《蒲柳人家》中,以何满子的视角勾勒出运河摊上儿童的生活乐趣,“何满子最喜欢到河滩上玩耍。光着屁股浸入河汊,捞虾米,掏螃蟹,摸小鱼儿;钻进苇塘里,搜寻红脖水鸡儿,驱赶红蜻蜓满天飞舞,更是有趣;但是,最好玩的还是在大树下、茂草中和柳棵子地里,埋下夹子和拍网打鸟”n。在儿童的嬉笑中,刘绍棠用亲身经历和细腻的笔触绘制出一幅幅独属于北运河的风情画。
作为乡土作家的代表,刘绍棠对家乡深深的眷恋都凝聚于笔端,书写在大运河之上,他曾说:“在我眼里,我的家乡的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都无比可爱,美不胜收。我要以全部的心血和笔墨,描绘出京东北运河农村二十世纪的风貌,为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o,因此,刘绍棠的北运河“乡土”气味十足,从运河风光、风土人情,再到民族情怀等,都展现出小空间里的运河风情。正因为取材的局限性,导致了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在空间转换上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将运河“静止”,缺乏空间关照和对比,仅凭借不同景观和历史事件的变迁来显示运河的“动态”发展。这也促使后期创作出现“同质化”的倾向:一样的运河,相似的故事展开方式。典型的如《运河的桨声》与《夏天》,这两本作为姊妹篇,选取了同一地点山楂村,相同的人物春枝、俞山松等,同样的历史事件农村合作化运动,同样结局正义战胜邪恶,未免过于单一和普遍化。因此,过于乡土化的运河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使运河丧失了空间上的独特性,文学书写与一般河流书写形式趋同、合流。
相比于早期的运河文学书写,徐则臣的《北上》对运河的空间性特征给予高度重视。大运河早在古代就显现出独特的整体性和辐射性的特征。溯源隋炀帝开凿贯通大运河,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沟通南北,运输南方粮食,带动南北经济的协同发展,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建设。在贯通南北的同时,大运河又联系各条小河流,呈辐射状漫延至各城各县,流经千家万户的家门口。大运河像一张网,网住了南北,密密麻麻;像大动脉,通过遍布各地的毛细血管深入各家各户,带动区域整体跳动着、发展的。因此,对于大运河的文学书写不能脱离整体性,大运河是一条完整的河,只有将运河的七段合成一起才是大运河真正的价值p。《北上》中,小波罗一行人从南往北顺水走一遍,大致途径了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清江浦、南阳镇、济宁、临清、沧州、天津、通州等运河流经的重要城镇。他们在船上行、路上走,领略各地的风光和乡土人情。同样的,百年后周海阔的12个“小博物馆”沿运河次第诞生,周海阔也常常坐着“小博物馆号”从南到北例行巡视一轮。由此可见在空间维度上,徐则臣的运河文学书写,以全国观照地域,既展现了各地的运河风采,又凸显了整体性的民族文化脉络,与新时代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相互照应,进一步深化了运河文学书写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从空间维度来看,运河文学书写经历了从归属乡土的局部运河书写到整体性的完整运河书写的转变。但刘绍棠和徐则臣在运河空间上的选择都是时代所赋予的选择,刘绍棠深耕乡土,徐则臣放眼全局,都将运河的空间书写不断扩展、完善。
三、象征层面的运河书写之变
古代文人重视将人的“有情”付诸世间“无情”之物上,使人的情感得到认同、价值得到重构,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追求和情感共鸣。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当代文学作品,也具有此特点。因此,对于运河文学的研究,象征层面也愈发显示出重要的地位。作为运河文学的主体——运河从来都不仅仅是作为一条河流出现,多被赋予作者、时代的思想价值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绍棠的小说中对于运河的直接描写很少,多在全书开头、结尾或者段落的开头。他赋予运河两层象征含义:一是作为生活景观,二是作为民族精神底色。第一种作为生活景观出现的运河是最为常见,其描写也是最直接的,大多出现在全文或者段落的开头。在《运河的桨声》中,刘绍棠以清新质朴的笔墨,用带有诗意的语言重点描绘了北运河四季的美景:“夏天,是运河滩最美丽的季节。青色的天空,白茫茫的大河,一望无边的青纱帐,掩盖了村庄。天空,苍鹰在盘旋;河上,行驶着白帆运货船;青纱帐里,有劳动的欢笑声;茂密高耸的树林中,布谷鸟不知疲倦地在歌唱”q“八月,运河平原的落雨季,到了最后也是最凶恶的阶段了。有时,夜晚瓢泼大雨,天明,太阳升起,平原上泛着金光,冒着清香的湿气,新洗过的青纱帐,绿油油的像要滴下绿滴来”r。作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刘绍棠对于运河的自然描写着力追求诗情画意的美,效法于孙犁,却又生成了专属于自己的“运河牧歌”,专属于北运河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质朴s。而作为生活景观的运河又象征了人民生活的状况,从自然转向社会风俗,如写落雨季,凶猛的运河象征着山楂村党员正为了运河滩居民的生命和丰收,与破坏分子展开紧张的决斗,运河成为生活的写照。
而第二种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运河描写多出现在字里行间和文末。刘绍棠潜移默化地将运河作为运河滩人民奋斗的背景陪衬,是勤劳智慧的劳动农民美好精神的底色。刘绍棠在《运河的桨声》和《夏天》中将运河四季的变化与“山楂村”农村合作社运动的发展相融合,运河的汹涌澎湃孕育出豪迈爽朗的运河文化,成为沿岸人们积极向上、为生活奋斗的精神底色和不竭源泉。“雪白的桅灯照亮了运河滩,照见了运河的远方。运河里,响起一片行船的桨声。这是运河平原前进的脚步声!这是运河平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脚步声!”t,运河是沿岸人民生命的依托,它用无声但顽强的生命力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运河人”,而到了新中国时期,运河文化中蕴藏的民族精神底色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强音相融合,铸造起属于人民的、家国同构的精神家园,激励着“运河人”在运河上奋勇前行。
相比于刘绍棠笔下作为“背景板”出现的运河,徐则臣的《北上》则将运河文学的主体重新归还运河本身,将运河视为有生命的个体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将宏观叙述落其本身,关注运河的命运沉浮,真正将运河作为民族的象征来书写、来保护。《北上》突破乡恋情结的束缚,采用外来视角,让运河呈现出本色。小波罗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摒弃其他情感的纷扰,在生命最后时刻与运河同呼吸,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运河本身激昂澎湃的生命,而这也是徐则臣所想表达的:运河存在价值并非是人类情感的牵强附会,而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生命体,“运河说话了。运河是能说话的。它用连绵不绝的涛声跟我说:该来就来.该去就去。就像这条大河里上上下下的水,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u。
2014年,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再次彰显了运河本身的生命力和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借此契机,《北上》中大运河一改以往形象,脱离沉重的宏观叙事框架,不再作为历史的衬托,而成为文化遗产的代表,象征着文化的当代继承与创新。如果说1901年小波罗一行人的北上,是一场运河文化的溯源之旅,那么百年后的谢望和、邵氏父子、孙宴临、周海阔和胡念之的重聚,则是一场与运河文化不期而遇的邂逅。不管是邵星池的“上岸”与回归,还是谢望和《大河谭》的垂死与复苏,都展现了新一代“运河人”的命运选择:经历过面对时代浪潮冲击时迷茫与无措,但最终在对文化遗产大运河的继承与保护中,重新获得文化认同,实现自身与大运河的转变和发展。
简而言之,在刘绍棠的笔下,运河作为生活景观,是沿岸人民蓬勃向上的生活和民族精神底色的象征;而徐则臣纵观百年运河和民族命运的发展,其笔下的运河成为独立的生命体和文化遗产代表,象征着民族文化生命力的顽强,探寻新时代运河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四、运河书写之变的时代语境
回归作家的创作本身,就刘绍棠和徐则臣的创作时间而言,二者的运河文学书写年代相差六十多年,几乎横跨了我国当代发展的主要阶段。在我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瞬息万变的时代语境对文学风气的塑造和作家创作的追求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作品上更为明显。从刘绍棠到徐则臣,运河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面貌逐渐完整、丰富、深刻,逐步实现了时代语境变迁下的运河在文学上的“再生”和“再创造”。
刘绍棠的时代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文学着眼于反映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当代风貌。对于文学有着较为严格的规范,作家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新文艺方向下进行的有目的的创作,题材有着严格的分类尺度和价值等级。在此时代语境下,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在题材上注重农民题材小说书写,所塑造的人物、所选取的事件与现实中的农民斗争息息相关,他将满腔热情投入到对家乡人、事、景的赞扬之中,而对运河的关注多在于其为人和社会发展提供的实用和精神价值。简而言之,刘绍棠更偏爱于书写运河之上的人,他们是如何生活、奋斗着,而运河仅仅作为刘绍棠作品的空间底色的专属标记而存在。
徐则臣作为70年代作家,生长于改革开放时期,奋斗在新时代时期,视野愈发开阔、开放。在当代国家强盛发展的背景下,文化自信、文学本身的重要性被凸显,在文学创作上更为多元、开放。运河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见证,作为文学遗产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徐则臣的运河文学不仅继承了传统运河文学的书写特征,更融入了新时代的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观照,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怀揣着自信开放的胸怀。与刘绍棠的运河文学相比,他在创作上增加了对运河历史命运的深思、外来视角的关照,作品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当代气魄,突破了乡土运河的局限性,更显史诗气派。
从两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到运河本身在运河文学中的比例越来越重要,这也与作家关注重点的转移有关。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并不是为了运河而书写,而是借运河这个熟悉的家乡景物进行规范性写作。总体上文学是反映现实,与政治配合的衍生品,因此运河本身被放置于次之的位置。但是徐则臣将运河作为小说主体进行创作,反映出文学与时代的发展,彰显运河自身的价值所在。
在时代语境变迁的影响下,运河文学的发展出现新的转机,它不再归属于单一类型化写作的一员,不再是单纯作为政治书写中的背景而出现。徐则臣也多次强调为运河写史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运河文学如何去写好运河本身,如何去适应运河在新时代的身份转变等问题尤为重要。徐则臣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启发下,给出了新的写作范式:将运河视为文化遗产这一独立的个体,关注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内涵,用文学去摹写完整的运河、生命跳动着运河,让其自身发光发热。但如何进一步去发展运河、如何用文学让运河更深层次“活”起来,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结语
总的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运河文化基于乡土文学,通过刘绍棠等作家一系列的文学书写,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学体系,并随着时代不断扩大、补充。到了新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文化自信和文化精神力量被放置于重要位置。随着代际更迭,以徐则臣为代表的70年代作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身先士卒、大胆创新,将时代精神注入文学写作之中。《北上》的成功标志着运河文学发展进入新阶段,成为新的运河文学书写范式。
大运河申遗成功仅仅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如何适应书写范式的时代变迁,如何利用申遗为契机进行文化遗产的文学书写,如何用文学反哺、保护文化遗产等等问题都是当代作家运河书写面临的全新挑战。而从刘绍棠到徐则臣的范式的成功转换,为当代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为展现新时代的不一样的运河提供了更广阔的书写空间,同时为其他文学遗产书写,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范式。
注释:
as伦海:《刘绍棠的“运河文学”》,《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bp刘勇、陶梦真:《运河文化的历史品格及其文学书写》,《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18年第16期。
c萧映、李冰璇:《突围与担当:论徐则臣〈北上〉的写作策略》,《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第3期。
d雷雨、王一苇:《运河与文学及其他》,《东吴学术》2019年第2期。
ef刘绍棠:《蒲柳人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页,第89页。
gqrt刘绍棠:《运河的桨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第100页,第114页,第137页。
h陈佳冀、丁思丹:《观百年运河史·践国族文化想象——从〈北上〉看徐则臣的运河书写》,《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i蒋林欣:《近年来中国河流小说创作态势观察》,《当代文坛》2022年第5期。
jklu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39页,第93页,第466页,第336页。
mn刘绍棠:《蒲柳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5页,第15页。
o高德澍、张钰丛:《大运河畔乡土根 矢志不渝赤子心——著名乡土文学大师刘绍棠的运河情结》,《北京档案》2014年第9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汉语写作研究中心)
——论徐则臣文学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