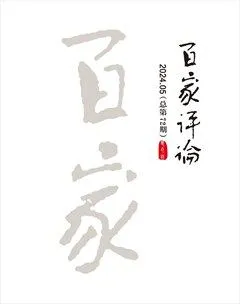晚生代的“内”与“外”

内容提要:晚生代群体及其中短篇小说创作,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他们身上暗含了这样的文学史问题:90年代如何消化和选择性地继承80年代形成的文学传统,并将之转化为新世纪文学的起源性因素。作为这个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李洱的文学实践勾勒出了晚生代出场和流变的文学线索。期刊改制及其制造概念的策划行为,形成了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围绕在晚生代周边的小环境。通过先锋文学与新写实文学传统的清理,他们对于现实主义形成了新的理解方式,折射出两个文学时代的赓续和流变。
关键词:晚生代 李洱 期刊改制 内面
晚生代,又称新生代,指出生于1960年代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引起文坛注目的一批作家,大致是以时间为基点对作家世代进行的划分。鉴于“新生代”的使用存在泛化的倾向,衍化成新生力量的代名词,本文采用“晚生代”的说法以期保持这个概念的文学史张力。晚生代既没有提出宣言式的文学主张,内部之间也有很大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确实显示出了与前辈作家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因而,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而是如群星之于星座般形成的作家群落。
晚生代群体中,无论是在文学创作的实绩还是在理论自觉的程度上,李洱都是极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以李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为中心,探讨晚生代的出场和流变,不仅有助于对于这一作家群落的再认识,同时也寄寓着激活90年代文学研究的意图。如果说“50后”作家体现出的是一种固态的、同质化的文学史,那么在晚生代身上,我们则可以看到一种流动的、不规则的文学史。某种程度上讲,晚生代扮演了从80年代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转换器的角色。相对于同时期的长篇小说,晚生代在90年代的创作实绩并不足以成为标志一个时代高端成就的文学地标,然而却有可能更接近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学秘密。他们积极回应新的文学场域的规则,有意识地清理文学传统、反思个人创作,在内外两个方向上标示出一代人的文学探索,由此也为我们重新进入90年代文学留下了一条小径。
一、90年代文学留下什么
90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自足的文学年代,倒不如说是一个喧嚣的文学时段。它夹在“八十年代”和“新世纪”两个文学史的“庞然大物”之间,显得面目模糊,而带有某种突变和过渡的意味。且看学界对90年代文学最早的建构尝试——“后新时期”a,仅从偏正式的构词方式便可看出,中心语“新时期”是进入90年代的逻辑起点,如何处理与80年代的关系,构成了理解90年代的前提。修饰语“后”则带有崩解、解构的涵义。90年代的到来,被赋予了宣告80年代的终结并与之告别的使命。身在历史现场的作家,也明确地意识到“‘新时期文学’已经划上句号”,他们忧心忡忡,预感文学的未来像是“一个大汉扛着舢板寻找河流”。b
然而,当我们站在后设的历史视角,回顾90年代至今的文学历程,我们或许会转而认可施战军的观点:90年代是一个“写作实验真正敞开和结出硕果的时代”,“八十年代很多潮流的结算在九十年代”。c《丰乳肥臀》《白鹿原》《心灵史》《废都》《九月寓言》《长恨歌》《平凡的世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即使放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中,长篇小说的丰收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不仅如此,人文精神大讨论、《废都》批判、王朔现象、学者散文、女性写作、期刊策划出的文学新概念……文化领域的众神狂欢和众声喧哗让90年代成为一个高密度的文学年代。文学外部环境和作家文学理念的变革——内外交织的新格局为90年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大致还是以归纳和总结为主,有待更多的概括和分析的眼光。因此,要将90年代文学研究从时段学引向年代学,首先需要经过一个做“减法”的阶段,对90年代文学能够留下什么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与上文提及的长篇小说现象并举,我以为晚生代群体及其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创作,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学史问题。晚生代的代表作家有朱文、韩东、毕飞宇、李洱、艾伟、邱华栋、张旻、李大卫、李冯、东西、鬼子、何顿、李敬泽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作家很少结构长篇,普遍集中精力写作中短篇小说。以“50后”作家为创作主体的长篇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写作。这不是题材意义上的历史,而是说对大历史的记忆沉淀在他们人生经验的底层,以至于作品的底层都有一个关于历史认知的整体结构。90年代的长篇是面向过去的,是作家在历史转变之中,站在一个新的位置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的总结式的写作。晚生代及其创作则应和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潮汐,彰显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构成了90年代最具“年代性”的写作。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脉络来看,晚生代暗含了这样的文学史问题:90年代如何消化和选择性地继承80年代形成的文学传统,并将之转化为新世纪文学的起源性因素。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90年代的现场感和年代感,并由此见出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和一种新的文学流向。
描绘其成员和创作面貌的论文著作已有不少,在此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历史文本”:张钧的《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李敬泽、李大卫、邱华栋、李冯与李洱的《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自1997年开始,从长春到广西,张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与28位新生代作家进行专业对话:朱文、韩东、鲁羊、吴晨骏、荆歌、罗望子、毕飞宇、张旻、西飏、夏商、李大卫、李冯、徐坤、邱华栋、林白、丁天、刁斗、海南、陈家桥、东西、鬼子、李洱、墨白、行者、刘继明、何顿、曾维、王彪……这代作家的文学观念因他的串联而得到集中展示。1999年,张钧因肺癌去世,计划中的新生代作家小说理论集和个人研究论著均未能问世,仅留下这部访谈遗稿。如果说张钧的工作勾勒了晚生代的面部轮廓,那么四李一邱的对话则是对这一群体的工笔细描。1998年11月3日,在李大卫的单身公寓,五人从上午持续谈到深夜,涉及到的话题包括“个人写作”“日常生活”“传统与语言”以及“想象力与先锋”。他们以此对90年代文学的关键词进行踩点和勘探,试图在“断裂问卷”的路径之外,建设性地阐述一代人的文学观念。
李洱1966年出生于河南济源,198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被他视为文学童年的人生阶段。系统的文学训练、良好的理论素养以及世界文学的视野,让他的写作一开始就带有“智性”的色彩。这种“智性”不仅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持续关注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方式上,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身上那种反思文学传统的意识,以及对当下生活命名的能力。“午后的诗学”“生活在自身之外”“行走的影子”“饶舌的哑巴”“悬浮”……他在进行表现的同时也在进行概括。从90年代的《午后的诗学》《葬礼》等中短篇小说到新世纪的长篇小说《花腔》和《应物兄》,李洱有变化,但远称不上突变或转向,他的写作状态如河流一般绵延、连续,一边顺着80年代的文学风貌而来,一边又在新世纪得到充分展开。在他以及他的晚生代同人那里,我们可以见出百年中国作家身上少见的不被外力打断的自然生长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洱为我们回溯90年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个案。
二、文学期刊与一代人的历史出场
“晚生代”的概念,除了60年代出生的维度,还特意强调9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间节点。李洁非将“新生代作家”的崛起勘定在1994年之后,一个主要依据便是文学期刊以新生代作家为主体而策划的“联网四重奏”、“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以及“跨世纪星群”等栏目亦未开设。d可见,文学期刊对于晚生代群体的形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990年代,经济体制的改革下沉到文学领域,政府放宽期刊自主权,同时逐渐减少甚至中断财政拨款,鼓励期刊自谋生路。文学期刊的运行被推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生存状况普遍不容乐观,办刊经费不足是最大的难题。困则思变,为探寻生存之道,主编们推动文学期刊“转换机制,探讨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以改革求生存”。e于是,期刊与编辑从幕后走到台前,主动制造文学话题,引导文学生产,成为文学场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主体。以至于有论者认为,90年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编辑的文学”。f期刊改制与期刊的策划行为,形成了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围绕在作家作品周边的小环境。李洱以及晚生代的创作风格,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与期刊导向之间相互平衡与调谐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仅以在90年代集中刊发李洱作品五个文学期刊为来源,通过简单的统计学的方法,看一看这样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和生产方式如何形成和运作。
90年代,李洱大约发表了37篇中短篇小说,占其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二以上,上表统计的信息大致反映了此期的文学风格和样态。刊发李洱作品的栏目,除“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这种传统设置,背后大多带有文学期刊的建构意图。进一步来看,期刊的建构路径可以分为推出作家和推出概念两类。
《作家》的李洱短篇小说专辑、短篇小说五家十篇、短篇小说元月展,《山花》的跨世纪星群、跨世纪十二家、99作品联展等栏目,或是集束式地推出李洱多部作品,或是将他置于晚生代群体的序列中,客观上“制造”出一种作家世代更替的印象。期刊改制之际,文学期刊尤其是地方性文学期刊,格外倚重“青年”的力量,倾向于奖掖后进,培养新人。宗仁发谈到,“衡量一位编辑有没有眼光、一本杂志有没有水平,发现新人、刊发新作,是一个标志性的衡量标准。”g从《关东文学》到《作家》,宗仁发任职的期刊成为李洱发表小说的重要园地。作家成长的背后脱不开与编辑的扶持与友谊。《山花》也是新概念的热心推出者和策划者。主编何锐认为,“一本刊物除了定位而外,栏目策划也相当重要,有创意的栏目设计不仅对读者有吸引力,而且会对作者产生感召力和凝聚力。”h因而,《山花》极力在栏目上求新,制造了许多文学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从囊括37位作家的“跨世纪星群”到仅有12位作家的“跨世纪十二家”,文学期刊实际上揽过了对同时代作家的遴选工作,试图实质性地参与当代作家的经典化程序。
“后先锋小说”和“凸凹文本”的提法则属于推出概念的行为。《遗忘》当是“凸凹文本”的标志性作品。90年代末,85先锋作家业已完成现实主义转向,凸凹文本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实际上提出了先锋之后谁来继续推进小说形式实验的问题。后先锋小说的命名也有类似的意图。它们的出现表明文学期刊实则是在“先锋文学”的延长线上界定晚生代的。这种认识方式强调世代的区隔,更强调美学上的延续,与学界最初对晚生代的定义一致。陈晓明提出“晚生代”的概念,指称的正是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带有先锋色彩的作家,判断依据在于他们是“当代生活的‘迟到者’,摆脱不了艺术史和生活史的‘晚生感’”。i可见,晚生代之成立,主要是以先锋文学为参照,如毕飞宇所说,“它潜在的中心词还是先锋文学。”j因而,当四李一邱展开对话时,他们的一项主要工作便是通过对先锋文学的反思,将晚生代与他们的“传统”剥离。李敬泽谈到,“新写实”之所以强调日常生活,主要针对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启蒙传奇、英雄传奇。李洱很自然地接话:“还有先锋传奇”。可见,他们固然是被先锋文学滋养而成长的一代作家,但他们自认为“与先锋文学的联系是分享了他们在文学技术上革新带来的成果”,“在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上,则较为鲜明地有所区别”。k“先锋文学”之于他们,是一个需要跨越以确证“个人”价值的障碍,一个需要与之对抗的文学成规。
相比地方性文学期刊的积极策划,《人民文学》《收获》在版面设计上趋于保守,沿用常见的“四大块”(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模式,可以说是期刊改制风潮中的守成派。不过,《人民文学》并非毫无动作,1997年12期的《再致读者》预告刊物将在次年改版,展示一种新的面目。从次年第1期的版面看,改版的亮点一是着力于推举新人的“小说新人”栏目。只不过,此时的“新人”已更多地指向70后作家;二是令人备感意外的“小说连环”栏目。编者阐述栏目设想:通过邀请十二位作家以接力写作的方式,共同为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无疑是由一个个的悬念组成的故事。李大卫的故事开始了,也结束了;下一个出场的作家,他在破译李大卫留下的这堆密码的同时,也把新的悬念与疑情留给了下一个。没有既定的谋篇布局,也没有一个贯穿到底的策划与构想,这种‘违规操作’也因其不可预测性而魅力横生。”然而,读者对这种讲故事的形式并不买账。《人民文学》第十期上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读者不喜欢的栏目前五名,排在第一位的正是小说连环。不知是因为读者反馈起了作用还是接力的方式难以为继,“小说连环”进行六期之后突然中断。四李一邱中,李敬泽时为《人民文学》编辑,其余四位均参与了小说连环,这一项或也可以视他们的“集体作业”的尝试。
在这些期刊策划行为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联网四重奏”。“联网四重奏”声势浩大,由四刊一报(《作家》《大家》《钟山》《山花》与《文学报》)在1995年联手举办,四家期刊同时开辟“联网四重奏”这一新栏目,逢单月份同步推出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并以《作家报》同步配发评论文章的方式,为作家造势,以提高社会关注度。l至2000年结束,持续近6年,共有25位作家参与,其中又以晚生代作家为绝对主力。合作期刊数量之多,地域跨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入网作家之众,在90年代首屈一指。1998年,李洱应邀“入网”,除了表格中的作品之外,还有《钟山》第二期上的短篇小说《夜游图书馆》。由于刊期集中,从选定入网到作品刊载,留给李洱的创作时间大概只有三个月左右。作家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的创作,在一篇作品中形成的心境势必会带入下一篇作品中去,以至于造成创作上的重复和趋同。这一年,李洱共有12篇中短篇小说问世。统观这些小说,我们能清晰地辨认出李洱的文学风格,也能隐约觉察到他从个人化写作落入风格化写作的危险。张钧访谈时即对此表示了忧虑:“你的这种写作在独具一份意味的同时是否也会在某些方面限定你的视野?”m与期刊策划的对接,拓宽了李洱的文学空间,但也难以避免地使他受到外部的影响。毕竟,文学期刊更青睐于那些已经在文坛上确立了风格的青年作家。相对于可能性,它们看重的是确定性。结果是迫使晚生代作家在某一种风格上固定下来,透露出老成的气息。90年代末期的李洱就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线上徘徊,处在这种高产而又缺少变化的阶段。在借助“晚生代”的概念获取出场机会之后,如何走出一条个人的道路对于作家的成长来说是惊险而关键的一跃。
三、“十五分钟”之后怎么办
李冯曾把“总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钟”看作晚生代的写照。在他看来,每一代人都有出场的机会,问题是十五分钟之后怎么办?“可能是下一个十五分钟……可能也是危机”。n进入新世纪之后,晚生代群体经历了分化、流散,不少作家在短暂的爆发后似乎耗尽了自己的文学势能,如引导过一时风潮的朱文,不再有突破性的作品甚至中断了写作;有的作家则转向影视剧本写作,如李冯,虽有小说问世但影响远不如他编剧的《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只有少数作家度过危机,向着新世纪文学的中心作家默默生长,体现出邱华栋所说的那种“独特性”和“生长性”:“无论怎样进行代际划分,最后脱颖而出、代表整个时代的,往往只有几个人,这些作家都是默默生长的,而且单纯的代际划分对这一类作家甚至都不起作用。好作家的独特性与生长性是不可用代际替代的。”o李洱无疑属于这其中的一员。
如果说期刊改制创造了晚生代历史出场的外部“场域”,那么“十五分钟”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终究要从作家的“内面”中寻找答案。
同先锋文学一样,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兴起的“新写实”也是被四李一邱视为需要清理的文学传统。新写实最初出现时,“以现象学式的还原态度准确地描摹了日常生活的某些表象……很快升华成一种更为隐蔽的形而上学,一种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p他们所理解的“日常生活”,先在地暗含了对形而上学的反抗。在李洱看来,“写日常生活,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基本的主题,即个人存在的真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受到了威胁,日常生活是个人、权力和历史相交错的最真实的地带。”q如此一来,“日常生活”就与“个人”联系到一起,共同构成了写作的支点。
李洱因此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寻找到一处未被探明的文学空间。沿着先锋文学和新写实的脉络,是从宏大叙事中走出,转向对“个人”处境的关注,将个人经验摆放在文学的中心位置;反着这两个文学潮流,则是对“日常生活”诗学空间的开掘,通过现象学式的还原,追求一种“真实性”的反映。如果说80年代文学的主题,是将“现实主义”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取出,那么晚生代所做的便是将“现实”从“现实主义”中取出。对于李洱等人而言,恩格斯意义上的经典现实主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已经不能恰切地表达他们对时代的感受。作为修正方案,他们将“典型人物”置换成“个人”,将“典型环境”置换成“日常生活”,趋向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文学公式。经过先锋文学和现象学的渗透,现实主义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面对晚生代的创作,评论界往往将个人经验指认为对集体话语、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拨,也就是将“个人”视为一个超历史的概念。然而,从五人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对“个人”的理解恰恰是历史化的产物,确切地说,是一代人的历史焦虑感的外化。李洱提出“个人写作”“第一是逼近个人经验,第二是呈现个人生活的真实性。”这一观点刚一抛出便在同人中引起很大争论。李敬泽不认同第一层面的叙述,强调的是“个人与时代、与历史的、内在的、批判性的关联”。李大卫也认为,作家“必须在公众面前维护自己在意义问题上的被咨询权。”经过一番讨论,“个人写作实际上是敞开的写作”成为五人的共识。他们实则反感个人写作的“小家子气”,希望能把个人和时代、历史的联系“调整到更宏大的关系里去”。r
问题是,建立个人与时代的联系,于“50后”作家而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晚生代来说却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大历史的记忆或者说革命年代的经验对于他们的成长只是一种背景式的东西。李洱曾谈道:
具体说到六十年代作家的共性,我想把他们说成是悬浮的一代。与上代作家相比,他们没有跌宕起伏的经历,至少在九十年代之前,他们很少体验到生活的巨大落差。不过,他们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某种体制性文化的分崩离析,但与此相适应,某种美好的乌托邦冲动也一起消失了。这个变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们的青春期前后!而他们的世界观,正是那个阶段形成的。对于如何理解这一代人,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点。s
“体制性文化的分崩离析”,造成的结果是共同经验在个人体验中的崩溃,“个人”向外的通道被堵塞,悬浮于时代之上。因而,他们对于时代总体性的把握需要在经验的碎屑中努力拼凑:
我们这代人的经验,可以说是“三足鼎立”:我们都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也有市场经济时代的经验,9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也有了全球化的经验。这或许可以说,在这些年持续写作的过程中,这三种经验共同构筑了我们。t
这两段谈话对读起来颇有意味,可以从中看到一条晚生代从悬浮到落地的线索。无论是《午后的诗学》中的知识分子还是《奥斯卡超级市场》中的小市民,李洱塑造的都是回归生活的人。只是,“生活”本身在90年代发生了变化。个人主体性在商品社会中的虚幻满足和瞬间溃败,构成了李洱这一时期中短篇小说的一个总主题。与张钧对话时,李洱反思自己的创作,“小说的毛孔可能已经张开了,但好多重要的器官还没有打开”。u“打开”小说的“器官”的过程,伴生于发现自身经验的过程,其实就是个人向外部的敞开,以寻找一种与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时代的生活结构相调谐的文学结构。通过对李洱新世纪以来的《花腔》《应物兄》的回溯式阅读,可以发现,李洱的“敞开”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
首先是“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李洱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红楼梦》。作家对于这部古典文学的喜爱,投注了关于自己以及当下文学写作路向的思考。这里的“贾宝玉”其实就是“个人”的代名词。李洱谈到,“中国文学跟西方文学有一点不一样,它有这样一个起点,也就是它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贾宝玉怎么长大,以及长大以后怎么办。”v“作为成人的贾宝玉,应该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应该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w构成了他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在晚生代阶段,李洱理解的“个人”处在分崩离析的境况里,作品反映的是总体生活解体之后的散乱状态。个人化和日常生活被放置核心的位置,对应着对于时代的碎片化的感受。随着李洱自觉地建立自己与时代的联系,作品中建构性的内容随之多了起来,最终导向《花腔》的产生。他有意点出葛任(个人)生于青峺峰,殁于大荒山,引导读者在葛任与贾宝玉之间建立联系,以迫近他所要处理的“‘个人’在成熟之后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命题”。x如他自辩,《花腔》“不是相对主义的虚无,里面包含着建构的企图”。y
其次是“写作应该是在各种东西的交接点上,应该能够辐射周围的生活,各个层面都能辐射到。”z交接点的位置,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中才能安放,如此才能完成“个人”的敞开。这与上面的问题其实是连着的。“交接点的意识”反映在文学上便是“辐射式的写作”,自觉地与线性叙事区别开来,试图消解宏大叙事的意义,呈现日常生活的互文性。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是个人、权力和历史相交错的最真实的地带。”从日常生活可以进入到一代人经验的内部,同时也从他个人所在的位置,给予读者一个透视时代的角度。近作《应物兄》更多地联系着90年代的《午后的诗学》《葬礼》等中短篇小说,在探索日常生活的诗性空间的脉络上展开。
李洱向外部“敞开”的过程,既是个人创作史的一条线索,同时也折射出两个文学时代的赓续和流变。新世纪文学的来路在这样一种探询的视野中,得以更加清晰地呈现。
注释:
a1992年秋,北京大学与《作家报》联合举办“后新时期——走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讨会,明确提出“后新时期”的概念。相关的文章还有谢冕的《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以及张颐武的《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等。他们对于“后新时期文学”的阐释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新时期文学内部便有新质产生并开始它的裂变”。
b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c李敬泽等:《九十年代文学——从“断裂问卷”与〈集体作业〉谈起》,《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d李洁非:《新生代小说(1994—)》,《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e《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出路——‘98全国文学期刊主编研讨会侧记》,《人民文学》1998年第10期。
f黄发有:《文学期刊与九十年代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g宗仁发、鲁弘:《当代文学现场中的〈作家〉——对话〈作家〉主编宗仁发》,《小说林》2011年第1期。
h何锐:《文学性与先锋性——纯文学期刊的坚守与追求》,《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i陈晓明:《晚生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山花》1995年第1期。
j毕飞宇、李洱、艾伟、东西、张清华:《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谈》,《花城》2020年第2期。
koprvz李敬泽、李大卫、邱华栋、李冯、李洱:《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第112页,第136页,第150—155页,第183页,第181页。
l参见《实力派作家呼之欲出 文学联网面向新世纪———五刊一报文学联网协作会在贵阳举行》,《山花》1995年第6期。
mqu张钧:《知识分子的叙述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第423页,第423—424页。
n李冯:《晚生代的十五分钟》,《南方文坛》1997年第5期。
s李洱:《九十年代写作的难度——与梁鸿的对话之四》,《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t毕飞宇、李洱、艾伟、东西、张清华:《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谈》,《花城》2020年第2期。原文为“商品经济时代的经验”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验”,笔者向李洱先生求证后更正为现在的说法。根据谈话语境及上下文,也可判断出原文的讹误之处。座谈会中,张清华将李洱提出的三种经验概括为革命经验、改革经验与全球化经验。
w李洱:《与批评家魏天真的对话》,《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
x李洱、王纪人:《我试图解答贾宝玉长大后该怎么办》,《新文化报》2012年9月23日。
y李洱、梁鸿:《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与梁鸿的对话之三》,《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页。
张钧:《知识分子的叙述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