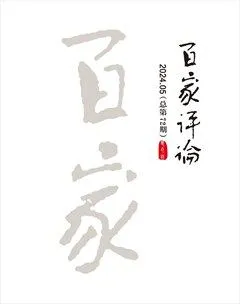地方经验与记忆的诗学
内容提要:老四是活跃于新世纪诗坛的80后诗人,他善于书写“自我”与生存世界的多重关系,致力于深层生命经验的开凿与书写。老四诗歌有强烈的“在地性”,这一方面体现为他对沂蒙故乡和生活地济南的地域经验书写,更体现为他在漂泊行旅过程中的文化体验与精神地理建构。他对地方经验的呈现与审视,实现了从“文化地理”向“精神地理”的诗学转化。老四对文化传统的高度自觉与诗学实践,构筑了宏阔而又坚固的精神底座,召唤着诗歌审美的多元建构。
关键词:老四 诗歌 自我 地方经验 文化传统
老四是活跃于新世纪诗坛的80后诗人,他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2006年在《山东文学》发表处女作,2013年参加《人民文学》第二届“新浪潮”诗会,2019年成为山东省作协第五批签约作家。2013年到2014年间,是老四诗歌创作的转折期和成熟期,他逐渐脱离80后青春写作的集体合唱,开始在诗歌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阅读老四的诗集如《自白书》(文学鲁军新锐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沂蒙笔记》(张炜工作室文丛之一,即将出版),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诗歌文本仍不乏80后诗歌中普遍存在的青春书写与感伤气息,但更多是一种具有审美辨识度的诗歌声音呈现。这种独特的诗歌面貌既与他的语调和修辞相关,更是其生命经验的独特体现,标志着一个诗人建立了独属性的诗性语言与诗艺机制。老四善于书写“自我”与生存世界的多重关系,致力于深层生命经验的开凿与书写。老四诗歌有强烈的“在地性”,这一方面体现为他对沂蒙故乡和生活地济南的地域经验书写,更体现为他在漂泊行旅过程中的文化体验与精神地理建构。老四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孤独而又敏锐,封闭而又敞开,不停地出走而又归来,始终葆有一种诗性的张力。近年来,随着诗歌心智的愈发成熟和文化心理的持续觉醒,他愈发倚重地方经验与文化传统,在对齐鲁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历史文化和生存景观的深度开凿中敞开诗歌经验,尝试着从个体经验书写到文化记忆书写的范式转型。
一、“一个人”及其精神镜像
老四诗歌的抒情基点,最初来自对“一个人”之生命与情感状态的诗性体悟。“一个人”是老四早期诗歌反复出现的主体称谓和生活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其诗意发生的起点。他在《一个人》中以“咏叹调”的方式书写这种情境:
“在文字里持刀远行/这么多年我只是一个人/一个人坐公交车,车上空无一人/一个人上班,单位空无一人/一个人赴酒局,宴席上空无一人/一个人在人山人海,人山人海里空无一人”
某种意义上,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个诗人的宣言。在中国文化中,“以笔为刀”有着漫长且深刻的精神传统,“在文字里持刀远行”暗示了某种抉择与无畏。老四自觉加入“持刀远行”的历史队伍,这暗含了对写作这一道路之孤独、困厄、艰难的体认与了悟。“一个人”意味着某种孤独状态,但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孤独,而是文学世界与精神维度的孤独,这种孤独包蕴着一种内心的坚定与无畏,这种孤独甚至是一种刻意的选择与追求。“一个人”在深层上是一种精神的高峰体验,正是这种心灵与精神上的孤独感催发“诗人的诞生”。《一个人》与其说是书写孤独体验,毋宁说是表达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碰撞、交融。诗歌最后的四行,每一行的前半句可看作是写实,是真实的生活状态,后半句则是一种虚构,具有多重隐喻意涵。这首诗意味着一种诗歌创作的状态和诗意燃烧的时刻,这种句式同时预示着老四诗歌经验的敞开,他后来的诗歌较多是“空无一人”状态下的精神产物。
“一个人”意味着某种“独处”的精神状态,老四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引用他心仪的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话,“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他的《水上行》是对这种独处方式的再次确认:“我爱独处/一个人守着一条河/一个人和天下所有人恋爱/一个人怀揣惧怕/一个人在河上,每一滴水里/安置我的一段孽债”。老四一方面反复地书写这一个孤独的内心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出众多的自我镜像。与“一个人”的精神探寻相对,老四诗歌中的“我”经常会投射出多元镜像:众多不同的“我”同时出现,与“我”互为镜像,与“我”展开对话,在略显荒诞的情境中表达某种悖谬化的生存体验。不断重临自我的生命起点,在时间的深处遥望自己,拉开时间距离审视自我,是老四诗歌的显豁主题。他的《自白书》将叙述的起点回溯至“我”从母亲子宫降生的时刻:“人生中第一个黎明和黄昏/他将爱上青草、汶河,在河边的菜园里/度过童年,抵达并不久远的中年/他将爱上荒芜、寂寞,在孤独的一生中/治疗伤口,最终沿着过去的村道/回归宿命中的来处和去处”。不断重临生命的起点,究其实是一种精神还乡。《自白书》寥寥数笔完成了对自我人生历程的悲剧性体认,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对老四而言,诗歌是回忆的艺术,是不断激活个体精神史的艺术。他总是在某个时刻陷入对自我的记忆,将之描述为《谋杀时间的旅程》:“山那边的一所学校/多年前我曾在校园里/我看到了无数个我/在楼宇和广场的缝隙/像蚂蚁一样/奔跑、焦虑、绝望乃至痛哭。”不管是对“人生中第一个黎明和黄昏”的凝视,抑或是“多年前我曾在校园里”的场景再现,都是此刻之我的一种精神镜像,这种回望与凝视具有一种“变形”的情感与诗学功效,暗含着一种悲剧性的内审意识。现实之“我”与“我”之镜像的对话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如现代诗人戴望舒在《我的记忆》中所描述的,“它的拜访是没有一定的/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于是,在《海阳至济南过潍坊》的车中,诗人看到,“车窗外,我看到了一个我/他不是我,是这个世界的一根稻草”。这是一种由速度而起的精神幻象,高速运转的现代交通隐喻了移动、飘零的封闭性生存空间,将我们迅速地抛入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指出,随着不断的社会加速,我们“被抛入世界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而且人类在世界当中移动与确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a老四的诗折射出我们生存背景的模糊与破碎,生存世界因此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老四所虚构的自我镜像,在他的诗歌中不仅仅是“我”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的滋生与繁衍,他还虚拟了其他镜像化的人物,譬如“儿子”“付小芳”等。在《我可能还有一个儿子》中,诗人由自己现实中的儿子展开想象:“我需要另一个儿子,作为我儿子的镜子/作为我的镜子,作为人间的镜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看到了时间转化为空间的整个过程”。在中国人朴素的伦理观念中,儿子是血脉和基因的延续,是父亲的“新我”,担负着实现甚至突破父辈人生成就的殷切期待。而在这首诗中,老四旨在书写不同生命之间的相互折射、相互印证。“付小芳”是老四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付小芳这一书写对象,同样是其自我的某种镜像,是“我”的情感成长与心智转型的参照物。付小芳被幻化为各种角色,如《再忆付小芳》中的姐姐:“姐,我用整个童年、少年虚构了你/今日添一件花衣裳,明日增一抹腮红/眼睛用林黛玉的,嘴巴用红山子/额头是一朵喇叭花,尾巴是我牵着你的那只小手/我如何制造你,就如何制造我的过去/如同后来的二十年把你填进记忆的伤疤”。在对付小芳的“虚构”与“制造”中,抒情主体的童年经验、情感历程得以更丰富地敞开。在诗学意义上,付小芳的真实与否、身份归属已经不再重要,作为“我”的精神镜像,她的身份愈是多变,“我”的情感世界就愈发丰富。她因此成为“我”的个体经验与故乡记忆的凝聚:“你终于成了最圣洁的女人/是所有女人的集合/我的故乡,所有女人聚在你身上”(《付小芳前传及生之过往》)。这是一种化主观为客观、将整体不断抽离的诗歌过程,“姐,在我虚拟你的过程中/你也抽走了我身上的许多部件”。在不断地抽取中,抒情主体的记忆被持续填充。
二、故乡记忆中的“精神地理”
从诗歌写作之初,老四的诗歌就有鲜明的地方指向,新世纪以来的“临沂诗群”构成老四诗歌写作的背景与“起点”。作为新世纪山东诗歌的重要群体,“临沂诗群”的独异贡献在于对地域文化的书写。《诗刊》2003年第2期首开“群落展示”专辑,第一期推出临沂诗群,标志着其作为代表性地域诗群的正式出场。江非、邰筐和轩辕轼轲被称为临沂诗群的“三驾马车”,江非以“平墩湖”为基质的乡土经验建构、邰筐对临沂城的浮世绘书写、轩辕轼轲的解构性口语探索等成为新世纪诗歌的重要现象。另外如辰水、尤克利、白玛、朱庆和等以各自的创作展示了临沂诗群的丰厚实绩和多元取向。老四是这个群体的后起之秀,是地域诗学的开拓者。纵观老四的诗歌写作,他始终坚守一种“在地性”的诗歌原则,致力于对故乡地理风物与情感记忆的书写,其中建立在河流、亲情与乡愁基础上的情感勘探,尤为值得重视。
老四曾在创作谈中谈及张承志《北方的河》对于他的影响,“河流”是老四故乡书写的重要精神空间,是他诗歌的核心意象,呈现出丰富的象征意蕴。老四的诗集中有多首以“汶河”命名的同题诗,另外还有《黄河行》《河之洲》这样的小长诗。在面对故乡时,老四是在与汶河的对话中唤醒自身的精神记忆,汶河的流淌绘制出个体精神的地图,譬如其中的一首《汶河》:
“只有汶河是幸运的,它没有长成/绵长的黄河,也没有挥刀自宫/只把一条细流完整地送给我的童年/而我也不过是它的一场游戏/它总是把我吞没/然后又轻轻地吐出来,吐给/遥远的天空,以及命运”
“吞没”与“吐出”隐喻着“我”与故乡之间循环往复的“离”“返”关系。出走,构成80后一代人的共同命运,而返回,则成为80后一代人共同的精神趋向。从汶河到黄河,意味着诗人从蒙阴到济南的生存环境变迁,也是其精神地理变迁的线索。在《河之洲》这首长诗中,老四以河流为线索书写个人史,完成了某种关于河流的总体性诗学建构:“我看见世界上所有的男孩/在同一条河里走来走去/世界上所有的农民也在河里/所有的远方和过去,水滴破碎的声音/与等待有关的一场梦/在静止的河里,在黄河的所有面孔中/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河之洲》既是个体精神地理的建构,同时也呼应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根基,老四的河流书写最终汇入关于黄河的总体性经验之中。
老四诗歌中的河流,既包括“汶河”“黄河”等具有鲜明地理标识的河流,他对那些无名的河流更感兴趣,在他这里,河流史即心灵史,河流构成他观照故乡的重要入口和镜像。如《河流史》:“我常常以河流为兴奋的起源/没有谁能描绘这么多绿色的小蛇/在丘陵的缝隙里,苦苦挣扎的/像每一座村庄里走出的女子/灰黄的头发,干瘪的乳房”。这些籍籍无名的河流,流淌着那些无名村庄中的无名女子的命运,由此,河流史也是苦难史,河流成为诗人老四难以抹去的精神胎记。江弱水说,“仅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着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与速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从一个农业社会一下子进入到现代社会,这种急遽的变动使人们心理不适,乡愁成了镇痛剂和麻醉剂,让人缓释焦虑。这一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改写了我们的城市,也使得乡村失血,乡土失色。”b老四在无名河流和灰黄、干瘪女子之间的诗歌比兴,恰是对现代化“加速”语境中乡村境遇的诗意抚摸。他反复书写汶河,其实是在抚摸自己的童年和命运;他不厌其烦地勘探故乡河流的地理,其实是在建构故乡与自我的精神流向图。
多年前,著名诗人于坚有一首题为《故乡》的诗:“从未离开 "我已不认识故乡/穿过这新生之城 "就像流亡者归来/就像幽灵回到祠堂”。如果说于坚那一代人是留守的一代,80后则是离开的一代,但这种对于故乡的悖论化感受却惊人的相似。如其在《山中的日子或故乡》中所写:
“你善于总结,下午开车在这片山区行走/小溪、桃林、山崮,洞府中的/钟乳石寄托了亿万年的变迁与视而不见/常遇见墓地,或消失的墓地/你的祖先已风化成无处不在的风化本身/一个念头让你停下车对着/溪水里升起的山崖发呆:/我身在故乡,却无可救药思念故乡”
这种“身在故乡”却又“思念故乡”的悖论化感受,暗示了故乡的历史巨变,以及这一过程中持续的精神缺失。《孟王村》是为残留的村庄立像:“从城市刮来的风,风里的媳妇们/从更远处的村庄朝贡来的水果和蔬菜/从他们体内排泄的铝合金、碳氧化合物//五分钟,我们在村庄里乱闯,闯着闯着/就走出去了,进了另一个村庄/那么多残留的老农立在路边,成了活的化石”。这只是一次迷路过程中的“误闯”,甚至整首诗也只是某种速写式的画像,但其暗含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却相当浓郁。“媳妇”与“老农”分享着当下村庄生活的两端,一端与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风”构成隐喻化的时代书写;一端则是农村的封闭与保守,“化石”强化了“风”的剥蚀以及他们无效而倔强的抵抗。
对于诗人老四而言,“亲情”是其书写乡愁的重要方式。老四诗集中,对母亲、父亲、兄弟和儿子的记忆与书写,触目皆是。他在《自白书》中深情回忆“母亲”这一身份的生成时刻,“劳累了一夜的母亲,在这个早晨陷入/持久的睡眠,这是她第一次/以母亲的身份,迎接寂静的光环”。他在《父亲列传》中追忆父亲的日常,“他常偷偷起床,赶着一群蔬菜去往/县城的集市/凌晨三点或四点,总有一些阳光/在他的额头散开”。童年时代父母双亲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往往成为背井离乡的成年人乡愁的集聚点。老四对这些不经意瞬间的书写,以乡愁之光照亮了暗黑的记忆隧道。沿着亲情的线索上溯,老四对故乡的精神地理勘探指向对死亡及其象征物的书写。作为生存世界与死亡世界的情感触媒,坟墓既是北方乡间常见的地理景观,同时成为精神寻根的重要意象。老四的《姥姥的坟》《火葬场》《墓碑》《祖坟》等诗歌是在对“死亡”的审视中寻找“我”与故乡之间的精神纽带。老四对故乡的情感投射,时常会聚焦于作为永恒的故乡之根的坟墓,如其在《墓碑》中的经验书写:“无碑的坟头在山坡上兀自/错乱着,不记准方位和参照物/会很容易拜错了祖宗”。某种意义上,墓碑才是真正永恒的故乡。这种无名的“错乱”状态,对于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是无比真实的,它构成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正在消失的深层隐喻。
老四对“茶棚村”、沂蒙、济南乃至齐鲁大地的地方经验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地域经验”“地域文化”的所指,而致力于一种“精神地理”的诗学建构。用诗人沈苇的话说,“是一种与地域有关并超越地域的文学精神”:“一片土地上的精神地理由那片土地上的人来呈现。精神地理是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相呼应的概念,却是超越并提升二者的。我们对自然、地貌、风光、风土等关注较多,对人,对现实的人、此在的人、人的命运、人的挣扎、人的悲剧等则关注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只留意、只看到一个地方风情和风景的表象,看不到人的内心。”c老四以故乡的山川河流、人事流转为基础所建构的诗歌地理,恰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地理”,这“不仅是一种地理气象,更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是人和地理融合后的一种气质与个性。”他以自己不懈的精神探索,推动了对地域经验的深层勘探,实现了从“文化地理”向“精神地理”的诗学转化。
三、从“个人史”到“地方志”:诗学路径的转换
在即将出版的诗集《沂蒙笔记》中,老四将其中的第四辑命名为“地方志”,如果加上前面的“地理书”,读者会深切地意识到他对地域经验的沉迷。从早年对个体经验的书写,到近年来对地域文化的关注,老四诗学路径的转换轨迹得以呈现。不妨说,老四试图在他的诗歌中完成从“个人史”到“地方志”的诗学转化。他的前期诗歌从“一个人”的孤独体验出发,在不断深入的生命记忆中展开个人史的讲述,个人史意味着生活史、生命史、情感史和心灵史,在这个过程中,诗人调校着他的诗学镜头,对自我的生命历程进行反复质询与确认,探测着自我意识的诸多可能。但老四没有遁入空洞玄想或繁复修辞的诗歌陷阱,而是坚持用口语和朴素的叙事呈现诗意。他的诗歌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母亲、父亲、儿子、朋友等时常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我们亦可以从诗歌文本中梳理他的生活史。在此过程中,老四培植了自己的冥想意识和凝视能力,他经常在生活的某个瞬间陷入冥想,在喧嚣的世界中洞见“不同的自己”。如《儿子和祖先在蔬菜大棚相遇》:“后来天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趴在草毡子上睡着了。父亲把我抱下来/像抱着他的祖先,我们用他的腿走回村庄/星星和田野驮着我们,如同驮着之前的无数个我们”。这是诗人对童年经验的一种超现实想象,诗意的转化与升华了无痕迹,连接起故乡的大地和祖先的魂灵,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精神感染力。老四维护着这种诗艺的巧妙平衡,彰显其独特的诗艺策略。
老四对“个人史”的精神探寻中,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化灵魂不断闪现,这似乎预言了他后来对地域经验和文化传统的执著探寻。老四有一些诗歌可称为“行旅诗”,它们多以“访……”“……道上”等进行命名,他在齐鲁大地上的行走,诉诸一种精神地理的诗学。诗人徒步翻越蒙山,书写内心的犹豫与矛盾:“把这个下午塞进那个永恒的初秋/竟有一股忏悔:既辜负了一座山的挽留/又辜负了一辆车的速度/我这一生,总是用脚背着/越来越重的身体,蜗行在飘荡的风里”(《蒙山道上》)。这种矛盾恰恰构成我们时代的生存隐喻,“当所有的物件被裹挟到时代运转的高速公路上,诗歌却遵照自身内在律令的胁迫,以漫长的心智辩驳、延缓乃至拒斥时代的加速度。”d诗人的“忏悔”,是现代人矛盾心理的一种折射,我们既无法像古人那样隐居山间,也不愿被现代化的速度裹挟。
老四直面齐鲁文化的精神遗迹,他对山东大地上的历史遗迹与文化传统有自觉的对话意识,这从其诗集目录中与之相关的题目即可粗略得知,他在诗歌中对齐国、鲁国等地域历史文化展开反复书写与对话。他自称是东夷人的后代,行走在齐、鲁文化之间,探访齐鲁大地上的历史先贤,为齐鲁大地上的山川河流立传。老四诗歌的“地方志”书写,并不是个体经验的完全放逐,而是在更深广的历史文化空间中烛照个体经验。《鲁南行》在对“鲁地”历史地理的书写中贯穿了浓郁的历史凭吊意识,“那些山间的草木,随时化为人形/而我准备着化身一株草/从《论语》《诗三百》里/流浪而来的夫子,总是在/第一时间踏步在我的身侧”,《齐长城曰》《报蒲先生书》等通过历史遗迹或文化逸闻遁入历史的深处,探寻“我”与历史文化的深层精神联系。老四诗歌的“地方志”书写还指向近代的历史人物与事迹,譬如对陈克若、“红嫂”的书写:“红嫂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的总和/也不是一代人,而是这片山区/一代又一代女人的集合/比如在更北边的影视城/村庄以石头的名义,和山融为一体/电视剧中,红嫂恢复年轻时的模样/我们的祖母,或祖母的祖母/用永恒不变的爱,承载山区的/一种样貌。”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红嫂’现象是齐鲁大地奉献给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一个丰富的文化现象。”e“红嫂”不仅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种现象,更是一种地域文化精神的传承,内蕴着一种文化特质。老四对文化传统的书写始终保持一种对话性,贯穿并高扬着诗人的精神主体性,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地方志”而演化为一种“文化诗学”。
老四对文化传统的自觉面对与深度书写,凸显了一种诗歌书写的“历史意识”,如艾略特所言,“我们可以说这种意识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锐敏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f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老四诗学路径转换的枢纽。老四以个体精神史和地域经验为基础,在一种整体性的诗学视野中审视历史与文化,建构了一个与不同时代的“文化亡灵”“精神遗迹”展开对话的共时性诗歌空间,显示了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稳健的诗学姿态。对于一个青年诗人而言,这份文化与诗学上的自觉是非常难得的。诗人只有不断激活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中照见未来,在不断地对话中夯实、加固自己的文化意识,才可能真正理解传统,融入传统,成为这个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a罗萨:《新异化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b江弱水:《诗的八堂课》,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66—167页。
c沈苇:《亚洲腹地:我们的精神地理》,《名作欣赏》2016年第4期。
d张桃洲:《沪杭道上》,《读书》2003年第2期。
e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f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