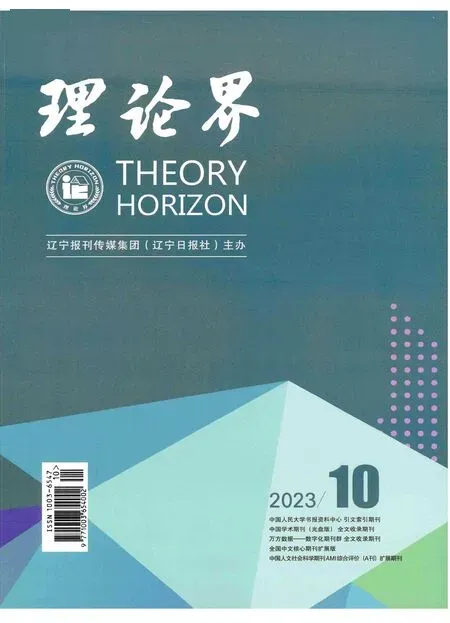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的民族文化书写
夏铭爽 王启东
一、民族文化的呈现
朝鲜族文化是朝鲜族作家文学观念形成的文化母体,在这一“母体”下孕育而生的朝鲜族女性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朝鲜族人民在落根延边大地的开始就将本民族文化的固著坚守意识扎根于心灵深处”,〔1〕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进行民族文化的表达。
朝鲜族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朝鲜族社会的心理结构,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对民族文化的书写首先通过作品中对朝鲜族传说的引用呈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许连顺在《请饶了蜘蛛吧》中写到的“弄死夜蜘蛛,会招夜行客的”,以及朴兰草在《飞吧,龙!龙!龙!》中所提及的关于“龙井”名称之由来的传说。对朝鲜族民间传说的叙写,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朝鲜族民族气息。小说文本中多样化民族传说的介入,也为其增添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容。
朝鲜族民俗是朝鲜族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它反映着朝鲜族的风土人情,体现朝鲜族人民的情感特征与文化心理。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通过对朝鲜族民俗的书写,传达出朝鲜族的文化情感,显露出民族文化对于延边地区朝鲜族女性作家创作的渗透。如千华在《假如我不是歌手》中对朝鲜族丧葬习俗的描写,在《没有你的日子里》中对朝鲜族婚俗的表现等。可以看出,朝鲜族女作家千华对朝鲜民族礼俗的反思,这样的民族文化书写,切入朝鲜族文化的肌理,显示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省意识。对朝鲜族民俗的书写,使作品氤氲着朝鲜族的文化气息,形成了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独特的审美感受,从而成为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民族文化书写的一个方面。
朝鲜族饮食文化蕴含着朝鲜民族“深厚的民族情感与文化定义”,〔2〕是朝鲜族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通过大量的朝鲜族特色饮食的书写,实现了作品中民族文化的呈现。《回来吧,妈妈》中的“萝卜泡菜”“大酱汤”,《链条是可以砍断的么》中的“泡菜”,《谁曾见过蝴蝶的家》中的“泡菜疙瘩”,《慢车》中的“紫菜饭卷”“明太鱼鱼籽酱”,《红蝴蝶》中的“黏糕”“土豆酱汤”“糯米饼”,《爱情》中的“打糕”,以及《祖母的旧皮箱》中的“绿豆冻子”“芝麻汤”“冷面”“荠菜包”“沙参汤”“米肠汤”等,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朝鲜族传统饮食,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些带有鲜明的朝鲜族民族特征的食物的书写,为作品注入了浓厚的朝鲜族民族气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朝鲜族作家似乎并不满足于对朝鲜族传统饮食的简单罗列,如许连顺在《回来吧,妈妈》中就对朝鲜族菜肴“冻明太鱼汤”的制作过程进行了描写。无独有偶,李惠善也在《童话的悲哀》中对“朝鲜族炖鸡”制作方法作出了介绍。作家对于民族饮食的详细书写,体现出的恰是朝鲜族作家对于本民族的饮食文化所进行的情感倾注,这些都彰显出朝鲜族作家对本民族饮食的热爱,反映出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浓厚的民族意识。通过这些民族饮食的书写,延边朝鲜族女作家构筑起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文学世界”,〔3〕并由此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景观。
生活于同一民族内部的人,在姓名上常常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姓’作为区别人名的重要因素之一,凝聚了各个民族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姓氏体系。”〔4〕在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笔下,人物常常以“金”“朴”“李”等为姓氏,比如《虚构的美丽》中的“小金”“朴记者”,《谁曾见过蝴蝶的家》中的“李丰彦”“金美子”,《跟屠宰场里的肉块儿搭讪》里的“朴凤姬”,《久远的沉默》中的“朴武松”“金书记”,《请饶了蜘蛛吧》中的“李主任”,《红蝴蝶》中的“朴排长”……从而形成朝鲜族文学中独特的姓氏特征。名字常常承载着某些期望,表达着某种祝愿,反映着朝鲜族人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姬”“淑”作为朝鲜族女性名字中的常用字,多次在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作品中被使用,《红蝴蝶》里的“姬珠”“兰姬”,《空缺的位置》中的“世姬”“顺姬”,《谁曾见过蝴蝶的家》中的“末淑”“彩淑”,《爱情》中的“英淑”……这些名字反映出朝鲜族家庭对于女性的期待和朝鲜族社会对于女性形象的想象,通过这些人名的使用,朝鲜族女性文学中的人物姓名呈现出了鲜明的性别特征。对于人名的书写是朝鲜族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书写方式,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人物的姓名,因其常常带有的鲜明的朝鲜族特点,而形成了较高的民族辨识度。同时,这些出现在朝鲜族作家笔下的姓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民族心理的一种表征。
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透过民族语言的窗口,可以窥探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的文本中,便多次提及朝鲜族的语言,如《慢车》中的“庆尚道方言”和“延边话”,《红蝴蝶》中的“咸镜北道方言”等,从而反映出朝鲜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
另外,长时间以来的朝鲜族文化浸染,也使得朝鲜族作家在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朝鲜族文化影响的痕迹。比如在比喻的喻体选择上,“紫菜”这种朝鲜族民族饮食中的常见物便为作家所注意。许连顺的短篇小说《她身上十只猫》开篇描写主人公慵懒的状态时,选取了“受潮的紫菜”这一喻体,而李惠善的《慢车》在形容女主人公胸闷的感受时,也写道“好像一团儿紫菜饭堵在那里”。朝鲜族元素的融入,使得作品中的比喻具有了新颖性,而民族特征的凸显也为小说语言增添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中国朝鲜族文化”“在具备朝鲜民族文化要素的同时,还具备了中国文化要素,成为了具有双重文化性质的朝鲜族特色文化”〔5〕。从这个意义上说,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则跳出了单纯的朝鲜族传统文化范畴,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对于中华文化的书写与展示成为延边地域内女性文学创作中有关民族文化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多次引用中华民族的民间俗语,如赵星姬在《蛤蜊料理》中化用汉语俗语“一日夫妻百日情”。许连顺在《谁曾见过蝴蝶的家》中写道“中国有句老古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通过引用中华民族的惯用语,来比喻“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肯罢休或认输”;〔6〕在《链条是可以砍断的么》中使用歇后语“狗拿耗子”来表示“多管闲事”之意。李惠善在《慢车》中使用“哑巴吃黄连”这样的歇后语,来表示“有苦难言”的含义;在《炳在家的晾衣绳》中使用歇后语“黑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而她的长篇小说《红蝴蝶》,更是用到“门缝里瞧人”“快刀斩乱麻”“远亲不如近邻”“庙小菩萨大,水浅王八多”等多句俗语,来为作品中不同的文学场景服务,使小说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对中华民族民间习俗的描绘是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对民族文化进行呈现的一种方式,赵星姬的《童年的记忆》通过对“新娘子燕一袭红袄红裤蒙着红盖头”的描写,从服饰方面入手对汉族的婚嫁习俗进行了展示,从而完成了对民族文化的一种书写。另外,朝鲜族女性文学中还存在中华民族民间传说的化用。在《慢车》中,作者就使用了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田螺姑娘”来称呼为女主人公的丈夫整理房间的女人——小王。对民间传说故事的化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民间文化气息,增添了作品的民族文化韵味。除此之外,李惠善的《红蝴蝶》中还写到“五香花生”“酸菜”“疙瘩菜”等“汉族小菜”,以及汉族人家吃的“大葱卷煎饼”,这种对中华传统饮食的书写也成为朝鲜族女性文学中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呈现。可以说,对中华文化的书写,丰富了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内容,而对于“中华文化要素”的吸收与呈现也体现出朝鲜族作家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二、女性主义的书写向度
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通过具有鲜明女性特征的文学写作,为文学表现提供了一种女性主义的书写视角。她们或截取朝鲜族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揭示出朝鲜族女性所遭遇的性别困境;或将笔触探入心理层面,通过对女性心理的描写,勾画出朝鲜族社会女性意识觉醒的脉络;或是关注“母亲”这样一类身份角色,通过对这类带有明显的女性特征的群体的书写与刻画,表现出深刻的女性主义书写向度;再或是聚焦婚恋和家庭,在私密性话语的视野下,频频书写女性经验;或是建构丰富的女性形象世界,在形态各异的朝鲜族女性形象的刻画中,生发出女性主义相关的文学话题。
1.性别困境的揭示
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对朝鲜族女性所遭遇的性别困境进行了展示,犀利地揭露出朝鲜族女性所面临的性别身份问题。许连顺的《虚构的美丽》讲述了身为电台记者的女主人公在遭受男性对其外貌的评价后而萌生出整容的想法,试图通过整容迎合男权社会标准下对女性的评价,却最终落空,在经历了自我的迷失后,陷入失落、迷茫的心理状态中。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影响着朝鲜族女性对“整容”这一事件的选择,职场环境的畸变,男性话语体系下的女性评判标准的建构,以及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评价与想象,无一不在催生着女性的容貌焦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经历着自我的否定,她对自我价值的评判依托于男性的评价而发生。在这里,整容这个事件成为了女性为满足男性的审美期待,而不断打碎原本的自己的过程。这样的文学书写所揭示出的是朝鲜族女性依然无法完全摆脱“被塑造”的命运,只能在男权话语主导的朝鲜族社会中充当着“被建构”的角色的困境。
在男权话语下,“生育能力”似乎是女性最突出的性别特征和最重要的性别价值。“做母亲,成了女人唯一的‘职业’,唯一的荣耀。它是男权社会中女人——容器的唯一社会功用。是女人最‘适合’的社会角色。”〔7〕《红蝴蝶》中的姬珠因无法再次生育,使家中有男孩的期待落空,而只能被迫忍受丈夫“借腹生子”的屈辱;《女儿六岁初长成》中的女主人公因丧失了生育能力,而经历着来自丈夫与自我的双重否定;《蛤蜊料理》中的老板娘因摘除了子宫而被当作“不男不女的人”……在男权话语下,这些女性形象的自我“真实”被忽略,女性的“工具性”被强调,在这里,“女性形象变成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空洞能指’”〔8〕,女性自我的意义与价值成为“虚设”,身为女性的意义本身为男权话语所遮蔽,女性本体的价值被由男权思想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排斥在外。在男权思想所建构起来的认知体系中,女性最为突出的特征——生育功能的丧失,加重了女性的身份焦虑。在男权话语占据主要地位的朝鲜族社会中,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笔下这些丧失了女性“功能”的女主人公便成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符号,她们被迫接受着来自男性以及为男权话语所同化的女性群体的解构,在为男权话语所扭曲的社会目光的扫射下,女性不再是鲜活的生命个体,而是被“机器化”“符号化”,甚至是沦为欲望的表征,这是朝鲜族女性所面临的性别困境。
2.女性心理的展露
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还通过对女性心理的展露,反映出朝鲜族社会中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如《女儿六岁初长成》中,女主人公对于自己在婚姻生活中卑微处境的不认同,和因“服从和忍受”所产生的“羞愧”感受,就构成了她对于男性主导话语的一种心理上的反叛,反映出其长期为男权话语所催眠的女性意识的艰难苏醒。作为长期生活在父权文化下的朝鲜族女性,女主人公并没有沉溺于既有秩序当中,而是敏锐地感受到原有秩序的不合理性,并因此而产生不适感,这对于长期为男权思想所禁锢的朝鲜族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而《爱情》中英淑对于爱情纯粹且坚定的选择,也体现出她不依附于男性,勇于“创造幸福”的情感态度,表现出朝鲜族女性对于自我独立性的认同与强调,是朝鲜族女性独立意识的一种表现。
女性心理的展露为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视角,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透过人物的外部行为,将笔触探入女性角色的心灵深处,细致地探秘女性心理的隐忧,通过这样的书写,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作品既完成了对朝鲜族女性形象的完整表达,同时也表现出其身为女性作家所具有的细腻性,从而显露出较为强烈的女性写作特征。
3.“母亲”角色的书写
“母亲身份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部分”,〔9〕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敏锐地关注到“母亲”这一身份的独特性,在对“母亲”角色的书写中实践着其作品里女性主义的表达。
比如,许连顺在《女儿六岁初长成》中就为“母亲”这一身份赋予了更为厚重的意义。在这篇小说里,母亲成为了孩子面临委屈和痛楚时的庇佑与安慰。护工在受到女主人公的指责后,写下满满一张纸的“妈妈”,而六岁时的女主人公在幼儿园遭受委屈时,也“哀哀地喊着妈妈”。母亲这个角色,在孩子遭受委屈的时候被想起,这是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具有的一种社会心理,而这种行为背后所承载的其实是一种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母亲”作为女性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具有独特的情感意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看到护工写的“妈妈”而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反映的是母亲这一角色的情感唤起功能,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有关“母亲”的情感的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这一词语因具有强烈的情感表征而被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
同是书写母亲,在《回来吧,妈妈》中呈现出的却是母亲与女儿这两种身份所构成的张力,以及女主人公面对母亲与女儿的双重角色时,在心理上所产生的那种矛盾与冲突。在这篇小说里,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被着重表现,由此作者进行的是自我与母亲关系的思考。而女主人公在孩子与母亲身份间不断切换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也展示出女性处理自我身份时的艰难,通过这样的文学表达,作者敏锐地揭示出朝鲜族社会女性所面临的身份困境,从而构成了其作品中女性书写的一个侧面。
4.婚恋和家庭的书写维度
对婚恋和家庭问题的关注是女性写作特征的一种体现。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作品中较多地涉及对婚恋问题和家庭关系的书写,如《空缺的位置》中对世姬和丈夫分别与其他异性之间所产生的情感关系的呈现,《炳在家的晾衣绳》对于炳在家家庭矛盾的书写,《祖母的旧皮箱》中对于婆媳关系的揭示……这些都体现出朝鲜族女性作家聚焦家庭、书写家庭关系的女性写作特征。通过这些文学世界的建构,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频繁地进行着对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处境的思考,从而表现出其强烈的女性写作意识。
婚恋和家庭作为一种私密性话语,是女性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正是通过对这种与女性写作具有亲缘关系的话题的建构,完成其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别身份的阐述,并在婚恋和家庭视域下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中,表现出朝鲜族女性对婚恋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独特体验,从而完成了其文学创作中对女性主义话语的表达。
5.多样化的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越是丰富多样,越能够表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表明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与重视。”〔10〕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对身份各异、形象不同的女性群像的展示,恰是说明了朝鲜民族女性意识的不断发展。
作为女性作家,李惠善、许连顺、赵星姬等人在作品中塑造出形象与身份多样的女性形象,由此构成了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丰富的女性形象世界。如《红蝴蝶》中的护士姬珠、为正宇一家代孕的村妇凤顺、中央小学的老师文艺华,《跟屠宰场里的肉块儿搭讪》中的旅店清扫员朴凤姬,《虚构的美丽》里写到的在电台工作的朴记者,以及《蛤蜊料理》中的“身为知名的服装设计师的老板娘”……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书写,反映出朝鲜族社会对女性群体关注度的提升,具有不同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朝鲜族女性被纳入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的创作视野,她们将笔触伸入朝鲜族女性生活的各种领域,描摹她们的生活状貌,揭示她们的精神伤痛,并为她们发声,体现了朝鲜族女性作家的女性文学创作的自觉。
三、延边的地域书写
延边,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吉林省东部。作为我国重要的朝鲜族聚居区,延边既承载着东北地域文化的普遍性,也具有许多区别于东北其他地区的独特之处。因而,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关于延边地域的书写也就常常从对东北地域特征的描绘和延边地域之独特性的呈现这两个主要部分来展开。
首先是东北地域的书写。在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东北意象,从而形成了地域色彩鲜明的东北意象群。比如,《链条是可以砍断的么》中的“大众浴池”,《炳在家的晾衣绳》中的“东北大秧歌”,《童年的记忆》中的“秧歌队”,这些带有鲜明东北文化特征的意象,成为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存在,反映着延边地区所具有的东北文化情感与内涵。
对延边独特性的书写是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中延边地域书写的另外一种内容。《荆棘鸟》中的“延吉空港”,《红蝴蝶》中的“长白山”“图们江”“帽儿山”“海兰江”,以及“延边日报”“延边医学院”“延吉市中医院”“延边一中”“延吉百货商店”和“延边大学”,《空缺的位置》中的“布尔哈通河”,《礼花怒放》中的“延吉机场”“延吉火车站”……这些有关延边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书写,使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通过独特的意象群建构,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实现了对延边地域文化的展示与表现。
另外,延边作为以朝鲜族和汉族为主的民族杂居地,在朝鲜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长期浸染下形成了复杂且丰富的地域性格,朝鲜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并存成为延边地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李惠善在《红蝴蝶》中便多次进行朝鲜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对比式书写,比如,朝鲜族居住的是“刷得粉白的房子”,而“汉族人家的房子周围大都围着黑墙,上着黑瓦,大黑门上插着长长的门闩”,以及棺材铺门口摆放的“汉族人的大红棺材和朝鲜族的白棺材”等,这种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既呈现出朝鲜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差异,同时也反映出延边地域的独特性,展现出朝鲜族与汉族文化元素并存的延边地区独特文化风貌。可以说,对于延边地域文化的书写使得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作品“在表达女性个人经验与为民族代言两个维度上达到平衡”〔11〕之余,融入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从而在作品中形成了民族文化、女性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统一。
结语
通过对民族文化和女性文化的书写,延边朝鲜族女性作家完成了民族话语与女性经验的双重讲述,在这个意义上,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既实现了民族情感的注入和民族文化的表达,也完成了女性文学的书写和女性话语的建构。同时,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对延边地域特征的表现,更是为延边朝鲜族女性文学增添了地域性这一鲜明的特色,使其成为生长于中国当代文苑中的一束瑰丽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