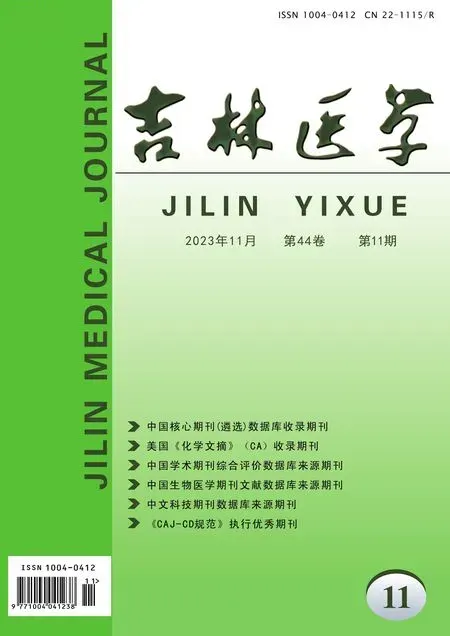外泌体miRNA在NAFLD疾病进展中的作用与诊断潜力
庞碧滢,黄娜娜,黄晓霞,李 馨,熊文婷,孔 波,姚 焱
(广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常与以肥胖、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NAFLD全球患病率高达25%,我国NAFLD患病率已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成为我国最大的慢性肝病,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和社会发展[1]。 NAFLD发病机制复杂,发展周期长,其病理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无高效的微创诊断工具[2]。近年多数研究发现不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miRNA串扰细胞间信息交流,调控脂肪肝、肝脏炎性反应、肝纤维化的形成,参与NAFLD疾病各阶段的发展,是潜在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具有NAFLD疾病分期诊断潜力。本文就外泌体miRNA对脂肪肝、肝脏炎性反应和肝纤维化的影响,探讨外泌体miRNA作为生物标志物在NAFLD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和诊断价值,为其在NAFLD进展中的基础研究和诊断应用提供新的见解。
1 外泌体miRNA的生物形成
miRNA作为短的非编码序列,广泛表达且稳定存在,是调节基因表达的重要手段。成熟的miRNA与其他蛋白等成分运输进入细胞外囊泡(EVs),根据大小和来源,EVs主要分为外泌体、微囊泡(MVs)和凋亡小体,EVs通过质膜向外出芽的微囊泡途径以及内体膜内向出芽的外泌体途径进行细胞释放,是运输细胞间和组织器官间的通讯及细胞外循环生物标志物的重要载体,对疾病诊断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3]。成熟的miRNA常通过诱导沉默复合体(RISC)相关途径、miRNA基序介导的异质性核蛋白(hnRNPs)依赖途径、神经酰胺依赖途径和3′miRNA序列依赖途径进入外泌体中,被释放出细胞,通过与受体细胞膜融合、吞噬作用或配体受体结合的方式传递给受体细胞,进行细胞间信号转导[3-4]。
2 肝脏外泌体miRNA的主要来源
影响NAFLD疾病的外泌体miRNA主要来自脂肪组织、免疫细胞和肝脏细胞的分泌。脂肪组织作为动态的内分泌器官,是外泌体miRNAs的主要来源,脂肪组织代谢和功能受损释放的miRNAs与肥胖相关疾病发病机制密切相关[5]。脂肪组织和肝脏等主要代谢器官在功能受损时,脂肪组织中的脂肪细胞和免疫细胞改变循环中外泌体miRNA池,脂肪组织来源外泌体miRNA常将脂质过剩信号传导至肝脏,引起肝脏脂质堆积,脂肪组织驻留的巨噬细胞的活化与脂毒性的双重作用加剧NASH的发生[6]。肝脏健康或受损时,肝脏自身分泌的外泌体miRNA介导肝细胞间,肝实质细胞与肝非实质细胞间重要的通讯连接,肝脏免疫细胞和肝非实质细胞活化促进肝脏炎症因子和纤维化产生[7-8]。脂肪组织将外泌体miRNA分泌至肝脏调节代谢,肝脏也通过感知不同的代谢状态分泌外泌体miRNA发送相应的信号以应对脂质过载时的代谢变化[9]。外泌体miRNAs是连接肝脏和脂肪组织内分泌调节回路的基础。目前,串扰NAFLD发病的不同组织来源外泌体miRNA的作用机制仍是一大研究挑战。
3 外泌体miRNA在NAFLD疾病发展中的作用
NAFLD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表现,脂质大量堆积,持续性NAFLD进一步导致肝细胞的脂肪毒性、库普弗细胞的氧化应激升高和促炎因子的激活以及肝星状细胞的活化,促进NAFLD的发展。脂肪组织、免疫细胞和肝脏细胞来源的外泌体miRNA与肝细胞间的信号通讯在脂肪变性、肝脏炎性反应和肝纤维化发生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不同来源外泌体miRNA与脂质代谢、炎性反应和肝纤维化的串扰机制,对认识NAFLD疾病发展的基础研究现状有重要意义。
3.1外泌体miRNA与脂肪肝:体内循环中的脂肪酸超过组织储存和氧化能力时,游离脂肪酸被摄入肝细胞内,脂肪酸在肝内代谢失衡,脂质大量堆积,容易引起脂肪变性[10]。外泌体miRNA在脂质合成、脂肪酸氧化等脂质代谢中起重要调节作用。脂肪细胞衍生的外泌体(ADEs)含丰富的miR-122,miR-122直接结合NAD依赖性去乙酰化酶(Sirt1)的3′UTR抑制其表达,Sirt1过表达可逆转ADEs诱导的细胞凋亡、糖脂代谢、肝脏炎性反应和纤维化的增加,抑制ADEs中miR-122可缓解NAFLD的进展、脂质和糖代谢、肝脏炎性反应和纤维化[11]。研究表明,miR-122通过靶向Sirt1抑制LKB1/AMPK通路促进肝脏脂肪生成[12]。抑制miR-122可阻断TLR4/MyD88/NF-κB p65信号通路,缓解油酸诱导的人原代肝细胞脂质积累和炎性反应[13]。可知,富含miR-122的外泌体对降低脂肪酸β氧化,诱导脂肪变性形成脂肪肝的作用尤为突出。除了外泌体miR-122外,肥胖小鼠外泌体miR-192、miR-27a-3p和miR-27b-3p增加,降低脂肪组织和肝脏中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PARα)表达和脂肪酸氧化能力,肝脏吸收过量脂肪酸,诱发肝脏脂肪变性[14]。miR-199a-5p在小鼠脂肪组织和HEK293细胞的外泌体中高表达,下调哺乳动物不育20样激酶1 (MST1)表达,影响固醇调控序列结合蛋白(SREBP-1c)表达和AMPK信号级联,上调肉碱棕榈酰转移酶(CPT1α)和脂肪酸合酶(FASN)的表达,抑制脂肪分解,促进肝脂滴形成,加剧肝细胞脂质积累,使用含anti-miR-199a-5p的外泌体可减轻脂肪变性[15]。在脂肪肝形成过程中,脂肪组织常通过外泌体miRNAs将脂质代谢失调的信号传导至肝脏,在肝脏脂肪酸氧化、脂肪合成与分解等脂质代谢过程起动态调节作用,诱导肝脏吸收过量游离脂肪酸,大量蓄积脂肪。
3.2外泌体miRNA与肝脏炎性反应:脂毒性肝细胞周围的中性粒细胞浸润是NASH的标志性特征,脂肪组织巨噬细胞的数量和状态与炎性反应紧密相关,巨噬细胞从抗炎的M2型转换成促炎的M1型的过程中,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加剧炎性反应。脂肪毒性和巨噬细胞介导的炎性反应在NASH的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驱动脂肪肝向更加严重的NASH演变[16]。脂毒性损伤可诱导肝细胞源的外泌体miR-192-5p高水平释放,通过调节Rictor/Akt/FoxO1信号通路,介导促炎巨噬细胞的激活,诱导一氧化氮合酶、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α表达增加,同时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雷帕霉素不敏感伴侣(Rictor)的蛋白表达,从而进一步抑制Akt和叉头盒转录因子O1 (FoxO1)的磷酸化水平,诱导炎性反应,外泌体miR-192-5p是NASH的潜在无创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17]。脂肪毒性还通过诱导肝细胞溶酶体功能障碍,抑制细胞外囊泡的降解,增加外泌体miR-122-5p释放,引起M1巨噬细胞极化发生炎性反应,因此,改善溶酶体功能并抑制miR-122水平可能是NASH潜在的治疗手段[18]。抑制细胞外囊泡相关的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可消除细胞间肝miR-122向肝巨噬细胞的转移并减少性反应[19]。此外,研究发现肝巨噬细胞-库普弗细胞(KCs)在NASH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KCs产生内源性miR-690,通过外泌体分泌到肝细胞、肝巨噬细胞(RHMs)和肝星状细胞(HSC)中,直接抑制肝星状细胞中的纤维生成、RHMs中的炎性反应和肝细胞中的新生脂肪生成,库普弗细胞miR-690的特异性敲除可促进NASH发病[20]。有研究表明,肥胖小鼠中性粒细胞来源的外泌体miR-223被肝细胞上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选择性摄取,抑制肝巨噬细胞活化,减少活性氧的产生和促炎介质的产生,中性粒细胞与肝细胞之间的通讯在控制NAFLD的进展中起着重要作用[6]。脂肪细胞源外泌体miR-34a分泌到巨噬细胞中,作为促炎的关键介质通过抑制Kruppel样因子4的表达来抑制M2极化,刺激炎性反应发生,将脂质过剩的信号传递给脂肪驻留的巨噬细胞,加剧肥胖诱导的包括肝脏在内的全身炎性反应和代谢失调[21]。这些机制表明外泌体miR-690、miR-122、miR-223和miR-34a是减少肝脏炎性反应发生的干预靶标,脂毒性诱导的外泌体miRNAs介导的巨噬细胞活化和迁移是推动肝脏发生炎性反应损伤的主要因素。脂肪细胞、免疫细胞和肝细胞间外泌体miRNA信息的串扰,不仅加速肝细胞死亡,还促进NAFLD疾病向关键的NASH阶段发展。因此,深入研究肝细胞、外泌体miRNA与巨噬细胞的互作机制和通讯交流,对延缓甚至阻断NAFLD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3外泌体miRNA与肝脏纤维化:肝纤维化发生在慢性肝损伤过程中,肝星状细胞(HSCs)的活化是肝纤维化的关键原因。在免疫细胞、肝巨噬细胞造血干细胞与肝星状细胞间外泌体miRNA信息的串扰在驱动肝纤维化发生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脂毒性肝细胞源性外泌体miR-1297过表达,通过上调肝星状细胞中纤维化促进基因(PCNA)表达,下调磷酸酶-张力蛋白基因(PTEN)表达,调节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肝星状细胞的活化和增殖,加速NAFLD的进展[22]。酸感离子通道1a (ASIC1a)可导致HSC-T6细胞活化,活化的HSC-T6细胞产生的外泌体miR-301a-3p被静止的HSC-T6细胞重吸收,靶向B细胞易位基因1(BTG1),促使HSC活化,促进肝纤维化过程[23]。THP-1巨噬细胞的外泌体miR-103-3p可通过靶向Kruppel样因子4(KLF4)促进HSC的增殖和活化,肝纤维化患者血清外泌体miR-103-3p是肝纤维化的生物标志物,巨噬细胞和HSC之间的串扰在肝纤维化发病中起重要作用[24]。巨噬细胞可分化为促炎M1表型和抗炎M2表型,M1型巨噬细胞可促进肝纤维化的发展。M1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miR-125b-5p过表达靶向抑制Star相关脂质转移域基因(Stard13),提高HSC中MMP2、TIMP金属肽酶抑制剂1(TIMP1)、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Ⅰ型胶原蛋白(COL1)和NF-κB的表达,促进HSC活化[25]。间充质干细胞(MSCs)的旁分泌外泌体miRNA是细胞间通讯的重要信使,富集在MSCs外泌体中的miR-148a通过抑制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通路,靶向Kruppel样因子6(KLF6),抑制巨噬细胞炎性反应,防止肝脏纤维化,miR-148a通过KLF6/STAT3信号调节肝内巨噬细胞功能,为肝纤维化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靶点[26]。
4 外泌体miRNA作为NAFLD疾病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外泌体miRNAs作为脂肪组织和肝脏基因表达的内源性调节因子,介导组织细胞间信息串扰,参与NAFLD疾病各阶段发生过程。
4.1目前NAFLD的诊断手段:侵入性的肝脏活检仍是临床NAFLD疾病诊断的主要手段,但其经济成本巨大、取样误差大、可及性和重复性低[27]。临床中,与NAFLD相关的脂肪变性、肝实质炎症和纤维化三种病理特征可能共存于同一肝脏内,并且特定区域有不同病理程度,影响肝活检评估肝脏状态的可靠性[28]。近年研究聚焦于非侵入性评估手段,现已引入超声、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和质子磁波谱等非侵入性成像检测手段替代活检,但这些技术严重依赖于专业人员和昂贵的设备[29-30]。因此迫切需要改进用于NAFLD疾病诊断分期的非侵入性微创工具。研究表明,外泌体miRNA参与NAFLD发展的病理生理过程,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微创性、测量成本低、易量化等特点,在NAFLD疾病分期中具有巨大的诊断应用潜力。
4.2外泌体miRNA在NAFLD疾病分期中的诊断价值:NAFLD严重程度的无创诊断手段有限。有研究根据NAFLD患者的炎性反应、脂肪变性、肿胀评分和NAFLD活动评分(NAS),分析外泌体miRNAs谱、临床及生化指标与mRNA表达的相关性,证实血清外泌体miRNAs可用于评估NAFLD疾病分期,这有助于确定NAFLD治疗的潜在靶点[31]。血清外泌体的相关指标可评价NAFLD和肝癌患者的严重程度,外泌体miRNA可用于诊断和预后评估[32-33]。miR-34a、miR-122和miR-21在肝细胞中丰度高,能反映肝脏毒性,是调控NAFLD发生发展的分子途径中研究广泛的miRNA。NAFLD患者肝脏miR-34a的表达水平随着疾病进展而不断升高,通过增加线粒体连接蛋白p66Shc的表达来增加肝细胞凋亡,将氧化应激信号传递到凋亡,同时,miR-34a/SIRT1/p53信号通路也在肝细胞中特异性激活,参与肝细胞凋亡和HSC活化,肝细胞分泌的miR-34a促使NAFLD发展到NASH阶段[34-35]。miR-122是人原代细胞高水平的肝脏特异性miRNA,由脂肪细胞和肝细胞分泌,在NAFLD早期脂肪肝阶段中,肝脏miR-122高水平存在,促进脂肪肝的形成,随着NASH的进展和纤维化的进展逐渐降低[36]。miR-21的表达水平随着NAFLD的进展而升高,在脂质堆积阶段受STAT3调控,靶向PPARα促进脂肪变性,还通过抑制肝细胞核因子4α(HNF4α)、PTEN和LDL受体相关蛋白6(LRP6)等基因表达,活化肝星状细胞和肝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MT)诱导纤维化,促进NAFLD向NASH发展,并在肝硬化和肝癌中保持高水平[36]。目前大部分外泌体miRNA的细胞来源不明确,但在体液中稳定存在,分泌到血液循环外泌体miRNA已被证明可作为特定人类疾病的生物标志物。血液miRNA谱分析证实外泌体miRNA具有改善NAFLD/NASH诊断的潜力,miR-122、miR-34a和miR-192的升高有助于区分NASH和NAFL,miR-122和miR-34a可区分NAFLD和健康对照状态以及NASH和NAFL,诊断准确性较高,miR-34a、miR-122和miR-99a这类miRNA 作为总的血清学生物标志物对NAFLD疾病分期具有较好的诊断效果,miRNA对NASH的诊断效果优于NAFLD,在区分NASH和NAFL方面具有很高的准确性[37-38]。
5 小结
NAFLD发病机制的复杂性仍是开发高效诊断工具和有效治疗方法的重大挑战,近年许多研究揭示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miRNA在人类NAFLD发病中的串扰,是该疾病演变机制的关键,外泌体miRNA作为NAFLD疾病分期的生物标志物和作为延缓或阻止疾病进展的治疗靶标均表现出巨大的前景,但作为一项新的诊断治疗工具还处在早期研究阶段,许多机制研究尚未明晰,深入研究外泌体miRNA在NAFLD进展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诊断工具开发和临床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