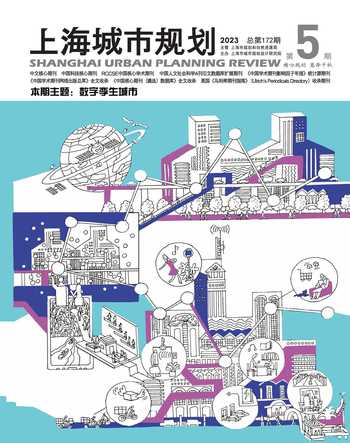数字孪生在城市规划实践应用中的批判性思考
万励 尹荦懿 汤俊卿 张龙飞
摘要:起源于航空制造业的数字孪生概念在2010年代后期引入城市领域,方兴未艾。城市数字孪生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城市中大量新兴数据源的兴起和计算机算力的飞跃提升(供给端),另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对高品质、可持续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城市管理者对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竞争力的诉求(需求端)。供给端与需求端在表象上的匹配解释了城市数字孪生市场当下的繁荣。通过对早期“智慧城市”运动的批判性剖析和对国外数字孪生发展近况的简要综述,指出期待仅凭数字技术即可解决城市固疾是对城市数字孪生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从非技术视角对城市数字孪生的必要性和革新性进行探讨,浅析当前城市数字孪生在城市规划领域应用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城市数字孪生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
关键词:数字孪生;规划支持系统;城市模型;城市规划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3)05-0018-06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基于实时传感器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的“数字孪生”起源于航空、航天制造业,对宇宙飞船和飞机引擎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是其早期的知名应用案例[1]。数字孪生概念在2010年代后期引入城市领域,方兴未艾。城市数字孪生在技术层面与早期制造业数字孪生应用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基于传感器的实时数据收集、处理和反馈机制。但是城市作为人类目前已知的最复杂的巨系统之一[2]377,数字孪生在城市领域的应用与其在工程制造领域的应用具有本质性、系统性的区别[3]3,[4]。工程领域的数字孪生对于设备“使用者”“拥有者”和“管理者”的定义通常相对简单,各个相关方有着较为清晰的角色划分,因此各自的行为类型也较容易确定。但是城市的“使用者”“拥有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划分则相对动态、缺乏明确的角色和责任边界。在各个身份大类中,通常也包含显著的差异性,例如一个社区内的所有居民,虽然共享“居民”身份,但是其对待城市数字技术的理解能力、态度、参与以及受影响的程度往往相差极大。同时,工程领域的数字孪生通常不直接模拟制度性要素(institutions),但城市数字孪生作为新兴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工具,如果缺乏对制度性要素(例如城市规划的决策和审批流程)的关注和批判性响应,则从本质上失去了对城市施加影响甚至直接控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城市的复杂性给数字孪生带来的挑战在文献中有详细论述[2]377。
因此,不能把城市数字孪生简单地理解为工程领域数字孪生的应用场景延伸,它更不是简单地在城市或基础设施的物理仿真模型里加入居民或者政府作为参与者。各种行为个体、组织和其他制度性要素是城市复杂系统的重要构成元素,是影响城市现有建成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决策主体。对决策参与者和受影响者的全面关注,以及对制度性要素的批判性响应是城市数字孪生迥异于工程领域数字孪生的基础性特征。忽视这些本质区别,将工程领域的数字孪生技术生搬硬套到城市,期待仅凭数字技术(例如可视化、实时交互以及各种优化算法)即可解决城市固疾,这是对城市数字孪生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不切实的期望。
本文通过对早期“智慧/数字城市”运动的批判性剖析和对国外数字城市发展近况的综述,讨论当前城市数字孪生在城市规划领域应用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城市数字孪生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
1 从“智慧城市”到“城市數字孪生”——重演或进化?
城市数字孪生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城市中大量新兴数据源的兴起和计算机算力的飞跃提升(供给端),另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对高品质、可持续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城市管理者对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竞争力的诉求(需求端)。供给端与需求端在表象上的匹配,解释了城市数字孪生市场当下的繁荣。但这种表象上的匹配并非第一次显现,其弊端在早期的“智慧城市”运动中已初见端倪。学界对早期“智慧城市”项目在解决具体城市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已有不少批判性剖析[5]66,[6-9],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早期的“智慧城市”项目(例如智能公共垃圾桶、智能交通灯)往往是“供给端”驱动,以展示技术的可行性为主要目标。技术供应商希望为自己的新产品或服务开辟新的城市市场,因此宣称新产品或服务可以解决困扰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城市病”。这类项目通常以“试点”的方式,在政府的默许或协助下由技术供应商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测试技术的可行性,并为后续技术优化和创新收集新的数据和用户反馈。这类项目的常见弊端在于技术方案本身完全以技术为主导,缺乏对问题本源和城市特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context)的考量[5]73,企图通过通用的技术方法或工具解决社会问题,忽略了“需求端”内部的差异化诉求和各种隐性约束条件(例如对数字技术的不同熟悉/接纳程度)。
第二,早期“智慧城市”项目往往局限在单一的政策领域,例如智慧交通、智慧市政和智慧政务,缺乏对多个城市系统、政策领域或相关方之间相互依存关系(interdependence)的考虑。对于重大的社会发展问题(如新城规划、低碳经济)和久治不愈的“城市病”(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亟需基于多系统、多相关方协同的决策支持系统。受限于政府的部门职能划分和传统的学科边界,跨越多系统、多相关方的城市建模仍有待深入探索。典型的模型案例包括城市土地和交通整合模型[10-13]和城市规划多主体模型[14-15]。
第三,有些“智慧城市”项目不以解决具体城市问题为导向,而是希望依托“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部投资、提升城市竞争力等宏观政策目标[16]。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竞争的加剧导致大量城市将“智慧城市”提升为城市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这类项目中,“智慧城市”的“智能性”不再是单一政策领域或者试点区域的属性,而转变为整个城市的标签;“智慧城市”成为激励技术创新、吸引创业投资、重整经济发展的政策口号和代名词[17]。不可否认,“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但上述目标实难通过简单的“技术解”得以实现。对数字技术和“智能化”的片面追求而忽视对制度性要素改革的关注,是“智慧城市”概念政治化的早期典型特征。
数字孪生在城市和重大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在外文文献中已有不少讨论。WAN等[3]29对全球城市数字孪生的前沿案例进行分类、分析和对比研究,其中包含城市数字孪生、区域数字孪生和城市地下设施数字孪生3个案例分类。2018年英国发布的“启明星原则”(Gemini Principle)[18]为理解和推广数字孪生提供了一个理论概念框架。该概念框架由业界和学界共同提出,强调数字孪生在城市建成环境中的应用必须遵循3个原则:以具体目标(purpose)为导向,以信任(trust)为基础,以有效的功能设计(function)为前提。奥雅纳[19]发布的城市数字孪生白皮书,通过对多位全球数字技术行业领袖的访谈,提出城市数字孪生应该以新的城市愿景(vision)而非技术为引导,对城市数字孪生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批判性思考。WAN等[3]126在“启明星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城市数字孪生的概念框架,探讨了城市数字孪生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挑战,对数字孪生在城市规划和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提出具体建议。NIEDERER等[20]探讨了数字孪生在生物医药和工程制造领域从缓慢、昂贵的定制化系统向快速、低廉的工业化生产转变的难点和潜在路径,为数字孪生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应用提供了重要指导。
当下的城市数字孪生热潮是早期“智慧城市”运动的重演,还是进化后的产物?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城市数字孪生的发展有更加长期、深度的观察。总结早期“智慧城市”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迫使我们跳出单纯的技术视角去审视城市数字孪生的必要性和革新性。
2 从非技术视角定义“城市数字孪生”
基于对早期“智慧城市”运动的反思,本章节从“非技术视角”对城市数字孪生的必要性和革新性进行简要讨论。城市数字孪生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一方面,“智慧城市”运动已经为城市数字孪生谱写了序章;另一方面,运用城市仿真模型进行城市研究、指导城市规划和管理实践,自1960年代开始已有数十年的历史[21-24]。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为创造城市数字孪生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但是从非技术视角,城市数字孪生的必要性和革新性集中反映在以下3方面。
第一,对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韧性的迫切需求促使城市管理者跳出传统的行业或学科边界和决策方式,希冀从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25]的视角去理解城市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强化基于实证的政策制定模式。城市数字孪生作为最新的城市尺度仿真建模概念,为城市管理者的政策需求提供了有力响应。相较于传统的、基于单一学科/政策部门的城市仿真模型(如交通模型、能源模型),跨学科、跨领域是城市数字孪生的一个特有优势。城市数字孪生可以对多源、异质数据进行有效的相互匹配、验证和融合,从而为多系统、多尺度建模提供有力数据支撑。多系统、多尺度建模虽然增加了模型的数据要求和建模复杂性,但在应对复杂的政策问题时,例如城市危机应急响应(短期)和城市新区的选址和产业规划(中长期),能有效识别系统风险,提升多部门协同决策的能力(如自然灾害中的市政、交通、医疗和电力部门的协同,新城/新区开发项目中产业发展与住房、公共服务配套供给之间的协同)。跨越多系统、多尺度的风险识别和管控是城市数字孪生有别于传统单一领域城市模型的革新性特征。
第二,城市數字孪生可加快政策效应评估的频次和质量。在前一时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决策的滞后性(如住房增长与人口增长的脱节)和复杂的附带效应(如快速发展地区对周边区域的虹吸效应)日益显现。为进一步提升规划政策的时效性、减少负面附带效应,对规划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进行及时、系统、持续的评估尤为重要。有效的政策效应评估能够及时发现政策设计中的不足、收集市场反应弹性的实证数据(如房屋限价政策对住房供给和销售量的影响弹性)并通过政策设计的迭代积累宝贵的政策经验。城市数字孪生及其背后的数据收集基础设施为加快政策效应评估的频次和质量提供了新的实施平台。例如,在工业园/科技园开发项目中,实时收集企业入驻、投资强度、税收缴纳、研发投资和园区土地利用数据,通过数学建模识别影响园区土地需求和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能够帮助园区管委会针对企业的特定行业和特定的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在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同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第三,城市数字孪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成熟过程[26],更依赖于城市数字孪生的技术创新与孪生系统的开发者、使用者、管理者和受影响者共同进化。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系统理论[27-28]为理解城市数字孪生的潜在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该概念框架指出,大规模技术变革的出现和传播并非单纯由技术本身的功能特征所决定,而是技术与其所处的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主动或被动造成的社会系统的变革为技术大规模应用创造了条件。从该理论框架出发,城市数字孪生相较于早期“智慧城市”运动的另一革新性在于其驱动城市规划制度性优化的能力。
3 当前“城市数字孪生”发展的3个问题
3.1 缺乏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数字孪生系统设计
从方法论的角度,城市数字孪生的典型工作流程是以递进、迭代的方式,分析问题、定义问题、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和社会试验,然后针对模拟和试验结果进行检验和方案优化,最终实施反馈并持续监测。因此,一个有效的城市数字孪生必须以解决具体场景下的具体问题为导向,动态选择信息收集、分析和展示的对象与精度。数字孪生系统设计的核心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流程链条,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功能。但是当前城市数字孪生常常过于强调数据的收集和展示,特别是对可视化技术的盲目追捧,忽略了对具体政策问题的关注和对现有决策流程的批判性审视。很多城市数字孪生系统实为数据可视化平台,缺乏在不同源数据集之间进行选择、校验和融合的功能,因此难以在具体的城市规划决策中发挥实质性的支撑作用。
值得说明的是,基于实时数据的可视化平台是城市数字孪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应用场景下(例如实时交通监控)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其他场景下,特别是与城市中长期发展相关的战略问题上,城市数字孪生应该超越描述性(基于相关性)工具的属性,向基于因果关系的解释性、预测性工具转变,通过系统建模揭示影响政策效应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3.2 将城市数字孪生建设等同于软件采购
城市数字孪生并非一个独立的通用技术,因此不能仅凭“模版”或者软件的形式在不同的城市或政策场景之间快速复制。城市数字孪生的设计和运行应充分考虑各类型的约束条件(如决策流程、权责分配、人力资源配置和技术支撑),需要数字孪生的开发者、使用者和受影响者等多方参与者的高度协同和长期配合。孪生系统需要伴随技术、使用功能和制度的变革而进化,模型算法的优化应建立在对政策问题和决策流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现有城市数字孪生平台的开发常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由软件开发商提供开发服务。城市数字孪生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城市管理者在制定招标文稿时,通常难以对孪生平台的数据资源、具体功能和后续扩展性做出准确的定义。对于具体用途的模糊定义导致现阶段的城市数字孪生重现早期“智慧城市”项目中“供给端主导”的弊端。软件开发商,特别是城市数据大屏的供应商,为控制开发成本和缩减开发周期,常采用通用模版和静态数据输入,仅在用户界面上做出微调,后台架构无法对数据进行有效甄别,缺乏与实际决策流程的交互接口,导致城市数字孪生平台“好看不好用”。
在某些政策场景下,数字孪生还应该发挥驱动变革的作用,通过政务信息化,披露决策过程的短板、强化权责分配,倒逼低效、落后的决策制度进行改造升级。城市数字孪生驱动制度性变革的能力在近期的国土空间规划改革[29-30]和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31-32]建设中已经初显成效。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案例中的技术平台虽然不全冠有“数字孪生”之名,但其包含的数据收集和融合功能均有数字孪生平台的雏型。这些技术平台的开发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制度性变革,同时是制度性变革的产物。
3.3 对城市数字孪生“系统优化”和“实时性”的过分吹捧
当前城市数字孪生过于偏向新数据收集,过于强调对复杂城市问题(如交通拥堵)进行基于工程学的“系统优化”。在城市数字孪生的开发早期出现常见数据“越多越好,越精细越好”的片面观点。建立城市数字孪生不应盲目求大求全,应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动态定义数据收集的时序、广度和精度。在常规应用场景下,应该优先利用现有数据源,通过深度挖掘和多源融合,识别现有数据资源和收集机制的不足,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和持续评估。与此同时,城市管理者和人民对城市数字孪生解决复杂城市问题的能力应该保持批判的眼光。一方面,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的决策模拟环境,可以测试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并进行整合优化;另一方面,很多城市问题的症结不是技术缺陷,常常涉及复杂的历史、制度性因素,因此单纯技术层面的“优化”实难奏效。基于数理的系统优化虽然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启发性,但复杂算法的应用会同时加剧模型的“黑箱”问题。在公共政策领域,模型“黑箱”会直接导致权责不明、扩大决策风险,更严重的会导致城市数字孪生沦为“领导意志”的解释工具。面对层出不穷的优化算法,运用数字孪生模型进行跨越单一系统/维度的政策风险识别可能比系统优化更具实践意义。系统性风险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典型实例包括城市无序扩张或过度集聚、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配套的短缺或失衡等。
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是对城市数字孪生“实时性”的盲目追求。工程制造业数字孪生系统对工况的监测和控制通常需要较高的时间精度(如秒或毫秒级)。这样的数据精度要求反映了工况发生改变的速率。随着数字孪生进入城市领域,开发者和使用者会自然而然地期待城市数字孪生系统也具有高精度数据采集的功能。但城市数据精细到什么程度才算足够精细?是否越精细越好?本文提出城市数字孪生的实时性是一个相对概念[33],数据的采集精度应该与数字孪生系统所应对的政策问题的变化速率相匹配,不可盲目追求“实时性”。例如城市住房市场(特别是供给侧)的变化相对缓慢,因此周或月度数据即可满足大部分政策分析需求,而城市交通和市政基礎设施的需求变化相对快速,因此需要更加精细(例如每分钟或每小时)的数据输入。忽视具体的政策问题和决策需求、盲目追求“实时性”会导致采购、实施和维护成本的增加,增加不必要的系统复杂性。
4 若干思考
展望城市数字孪生在支持城市规划,特别是中远期战略规划中的应用前景,本文提出以下若干思考。
4.1 运用城市数字孪生解决规划决策中出现的层级混淆与矛盾问题
城市规划决策常常涉及多种不同的时空和行政维度,从城市、城市圈尺度的战略规划、中观尺度的分区规划和城市设计,到微观尺度单一项目的规划与审批,城市规划决策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但在实践中,上述决策内容往往出现层次混淆的问题,例如依照低层级数据做高等层级决策,或做低层级决策时忽视高等级决策约束。在高层级决策中过度追求数据的精度会增加不必要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负担;在低层级决策时依赖高度集成的数据资源会牺牲决策精度和响应时效;无视高层级约束条件,更是会让决策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针对这些问题,城市数字孪生可以在两个方面助力变革。一方面,依托数字孪生的开发过程,逐步梳理、明确各决策相关方的角色定位和权责分配,对决策流程和时序进行批判性提升,促进多职能部门的协作和相互监督。另一方面,通过搭建不同尺度、不同问题的城市数字孪生体系,对规划空间分析单元和相应数据流进行分类、分级。在我国大量城市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是典型的多层级规划决策实践,通过数字孪生对项目进行多时空维度、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效益和风险评估,将有助于数字孪生城市“落地生根”。
4.2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建立一套城市数字孪生平台的功能性评价体系
依托數字孪生城市,建立系统的城市数据安全分享体系,以此激发规划决策公共参与、群智群策,并支持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参照国际经验,通过开放平台分享城市数据不仅可以增加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的透明度,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城市大数据收集和研究领域,我国走在世界前列,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城市数字孪生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既有数据优势,深耕基础算法和模型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为开拓国际化市场铺平道路。开放数据平台和相应的数据分享、交易机制的建立,还可以催生城市数字孪生技术的市场化竞争。一座城市、一种功能可以且应该有不只一个数字孪生系统,希冀一个数字孪生系统可以覆盖所有的城市政策领域是不现实的。多种孪生系统的良性竞争可以激励技术进步并降低城市孪生服务的开发和使用成本。目前国内的城市数字孪生市场,特别是在可视化平台建设上,存在大量低效、同质竞争。各种可视化平台多在“可视化”这个层面进行相互模仿,而不是在支持、优化决策流程这个核心功能上突破创新。为引导城市数字孪生产业发展、鼓励行业创新,应尽快引入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一套城市数字孪生平台的功能性评价体系,并扩展行业上、下游建立一个城市数字孪生的生态系统。
4.3 城市数字孪生系统应着力关注规划决策理念、流程和制度创新
城市数字孪生技术诸多革新性优点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的提升,必须依赖所服务或受影响的对象和制度做出相应改变,实现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的相互作用、共同进化。在城市规划领域,特别是战略规划层面,决策者需要改变传统的规划决策理念和方法,积极探索新的、基于实证研究的决策支持。通过政策后评估的手段,对决策过程和质量进行总结反思,将所积累的经验在其他项目中加以验证和提炼。城市在投资数字孪生系统时,应摒弃技术决定论,着力关注规划决策理念、流程和制度创新。观念和制度上的转变是数字孪生城市能够可持续发展、发挥其革新性优势的必要条件。
5 结语
城市数字孪生作为下一代的城市研究和治理工具,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是无视城市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照搬数字孪生在工程制造领域的方法论,将极大限制城市数字孪生的适用性,甚至动摇其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为了让城市数字孪生摆脱“技术炒作”的质疑,真正助力城市规划和管理实践,城市数字孪生亟需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笔者指出城市数字孪生建设是一个开发者、使用者和受影响者共同生产(co-produce)、共同进化(co-evolve)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可简单拷贝的“软件”。数字孪生系统设计的核心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流程链条,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功能。除了支持现有决策流程外,城市数字孪生建设还有潜力成为城市规划制度性变革的新驱动力。对决策参与者和受影响者的全面关注,以及对制度性要素的批判性响应是下一阶段城市数字孪生发展应关注的重点。
(感谢奥韦·奥雅纳基金(The Ove Arup Foundation)对剑桥智慧基础设施建设中心“转型中的数字城市”(DC2-Digital Cities for Change)项目的资助,以及对本文的帮助。)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GRIEVES M. Digital twin: manufacturing excellence through virtual factory replication[R/OL]. [2023-07-15]. http://innovate.fit.edu/plm/documents/doc_mgr/912/1411.0_Digital_Twin_White_Paper_Dr_Grieves.pdf.
[2]CALDARELLI G, ARCAUTE E, BARTHELEMY M, et al. The role of complexity for digital twins of cities[J]. Nature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23, 3: 374-381.
[3]WAN L, NOCHTA T, TANG J, et al. Digital twins for smart cities: conceptualisation, challenges and practices[M]. London: ICE Publishing, 2023.
[4]NOCHTA T, WAN L, SCHOOLING J M, et al.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on urban analytics: the case of city-scale digital twins[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21, 28(1-2): 263-287.
[5]HOLLANDS R G. Critical interventions into the corporate smart city[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5, 8(1): 61-77.
[6]MORA L, DEAKIN M, REID A.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 multiple case study analysis of European best practice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9, 142: 70-97.
[7]NOCHTA T, WAN L, SCHOOLING J M, et al. Digitalisation for smarter cities: moving from a static to a dynamic view[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 Smart Infra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2018, 171(4): 117-130.
[8]HOUGHTON K R, FOTH M, HEARN G. Working from the other office: trialling co-working spaces for public servant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8, 77(4): 757-778.
[9]Future Cities Catapult. Smart city demonstra-tors[R/OL]. [2023-07-15]. https://cp.catapult.org.uk/wp-content/uploads/2021/01/SMART-CITY-DEMONSTRATORS-A-global-review-of-challenges-and-lessons-learned.pdf.
[10]JIN Y, DENMAN S, DENG D, et 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ransformative land use and transport developments in the Greater Beijing Region: insights from a new dynamic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7, 52(B): 548-561.
[11]WAN L, JIN Y. Assessment of model validation outcomes of a new recursive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for the Greater Beij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2019, 46(5): 805-825.
[12]萬励,金鹰. 国外应用城市模型发展回顾与新型空间政策模型综述[J]. 城市规划学刊,2014(1):81-91.
WAN Li, JIN Ying. Review on applied urban modelling and new trends of urban spatial policy model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1): 81-91.
[13]万励,金鹰,崔博庶,等. 空间均衡模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中的应用[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9(2):140-158.
WAN Li, JIN Ying, CUI Boshu, et al. Application of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in sub-center planning of Beijing[J].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9(2): 140-158.
[14]SAARLOOS D J M, ARENTZE T A, BORGERS A W J, et al. A multi-agent paradigm as structuring principle for planning support systems[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2008, 32(1): 29-40.
[15]LONG Y, ZHANG Y. Land-use pattern scenario analysis using planner agent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2015, 42(4): 615-637.
[16]WATSON V. African urban fantasies: dreams or nightmares?[J].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2014, 26(1): 215-231.
[17]MOISIO S, ROSSI U. The start-up state: governing urbanised capitalis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20, 52(3): 532-552.
[18]BOLTON A, ENZER M, SCHOOLING J, et al. The Gemini principles[R]. 2018.
[19]ARUP. Digital twin - towards a meaningful framework[R/OL]. [2023-07-15].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digital-twin-towards-a-meaningful-framework.
[20]NIEDERER S A, SACKS M S, GIROLAMI M, et al. Scaling digital twins from the artisanal to the industrial[J]. Nature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21, 1: 313-320.
[21]BATTY M. Urban modell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2]BATTY M. Progres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urban modell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1979, 11(8): 863-878.
[23]LOWRY I S. A model of metropolis[M].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64.
[24]ECHENIQUE M, CROWTHER D, LINDSAY W. A spatial model of urban stock and activity[J]. Regional Studies, 1969, 3(3): 281-312.
[25]JACKSON M C, KEYS P. Towards a system of systems methodologies[J].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1984, 35(6): 473-486.
[26]FOSTER R N. Timing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J]. Technology in Society, 1985, 7(2-3): 127-141.
[27]GEELS F W. From 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 socio-technical systems: insights about dynamics and change from sociolog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J]. Research Policy, 2004, 33(6-7): 897-920.
[28]GEELS F W.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to sustainability: a review of criticisms and elaborations of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9, 39: 187-201.
[29]顧朝林. 科学的“双评价”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和基础[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9,11(2):1-4.
GU Chaolin. Scientific "dual-evaluation" as the key and foundation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9, 11(2): 1-4.
[30]赵广英,李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详细规划技术改革思路[J]. 城市规划学刊,2019(4):37-46.
ZHAO Guangying, LI Chen. Thoughts on the reform of detailed planning within the territory development planning system[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4): 37-46.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EB/OL]. (2022-10-28)[2023-07-15].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10/28/content_5722322.htm.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ice on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ntegrated government big data system[EB/OL]. (2022-10-28) [2023-07-15].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10/28/content_5722322.htm.
[32]曹阳,甄峰,席广亮. 大数据支撑的智慧化城市治理: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J]. 国际城市规划,2019(3):71-77.
CAO Yang, ZHEN Feng, XI Guangliang. The intelligent urban governance based on big data: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a strategy[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9(3): 71-77.
[33]WAN L, NOCHTA T, SCHOOLING J M. Developing a city-level digital twin—propositions and a case study[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Infra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2019 (ICSIC). London: ICE Publishing, 2019: 187-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