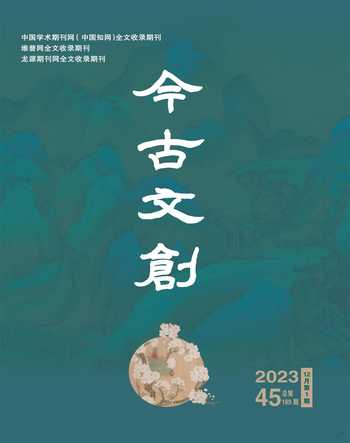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小说《西京故事》中的城乡地理空间书写
【摘要】陕西籍作家陈彦,在《西京故事》中围绕社会底层人物罗天福及其家人所处的生存境遇,勾勒了“文庙村”、大学宿舍以及塔云山三个地理空间。本文试从文学地理学角度,通过对小说中地理空间的呈现形态、建构及意义的分析,力图展现陈彦城乡地理空间书写的独特视角、地域特色以及文学地理空间参与社会文化表征的独立价值;揭示其为打破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提供的新思考,并阐释陈彦立足现代发展对民族文化传统及恒常价值精神再度挖掘的深刻现实旨向。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西京故事》;城乡地理空间;民族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5-008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5.024
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校级创新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JSCX22YB21)。
作家陈彦在《西京故事》中,通过对城乡地理空间的建构,展现出城乡发展及其文明之间的差异;同时以具有城乡过渡性质的“城中村”为中心,在与踏实劳动为本的乡土文明融汇后,使得被功利主义气息所熏染的城市褶皱处也承载着真诚生命的律动。因而小说中所塑造的城乡地理空间不仅作为人物生活的背景出现,还集中反映了中国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城乡二元结构下普通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及价值选择问题。但就现有对《西京故事》的研究中少有关注到文本地理空间的意义,因此本文试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对小说中的城乡地理空间展开分析。
一、《西京故事》中城乡地理空间的呈现
文学所描摹的地理空间是“文学家创造的二度地理空间,或者可说是具有文学意义的地理空间”[1],即并非对现实地理空間的原样再现,而是经过艺术手法虚构的审美空间。在《西京故事》中,罗天福一家主要在“文庙村”、大学宿舍这两个城市空间以及塔云山这个乡村空间中流转。
(一)城市地理空间:城中村和大学宿舍
1.文庙村:排挤中蕴含温情的生存空间
首先,文庙村作为城中村的性质,构成其窄、挤、乱的基本形态。因而罗天福一家来到文庙村时所见到的楼房是“又细又高的宝塔形状,一座塔与一座塔之间,又都很难找到分离的分界线。”[2]13在这逼仄的空间里,罗天福及家人暂居在一处杂乱、潮湿且简陋的大院,艰苦、简易与新鲜汇成了罗天福一家在城市里的基本生活状态。进而则是受排斥和挤压的生存空间。农民工作为现存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系下的特殊群体,被排除在城市市民之外,因此城中村的土著居民对于在此租住的外来务工人员持有戒备态度,并且以圈层不同的观念进行“我们”和“他们”的划分,从而以强势群体视角对农民工产生如愚昧、不安分等的刻板认知。罗天福仅是旁听闲话,就被告诫勿要瞎打听;拾垃圾的老罗在遗失东西的女房东眼里颇具怀疑色彩;以及“你们这些乡下人”“山里的铁壳核桃”的称谓中渐隐着不自觉的区分。再者,由于农民工自身技能的限制性以及未被纳入城市运作体系而产生的非正式工作市场,促使农民工多从事薪酬低、强度大且无保障的工作,难以融入现代化高效的生产中。罗天福夫妇为维持一家生计以及儿女的学费,所经营的饼摊可获利润微乎其微,且几乎每天可供休息时间不超过5、6个小时,长时间的高强度机械劳作加之抵抗恶劣的环境,以及随时面临检查、整顿时的无法出摊和劳作工具被没收的风险。生病、拖欠薪资、意外都有可能拖垮一个家庭,这种辛苦低效的劳作不仅严重摧残着农民工的身体,也使得生存几乎占据生活的全部,从而陷入起早贪黑也依旧困窘的怪圈。
小说中的文庙村并非只呈现为狭窄、乱、充满挤压,同时也蕴含温情的关怀。故事中的老人东方雨和副主任贺冬梅就是文庙村正义和良知的代表。东方雨老人无私对老罗一家施以援手,对罗天福身上所具有的恒常精神持以敬重,并影响着罗甲成对于父亲、自身以及城市的认知;副主任贺东梅切实践行着村主任的职责,积极为农民工在城中村立足做出努力;同样处在城市底层的罗天福深知农民工的艰辛和苦楚,即使自己未必宽裕但也接纳了从乡下投奔而来的亲戚并妥善安置,并在冬日为讨薪未果的农民工们煮粥送饼。在这个浸染着“小付出,大收益”思想的城中村,人与人之间的扶持与理解充溢着温暖的人文关怀。
2.大学宿舍:分化且满含冲突的学习空间
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小说中的宿舍充斥着圈层分化现象。在明显的物质与身份条件对比中,罗甲成逐渐被分划到三个室友的生活圈之外即在无形中形成了两种“空间”,由此罗甲成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心理并表现为对自尊的过度维护,开始以图书馆为主要阵地,以发奋学习作为目标避免与室友进行正面交流与相处,因此在缺乏了解和抵触中走向了三人的对立面。而朱豆豆等人由于相近的生活基础自然地形成小团体,并在自我张扬心理的作用下,时不时以高调姿态展示着优渥处境;在相互误解和抵抗中,罗甲成与室友们实际分处在不同的世界中。另一方面狭隘的经济决定观念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随口说出“未开化的野人”“物质匮乏”“这号穷鬼”的话语,以钱指使罗甲成买水的行为,未经查证就暗指罗甲成恶搞的猜疑,以经济为话语权衡量标准的思想挟制着三人与罗甲成深入交往的可能,而罗甲成在落差的刺激作用下以自卑与抗拒作为防御方式,由此在冷漠、歧视以及有意隔离、疏远的情形下构成了两个对立的空间形态,进而演变为以相互攻击收场的结果。
(二)塔云山:闭塞淳朴、崇礼守德的乡村地理空间
山高沟深的地势特点阻碍了山内外的交流形成了较为闭塞的环境,也影响着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但幸运的是老罗在父亲的支持下读完了高中。闭塞在限制塔云山发展的同时亦保存了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淳朴的人情风貌。首先是就地取材的生活方式和闲适的生活状态。山地多林木,以烧柴为主的土灶便成为主要的烹饪器具;丰富的草料成为养殖猪、鸡、羊等牲畜的重要前提,不管是乡民自然而然地依照生命常态存活,抑或是小动物们的安然自得,无不显示出自由而又真实的乡土韵味。其次则是淳朴的人情关怀。即使生活紧张,老罗也不忘为乡亲父老置办过节礼品;替乡邻画、挂灯笼成为罗家人传承的惯例;年事已高的母亲独居在家,不仅没有抱怨,还将丰收的蔬菜做成酱料,卖掉珍贵的土鸡蛋为两个孙子攒学费,而母亲也是罗天福一家坚定的后盾和精神纽带。在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乡村中,家人、亲属以及乡亲们之间的守望扶持、分甘共苦表露着人情的温暖。
其次,塔云山还保留着鲜明的礼俗传统以及儒家文化理念。首先体现在灯笼所画的内容上:不是随处可见的福禄财寿,而是梅兰竹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万物皆有灵在此处得到深刻展现,牲畜所处之窝以及紫薇树均要贴上对联;不论是清明、大寒还是春节时分,罗天福定会领着后辈遵从礼俗祭拜祖先,并虔诚地烧纸、磕头、禀告一年的收获,见证罗家成长的两棵老紫薇树自然也受到庄重地祭拜;其次则是独特的祭祀、丧葬礼仪,以抱柴火寓意红火兴旺,从初一到初十每天都有主祭的牲畜或食物,人死后还需嘴里衔珠宝金银之类的物品以祈求到达天堂。传统的农耕劳作与自然紧密联系,从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弥漫着浓厚的自然崇拜、安土、保族理念,也催生着谋生与做人一体的“耕读传家”风尚。因而在罗家的传承体系中,既明显保留着劳动人民的踏实勤恳又有乡村知识分子的价值秉持。作者以细腻的笔法描摹出了具有强烈传统意识而又淳朴、自然不失人性美好的乡土空间。
二、《西京故事》中城乡地理空间的建构
虽然文学文本中勾勒的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再创造,但也无法完全脱离作家生活、体验和感知过的地方性地理及人文环境,并且在此土壤之中会生成作家的基本文化心理及价值观念,从而影响着作家创作的选择视角。带着对故土的记忆,陈彦自觉地将对家乡的感知融入到来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身上,以文本形式建构着现实与历史重叠的城乡叙事空间。
(一)现实空间基础:城中村与塔云山
陈彦在《西京故事》的后记中提到,他曾经深入到西安东、西八里村以及木塔寨村这样的城中村中采访过租住的农民工,感受到“在巷内,人与人之间的进退避让,是需要提气收腹、侧身打转的。”[2]432虽然小说中的“文庙村”经过作家艺术性的创作,但还是基于西安城中村现状之上的创造。首先城中村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产物,其虽被纳入城市规划区,但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依旧是城市与农村过渡的中间地带。尤其以宅基地为主要生存保障,追求土地利益最大化的现象便迅速增长,其后果即为在有限的地基面积之上出现高密度的建筑群落,形成“一线天”“贴面楼”等“景观”。采光、通风效果欠佳、通行道路拥挤、排水系统不健全、电线缠绕、防火防震设施缺乏、卫生脏乱差等情况随处可见。但由于靠近工作区域或通行便利之处,且可供租住的房间众多和低廉的租金,城中村自然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首选之地;相比高度城市化的都市,城中村更具有包容性,也正是在这矮小、杂乱的空间中汇聚着不同的城市梦。
小说描绘的塔云山,位于陕西南部镇安县柴坪镇境内,是驰名秦、鄂、川、豫等地的道教名山。陈彦在访谈中曾说到自己出生于塔云山下的松柏公社,此地现已合并归入柴坪镇。镇安处于秦岭南麓中段,汉江支流乾佑河与旬河中游,是西安通往安康的必经之地,也是沟通陕西与湖北的重要桥梁,素有“秦楚咽喉”之称。气候湿润宜人,兼有南北景观,由于山多沟深,可供耕地相对有限,因此也被形象地描述为“九山半水半分田”。柴坪距离镇安县城西南50公里,素有“八百里旬河金铺底”之美誉的旬河从村落中穿行而过,两岸村民背靠大山、临河而居,曾因此处柴姓居民众多加之以地形特点而取名为“柴家坪”;镇内名胜塔云山高耸入云、雄奇险绝,不仅具有浓厚的道教文化,同时与周围的林海、怪石、云雾、峡谷浑然一体,近观肃穆庄严,远眺绮丽缥缈,镇安旧县志称其为“邑西仙境”。忠厚而坚实的大山阻挡了外面世界的景象,但也养育着镇安人民,孕育着独特而又质朴的地域风情,塑造着坚韧、勤劳、乐于吃苦的人格力量。
(二)主体空间情结动力:乡土依恋和本籍文化
梅新林、葛永海在《文學地理学原理》中提出:“主体空间”的“显性空间”和“隐性空间”,“显性空间”主要由“文人群体的籍贯地理与活动地理”构成,而“隐性空间”则是“通过由外而内的空间内化而积淀为空间经验、记忆和想象”构成,是“通向‘文本空间’的桥梁。”[3]401即作家在对现实地理空间体验、感知的基础上会形成独特的空间经验和认知,更深一步的“空间情结”则是以空间情感为核心具有原型意义的精神源泉。陈彦将视角对准城中村以及文本呈现出的城乡空间的温情面貌,与故土地理空间对于陈彦的意义有着密切关联。
首先,乡土依恋影响着创作焦点及文本城市空间建构视角的选择。陈彦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过程中,谈到乡土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时说:“我之所以老为小人物立传,也与乡土的记忆有关。我在骨子里就觉得这些人的故事是有意味。因为我存储着他们根须与毛发的纹路。”[4]5出生地与生长地对一个人最初的人生经验和文化熏陶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意义,由于“扎根于地方就是拥有一个面向世界的牢固基点,就是把握一个人在事物秩序中自己的位置,就是对特定地方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深深依恋。”[5]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作家陈彦,与山里质朴的农民乡亲们有着割舍不断的地方亲切感和地域血脉联系,即使身处城市关注的焦点依旧集中在最普通的劳动大众,并且是和他一样“从乡土卷入到城市来的‘后城市人’”[4]59,出生地塔云山的生活是陈彦最初的空间经验起点,其淳朴厚实的农民情怀及人格力量已经内化为陈彦创作的一个出发点,因此陈彦对城市的认知始终离不开这群为生存而坚守的“农民工”群体,在此基础上也制约着小说对城市空间的建构。陈彦没有选择炫彩多姿的城市景观或城市文化而是选择了号称“城市伤疤”的城中村来呈现不一样的城市空间,其根坻离不开已经融入他思想内蕴的故乡印记,对于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不管是从现实空间选择抑或文本空间建构,城中村都是合理且值得注意的城市空间。
其次,“本籍文化”制约着文本中城乡空间的呈现。依据曾大兴先生的观点“本籍文化”主要是指“出生成长之地的地域文化”,[6]58并认为:“‘本籍文化’是他(作者)的‘文化母体’,是他作为一棵文学之树得以萌生和成长的地方。”[6]59由于镇安地处秦岭腹地,山地连绵且高大崇峻,多水流侵蚀地貌相对破碎,但处在半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因此多以农业辅之林业及牧业生产为主,再加上闭塞的环境,土地以及自然资源便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产生了深刻的情感联系。不管是以供人们生存、生产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抑或是家禽牲畜,在当地人民眼中它们除了满足口腹之欲之外,也是具有灵性的精神象征。小说中对塔云山的春节习俗进行了详细的刻画,从初一到初十祭祀不同动物或物种,《镇安县志》中提到:“这是一种按天气好坏来定吉凶的迷信观念。如初一管鸡,天气晴朗,预示全年鸡鸭成群,阴天多雨,必遭鸡瘟。”[7]实际上反映出在农耕文明中自然之物的变化影响着人生存的变化,尤为突出的是小说赋予罗天福一家的两棵紫薇树和文庙村唐槐的意义。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人不仅通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来进行农业生产,同时参合天地日月万物以察自身的生命规律,从而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万物与人一样拥有鲜活生命。塔云山的紫薇树不仅抵御洪水挽救了罗天福一家,也是罗家人精神坚守的重要象征,出现在文庙村大杂院的唐槐则与紫薇树遥相呼应。再者,农耕文明孕育下的淳朴、善良、热情的民性。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和生产中,以土地为中心,则要求勤恳踏实劳作以获得延续,即在劳动过程中不断产生重实的思想并加以形塑,因而易保持淳朴厚重的文化心理特色;在有限的生产资源和活动空间中,对家庭及亲缘关系的重视则是应有之义,突出表现为重视家族传承和礼俗礼仪,亦是对传统伦理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的彰显。在清代知县聂焘纂修的《镇安县志点释》中记载着对镇安风俗的整体评价:“风气淳庞,俗尚朴野,虽处关陕,而性情和平,无强悍难驯之习,在商属四邑中最称易治。”[8]可见,朴实、勤恳、善良是身处这片大山人民共有的精神和文化底蕴,从而在小说中的塔云山呈现出祥和、质朴的心灵慰藉之域,以及受到现代商业文明冲击的城中村也不失人性的温暖。
(三)文本空间的组织:结构形式
文学地理空间的建构离不开作者的现实地理空间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内化的空间情结动力,同时还需要通过结构形式转化为文本空间。由于作者在创作和搭建文本空间的过程中,是以当下视角及心境回溯过往的空间经验、记忆或对空间的独特情感内蕴,是“交织着空间经验、记忆与想象的复合式重构机制”[3]421,因此文本空间已不仅仅是对客观地理空间的描摹,而是融合作者思考后进行艺术化创作的产物。
首先,“离开—回来”模式是文本城乡空间得以组织的前提。“离开—回来”不只呈现为空间位移的变化,更是以一定心理距离对所处空间进行重新审视。在第一次的“离开—回来”过程中,罗天福和罗甲成由开始对城市的期待到感受到生存的挤压、异质感,由对乡村的闭塞印象到亲切的归属感,在空间的轮转和对比中逐渐触及城乡空间内质的复杂面;在罗天福离家继续前往西京打饼到为儿子闯祸一事回家后又离开这一过程中,映射着在文庙村辛苦的打饼生意不能完全满足一家的生存,因而罗天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动起了卖和罗家人血脉相连的紫薇树的念头,表明城市空间对农民工生存空间的压迫;在罗甲两次“离开—回来”的过程中展露出在商业化城市空间中人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拷问以及站在城市空间角度对乡村空间地再度认识;在最后罗甲成离开西京到煤矿再回来以及回到塔云山送走奶奶到离开重新回到西京的过程中,罗甲成经历了思想的崩溃与重建,也真正冷静地思考着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的意义。实质上,在“离开—回来”模式下的空间变化中,文本中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的意义得到逐步的推进和延展。
其次,在冲突、对比与回忆中文本城乡空间得到深化。除了在“离开—回来”模式中的两种空间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在冲突碰撞和对比、回忆中对两种空间地深化。冲突主要表现在罗天福一家与女房东、同行、罗天福与儿子以及罗甲成与室友之间。女房东的无礼和贪得无厌使得本就艰难的罗天福一家雪上加霜;微薄的打饼生意竟无端遭到同行两次抹黑;受到明显贫富差距冲击的罗甲成竟对父亲坚守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产生了强烈的怀疑,甚至认为父亲的所作所为就是鲁迅笔下所描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罗甲成与室友之间不仅存在生活习惯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博弈;在不同的冲突中凸显出现代商业文化所秉持的利益至上对诚实劳动的挤压以及人格精神的异化。小说中显性对比主要通过现实与回忆的交叉呈现,隐性对比则体现在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教育等方面。当董薇薇讲述波罗的海的风情时,罗甲成回想到跌进池塘淹死的猪;当罗天福回想起一家围坐的热闹时却要为明天的房租劳作不止;当看到庄重而又严肃的大学毕业典礼时,罗天福想到孩子们在破败不堪的教室里怀着对未来的想象。罗天福一家的相互取暖与西门锁夫妇的猜疑、打闹争吵、算计;罗天福對子女的人格教育与女房东对儿子的哄、宠和金钱教育;罗天福一家的勤恳和知足与女房东的打牌、游玩却永不满足等形成对比。城市以其优势占有相对良好的资源与环境,却充满着疏离与利用;乡村虽无法与城市的条件相比肩,却不失人性的温暖。
三、《西京故事》城乡地理空间的意义
由现实地理空间到主体空间情结建立再转化为文本地理空间的组织与呈现,此时的地理空间已经不只是客观的存在,而是熔炼着作家情感、思想的意蕴空间。陈彦饱含着对与他一样的“后城市人”的关怀,塑造了《西京故事》中的城乡地理空间,借助这些空间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精神价值缺失、教育等问题,同时见证了来自乡村的“小人物”在城市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及其所蕴含的生命价值。
陈彦所书写的“城中村”不再仅是遭人诟病的“城市伤疤”,而是承载普通大众生命真实形态的人生舞台,是构成西京城律动活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孕育朴实忠厚、乐于吃苦、勤于奋斗精神信念的陕南乡村塔云山,也将启示我们重新审视和发掘乡土文明中蕴含的文化血脉;教育乃国之大计,人才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陈彦笔下的大学宿舍可以作为检视学生思想教育以及城乡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一面镜子。文学中的地理空间不止于对现实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赋予空间以意义和价值内涵,并达成人与空间的互动交流,显现空间的生存意蕴,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9]因此,文学地理空间的书写也在塑造着人们对现实空间的认知,构成地理空间的社会文化意蕴。小说中的城乡地理空间不仅呈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及人文传统,同时陈彦以独特的视角打破以往对城市、乡村空间的书写,使得“文庙村”“大学宿舍”“塔云山”成为陕西文学艺术创作长廊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以其隐含的意义勾连起现代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反映出小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恒常价值,体现出中国社会塔基的强大生存力量。
参考文献:
[1]杜华平.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突围与概念体系的建构[J].临沂大学学报,2016,(3):56-62.
[2]陈彦.西京故事[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13,432,419.
[3]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01,421.
[4]陈彦,程青.舞台小世界人生大舞台——访陈彦[J].瞭望,2020,(1):56-59.
[5](美)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8.
[6]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8,59.
[7]镇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镇安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563.
[8]镇安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镇安县志点释[M].镇安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85:115.
[9]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D].沈阳:辽宁大学,2008:61.
作者简介:
汪晓航,女,汉族,陕西商洛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