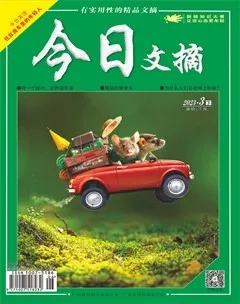紫禁城里的粽子,甜党赢还是咸党赢?

一直到宣统年间,清宫一直是甜粽党的天下。
这当然是因为咸粽子是南方产物,只有住在江南的袁枚(清代诗人、文学家),才吃过火腿粽子。袁枚在其著作《随园食单》中写道:“洪府制粽,取顶高糯米……用大箸叶裏之,中放好火腿一大块,封锅闷煨一日一夜,柴薪不断。”但袁枚写做饭,总是容易夸张,个个菜都像《红楼梦》里的茄鲞(书中写得最为详实的一道菜),要是粽子要烧“一日一夜”早就烧化了。我有一日热粽子,多热了几分钟,已经软趴趴的,进了太多水蒸气,无甚况味。
宫里的粽子是糖粽子,用江米或者白米来制作,式样和外面的也差不多,但需求量很大。每年刚刚过完年,就要做好规划,需要做多少粽子,需用多少米和粽叶,都要提前上报,之后到内务府造办处领取。宫里包粽子的厨役有限,每年节前还需要临时调入许多帮厨,日夜不停包煮。粽子的外形到粽馅,每年都要翻出花样,都需要逐级上报,直到皇帝满意为止。一到五月初一,粽子就成了宫里的主角,《宫女谈往录》里,那“闲坐说玄宗”的老宫女略带激动地说,有“各种馅、各种形式——方的、尖的、抓髻式的——粽子”。
到了端午那一天,宫里到底要吃多少个粽子呢?说出来吓死你,据乾隆十八年(1753)端午节的膳单所载,乾隆帝的膳桌上摆粽子1276个,皇后的膳桌上摆粽子400个,其他重要皇室成员的膳桌上共摆粽子650个——也就是说,仅仅是摆着看的粽子,就要两千多个!
这些粽子除了上粽子供、设粽席,皇帝还要赏赐文武大臣,连太监宫女也能分到一个。唐鲁孙先生是珍妃的堂侄孙,自幼出入宫廷,他在《清宫过端阳》中提及曾经吃到江米小枣粽和白粽子,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但是宫中有一种玫瑰卤、一种桂花卤拿来蘸粽子吃,蜜渍柔红,玉灵芳香”。另外,还有一种奶心粽子,是满族特色,大约是加了奶酪或是奶油,听起来颇为诱人,这大概是网红“奶黄”馅的师祖。
宣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年号)未出宫之前,咸粽子终于得到机会进入了宫廷。浙江遗老进呈50枚火腿鲜肉湖氏粽子给端康皇太妃、同治的瑜太妃分食后甚觉好,传谕御膳房,每年包些湖式肉粽换换口味——可惜这样的日子也没有几年,端康皇太妃便去世了。
再过几年,连御膳房也没有了。
(黄飞文荐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