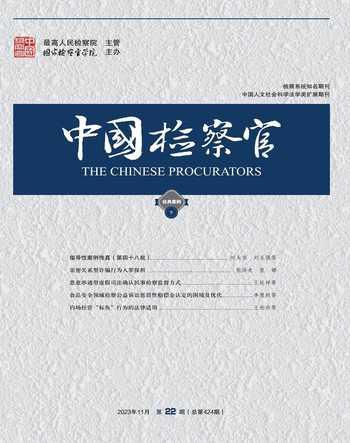缓刑上诉期内违法情形的处理
郑旭江 等
摘 要:被告人在缓刑上诉期内实施违法行为是否应被撤销缓刑,是当前缓刑执行领域的“空白地带”。根据缓刑制度的设立初衷和“举轻以明重”的基本法理,缓刑上诉期内违法不符合缓刑的实质条件。原审判决错误应包含量刑事实错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也需结合主客观证据作出综合判断,上诉期内的违法处罚可认定为“新的证据”,因此缓刑上诉期内违法符合抗诉的法定条件。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角度分析,缓刑上诉期内违法满足撤销缓刑执行的条件。检察机关应通过加强对被告人违法行为性质的综合把握、与社区矫正机构的充分衔接和坚持依法能动履职等,进一步完善撤销缓刑案件的办理路径,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关键词:缓刑上诉期内违法 撤销缓刑 抗诉
我国刑法第77条第2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然而,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可能会在缓刑判决上诉期内实施相关行政违法行为,由此产生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及能否直接撤销缓刑的争议。
一、缓刑上诉期内违法是否应被撤销缓刑
[基本案情]2023年1月3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未委托相关机构或组织进行社区矫正调查评估而作出一审刑事判决,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贾某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2023年1月8日,贾某某实施嫖娼行为被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13日。2023年2月1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就该案提出抗诉,认为贾某某在缓刑判决上诉期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违法行为,不符合缓刑条件,致使一审判决适用缓刑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最终法院认可检察机关对贾某某不应适用缓刑的意见,撤销了缓刑适用。
办案过程中,针对贾某某是否应被撤销缓刑存在不同的观点。肯定方认为,应对立法原意做实质把握,虽然贾某某的违法行为发生在缓刑上诉期内,但其已不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反对方认为,应严格按照法条规定,违法行为没有发生在“缓刑考验期内”,依然可以适用缓刑。对此笔者认为需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被告人在实体层面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二是检察机关能否因缓刑上诉期内出现行政违法行为而提出抗诉;三是检察机关如何监督此类特殊案件。
二、缓刑上诉期内违法应被撤销缓刑的分析论证
(一)缓刑上诉期内违法不符合缓刑的实质条件
根据缓刑制度的设立初衷和“举轻以明重”的基本法理,笔者认为被告人贾某某在缓刑上诉期内实施嫖娼这一违法行为,不再符合缓刑的实质条件。从实体层面来说,缓刑上诉期内实施违法行为比缓刑考验期内实施违法行为,在主观恶性、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等方面都更为严重,确有撤销缓刑的必要性。
1.是否适用缓刑是根据被告人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来判断的,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已违背缓刑的初衷。缓刑是一种附条件地暂不执行所判刑罚的刑罚執行方式,旨在通过被告人的自我约束达到宣告刑罚免除执行的结果,从而实现刑罚惩罚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平衡。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缓刑的适用条件是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犯罪情节较轻是在限定判处刑罚范围的情况下对社会危害性的概括,法律将缓刑适用限缩在情节较轻的犯罪中,同时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出发列举了悔罪表现、再犯危险和重大不良影响三个考量因素。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和再犯危险是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主要因素。司法实践中,悔罪表现的判断不仅要看被告人对其所犯罪行有无追悔,更要看其有无改过自新的行为,如主动认罪认罚、弥补损害、自我谴责等。再犯危险是对被告人再次犯罪可能性的预测,应综合案件和行为人的主客观因素作出整体评价。本案被告人在缓刑上诉期内即实施违法行为,足见被告人既无真诚悔过之意,也未吸取前罪教训,具有再犯可能性,不符合缓刑的制度初衷。
2.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符合缓刑考验期内撤销缓刑的条件。刑法第77条将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发现漏罪、违法违规或违反禁止令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应当撤销缓刑的三种具体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46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仍不改正的或存在其他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可由社区矫正机构提出撤销缓刑建议。本案被告人贾某某在缓刑上诉期内嫖娼并被处以行政拘留的情况是否符合上述“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或“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关键在于“情节严重”的认定。笔者认为贾某某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贾某某被处以13日的行政拘留属于嫖娼中“情节严重”的情形。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一般也认为13日的行政拘留已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比如,社区矫正对象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酒驾被行政拘留6日,法院裁定对徐某撤销缓刑、收监执行[1];邵某在缓刑考验期内赌博被行政拘留13日,法院也裁定对徐某撤销缓刑、收监执行。[2]
(二)缓刑上诉期内违法符合抗诉监督的法定条件
1. 本案贾某某上诉期内实施违法行为符合“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抗诉情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584条、591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裁定或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提出抗诉。对此有观点认为原审判决没有错误,缓刑适用是基于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属于价值判断问题,而非事实认定,不能以事实认定错误提出抗诉。但笔者认为从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来看,应坚持原审判决错误的实质理解,将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分为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刑法将缓刑的性质界定为刑罚裁量制度,而量刑事实包含了对被告人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综合认定,故其认定错误属于“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情形,符合法定抗诉条件。
2.本案法院未经调查评估判处贾某某缓刑,而贾某某又在上诉期内实施违法行为,符合“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抗诉情形。有反对的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一种价值判断,即使犯罪人在判决前就存在违法行为,也仅能认定其存在违法的事实,并不必然得出其具有危险性的结论。一审判决依据被告人判决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并无不当,判决后出现的行政拘留等违法情形不属于原审判决据以定罪量刑、适用法律的依据,不能用“后行为”去倒推“前判决”错误,不应据此提出抗诉。笔者认为,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结合的评定标准,是裁判者结合被告人的具体行为、犯罪情节、前科劣迹及认罪悔罪态度等诸多因素所作出的综合考量。这虽然存在价值判断的成分,但司法裁判的价值判断结果只有符合社会生活一般规律及普世价值,才能被普遍接受和认可。事实上,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本质上属于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主观判断。目前調查评估报告作为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客观性判定的文书已成为法院裁判被告人是否适合缓刑的重要依据,且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同时,刑法也规定宣告缓刑要对所在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因此,本案一审判决在前期没有进行调查评估的情况下直接适用缓刑,后续被告人在上诉期内就实施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也会对所在社区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反证出原判决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主观判断缺乏客观事实基础,符合“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情形。
3.本案贾某某上诉期内实施违法行为符合“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抗诉情形。[3]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58条规定,“新的证据”是指原判决、裁定生效后新发现、生效前已发现但未收集、生效前已收集但未质证等,不包括“新产生”的证据。有观点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判前“既已存在”的证据,判决后出现的行政处罚,不属于“新证据”的情形,不能据此认定原审判决有错误,因此也不能等生效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笔者认为,被告人新实施的行政违法行为也可认定为“新的证据”。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证据包含了犯罪证据和量刑证据,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新的证据”既应包括“新的犯罪证据”,也应包括“新的量刑证据”。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新的量刑证据”的具体情形,对此应与“新的犯罪证据”进行同质性解释,包含出现新的自首、立功证据等证明原判量刑适用错误的各类情形。“上诉期内违法行为”发生在原审判决生效前,其违法的证据已被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发现,但还没有及时被法院收集或质证,故将其视为“新的证据”没有法律解释上的障碍。同时,针对认罪认罚后反悔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可因出现“新情况”对原判决提出抗诉,本案亦可借鉴此类案件的做法,对原审判决量刑适用不当提出抗诉。因此,本案法院在对被告人贾某某判处缓刑前未对其进行过调查评估,一审判决对被告人贾某某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判定依据不充分。被告人在判决后生效前实施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该新出现的证据情况,进一步证明了贾某某不宜适用缓刑。需要说明的是,此时不是纯粹用“后行为”去倒推“前判决”错误,而是前判决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认定依据不充分,即未进行适当且客观的调查评估,导致原判决量刑事实认定错误,“后行为”的出现进一步强化证明了“前判决”关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判定依据不充分,致使适用法律错误。
(三)缓刑上诉期内违法满足撤销缓刑执行的条件
1.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判决确定之日”可以解释为“判决作出之日”,不限于判决生效之后的期间。刑法第73条规定,“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一般认为,缓刑“判决确定之日”即“判决生效之日”,致使缓刑上诉期内即“判决后生效前”这段期间出现“法律漏洞”,社区矫正机构处理本案这类特殊情形时无法可依、分歧不断,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但笔者认为对“判决确定之日”可有不同的解释。首先,国家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并未对缓刑“判决确定之日”作出有权解释,将其定义为“判决生效之日”只是一种一般认识。其次,将缓刑“判决作出之日”作为“判决确定之日”不违背文义解释。刑法对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刑期的规定都是在生效之后执行,而对于缓刑考验期的起算却专门使用了“判决确定之日”。当法院作出判决时,判决的定罪量刑内容即已确定,因此将缓刑“判决确定之日”理解为“判决作出之日”也落在语义的射程范围之内,没有超出一般公众的认知范围。最后,撤销缓刑的规定从“判决作出之日”起可以适用也符合缓刑条文的目的解释,能够更早地将被告人的行为纳入缓刑的考验期限,更好考察被告人的行为表现,以弥补缓刑适用和撤销的“空白地带”。
2.退一步说,即使囿于缓刑考验期限时间起算节点的争议,选择参照适用刑法第77条来撤销缓刑也不失为一种科学合理的做法。根据刑事审判参考的指导案例,缓刑的适用需具备实质条件和时间条件。相比较而言,实质条件是根本要件,是撤销缓刑的根本理由,而时间条件只是必要的补充要件。根据缓刑的本质精神,参照适用刑法第77条撤销缓刑,符合适用法律的正当性原则。[4]
三、缓刑上诉期内违法的监督路径
(一)全面考虑被告人违法行为的性质以把握适用缓刑的尺度
笔者认为,对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认定应综合判断,严格把握量刑适用不当的尺度。虽然本案被告人被撤销了缓刑,但实践中也不应一有行政违法就一律判定危险性过大而撤销缓刑或提起抗诉。对于原审判决已对犯罪行为、法定从宽情节进行过全面评判且经过调查评估的被告人,要结合行政违法行为的类型、频率、后果等客观事实慎重认定是否已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这不仅符合一般司法判断的逻辑和原则,也是实现司法正义的需要和关键。
(二)有效对接社区矫正机构完成案件后续处理
实践中,法院可能基于内部考核等因素不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并简单理解适用刑法第77条的规定,即若违法行为没有发生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则机械地判断不能撤销缓刑。社区矫正机构也因行政违法行为没有发生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不能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规定,而不提出撤销缓刑的建议。若被告人如本案一样在缓刑上诉期内实施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根据上文的论证判定被告并不适宜执行缓刑,此时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的沟通对接,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提出撤销缓刑执行的建议。
(三)坚持依法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检察机关应全面完善自身监督机制,通过日常检察和专项检察、线上检察和线下检察、书面审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对信息管理平台与社区矫正档案的定项督察、随机督察和派驻督察。针对缓刑上诉期内判决未生效前的“法律漏洞”,检察机关应加强与上级检察机关、同级法院等有关单位的信息互通和协作机制,构建数字检察监督模型,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对象违规、违法和犯罪行为的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从而及时完成调查核实、促进精准监督,并最终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