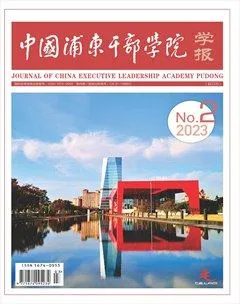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建构的思想体系
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研究和创立的,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解放目标的确定开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建构了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党、民主、治理和自由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立。
关键词:无产阶级解放;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学,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学,因为它是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研究和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阐明,无产阶级只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包括自身在内的、彻底的人类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从来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够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说明无产阶级的前途和命运。即使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只是同情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一个受苦受难最深、生活境遇最惨的阶级,需要像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样的“天才人物”去拯救。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真正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1]435制定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纲领和政治思想体系。《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诞生。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
解放和历史使命的阐论
马克思是在撰写于1843年10月至12月、发表在1844年2月《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里,提出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并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
《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缘于马克思同原“博士俱乐部”的朋友、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鲍威尔就犹太人问题展开的公开论战。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日益高涨。鉴于犹太人在德国深受歧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鲍威尔在他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文章中,完全混淆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他把犹太人的解放以及一般人的解放问题,说成是宗教解放的问题,主张犹太人放弃犹太教,基督徒放弃基督教,其他的一切人都放弃宗教,使宗教在政治上被废除,就能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并实现人类解放。这样一来,严肃的、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就被化为纯粹宗教问题。事实上,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决不是一回事。
马克思对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进行了批驳。马克思认为,宗教解放是要撕去披在封建专制政权身上的神圣外衣,使人民摆脱对神的信仰和对来世的幻想。但很显然的是,提出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不单是一个宗教解放问题,犹太人的解放斗争不能只停留在纯宗教斗争的水平上,它在实质上属于政治解放的范畴,反宗教斗争为政治斗争开辟了道路。政治解放是指,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即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要改变政教合一的政制,实行政教分离,使宗教从公共政治领域进入私人领域,国家不再是宗教的世俗权力的机关,把国家权力不仅从教皇手里,而且从国王手里夺过来,交还给市民。很清楚,这样的政治解放,还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普遍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它在本质上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也没有解决宗教解放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废除宗教,也无需废除宗教,而只要实现国家与宗教的分开,对公民实行宗教信仰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在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政权和等级制的条件下,在人民还信教的情况下获得政治解放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根本不是一回事,求得政治解放也无须放弃宗教。政治解放根本不以消灭宗教为前提,完全可以在绝大多数人还信教的情况下使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鲍威尔也“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2]168政治解放,即只是“资产阶级解放”,[2]390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是,“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2]180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解放。在已经获得了政治解放的国家里,人的自由和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政治国家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其法律也是保护私有制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2]189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反而保存着由私有制产生的人的异化。和鲍威尔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看到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认为不能把它和“普遍的人的解放”即人类解放混淆不分,必须区分这两种解放,并把人类解放置于政治解放之上。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政治解放之后还要进行人类解放。他指出,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才是人的最终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奋斗是“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2]192人类在自我解放的征程中,决不能停止在政治解放的阶段上,政治解放必然要向前发展为人类解放。这样的人类解放,是“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189也就是说,必须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必须废除私有制,使宗教消亡,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提出人类解放的任务后,还需要解答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必须由什么样的力量来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没有得到解决,而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到回答的。
马克思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2]213在这里,首先,马克思说明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是旧的社会解体、新兴工业崛起的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次,马克思说明了无产阶级队伍的构成,随着越来越多的贫民、农奴和中间阶级分化而产生的群众加入这支队伍,无产阶级成为了一个唯一不断成长壮大的阶级。
无产阶级是一个怎样的阶级呢?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2]213它和其他相同的阶级、等级一样,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私有制发生了全面矛盾,因而,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任何改良的措施,都不能使无产阶级摆脱自己的奴隶地位。为此,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重大任务是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2]213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已与私有制彻底决裂,因而它能坚决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213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造成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贫困,这本身就决定了私有制自身要被彻底否定。消灭私有制后,无产阶级并不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体现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原则是建立社会的公有制,只有确立这样的社会原则,才能使整个社会都摆脱私有财产。
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2]213因为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是“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2]213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2]213这说明,无产阶级和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与人的解放、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由此,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使社会永远从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也就不能争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在过去的阶级社会中,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级的解放,都意味着新的剥削和奴役的产生,而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则“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207-208这就包含了“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2]210因而,无产阶级解放就是人类解放。
马克思还分析了在无产阶级实现伟大历史使命过程中,哲学和理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虽然肯定“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209但他并不否认理论的作用。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2]207马克思的这段名言,深刻揭示了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他还形象地把无产阶级比喻为人类解放的“心脏”,把哲学比作“头脑”,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214
在无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上,恩格斯同马克思的认识完全一致。早在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开始第一次侨居国外的生活时,就深入到英国社会“生活的深处”,研究和分析了它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和现状,并在短短两三个月里先后写出《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等一系列理论文章,表达了自己对英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揭示了导致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内在因素。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问题,他认为政治革命只是用一种政权代替另一种政权,而社会革命则是根本改变人的生活条件、消除劳动者的贫困。恩格斯的这种提法,与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见解非常类似。这说明,恩格斯从那时起就持有和马克思相同的观点。恩格斯自从在英国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了无产阶级后,工人阶级就成为他经常研究的中心课题。特别是1844年秋至1845年3月,恩格斯在深入到工人阶级之中,了解了工人阶级的工作生活状况,并且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之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后,倾力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深刻揭示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争取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本书的意义,诚如列宁所指出的,“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基本思想”。[3]91-92由此可见,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看作社会主义开展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他有预见性地指出:“革命必然到来,要找到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已经太晚了”;[4]497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二、无产阶级解放目标的确定开显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后,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而是在他于1844年5月底至8月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7月底写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以及同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1月合著的《神圣家族》、1845年10月至1846年5月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的问题。他指出,私有财产是人的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由此,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中得出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278在这里,马克思再一次谈到人的解放问题。他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2]311就是说,要实现人的解放,就要实现共产主义。
1844年6月,德国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在当时的德国,工人深受工厂主、包卖商和封建主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为了同英国商品竞争,工厂主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以减少生产成本,使工人生活极端困苦。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一次纺织工人直接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而且起义者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问题。对于这场伟大的起义,当时,和马克思一起创办《德法年鉴》的合伙人卢格,却极力把它贬低为就像地方闹水灾或饥荒似的,只有局部性的意义,而且主要导因是行政机关办事不力或者慈善事业办得不够。马克思同卢格对起义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并发生了公开的争论。他写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驳斥了卢格的荒唐论点,将资产阶级的平庸俗气同工人阶级的高大勇猛相对照,高度赞扬了工人的起义行动,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包括其哲学家和学者在内,有哪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那种褊狭卑俗的平庸气同德国工人的这部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2]390从这次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中,马克思看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素质,并认为它同时就是德国的社会素质;看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所具有的解放自身的力量。他说:“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2]391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把宗教迷信同政治解放对立起来、以为有宗教迷信就没有政治解放的错误认识。他们指出,政治解放与宗教信仰并不矛盾,相反,只有实现了政治解放,才能真正获得宗教信仰的自由。所谓政治解放,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其实质就是对社会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目的就在于争取政治自由,争得人权,这是市民社会精神因素和政治因素的不可遏制的运动。与政治解放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类解放这一更高的目标。他们认为人类要获得解放,就要消灭“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4]262而鲍威尔却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完全混为一谈。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思考了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其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此他们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154其二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只有促成革命阶级的形成,才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地论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共产主义是形成了一个“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202
从以上马克思独著以及他和恩格斯合著的著作中可知,他们把人的解放聚焦在无产阶级的解放上,聚焦在共产主义的实现上。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理解为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297这样的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包含着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对人的三个层次和属性的分析。
第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324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动力量,另一方面又像动植物一样,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和限制。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不能离开同自然界物质的交互作用而生活。人作为自然存在的规定,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
第二,“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2]326这就是说,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人作为类存在物,有着自己产生发展,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部人的历史。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规定,体现了人和自身的关系,体现了人的生理属性。
第三,“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2]394共同体一般是指共同条件和共同利益的生存集体,如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是共同体的精髓,只有每一个单个人的需要和本质在共同体中彻底实现,这种共同体才是现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共同体”。共同体也包括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共同体带有鲜明的阶级和政治性质。例如,资产阶级建立的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就是与工人相脱离的“虚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1]201-202因此,“具有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是合理的、必然的,“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2]395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形成一个“无产者的共同体”,即“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
从人所拥有的属性和人的属性所面临的实际状况出发,马克思指出,人尚处在“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因为迄今为止,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自然、人的生理和社会的必然王国的约束,仍然处在盲目的状态。因而,马克思提出人的解放的条件和标准:首先,作为人征服自然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生产力的长足进步,当人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人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其次,人的解放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303-304人的生理器官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人类处在最适合自身的环境中而生存发展。最后,人已经完全摆脱了私有制的奴役、阶级的压迫和政治的统治。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297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使人从自然界、自身世界和人类社会中争取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最终成为自然界、自身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人。
论及无产阶级的解放,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无产阶级是靠别人来解放还是靠自己来解放自己?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他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中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回答。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若不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也就不能解放自己领域的阶级,意即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其他的社会阶级,同时把自己解放出来。如果说这个论述包含了无产阶级能够解放自己的意思,那么现在,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这一思想就被更加鲜明地表达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4]262这个论断揭示了深刻的道理。
首先,无产阶级无法不解放自己。因为在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能达到的非人性的顶点,无产阶级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所逼迫,无产阶级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它只有奋起反抗才有出路。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4]262无产阶级注定要为解放自己而战。
其次,无产阶级无法靠别人获得解放。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受压迫、受剥削程度最深、人数最多的阶级,也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组织性和团结性的阶级,无产阶级终将结束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这样的阶级特性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以往任何一个人或某个阶级的解放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奴隶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他们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成为无产者。历史上的农奴,其解放的道路更有多种:他们可以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可以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的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可以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当然,奴隶和农奴的这种解放,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单独解放出来的;他们也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构成了一个新的等级。至于资产阶级,它的解放条件不过是消灭一切等级。只要消灭了封建等级,摆脱封建羁绊,它就能获得解放,并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因此,上列某些人或某个阶级的解放,都是人的局部性解放,有的甚至是把自身的解放建筑在他人受奴役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的解放则不仅仅与奴隶和农奴的解放截然不同,也和资产阶级的解放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全部生存条件,是任何单个的无产者所无法控制的。无产者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把其他的阶级作为奴役对象,而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的彻底的解放。
最后,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无产阶级经受着最实际、最全面的锻炼,特别是大工业生产的锻炼,使它具备能够实现解放自己的素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4]262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还在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明确起来。
从以上论述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解放”(也包括他们先后提出的“无产者的解放”“工人解放”“工人的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等类似提法)和“人类解放”(也包括他们先后提出的“人的解放”“全人类解放”“普遍的人的解放”“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等类似提法),并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阐述,特别是对“无产阶级解放”的确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创始的开显。
既然“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只把“无产阶级解放”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创始的开显呢?这是因为:
一是“无产阶级解放”对于“人类解放”来说,具有特殊的含义。换言之,“无产阶级解放”除了具备与“人类解放”相同的含义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含义。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发展的各种措施。这些措施将使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随着生产力总量的不断增加,阶级和阶级差别逐渐消亡,旧社会的各种关系也才会最终消失。很显然,“无产阶级解放”的概念,包含着两层不可分割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地位和经济管理的权力。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得到本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本身也有一个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的必要。这一解放是以无产阶级经过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为标志的。所以,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手的日子,作为自己获得解放加以隆重庆祝的节日。然而,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就到此为止了。因此,第二,它是指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这种解放,也就是“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后,只不过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地位上来了个颠倒,并不表示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已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不能满足和停留在自身解放这一点上,还必须毫不懈怠地进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使所有的人都获得解放而奋斗。这正如恩格斯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5]285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解放”概念两层含义中的第一层含义特别重要,这是“人类解放”的概念所不具有的。
二是“无产阶级解放”对于“人类解放”来说,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历史上各个阶级的不同政治力量和仁人志士都可以提出“人类解放”的主张,但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提出“无产阶级解放”。这对于指导“人类解放”的革命实践来说,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作为革命的社会科学的真理性,成为它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解放学说的界碑。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最深切关心的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命运。尽管无产阶级也是人,但这样的说法不过是诡辩。如果从“人类解放”出发的话,既无助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得出社会革命的结论,就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什么,也不可能正确理解社会革命的进程。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些不分阶级、抽象地谈论人的论调,总是给予严厉的批判。当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胡诌“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①时,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讽刺道:“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6]551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可靠方法,如果不分阶级,笼统地从一切“人”出发,难道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依靠有社会性的包括一切阶级的人去进行吗?从“无产阶级解放”作为一个阶级解放的含义来说,只有它成为“人类解放”绕不开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步骤。
三是“无产阶级解放”对于“人类解放”来说,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中心和重点,只能放在无产阶级身上,这个阶级没有获得解放,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一句空话。对此,恩格斯阐述道:“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4]370恩格斯还指出:“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4]497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把无产阶级解放作为开端是完全科学的,“人类解放”必须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才能达到,如果不是从这样的开端出发,是无论如何走不到“人类解放”的终点的。
三、《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
主义政治学说的创立
1847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组织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他们接受了同盟的委托,为同盟起草党的纲领。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作为同盟党纲的《共产党宣言》。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一系列原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诞生。
还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时候,他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德国正义者同盟的盟员。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格律恩和蒲鲁东的批判,极大地提高了同盟的思想水平,使同盟盟员愈来愈认识到自己所信奉的理论观点的毫无根据,日益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正确性。于是,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伦敦总部派约瑟夫·莫尔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再次诚心诚意地邀请他们加入同盟。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同意加入同盟。1847年6月2日至9日,正义者同盟在伦敦秘密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题,是讨论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
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形成,经过三个主要阶段:1847年6月初,恩格斯编写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随后于10月底,恩格斯将其改写成《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原有稿本的基础上共同写成了《共产党宣言》。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先后写了三个纲领稿本,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以下分别简称《信条》《原理》《宣言》)。这三个纲领稿本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主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创立的标志性文献。
——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45年秋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4]536-537在《原理》中,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又明确得多了。他指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首先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304这里的“政治统治”,就是国家问题。而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直接地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413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正如列宁指出的,“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7]13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是什么,《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21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且还要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同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和被剥削劳动群众的联盟,动员和组织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最大可能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能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关于政党的理论。《信条》中还没有涉及政党问题的论述。但恩格斯在《原理》中,立即增写了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以及共产主义者对待各政党的态度两个问题。恩格斯在《原理》中阐明,共产党人必须支持“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1]311而到了《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大量篇幅直接论述了共产党是怎样的政党的问题。他们在《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组成为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党比以往的一切无产阶级政党都更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和其他的工人政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显著特点在于:“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413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为共产党规定了政治斗争的基本策略:“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434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党派的基本态度,并根据当时各国不同的革命进程以及各个政党面临的具体革命任务,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策略。他们还特别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最根本条件和最可靠保证;共产党在处理和其他工人政党的相互关系时,既要团结和依靠这些工人政党组织共同战斗,充分发挥它们的革命作用,又必须正确引导这些工人政党组织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决不是靠强制来实现的,而是靠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模范的行动体现出来的;共产党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革命和建设,是因为它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它除了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
——关于民主的理论。恩格斯在《信条》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是“民主的国家”。[8]379他在《原理》中重申了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1]304并且指出,共产主义者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前要首先参加民主革命,“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1]311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问题作了历史性回顾,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402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就在于否定了封建专制,带来了资产阶级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因此,他们主张,共产党人要积极投身资产阶级革命,大力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他们指出,德国的封建现状就是共产党人的更大的敌人,党应当巧妙地和资产阶级一起行动去争取宪法、选举权、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正因为这样,他们阐明:“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435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共产党人要继续向资产阶级进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斗争手段,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因而,他们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421在无产阶级争得属于自己的民主,也就是真正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后,共产党人必须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治理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不但是关于国家革命的理论,而且是关于国家建设的理论。“国家”这个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其广义的含义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分以及国防、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力部门,其狭义的含义就是专指行使行政权力的政府部门。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国家建设,主要指政府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自身的建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后,新型的国家也具有对内对外的职能。在对内职能中,社会管理与治理就是政府及其机构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政府的建设和治理问题,在《宣言》中就明确论述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系统的国家管理问题,提出要发展民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具体地提出十条治理国家的措施。马克思还曾使用过“政府治理”[9]237的概念,揭示了治理的实质,指出“要靠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治理国家”。[10]701恩格斯也使用了“治理国家”[2]405的提法,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地方治理十分重要,而“地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11]547特别是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建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强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关,必须履行好“社会公仆”的职责,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治理好各项社会事务,贯彻“真正的民主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和要求。
——关于自由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恩格斯在《信条》中谈及未来的社会时,指出要“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8]373自由,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灵魂和最高境界。在《原理》中,恩格斯继续发挥了他在《信条》中提出的“完全自由地发展”的观点,即形成一个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共产主义联合体”,“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308-309而到了《宣言》,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被完整地表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22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联合体”的限定语。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明确地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12]961894年,即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当有人请求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写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表述未来的社会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就在回信中选用了《宣言》中关于“联合体”的这句话,并说除了这句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3]647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是多么的重视,自由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又是何等的重要。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科学
社会主义的区别
从上述《信条》《原理》《宣言》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主要思想可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确实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学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科学社会主义正式诞生的标志。对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原理》中指出,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295那么,对于同样要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来讲,二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应该如何将它们区分开来并认识它们的异同呢?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研究的对象方面,还是在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方面,二者都有着很多的相同与交叉。但是,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应该看到,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其范围和内容都十分广泛,包括了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教育条件、科技条件、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国际条件等诸多方面,涉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恩格斯写于1876—1878年的《反杜林论》,其中的第三编“社会主义”,就包括了历史、理论、生产、分配、国家、家庭、教育等内容。显而易见,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也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但它只是集中于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条件,因而,它是一门专门性的科学。
其次,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都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条件,但二者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又有所区别。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条件,主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则还要研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发展,比起科学社会主义来要多研究三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条件的范围和内容,又比科学社会主义大得多、广得多。
最后,在研究的细节方面也有区别。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它要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众多条件,其中包括了政治条件,因此,它在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条件时,如同研究其他的解放条件一样,主要着眼于从整体上去研究,着重从宏观上阐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社会形态的政治关系以及变动与发展的趋势。而对于专门研究无产阶级政治解放条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恩格斯曾指出:“政治学以人作为基础”,[2]527即它是以人的利益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围绕着无产阶级利益而生成的政治与社会关系,全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革命、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政治系统、政治改革、政治治理和政治发展等的研究,形成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原理。因此,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具有系统性、宏观性共同特征的同时,又具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细节研究的特点。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列宁选集:第1卷[M].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列宁选集:第3卷[M].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张 华]
Abstract: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s established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which reveal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mission of the proletari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oal of proletarian liberation highlights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about proletarian state, party, democracy, governance, freedom and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Key Words: proletarian liberation;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proletariat;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The Communist Manifes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