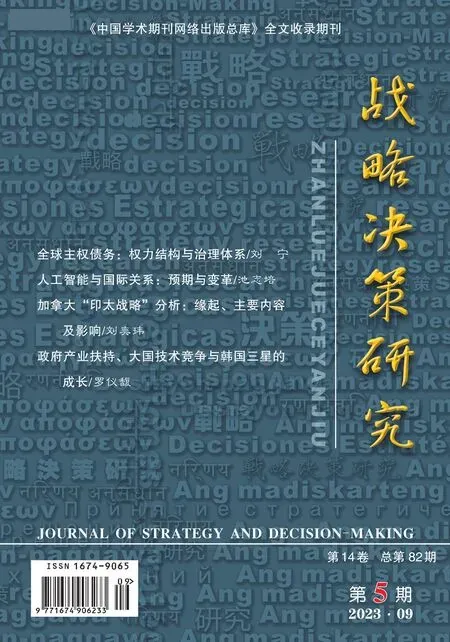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预期与变革
池志培
在科技竞争日益占据战略想象空间的当下,人工智能无疑是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技术。从阿尔法围棋(AlphaGo)战胜人类最顶尖的围棋手到ChatGPT 掀起的热潮,①不仅是媒体,学术界也迅速产出了一系列GPT 相关的研究,参见知网搜索。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似乎即将扑面而至。如果说以往的科技革命只是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那人工智能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革命,因为它直接颠覆了人类自身,人类可以制造出被视为最根本的人类特征——智能,甚至制造出比人类更高级的智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人工智能,人类可以成为“造物主”,或者至少可以媲美自然的最高成就——制造拥有最高理性的智能体。而这种想象带来的焦虑也同样是巨大的,如果真的出现了比人类更高级的智能体,那么人类存在的意义何在?人类是否会被取代?这也许是人类对人工智能关注的最根本的心理根源,一种关于自身存在的焦虑感。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将媲美人类的人工智能出现的时刻称为“奇点”,与物理学上最为奇异的点同名。
虽然人工智能离“奇点”时刻可能尚有距离,但是正如自动驾驶、ChatGPT 等技术所展示的,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它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这对国际关系也不例外。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正在发生,它可能是塑造未来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力量。当然,人类对于将来的讨论必然带有猜测性,更多是哲学思辨性质的。对于未来的探讨,必然面临挂一漏万的问题。正如伟大的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电梯效应所言,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即便猜中了某项技术,遗漏的变量也会导致对未来的预测产生巨大的偏差,特别是在只考虑了单一变量、单一机制的情况下。因此,在这种朝向未来的讨论中,特别需要机制性和系统性的讨论,特别需要理论的支撑以及对限制性因素的分析。
不同研究者对人工智能有不同的理解,在最经典的人工智能教科书《人工智能:现代方法》第四版中,其定义是“从环境中接收感知并执行动作的智能体的研究”,①斯图尔特·罗素、彼得·诺维格:《人工智能:现代方法》(第四版),张博雅、陈坤等译,中国邮电出版社2022 版这个人造的智能体能够从环境中获得信息并做出判断和行动。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基于这个定义。当然,不同学派对中间的判断过程有不同的理解,有些认为需要类似人或者人类理性,有些则认为只需智能体的行为结果是符合理性预期的。现有研究还区分了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也称狭义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前者指部分特定领域实现智能,比如视觉感知、听觉感知、解决简单问题等,而后者指类似或者超越人的智能,能够自行综合各种感知和知识进行理性的判断。
本文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讨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关注其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机制影响国际关系,并参考既有的理论框架和以往的技术变革给我们的启示。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演进发展中的技术,因此我们的讨论也不得不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差别。正如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未来学家罗伊·阿玛拉(Roy Amara)曾告诫的:“我们总是高估一项科技所带来的短期效益,却又低估它的长期影响。”而这个短期、中期和长期确切来说也并不完全是时间性的,也是技术性的,与技术演进的程度密切相关,尤其是面对中期和长期讨论的时候。
一、文献回顾
人工智能的理想在人类历史中出现得很早,至少在文明的轴心时代即有了将理性和思维过程形式化的努力,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三段论。而中国古代故事中对自动机器的描述①《墨子·鲁问》中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为鸢,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考虑到古人并无对远程控制的工程想象,这种飞鸟必然设想有某种自动控制装置。也是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最早想象之一。在近代自然科学起飞的时代也不乏对会思考的机器的设想。
一般认为现代的人工智能研究从1956 年的朴茨茅斯会议开始,经历了多次的起伏和波折。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想象和关注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国际关系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学科的影响,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推进国际关系的研究。②Hudson,Valerie M,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Westview Press,1991).其中的佼佼者如施罗德特(Schrodt),他一直从事事件自动编码的研究,并最终开发了目前最大的事件数据库(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Language and Tone,简称GDELT)。
在2006 年后的新一轮热潮中,结合了高速计算、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展示了颠覆性的变革潜力,因此出现了大量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与社会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讨论的一般著述,③如引起广泛讨论的2014 年《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见Nick Bostrom,Superintelligence:Paths,Dangers,Strateg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Tegmark,Max,Life 3.0: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intage,2018);Lee,Kai-Fu,AI superpowers:China,Silicon Valley,and the New World Order(Houghton Mifflin,2018);Kissinger,Henry A.,Eric Schmidt,and Daniel Huttenlocher,The Age of AI:And Our Human Future(Hachette UK,2021);Schmidt,Eric.“Innovation Power:Why Technology Will Define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Foreign Affairs,Vol. 102,No.2,2023,pp.38-52。其中也包括了相当的对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的讨论。国外的讨论更多是政策导向的,主要涉及对人工智能的管理问题,这些研究更多来自智库,主要谈论了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可能影响。有研究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应用的领域,包括军事、情报、经济竞争、信息战等等,①Greg Allen Taniel Cha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July 2017,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national-security.或者聚焦对军事革命——自动杀人武器——的影响。②Mary L. Cumming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Inter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and US and the Americas Programme,January 2017,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17/01/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future-warfare.也有学者关注自动杀人武器对战略稳定的影响。③Altmann,Jürgen,and Frank Sauer,“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and Strategic Stability”,Survival,Vol. 59,No. 5(2017),pp. 117-142.;Haas,Michael Carl,and Sophie-Charlotte Fischer,“The Evolution of Targeted Killing Practices:Autonomous Weapons,Future Conflict,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Martin Senn,Jodok Troy eds,The Transformation of Targeted Killing and International Order(Routledge,2020),pp. 107-132.还有学者讨论了人工智能在战场中使用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包括多智能主体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协调等问题。④Amodei,Dario,Chris Olah,Jacob Steinhardt,Paul Christiano,John Schulman,and Dan Mané.“Concrete problems in AI safety.”arXiv preprint arXiv:1606.06565(2016).对于恶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也有专门的讨论,⑤Brundage,Miles,Shahar Avin,Jack Clark,Helen Toner,Peter Eckersley,Ben Garfinkel,Allan Dafoe et al.“The maliciou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Forecasting,prevention,and mitigation.”arXiv preprint arXiv:1802.07228(2018).并从人工智能对电子安全、物理安全以及政治安全三个不同领域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在更为学术化的研究中,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以及科技竞争的激烈体现在对于技术在国际关系演变中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及其理论化。过往的研究者并非没有发现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反,许多理论家都将技术变量包含在理论框架中,当下需要重新发现和凸显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⑥Kaltofen,Carolin,Madeline Carr,and Michele Acuto,eds. Techn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ntinuity and change. Springer,2018;Eriksson,J.,Newlove-Eriksson,L.,“Theorizing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evailing Perspectives and New Horizonsin”,in Giampiero Giacomello,Francesco N. Moro and Marco Valigi(ed.),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w Frontier in Global Power.(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21).丹尼尔·德雷斯纳(Daniel Drezner)从技术的主导领域是公域还是私域(Public Sector Dominance or Private Sector Dominance)以及固定成本(Fixed Cost)的高或低区分了不同的技术类型,分析了不同的技术类型对权力、利益和制度的影响,发现文化、声望与技术创新一样在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起了很大作用,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而新技术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调整成本,但是人类的适应性也很强。①Drezner,Daniel W,“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3,No.2(2019),pp. 286-303.南非学者尼贞德(Bhaso Ndzendze)和马瓦拉(Tshilidzi Marwala)则从国际关系主要理论的核心概念出发,讨论了人工智能如何影响这些核心概念的变化。②Ndzendze,Bhaso,and Tshilidzi Marwala,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2023)
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③蔡自兴:《中国人工智能40 年》,载《科技导报》2016 年第15 期,第12~32 页。20 世纪80 年代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兴起以后,我国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包括专家系统在工业、环境以及医疗诊断等方面的应用,并一直持续到21 世纪早期,但是关于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等影响的研究则一直很少涉及。在1986 年《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中有一篇书评文章介绍了计算机对于人类的威胁,④葆真:《不容忽视的殷忧——西蒙斯新著:〈硅震荡,计算机入侵的威胁〉》,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 年第5 期,第70~71 页。其中探讨的计算机实际上大体相当于我们现今谈的人工智能,其中包含的问题与现今所讨论的问题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包括计算机过于复杂和快速的决定会使得人类失去对战争的掌控、导致大规模失业等。关于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对战争和军事的影响的关注也日渐增加,包括《解放军报》和《中国国防报》等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战争的影响都有一些简要的讨论,主要聚焦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使战争智能化,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对指挥系统的帮助。
随着人工智能热度的上升,自2017 年开始,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了对人工智能发展对国际关系演进影响的学术探索,⑤封帅,《建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历史考察与议程设置》,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 年第6 期,第59~59 页。这些研究探索了当前和长期的影响。对当下的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讨论各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政策、战略以及国际竞争。⑥如周琪、付随鑫:《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及政府发展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6 期,第28~54 页;华盾、封帅:《弱市场模式的曲折成长: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探微》,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3 期,第98~128 页;周生升、秦炎铭:《日本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与全球价值链能力再提升——基于顶层设计与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分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0 年第1期,第67~90 页;刘平、刘亮:《日本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人才、研发及社会实装应用》,载《现代日本经济》2020 年第6 期,第36~47 页。不同学者也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国际关系长期演变趋势的影响。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激烈竞争的推动下,大国之间也将进行更加激烈的博弈,恶化大国之间的关系,①傅莹:《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1 期,第1~18 页;Zhu,Qichao,and Kun Long,“How W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act Sino-US Relations?”,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Vol. 1,No. 1,2019,pp. 139-151。大国走向自给自足和相互猜忌甚至导致其安全战略转向进攻性现实主义。②王悠、陈定定:《迈向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5 期,第22~26 页。还有学者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军事与其他安全领域的影响,③阙天舒、张纪腾:《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 年01 期,第4~38 页。尤其是人工智能在战略博弈中的决策和信息优势,并且认为其会加剧国家间实力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国际均势的破坏,最早采用人工智能的国家会获得先发优势,④封帅、周亦奇:《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载《国际展望》2018 年第4 期,第34-59 页;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载《外交评论》2018 年第1 期,第128~156 页。而第三世界国家将面临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放大的可能。⑤韩永辉、张帆、彭嘉成:《秩序重构: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 期,第121~149 页;周琦,蒲松杨:《人工智能浪潮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困境与对策》,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第160~168 页。有学者则从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出发,分析了人工智能对不同的结构性权力的重塑或介入,对其具体的影响方式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和设想,不同性质的新兴权力将通过多元行为体崛起的方式予以充分表达。⑥部彦君许开轶:《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 年第1 期,第86~111 页。同时,国内社会结构和权力的分配也会受到影响,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广泛失业的问题,大量群体将会变得“无用”,人口不再是重要的国家实力指标,而新兴权力主体如掌控技术的科学家共同体(专家群体)将兴起。⑦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第148 页;封帅:《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载《外交评论》2020 年第6 期,第114 页。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公司也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⑧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9 期,第39 页。最后,人工智能还将对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带来冲击,如自动化杀人武器的出现。⑨朱荣生、冯紫雯、陈琪、陈劲:《人工智能的国际安全挑战及其治理》,载《中国科技论坛》2023 年第3 期,第160-167 页。而将视野放至更为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也可能意味着人类的解放,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替代人类进行各种劳动,那么人类就可以将精力放在更能发挥人类优势的方面,共产主义以及世界大同都更有可能实现。①高奇琦:《人工智能、人的解放与理想社会的实现》,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1 期,第40-49 页。世界政治也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乃至出现智能化世界政府,消解无政府状态。②封帅:《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第126 页。当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例如主体消失所带来的责任归属困难。③高奇琦、张蓥文:《主体弥散化与主体责任的终结:ChatGPT 对全球安全实践的影响》,载《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3 期,第3~27 页。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对大量相关议题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提供了许多可以进一步挖掘的议题。人工智能问题研究与一般的研究议题不同,由于其是朝向未来的思辨性讨论,几乎都是无法证实或者证伪的,因此本文的研究并不能说是补充或是改进了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增加一种新的视角,重点考虑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影响的整体作用机制,特别将限制这种影响的因素纳入机制当中。同时,也提出一个思考技术特性如何塑造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并基于这个框架,在中期和长期的视野下讨论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二、预期与冲突:人工智能与科技遏制
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行为的选择受到对未来预期的引导。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冲突和制裁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科普兰(Copeland)关于相互依赖与冲突的研究表明,在预期未来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会导向冲突,而在没有预期冲突的情况下,经济相互依赖会带来和平。④Copeland,Dale. C.,“Trade Expectations and The Outbreak of Peace:Détente 1970-74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91”,Security Studies,Vol. 9,No. 1-2,pp. 15-58;Copeland,Dale. 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104).德雷斯纳关于经济制裁的研究则表明,预期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则会导致经济制裁发起国更容易滥用经济制裁而目标国更不愿意妥协。⑤Drezner,Daniel W.“Conflict Expectations and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Coerc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4,1998,pp.709-731.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当下的行为,这正是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一个重要机制,也是其当下最大的影响。即使人工智能最终不能实现其所有的技术承诺,没能颠覆人类社会,人们对其的想象和期许也已经给当下带来巨大的影响。对人工智能颠覆性潜力的信仰正在重塑当今的大国竞争,尤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中美战略竞争。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战略,特别是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极限打压,其中最重要的动因之一就是美国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全面压制中国。
21世纪初,随着战斗机器人以及无人机等在反恐战争中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美军逐渐意识到了人工智能对于军事技术发展的巨大潜力,尤其是专注于大国竞争的美国战略研究者,包括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以及后来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阿什利·卡特(Ashley Carter)和副部长的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等。①Work,Robert O.,and Shawn Brimley,“ 20YY:Preparing for War in the Robotic Age”,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January 22,2014,p.28,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20yy-preparing-for-war-in-the-robotic-age.他们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美国国防战略的转型,特别是沃克等人力推第三次“抵消战略”。②Gian Gentile,et. al,A History of the Third Offset,2014-2018(Rand Corporation,2021).这个“抵消战略”将中俄尤其是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认为美国的国防战略应该从反恐转回到大国竞争中,在美军的相对技术优势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重新致力于建立新的战略技术优势。他们关注的这个新的战略技术即是自动化技术,而人工智能技术则顺理成章成为自动化技术的最重要的支撑,因此其是所谓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核心。在卡特和沃克的力推下,③卡特在2012 年在国防部设立了战略能力办公室,在2016 年公开其存在。该办公室目的也是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提升美军的技术优势。2014 年起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对华“抵消战略”在国防部全面展开。卡特建立了常驻美国各主要创新中心的国防创新小组,并邀请谷歌原总裁施密特(Schmidt)进入国防部的技术委员会。施密特主导了美国国防部与硅谷的深度联姻,其对人工智能技术尤为重视。施密特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是未来决定性的技术,而美国面临着中国的巨大挑战。④Alex Thompson,“A Google Billionaire's Fingerprints are All Over Biden's Science Office”,Politico,March 28,2022,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3/28/google-billionaire-joe-bidenscience-office-00020712#:~:text=Eric%20Schmidt%20has%20long%20sought,general%20counsel%20raised%20ethical%20flags奥巴马政府在临近任期结束时接连发布了三份人工智能报告,即《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在国防部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推动下,其主要理念包括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和人工智能的主导作用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精英的共识。①Mohar Chatterjee,“The Pentagon's Endless Struggle with AI”,Politico,June 27,2023,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6/27/pentagon-ai-00103876.
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对华政策逐步转向全面对抗,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 年,我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宣布要在2030 年成为世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这在美国则被广泛解读为中国要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2018 年,李开复的著作《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出版,对比了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引起了美国各方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关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导人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更将其推荐给当年《政客》的阅读书单。②Politico Magazine Staff,“The POLITICO 50 Reading List”,Politico,September 4,2018,https://www.politico.com/interactives/2018/politico-50-book-picks/.美国政界对中国在人工智能上相对美方的优势表达了警惕和忧虑。在2018 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中,美国成立了施密特担任主席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提交关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建议。2019 年,后来在美国国防部负责推动国防部人工智能政策的格雷戈里·艾伦(Gregory C. Allen)发布关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报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弱点之一是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和产业。③Gregory C. Allen,“Understanding China's AI Strategy”,CNAS,February 06,2019,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understanding-chinas-ai-strategy.在2021 年提交的最终报告中,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对中国采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措施来遏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要利用半导体设备中美国的不对称优势来进行打压。④“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Final Report,”2021,https://assets.foleon.com/eu-west-2/uploads-7e3kk3/48187/nscai_full_report_digital.04d6b124173c.pdf,p.231.特朗普政府几乎将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领军企业全部加入了出口管制的黑名单,包括芯片设计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图像识别、声音识别等)企业、芯片制造企业、超算研究机构和企业等。
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专注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施密特的影响仍在,其基金会甚至支付部分白宫科技相关职位的薪资,①Alex Thompson,“A Google Billionaire's Fingerprints are All Over Biden’s Science Office”.同时他还成立了一个名为特别竞争项目(The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的智库,接替已经完成使命、解散了的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动与中国的科技竞争特别是人工智能竞争。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立文(Sullivan)2022 年在该智库举办的新兴技术峰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被称为“沙立文主义”的对华科技竞争原则,即在战略科技领域,美国不满足于领先一两代,而是追求优势越大越好,②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t the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mmit,September 16,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9/16/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at-the-specialcompetitive-studies-project-global-emerging-technologies-summit/人工智能正是其战略科技领域之一。2022 年10 月7 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实施前所未有的严苛的出口管制,不仅限制了美国对华出口先进芯片及其制造设备,还利用外国产品直接规则限制了其他国家对华出口相关的芯片和设备,更进一步限制了美国实体(包括机构和自然人)协助中国先进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这次管制不仅要锁死中国的发展,甚至要让中国倒退。此举震惊了业界,《纽约时报》称其为一场围绕芯片的经济战争,并称如果列举2022 年发生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俄乌冲突,另一件则是美国对华的芯片战争。③Alex W. Palmer,“‘An Act of War’:Inside America’s Silicon Blockade Against China”,New York Times Magazine,July 12,2023,https://www.nytimes.com/2023/07/12/magazine/semiconductorchips-us-china.html.这场芯片战争的主要目的即是彻底压制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④Gregory C.Allen,“Choking off China’s Access to the Future of AI”,CSIS,October 11,2022,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oking-chinas-access-future-ai.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先进的芯片,所以美国一方面阻止美国公司将先进芯片出售给中国,另一方面又掐断中国获得自己生产先进芯片技术的渠道。⑤Ibid,pp.2-7.美国还进一步迫使其他掌握先进芯片技术的国家,如韩国、日本以及荷兰等同步修改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将单方打压升级为全球打压。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科技遏制极大地恶化了双边关系,损害了双边战略互信,同时也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这种遏制很大程度来自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关注。在美国的科技遏制战略下,各国都不得不寻求将重要的战略经济、科技资源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方法。不难看出,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预期极大地加剧了大国竞争的程度,冲击了既有的国际体系。对人工智能的期望越高,在短期内国家间因人工智能而产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虽然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契机,①Zhu,Qichao,and Kun Long.“How w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act Sino-US Relations?”.但是在两国未来将发生冲突的预期以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战略技术的背景下,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双方更关注的是彼此的相对收益。
三、技术特征及其影响:一个框架
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那么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将更有理论思辨性;如果随意地提取技术的一个特征来讨论其影响,则很容易失之偏颇,因为技术和国际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和社会现象,具有多元的特征。恰当的理解需要把握其关键性的特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个理解技术影响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对不同技术掌握的历史,新技术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但是,不同的技术对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显然有所不同。德雷斯纳在其分析中按照技术是公域还是私域为主以及固定成本的高低两个维度来讨论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是公域还是私域为主与技术的潜在能力并无直接关系,有些技术比别的技术具有更大的颠覆性,也会有更大的影响。主要的使用领域与其颠覆潜力并无直接关联。而且,有许多技术很难说是公域为主还是私域为主,比如许多两用技术。在技术日益融合发展的今天,技术两用性更为突出,区分其主要使用用途也将更为困难。而对固定成本的关注实际上是对技术扩散的讨论,高成本的技术不利于扩散,而低成本的技术则较容易扩散。除非对成本做极为宽泛的解释,不然也难以涵盖技术扩散中面临的诸多因素。因此,本文提出从颠覆性程度以及扩散程度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新技术总是意味着新的方式、新的知识或工具等实现目的方式的改变。有些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如马拉战车、火药、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等。也有些技术的影响相对更有限,比如许多日常使用的技术。在甄别这些技术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技术比另外一些技术更具有颠覆性,也即其相比于原有的技术而言在某些方面具有质的飞跃,有数量级的差距。蒸汽机比人力或畜力输出的能量要高几个数量级,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增加。类似地,原子弹相比于火药是核能与化学能的差距,一千克铀释放的能量是一千克TNT 炸药的约两千万倍。因此,更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显然更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拥有此技术的国家与缺少该技术的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可能会大大增加。
另一个涉及技术影响力的维度是技术的扩散程度,在现有的关于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的讨论中这个维度常常被忽略。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如果不能广泛地被采用,那么其对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相应会减少。学术界日益意识到技术扩散实际可能是一个影响国家间竞争的更重要的因素,甚至比单纯技术创新能力更为重要。①Ding,Jeffrey.“The Diffusion Defici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Re-Assessing China's Ris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23,pp.1-26,https://doi.org/10.1080/09692290.2023.2173633.一个技术扩散的范围与速度决定了其扩散程度。
一个技术的扩散程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以下几个。首先是社会规范和思想观念。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社会并不欢迎技术创新,反而会认为新的技术会破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稳定,这也是中国古代将许多新发明新工具贬低为“奇技淫巧”的原因。其次是社会制度。一个技术的产生和广泛使用具有分配效应,会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产生新的赢家和输家。附着在旧技术上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必然会因新技术的到来而受损害,他们也必然会影响政治来阻碍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而这也是新技术的推广所必须克服的障碍。②学者认为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受损的群体会反对新技术的扩散,但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认为因新技术权力受损的精英是技术扩散受阻的主要原因,他们有政治权力来推行阻碍新技术的政策,见Acemoglu,Daron,and James A. Robinson.“Political Losers as a Barrier to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2,pp.126-130。所谓的“卡德维尔定律”(Cardwell's Law)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这种社会反对力量,这个定律认为没有国家能够持续地引领创新,创新的领军国家总在不断地转移,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国内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会有强烈的动机影响新技术的推广。①Taylor,Mark Zachary,The Politics of Innovation:Why Some Countrie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领先的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就落后了,因为许多的国内利益集团反对新技术的推广。②高奇琦:《人工智能,四次工业革命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6 期,第13 页。只有在外部安全威胁大于内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国家才更有可能克服这些阻力。③Taylor,The Politics of Innovation:Why Some Countrie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p.13.因此,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国家之间竞争激烈,尤其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竞争激烈的时候,国家更有可能快速地采用新技术。④Milner,Helen V.,and Sondre Ulvund Solstad.“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World Politics,Vol. 73,No. 3,2021,pp. 545-589.最后,技术本身的特性也会影响其扩散程度。不同技术的采用成本不一样。有些技术更便于推广,而有些技术则需要更多的基础投资、更多的技能培训才能使用。没有良好的计算机网络基础设施,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显然会更慢。有些技术也会更依赖于广泛使用的规模效应来发展。扩散性强的技术更有利于权力的分散,对实力差距的影响较小,同时更可能重塑国家社会的权力分配,因此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可能通过重塑国内政治来影响国际政治。其他因素还包括技术接收国的能力、区位、需求等。⑤Comin,Diego,and Marti Mestieri.“Technology Diffusion:Measurement,Causes,And Consequences”,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N. Durlauf 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ol. 2(Elsevier,2014),pp.565-622.
颠覆性强且扩散程度低的技术有利于增加技术所有国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颠覆性强且扩散程度高的技术给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带来的影响较小,但很有可能会削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因为这些技术可能会赋权给更多的社会实体。当然,技术也并非单一的,不同技术结合产生的复合效应可能会远远超出单一技术的影响。如互联网技术是普遍扩散的,不会明显增加采用国相对无互联网技术的国家的实力优势,但是如果互联网技术跟其他的技术相结合则可能产生更大影响。因为通过结合其他技术就可以大大减少复合技术的扩散程度。比如5G+工业能大大提高效率,但这种复合技术的扩散程度会大为减少,因为这种技术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本投入,因此也就可以给先发国家带来很大的优势。
基于以上的分析,中期和远期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将从这两个维度展开,并同时参考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四、忠诚助手:弱人工智能下的权力、利益与制度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离真正的类人的智能乃至“弱人工智能”依然有相当的差距。2022 年底开始火遍全球的最新的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依然无法媲美人类的智能,即便它记录分析了所有的人类知识,却依然无法做出简单的真假判断。它不能根据真的知识判断其生成论述的真假,更无法通过其他手段如做实验等方式来验证事实。虽然媒体对其能力有大量的溢美之词,但是许多的说法很快被证明是言过其实,①任何用过ChatGPT 的人都会遇到其编造虚假信息的问题,甚至有美国律师使用ChatGPT协助准备辩护意见却未发现其提供的案例是自行编造的而导致被罚款,见Sara Merken,“New York Lawyers Sanctioned for Using Fake Chatgpt Cases in Legal Brief”,Reuters,June 26,2023,https://www.reuters.com/legal/new-york-lawyers-sanctioned-using-fake-chatgpt-cases-legal-brief-2023-06-22/。更不用说它生产单位语句所耗费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人脑。②Josh Saul and Dina Bas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Booming—So Is Its Carbon Footprint”,Bloomberg,March 9,2023,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3-09/how-much-energy-do-ai-and-chatgpt-use-no-one-knows-for-sure#xj4y7vzkg.虽然当前的人工智能能够做到非常准确地对外界进行某些感知,但是却缺少对这些感知进行综合处理的能力。人工智能能够精确地识别图形、声音等,但是却无法将这些知觉综合起来形成有效的知识,也无法根据已有的知识判断合理性。③比如,目前的生成式的画图人工智能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足以画出以假乱真的图像,但是也会犯一些匪夷所思的错误,比如有时会画出三只腿的人。当然,快速迭代的模型也会迅速更正这些错误。人工智能专家杨立昆(Yann LeCun)毫不客气地说:“当前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连狗的智能都还没达到,更遑论人类智能。”④Arjun Kharpal,“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t Yet as Smart as a Dog,Meta A.I. Chief Says”,CNBC,June 15 2023,https://www.cnbc.com/2023/06/15/ai-is-not-even-at-dog-level-intelligenceyet-meta-ai-chief.html.不过需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人工智能在近些年的发展迭代异常迅速。因此,中期的远景是人工智能实现了弱人工智能,即能够理解人类的需求,处理大量的信息以帮助人类做出判断,并在人类作出判断后协助实施。当前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的数据单靠人力显然已经无法快速地提取出有效的信息,因此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当前信息环境的必需,而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也已证明了其能力,并有足够的空间进一步提升。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角色相当于一个忠诚可靠的助手。它能准确地提取信息,并按照人类的判断高速、准确地执行任务,并且综合能耗有了较大的降低,但是综合处理信息做出判断的能力依然远不如人类,除了在一些简单的场景之中,比如自动驾驶中遇到障碍物紧急刹车。
那么,按照前一部分的分析框架,这种弱人工智能属于哪一种技术呢?就颠覆性而言,弱人工智能并不那么具有颠覆性,更像是一种逐步的提升。虽然有学者认为其在做决策时相比人类有优势,特别是在军事上,但实际上弱人工智能的决定能力只在相对直观的任务上有优势。在军事上,其可以快速地锁定目标,也能快速反应发射武器等,但是这些决定都有着简单的可以定义和量化的目标,在真正重要的战略问题上,在需要综合各种信息做出前瞻性判断而且很多时候带有直觉性质的军事决策上,很难相信弱人工智能比人类有优势。①目前论证人工智能的决策优势经常引用的是人工智能在一些棋类游戏中的优势,包括围棋等,但是相比于人类社会的真实决策而言,棋类博弈都是极为简单的。而且人类决策往往是基于对少数经验的理解,而人工智能的博弈是基于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决策往往数量极少,按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完全无法应对这种决策。这也意味着它更多只能是协助人类做决定,在复杂决策能力上无法与人类相比。在其协助下,人的工作效率会有相当的提升,特别是在某些特定行业中,工作效率的提升可能是惊人的。而从扩散性的角度而言,弱人工智能更多是一种软件,也就意味着其扩散的成本非常低,扩散程度会非常广。而且,弱人工智能的技术提供商可能会有许多家大型公司,各主要大国都会扶持自己国内的企业,在许多工具也是开源的情况下,单一大国垄断该技术的可能性较小。弱人工智能真正要发挥更大用途需要仰仗其他技术的同步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要求也很高,只有在一个满足了智能城市或国家的基本硬件要求的国家中,人工智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真正的扩散困难在于配套的基础设施或者技术所需要的投资和资源。
如果其颠覆性程度不是非常高,弱人工智能对大国间实力差距的影响会相对有限。特别是其扩散程度较高,大国基本都能利用这个技术,因此在大国间不会带来实力差距的巨大变化。当然,有些小国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特别是如果无法将弱人工智能整合进整体社会经济中,其劣势将进一步放大。国际关系主要由大国主导,如果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没有受到冲击,那么,中期来看,人工智能不会给国际体系带来革命,更可能是延续已有的权力结构。
不过,随着弱人工智能在社会的广泛运用,通过影响国内政治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是更可能的一条路径。广泛扩散的技术往往会增强个体的能力,因此弱人工智能的广泛扩散将增强社会群体乃至个体对于国家的挑战。如互联网极大增强了人们之间互相连接的能力,也使得社会运动的动员更为容易,在社交网络发展起来以后,多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传统上大众传媒集中在部分精英群体手中,他们作为观念的守门人能够筛选信息影响社会,但是互联网技术打破了这种垄断,不同的思想都可以找到直达大众的渠道,人工智能将会进一步强化这个趋势。当然,这种挑战对于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在能够主动引导民众的政治制度中,国家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加强自身能力,约束极端人物和思想的影响。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设计下,各种边缘、反智的思想被以权利的名义保留了下来,并且在互联网低成本的传播方式下广泛地传播开来,导致社会的分裂,严肃的政治讨论的基础和空间都被极大压缩。西方社会近年来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弊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这种政治制度和信息社会不适应的产物。同时,现有的制度强调在高度共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根本变革,而碎裂的社会现实又使得共识成为不可能。这就导致了一个僵局并不断地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在弱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危机会进一步加大。一方面,正如搜索引擎会让人觉得自己比实际更聪明一样,①Sarah Kaplan,“How the Internet makes you think you’re smarter than you really are”,Washington Post,April 1,201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5/04/01/howthe-internet-makes-you-think-youre-smarter-than-you-really-are/.弱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资源也会让个人对自己的观念更为自信,而人工智能几乎可以生成以假乱真的各种图像、声音和文字,个人被困在信息茧房的危险会更高。②著名美国学者托马斯·尼可拉斯(Thomas M. Nichols)认为互联网助长了对专家的蔑视态度,导致了美国的反智主义更为严重,接触到大量知识并不等于真正的学习,其论证逻辑也可以用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使得各种知识更为唾手可得,人们却更不愿意真正学习,人们对于专业知识的敬畏只会更少。参见Nichols,Tom,The Death of Expertise: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可获得性更高了,个人实施各种反社会的行为也更为容易,包括独狼式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极端行为有可能增加。政治和社会的弊病也会转移到对外关系上,正如美国的极化政治影响其外交政策一样,①Friedrichs,Gordon M,“Conceptualizing the Effects of Polarization for U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Revisiting the Two-Level Gam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 24,No. 1,2022,viac010,https://doi.org/10.1093/isr/viac010;Stephen M. Walt,“America’s Polarization Is a Foreign Policy Problem,Too”,Foreign Policy,March 11,2019,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3/11/americas-polarization-is-a-foreign-policy-problem-too/.极端思维占据了过多的政治空间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间政治可能会越来越偏离理性。
由于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导权在各大公司手中,考虑到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巨量计算资源、人才资源、数据资源等,进入门槛非常高,人工智能技术的提供者将仍是这些公司,但是一旦成为社会的关键服务,政府强化管理甚至接管部分公司的可能性较大。虽然大型科技公司对人类生活的直接影响可能会更大,但是它们未必能挑战政府的权力垄断。人工智能能否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与其能否跟其他技术结合产生新的产业有关。如蒸汽机跟手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产业工人,而内燃机则催生了汽车和飞机等行业进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使得社会权力进一步向资本倾斜。有学者认为专业阶层(如科学家、工程师等)会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是否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跟其掌控的社会资源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与其是否具有独立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有关。虽然人工智能也许会强化专业阶层的力量,但是在利益和政治权力诉求上这个阶层并没有太多的独特性。
新的技术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跟社会采取的应对方式有关。社会权力向资本的集中也产生了反作用,使得发达国家都普遍迈上了福利资本主义的道路,各种社会福利项目都建立了起来。许多人都预测人工智能将会极大地冲击就业市场,导致大量的失业,劳动阶层的社会地位将会被削弱。在中期来看,也即弱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就业冲击必然是会存在的,但是也不需要过度夸大。一方面是弱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人的作用,还无法完全取代人。特别是在服务行业中,人类带来的情感互动等都是难以取代的。也不能低估人类习惯的重要影响。其次,在人工智能消灭许多就业岗位之时也会产生新的岗位。在人类历史上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震荡和转型并不鲜见,而关键在于转型的成本能否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第三,任何的社会政治制度都不会无视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必然会针对性地降低调整成本,也就意味着政府一定会阻止人工智能应用的无序扩张,争取调整的空间和时间,保障一定的过渡期。不过,这种调整很可能会有国际效应,也即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比如贸易保护主义就容易激发国际矛盾,因此各国对于人工智能的限制也可能会引发国家间对立情绪和敌对政策的增加。而且,国家间军事和经济的激烈竞争会削弱国家进行调整应对的能力,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尽可能地采用新技术而放弃一些可以降低转型成本的措施。最后,普通人或者劳工阶层对于社会和经济而言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除了是生产者,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消费者,如果在经济循环中将他们剔除,那么经济也会崩溃,毕竟弱人工智能在经济循环中只能充当生产者。经济体系如果需要维持健康运转就必然需要将大多数人保留在经济循环中。如果弱人工智能对于社会权力结构的冲击有限,那么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偏好的变化也将相对有限。但是其中的风险是应对人工智能的转型成本过于高昂,时间过于长久,导致了社会分裂,这会强化民粹主义,导致社会不稳定。由于民粹主义往往也与排外主义相关联,人工智能也因此可能恶化国际冲突。
弱人工智能也会有助于人类解决一些共有的危机,比如气候变化。即便我们对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还无法完全看清,有许多未知的变化会发生,但是对于其将提高社会生产运转的效率是比较确定的。而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单位能耗会降低,这将有助于低碳社会的实现。而随着全球升温的不可避免,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时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
五、强人工智能:美丽新世界?
许多关于人工智能最引人入胜和极端的预测都是基于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包括机器反抗甚至支配人类导致人类灭绝。关于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也即所谓的“奇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预测。技术乐观者认为今后几十年或上百年就会出现,而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非常久远的、数个世纪以后的远景,①Grace,Katja,et al.“When will AI Exceed Huma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I Experts”,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Vol.62,2018,pp.729-754;《人工智能:现代方法》,第781页。毕竟当前的人工智能的路径有各自的局限性,似乎都难以突破实现类人的智能。人类对自身思维的了解,对脑科学的研究等都还有重大的不足。同时,不确定的还有在强人工智能出现的时候,其他的人类技术的发展如何,比如能源技术、计算技术,这些都将影响到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其扩散程度。但是即便只考虑强人工智能的技术,这个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冲击也将是非常大的。在这种宏观尺度上比较适合讨论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理论是建构主义,它的理论植根于人的身份、自我认知以及社会认知,在利益、权力形成之前的基本观念的塑造。强人工智能恰恰对人的身份的冲击是最大的。
强人工智能无疑将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它颠覆的不仅仅是社会运转的物质基础,还颠覆了人本身。对人是什么的思考将贯穿整个强人工智能的时代,因为一旦机器能够理性地思考,那么自古以来人类最引以为傲的理性将不再是人类的独有,人类必然只能从别处探寻其存在的独特意义。这种冲击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首先,作为人类基础社会制度之一的宗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如果说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不断地削弱宗教的基础,那么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是更为致命的一击。如果人类能够制造出类似人甚至超越人的智能生命,那么所有宗教中的人类中心论以及神的地位都将被直接挑战。人做到了宗教中的最大神迹——造人。宗教经常是人类和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缘由,在强人工智能时代,这个冲突的根源也许将最终消失。
其次,对于人的身份的独特性思考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将是难以避免的。人与机器之间的界线将日益模糊,所有的关于责任和自由意志的哲学和伦理都将重新建构。如果人能够制造智能体,而这个智能体能够自行选择、决定行为,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幻觉?毕竟,机器必然是按照设定的程序和参数运作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责任的基础在哪?人工智能体能否与自然人一样具有完整的“人格”?在今天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做出回答乃至预测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面对重大根本性的问题时,人类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智能体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这些不同的答案之间,不同的阵营将会形成,并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根源。
此外,人类的情感跟理智能否决然地分开?一个具有强人工智能的智能体是否具有情感?如果不具有情感,那么其价值观念是如何生成的?这些价值观念又如何影响其行为?现有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行为受到价值和情感的直接影响,理智与情感在做决定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分离的。①Lerner,Jennifer S.,et al.“Emotion and Decision Making”,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 66,2015,pp.799-823.在类人智能出现以后,其必然也会参与到决策中,而且其具有了独立决策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国际关系中将出现新的非人主体。在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人对权力的渴望是国家冲突的根源,那人工智能体会有这种对权力的渴望吗?结构现实主义则预设了国家对于安全的需求,其根本上也是植根于人对安全的需求,那么类人智能体会有这种需求吗?自由主义理论则是假定了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那么类人智能体也是如此决策吗?这些问题都预示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将产生根本性的重构。
第三,强人工智能还将面临一还是多的问题,即强人工智能是单一体还是多元体。如果强人工智能是单一体,所有的人工智能体共享一个中心处理机制,那就意味着只有单一的思考模式、单一的决策模式、单一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其是多元体,那就意味着强人工智能如自然人一样具有不同的决策模式和价值取向。这个区别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人工智能是单一体,就如同电影《终结者》中的天网系统,那么其控制支配人类的可能性将更大,因为不存在别的人工智能体来制衡它,它的对立面只会是人类。而如果人工智能是多元的,这意味着人类不会是其唯一的对立者,那么人与人工智能的世界末日般的冲突可能性会更小。当然,人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体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则会更大,正如现代有着利益和观念差异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总之,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关系将面对着一个彻底的重新建构,而其根源则是人关于自身的重新定位和人的身份的重新建构。人如何看待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的关系都将被彻底地改变。正如温特所言: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人类也将重新建构国际关系。
六、结语
人们经常引用海明威的名言来描述变化如何发生——“慢慢地,然后突然地”。人工智能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可能也会是如此,逐步的变化不停地累积,最终突然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在当前,由于人们预期人工智能将会决定未来战略竞争的胜败,因此催生了激烈的竞争,带来冲突升级的危险。科技竞争也成为主要的战略竞争领域。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注极大地增强了大国关系的负面因素,并呈现出由单一技术扩散至全面竞争与对抗的趋势。这也是当前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最大影响。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其对大国关系的冲击将比较有限,但各国国内政治可能首先受到直接的冲击,然后这种冲击将传导至国际关系。而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将迫使人类思考一些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人类的未来与人工智能的未来都是开放的,许多当前所不知的因素也将参与塑造最终的结果,这个过程不会是线性的,也不会是完全脱离人类掌控的,人类可以做出许多的准备和选择。如果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人类社会的适应性。对于当前的人类而言,最关键的是管控当下因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而升级的国家战略竞争,避免其走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