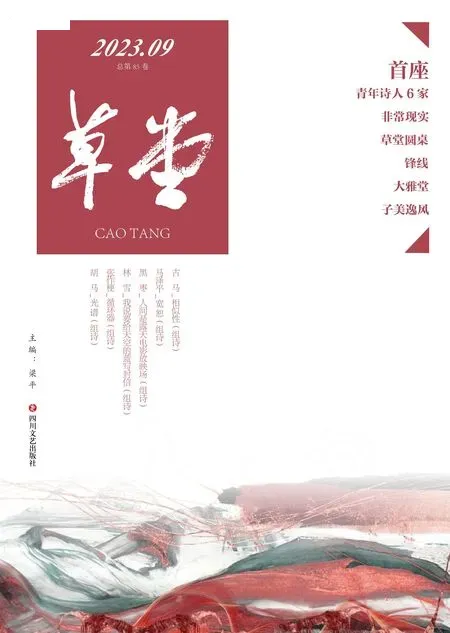白鹤南飞(组诗)
◎宋晓杰
[荒野中的半条船]
必定有一场摧枯拉朽的飓风
有撞击险滩的恶浪
折断桅杆的坼裂之声
必定有淫雨,从天缝儿里
泼——下——来——
必定有响鞭和尖锐的闪电
刺中它的心脏
必定有狼嚎,卷走苇海的草皮
必定有被掀翻的船舷、舱门
冲出来的一群野兽
必定有烈酒,血脉偾张的脖筋
高八度的喉咙
船舱外,必定有高挑的灯笼
像谁,信手捏碎的鱼泡儿……
荒野,这巨大的消音器
风暴止息,四野安详
“在夕阳的余晖下,
所有的一切,包括绞刑架,
都被怀旧的淡香所照亮。”
被撕裂的经纬,像不像拔丝的美食
纤毫毕现,逆着晖光
——作为无字的墓志铭
它必定咬紧牙关
倾斜着,支住摇摇下坠的
半个身体
[白鹤南飞]
两天前,正是立冬时节
在辽河入海口
观测斑海豹的朋友老田
发来图片:栖落于门头冈上的
白鹤,结队南飞了……
赤足、红唇的白鹤
黑白分明的白鹤
飞行时组成“人”字的白鹤
令作为人的我,汗颜——
我的翅膀,已经退化
坐地日行千百里,不过是自欺
苔草、荸荠等植物的茎块、叶芽
永远填不饱越来越大的胃口
甚至,我已不配穿素白的衣裙
顽固的黑斑、杂质太多
我也不及行于海上的旧船
像一头巨鲸,熟知生活的深浅
温柔地,舔着吃水线
它弧度自然的船舷
如铁青色的肋骨——
被风雨抛光,被海水腌制
再被晚霞镀上青铜
年复一年,终于熬成
胡子拉碴的老水手
我恐高、恐水
好好的一张海上行旅图
我却最先看到了吊在
缆绳间的救生圈
虚火升腾——它再次
捆绑了我,又“搭救”我
于水火之中
……目送。云云白鹤
孤悬于海天之间
像目送精神清洁的朋友
——瑞雪,纷纷飘落下来
无法移动之物
终于喘上了那致命的
一口气
[秋凉提前到来]
最先知道时间底细的
一定是紧贴地皮的植物
它们的直观表现,在于头顶细柔的茸毛
花木藤架上的葫芦、南瓜,就是这样
一两片叶子忽然就黄了,却不影响
月白、鹅黄的花朵,次第盛开
厮杀或掣肘,暗中较量
……凉风起于后半夜
树叶喧哗,正在商议大事
小恙,不得安生。我翻了个身
听到远处的暴雨滚滚而来
大地被反复淘洗,抽打
说“一叶知秋”是不够准确的
身体和大地一样,都是细敏之物
风吹草动背后,是幼兽旺盛
集结,沙沙地啃食最小的细胞
[流年… …]
年过半百了。到了这个年纪
发生什么都是正常的
惊雷潜入草丛,雨水湿过地皮
洪水、大火,天灾人祸,晴天霹雳
都有可能发生
大惊小怪又能怎样
只需一捧冷水,摔到脸上
再献上发炎的瘦肩膀
河流,已穿过险滩激流
再往前,就是入海口
身边的熟人,一个个消失
像滴水,转瞬无影无踪
两个世界正以说不清的秩序
达成平衡
坍塌时有发生:急着赶路的人
代替谁,潦草地过完一生?
动用并不擅长的加减法
开始反省:我又多吃多占了啊……
这朴素的教育,比书本管用
几年前,我陆续把可有可无的东西送人
近来,常为那几架藏书忧心
暗中物色人选接管,刚要欢欣,转而沮丧
——若干年后,谁会与某页中的浪线
不期而遇,温习我曾经的心跳?
那些看不见的电流、脉搏
文明的火种……
——那时,我正在火星巡游
此刻,那个人尚未出生
·创作谈·
野风景
野风景,关键在于“野”。它没有经过人工改造、驯化,没有人类说三道四、动手动脚,所有呈现皆为天成——来自它与风雨雷电角力、搏斗后的洽切和解。它如一头巨兽,风吹芦苇,那是它静卧于大地,皮毛顺着风;斜阳高挂,那是它凝视的万物,被镀上青铜。
然而,野风景去了哪里?
多久了,退化的不仅是水草丰美的自然,还有众多领域的自然生态。沉船成为茶台,铁锚成为标本。孤悬的马灯在夜风中悠悠荡荡,把谁人怀想?风中的院门兀自拍打,是谁的手在翻动时光的册页?
每年,我都要去湿地看看。如奔马,在大地上松开四蹄,扬起长鬃。否则,心是空的,这一年约等于白过。当自然保护区的大门訇然洞开,光芒涌入。它没有手脚,却扑面而来;没有语言,却众声喧哗。
多年以前,家乡的红海滩彻地连天。登上拦海大堤的一瞬,人便木在那里。目力所及,海天之间,嫣红的锦绣铺向天边。惊叹、不解无济于事,所有的一切已然发生,万念俱灰的绝望——我第一次感到:美至悬崖,唯有绝望。圆拱的苍穹和无边的旷野,构成天地间隐形的消音器,我迅速地矮下去……摇曳的赤碱蓬,小小的,却织就超低空飞翔的巨大魔毯,为大地披上锦衣。锦绣之下,万物涌动。春天,野风景只要水、草,再给它点阳光就能孕育,鸥鸟就可以谈情说爱,双宿双飞。大鸟凝重如小型航母,小雀欢叫如丝篁试弦。秋天,它藏得太深了!呈现出来的,是丰富釉彩下的辉煌殿堂。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还不够勇敢和纯粹。那一次,为了在黑暗降临之前冲出曲折的苇海,与人世接驳,我终于迷了路。心慌——慌张的慌,加上荒野的荒……很快!便心软如棉。因为,我看到了人间烟火。
第二天清晨,飘渺的音韵。熟悉的笑脸。坚固的屋顶。但我又开始怀念荒野。我知道,这样的轮回无可避免。驿动的心是主人,需要旷野那么大的心房。敏锐的直觉是火种,在荒野中才能看见。
——我在说我,也是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