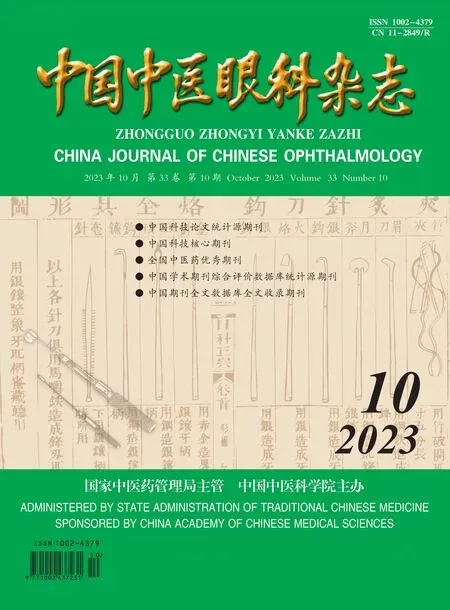浅析《审视瑶函》论治小儿眼病
罗悦,陈亦霞,曹雯媗,吴宁玲
《审视瑶函》[1]系明代著名眼科医家傅仁宇纂辑的一部古代中医眼科专著。全书共分六卷,卷一和卷二为总论,主要论述了五轮、八廓理论,是中医脏腑学说在眼科领域的体现;卷三至卷六分节论述了108 种眼科常见症候,以及多种外治法及方剂的运用,其中不乏小儿眼病的诊治方法。傅仁宇[1]在继承前代中医眼科学家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经验,删繁辑略,讨诸名家方书,采撷要领,最终成功纂辑出《审视瑶函》。书中对小儿眼病的论治特色鲜明,对眼科临床颇有裨益。《审视瑶函》[1]强调小儿眼疾的病因多为“胎毒”与饮食内伤,并基于五轮学说辨析小儿眼病病机。因小儿时期疾病病情多变、生理特点特殊,强调遣方用药时尤需顾护小儿脾胃,不可过用攻伐,并重视煎服方法的选择。因此临床必须结合眼科疾病的特点和患儿的生理特点综合分析,才能明确诊断,准确治疗。
《颅囟经·脉法》[2]载:“三岁以下,呼为纯阳”“纯阳”者,阳气尚未成熟之意。小儿为“纯阳”之体,受纯阳之气的作用,后天水谷之精充养机体,不断生长发育成熟。然小儿生长代谢旺盛,对水谷精气的需求迫切,在阴阳不断的滋长中,阴精相对显得不足,故形成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阳气相对偏旺的生理状态。《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3]曰:“阴阳不相得则病。”阴相对亏虚,阴不制阳,若此时外邪侵袭,易导致眼病。
钱乙《小儿药证直诀》[4]提出小儿“脏腑柔弱,血气未实”“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特点。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气、血、津液之化生不足[5]。正如《审视瑶函》[1]言:“小儿初害,营卫之虚”,小儿脏腑娇嫩,五脏不坚,脾胃运化之力较弱,形体未充,卫外御邪之力不足。小儿处在特殊的生理时期,精气营血未充,卫外不固,故对病邪的抵抗能力较成人不足。另外,根据小儿服药不宜多的特点,在药物的剂型、剂量和组方药味选择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因此,患儿在特殊阶段的生理病理因素是临床处方用药的关键。
结合以上的生理病理特点,小儿禀稚阳之气,肌肤疏松,腠理开泄,易感寒、热之邪,且发病后传变迅速;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抗病能力弱,病情多反复。但因其活力充沛、反应灵敏、生机勃勃,疾病的病因、病机相对单纯,若辨证准确,论治合理,则疾病易趋康复。通过研读《审视瑶函》,笔者总结出傅仁宇对小儿眼疾病因的认识,即小儿眼疾多因“胎毒”“饮食内伤”所致。
1 明析眼病病因
《审视瑶函》一书十分重视对眼病病因的辨析,文中指出“胎毒”“饮食内伤”为小儿眼病的常见病因。清代吴鞠通[6]论小儿疾病“内不过饮食胎毒而已”,亦充分说明这两种因素致病的特殊性。
胎毒理论是中医儿科学对疾病病因的独特认识。小儿尤其是新生儿的诸多眼病,与患儿母亲胎孕时期养护及饮食不当相关。《幼幼集成》[7]载:“凡胎毒之发,如虫疥流丹、湿疮、痈疖结核、重舌木舌、鹅口疮,与夫胎热、胎寒、胎搐、胎黄是也。”胎毒久伏于体内,遇外感、饮食内伤等诱因,则外发为眼病。正如《审视瑶函·卷之四·痘疹》[1]谓痘后眼病“小儿受胎毒……邪气入于肝胆二经,兼真元未复,则发目疾”。在小儿眼病中,胎毒可表现为风毒、热毒、湿毒等不同性质。胎毒的性质不同,因而眼部的表现也不同,在临证时需加以鉴别。
《黄帝内经》[3]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小儿脏腑娇嫩,脾禀未充,胃气未动,对饮食物的腐熟运化能力不足,极易因饮食失调而致脾胃受损。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具有升清降浊之功。眼居高位,脾胃相辅,则清阳之气上注于眼,而目窍得养[8];若升降失调,浊气上犯,目疾由生。如《审视瑶函·卷之二·深疳为害之病》[1]言:“疳病亦伤睛,生源而失化养之源”,小儿疳眼的发生即因饮食不当,而致“脾伤”,气血化生乏源,清阳不升,久则湿热内蕴,浊气上犯而为病。
2 详辨眼病病机
《审视瑶函》以五轮学说为基础,重视五轮与五脏的对应关系,阐析小儿眼病病机。气轮在目为白睛,在脏属肺,《异授眼科》[9]载:“白睛属肺,病则白睛肿起……或白膜侵睛”。小儿白膜表现为白膜遮睛,属气轮疾患,傅仁宇分析认为,此病常因外感风热不解,或肝火上炎,木火刑金,以致肺火,肺火循经上攻眼目,发为白膜。风轮在目为黑睛,在脏属肝;血轮在目为两眦,在脏属心;肉轮在目为胞睑,在脏属脾;水轮在目为瞳仁,在脏属肾[10]。尽管书中罕少从风轮、血轮、肉轮、水轮角度讨论小儿眼病,但其谨守五轮学说思想,详辨小儿眼病病机,对后世眼病的脏腑证治影响深远。
3 辨治特点
《审视瑶函》[1]提出小儿眼病治疗应“勿使太过”,否则“元气大伤,而变症生矣”。小儿脏腑娇嫩,对药物的敏感性和耐受力与成人不同,攻伐太过,耗伤精血,元气受损,易致正虚邪恋,疾病迁延难愈。傅仁宇在小儿用药时强调攻补兼施,在祛邪的同时,重视扶正,使正复邪去。如对于小儿癍疹,以羚羊角、升麻、黄芪、防风、车前子、决明子、黄芩,组方羚羊角散,共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盅,煎至半盅,去渍温服。本方主以羚羊角明目,又重用升麻补足太阴,实其内逐其毒;黄芪补肺经,实其外,御其邪;佐以防风升清阳之气,祛风散邪;车前子,引浊阴下行;决明子、黄芩清热明目,疗目赤痛之症。全方攻补兼施,内外同治,共奏益气升阳、泻浊解毒明目之功。为防止攻伐太过,而耗散精气,方中没有一味地使用解毒祛邪之品,在祛邪的同时注重扶正,正气得复,邪得外出,这对后世医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及指导意义。
眼部正常的功能状态有赖于脾胃功能的正常,但小儿脏腑娇嫩,脾胃虚弱。鉴于小儿时期特殊的生理特点,《审视瑶函·卷之二》[1]指出用药时应注重顾护小儿脾胃:“脾胃者,阴阳之会元也”,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胃升降正常,则浊阴下行,清阳上升,目病可愈。《血证论》[11]云:“苦寒药能大伐生气”,故小儿眼病的治疗中,药物不可过于寒凉。如治疗疳毒所致小儿眼病时,以苍术、茯苓、泽泻导浊阴下行,以羌活、独活、防风等祛风胜湿,此类药为多为苦、寒之品,易损及小儿脾胃,故在方中又加用白术、人参、甘草共补中焦脾胃。因此,在小儿眼病的治疗中,遣方用药应特别重视顾护小儿脾胃。
此外,《审视瑶函》常常用到特殊的煎服方法。如治小儿“每至夜不见物”[1],以夜明砂、晚蚕砂、谷精草、蛤粉,等分为末,煎黄蜡为丸,如鸡头大,三岁一丸,猪肝一片切开,置药于内,麻皮扎定,砂罐内煮熟,先熏眼,后食之;又如“小儿疳眼,不赤不肿不疼,但开畏明”[1],以川乌等研为细末,五岁一钱,雄鸡肝一具,净洗去筋膜,竹刀薄切开,掺药在内,箬叶包裹,麻皮扎定,用米泔水半盏,瓷器中煮熟,切作片,空心临卧冷食之,将煮肝汤送下。将鸡肝、猪肝与中药同煮,起到药食同源、治疗小儿眼病的作用,具有其科学性。现代研究[12]证实动物肝脏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与脂肪酸,其中含量最高的维生素A,是构成视色素的主要成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在中医理论中,猪肝、鸡肝与中药同煮,可发挥补肝养血明目之功[13],可用于肝肾阴虚型近视、夜盲、角膜炎等小儿眼病的防治。《审视瑶函》中特殊的煎服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提示后世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需考虑到小儿特殊的生理特点,采用适合小儿的煎服方法,可提升治疗效果。
4 验案举隅
牛某,男,6 岁,2021 年3 月18 日以“双眼发痒7 d”就诊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眼科检查:视力,双眼1.0。双眼胞睑内有淡红色颗粒,白睛红,黑睛缘处之白睛上有灰黄色胶样隆起。余未见异常。刻下症:双眼内作痒,伴分泌物、流泪,分泌物呈白色粘丝状,大便偏干,小便色黄,舌淡红,苔薄黄腻,脉濡数。既往体健,无眼部病史。西医诊断:双眼春季卡他性结膜炎;中医诊断:时复目痒(湿热毒蕴证)。中医治疗以清热除湿,祛风解毒为主。予自拟清热除湿解毒汤:黄芩、秦艽、地肤子、车前子、连翘、白蒺藜、荆芥、防风、生甘草、黄芪、生白术各6 g、蒲公英9 g。7剂,每日1剂,水煎服。
二诊(2021 年3 月25 日):患儿自觉眼痒明显减轻,分泌物、流泪减少,白睛微红。原方去连翘、地肤子、车前子,加乌梅、五味子各8 g,黄芪、生白术加量至8 g,继予14 剂,服法同前。后随访1 年,未有复发。
按语:本例患儿突然出现双眼内作痒,胞睑内有淡红色颗粒。胞睑属脾,白睛属肺,本病病机为脾肺湿热邪毒内蕴,复感风邪,风湿热毒上壅于目,症见双眼作痒,伴白色粘丝状分泌物、流泪,大便偏干,小便色黄,舌淡红,苔薄黄腻,脉濡数。结合《审视瑶函》论小儿目病学术思想,以风、湿、热、毒论治本案例,与小儿目病“胎毒”致病的思想一致。采用清热除湿,祛风解毒法,自拟清热除湿解毒汤治之。方中黄芩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秦艽、地肤子清皮肤腠理之湿;车前子利小便而清湿热,兼能清肺明目;连翘、蒲公英疏散风热,清热解毒;白蒺藜、荆芥、防风祛风明目;黄芪、生白术补气健脾;生甘草清热解毒,调和诸药。纵观全方,病因病机分析以《审视瑶函》“胎毒”致病为基础,用药选择亦遵循其扶正祛邪原则,方中除了清热、除湿、解毒、祛风之品,又加用黄芪、生白术补气健脾以扶助正气。诸药相合,共奏清热除湿祛风解毒之功,兼防正虚邪恋之弊。复诊时眼痒、眼红减轻,分泌物、流泪减少,说明湿热毒邪已减。因此,在原方的基础上,稍减清热除湿之品,加乌梅、五味子养阴生津,增加黄芪、生白术药量益气补中,防止邪气留恋,耗伤气阴。
5 小结
中医学[14]整体观念认为,局部是整体的反映,眼睛的状态亦是全身脏腑功能的体现。在临床诊疗中,应结合小儿特殊的生理病理特点,对眼病的病因病机、辨病辨证、治法方药做出全面细致的剖析判断。《审视瑶函》治疗小儿眼病以解毒、补中为主,并基于五轮学说分析其病机。小儿脏腑娇嫩,脾胃较弱,对药物的耐受度较差,故用药时切忌太过攻伐而耗伤正气;必须时时顾护脾胃,不可过用苦寒或滋腻之品;同时应重视煎服方法的选择,以提高临床疗效。因此,在小儿眼病的临床实践中,应提高用药安全意识,准确把握儿童眼病的具体情况,做到中病即止,攻不伤正,补不留邪。针对特殊阶段儿童的生理特点,辨证施治,并选择适宜的药物与方法,保障用药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