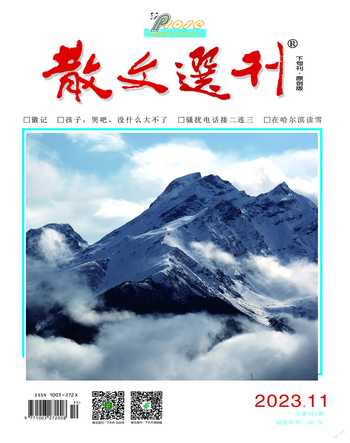徽记
指尖

一
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份,尽管已知晓并接受母亲会为我带来一个弟弟或妹妹的事实,乃至为预知他(她)的性别,跟最好的伙伴禾苗,摘下梨树叶子,学着村里大人的样子,试图在叶梗上找到答案。但他(她)显然只是母亲肚子的形状,一个枕头般柔软有型的物件,随着母亲去上班,回家,吃饭,休息,做家务,而无法独立呈现的生命个体状态。
南村妇女们走亲戚回来,路过我们村,目光仔细打量过母亲隆起的肚子,随口问:“你有几个孩子?”母亲笑笑:“一个。”
我拉住母亲的手,站在柰子树歪斜的树冠下,看着她们沿着河沟,一直走进阁洞,消失不见。
温河哗哗的响声像一双伶仃小脚,在黑夜的河边卵石滩徘徊好久,然后轻巧地跃过层层田堰,停在我家门前,跟榆树、杨树以及狗尾巴草们汇合,宏大又轻柔。我梦见绿油油的草丛,摇摆的长茎蒲公英,两只小鸟悄无声息地落到白石头上,一头牛笨拙地踩进水里,蹄子和卵石一同晃荡……祖母低沉婉转、悠长深邃的轻哼,从水流声中跳脱出来,似乎没有调子,也没有唱词,但每个停顿之间,都闪烁着我的名字,一个被冠以孙女身份、流淌和延续着自家血脉的小孩乳名。
白天,我追赶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它们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逃离躲避,发出叽叽咕咕的抗议和呼救声。祖母灯芯般明亮的目光盯着我,仿佛,我是点亮她的唯一火源。烟锅磕在门沿上,她的笑声像无声的应许,助长我的傲娇。我放肆地加快速度,冲撞着脚下绒团般的小鸡们。一只小鸡脚下一软,侧身倒下,来不及收回双脚,软乎乎的棉花黏在鞋底,低头时,小鸡原地打个滚儿,已经站起来,我却吓得哭出声来。一块带着木头、布匹、铜锈,还有时间味道的褐色冰糖,安抚了我的哭声。我贪婪地伸着舌头,狗一样舔着它。坐在门沿边的草甸子上,祖母抱着我轻摇,嘴里还骂着小鸡,说你个坏东西,吓着我宝宝有你好看的。母亲从街门口进来,我将冰糖快速塞进嘴里,跳起来,迎上去,黏糊糊的双手抱住她。她的肚子怪异而蛮横地顶着我。
我依旧会将动物饼干分给来家里玩耍的伙伴,让一只兔子通过她的嘴和喉咙,跳进她的身体。梨树下,我们用棍子去捅蚂蚁窝,一个凸起的圆形墓葬,蚂蚁队伍不得不四处逃窜,一些进入水坑,一些爬上石头,还有一些绕着凸起的小丘慌张离开。
我们也会遇见蝎子,同时惊叫,涨红脸匆忙地跑开。父亲寄回两双童鞋,母亲毫不犹疑地将其中一双送人了。周日,我穿上最好看的衣服,被母亲领着去外婆家,一路经过好几个村庄,那些闲坐的人们,都不无真诚地夸奖我干净好看。世界如此纷纭,似乎并不会影响乃至威胁到我的身份——唯一的孙女和女儿的身份。
温河的流水一夜之间变小变瘦,成群的蝌蚪和灰色的小鱼失了踪影,夜里,再也听不到流水的声音,人们用两根原木架在河上,上面垫了谷秸和黄土,牛走在桥上,也无畏惧。祖母去河里洗衣服,不再允许我到水里去玩,她说水凉了,小孩沾了水会生病。天一日胜似一日冷,田里的庄稼让出地盘,北风成天肆虐,潮湿的黑土很快变成硬邦邦的黄土。草木集体撤离,杨树尖上,挂着最后一片叶子,它颤颤巍巍的样子,真让人担心。农历十月,冬天正式到来。临睡前,祖母从柜子里翻寻出五枚铜钱,她说,等你生日那天,用红线串上给你戴。
二
黑黝黝的梨树上,猫头鹰在呱呱呱呱呱呱地叫。恐惧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潮水般向我涌来。坐在窗台上,初次感到一种被遗忘、被忽略的孤单。恍惚中,我正在缓慢后退,通过身后的玻璃窗、厚厚的墙壁、柴垛,从梨树的枝尖,一直退到梨树的横枝上。猫头鹰成为我的同盟,我们眼前的一切——炕上虚弱的母亲,小被子下的婴孩,还有坐在一旁吃烟的接生婆,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而她们的谈话声,也越来越轻,越来越薄,越来越模糊。彻骨的寒风吹来,猫头鹰的羽毛被掀起,颤抖着露出浅色的细绒。
突然有人喊我名字。
我惊恐地看着煤油灯下的这几个人,不是祖母,不是母亲,更不是炕上那个小娃娃,而是坐在凳子上的接生婆。是这个外人将我的魂灵召回,倘若她不喊,我肯定会变成一只黄眼白花羽毛的猫头鹰,那时,只能蹲在梨树上,孤独而忧伤地鸣叫,被人们咒骂,赶走。她身后的煤油灯,让她的影子像一幢黑黢黢的高墙,那影子不无威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你是姐姐了。”
我的父亲正在赶回来的路上。父亲于我来说,更像是祖母和母亲话题里的人,相片里受到夸耀的人,别人闲话里羡慕的人,或者一个叫爹的人。整个童年时期,父亲是通过一块枕巾、一件花衣裳、一袋动物饼干来与我发生关联的。他从遥远的东北寄信回家,母亲在油灯下读给祖母,我安静地等待自己出现在那些字迹中间,但没有,也不会。我们就像陌生人,在彼此的生命中呈现可有可无的状态。对他要回家的消息,也有几分期待,就像期待一个货郎担子,或者期待一场电影。像一首曲子的高潮段,或一出戏最热闹的一幕,短暂的几天几夜之后,他会再次离开。现在,端起饭碗的接生婆,话题转到我的父亲,夸奖他有出息,性情好,心善,并安慰祖母,说善良的人,老天都会赐予如意,“娃们还年轻,有大把时间生小子,嫂子你就等着吧”。鼓槌嘣的一下敲在脑壳,我惊愕地瞪大眼睛。显然,这个新生的娃娃远远不够,祖母和母亲还要更多的娃娃。巨大的失落从窑洞顶落下,我的眼里渗出泪水。接生婆很快吃完第二碗面,将包掖在腋下,推搡着不让祖母去送她,眼神飘来飘去,定在我脸上,欲言又止。我对她的仇恨,几个月后与日俱增,我一个人躲在厨房的门后面,偷偷抽泣,心里憎恨她将妹妹带到了我家,毁坏了我原本的生活。
父亲是第二天下午回来的,他看见脖子上戴着红线绳串着五枚铜钱的我,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齒:“今天是你生日,高兴不?”我转身便跑。
这是一个极其敷衍的生日,只在神呀祖呀牌位前磕了个头,之前的红稠饭、煮油糕,甚至去县城照相,买红头绳,这些统统都免了。
三
母亲要上班,捎话给外婆家。隔日,十五岁的小姨走了八里路,专职来看管我和妹妹。
一进门,涨红着脸站在那儿,按着胸脯说真吓人。原来在干草坡蜿蜒崎岖的小道上,她遇见一条黑花蛇,那条蛇横在路中央,又粗又长,将窄窄的小路堵得死死的。
她远远站在那里,等着蛇从这片庄稼地去往另一片庄稼地,但那蛇就像睡着了般,就是不走开。她牢记大人们说过不能从蛇身上跨过去的教诲,更怕自己走过去,惊扰了蛇的休眠,伸出芯子咬她。于是,她从上午等到下午,一直等到傍晚有人从铁厂下班回家,那蛇才开始缓慢移动。她喝着母亲在洋瓷缸里泼的糖水,依旧惊魂未定。当夜她就发起了高烧。后来小姨讲,她是经过母亲给她刮痧,拔罐,在指肚上放血,之后才好起来的。但所有这些我并没有看见,因为在我记忆中,似乎从未跟母亲睡在一盘炕上过。我只记得,在祖母怀里睡去,半夜被老鼠在头顶跳过的吱吱声惊醒,我身边的祖母,像一堵墙一样让人安心。而当我生病时,无一例外,所有的土法治疗,均来自祖母,每次我母亲替我叫完魂,从外面将门关上,她回自己的屋休息时,我都感觉自己像飘在风里薄薄的一张纸片。
小姨贪玩又逞强,妹妹常常往地上掉,没几天,头上脸上,全是乌青。但妹妹自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天性,她很少哭,不久就学会了说话,据说在同龄的小孩中,这也是少见的,母亲为此特别高兴。有次妹妹生病,母亲带着妹妹去南村卫生院看病,在那里,妹妹发着高烧,给贾医生表演了翻跟斗的技艺,从此被母亲当成乐事自豪地讲给别人。
外婆也来小住,家里突然多了这些人,祖母心里甚是不悦,言语里敲敲打打,我母亲装作听不见,但我小姨胆大,竟然顶撞我祖母,我小姨说:“这是我姐姐家,我来给她看小孩,我妈来住几天怎么了,我吃我姐姐的,喝我姐姐的,你管得着吗?”这样闹了几次,我外婆不得不回去。为此,小姨极其气愤,更是每天都要挑事,最终在一次大规模吵闹之后,我祖母坚持要跟我母亲分家。
我跟祖母一个厨房,我母亲、妹妹和小姨一个厨房。小姨这下喜笑颜开,更加肆无忌惮,上午让我看住妹妹,去厨房里炒豆子、炒玉米,或者压薄饼,作为我们的零食吃。
里面放了糖精,无论是豆子还是饼子,都好吃极了。我祖母每天气得七窍生烟,有时生闷气不吃饭,就让我端着自己的碗去找母亲。我连蹦带跳,不知什么心理。总之,我记得自己常常就跌倒了,手里那只黑釉碗扔出去好远,有一次,碗被扔到石碾上,当下就碎掉了,我终于为自己失去了吃饭的碗而大哭起来。
有天午后,我母亲刚走出院门,小姨就神神秘秘地说,今天我们炒瓜子吃。那是祖母晾在窗台上的南瓜子,小姨偷偷地将它们放到口袋里,吩咐我回屋看住妹妹。
妹妹还在睡觉,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像挂着两弯月牙,原先脸上的汗毛渐渐褪去,嘴唇粉嘟嘟的,看起来真是好看。突然,一声大叫喊醒了妹妹,黑黑的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透过窗玻璃,小姨站在厨房门口,像來我家那天一样涨红着脸。
一见祖母出来,小姨跑过去,边说边抱住了祖母的胳膊。原来她把锅放到火上,伸手取筷子时,摸到了冷冰冰的一团,扭回头,筷筒上竟然盘着一条蛇。祖母黑沉着脸,甩开小姨,用眼睛狠狠地剜了她一眼,然后从墙角拿了一把铁锹,进了我母亲的厨房,不大一会儿,铁锹上挑着一条细细的蛇出来,那蛇缓慢地伸展着自己的躯体,像是在伸懒腰,而我祖母竟然面色平静,用铁锹带着它出了院门。等祖母回来,我小姨还在梨树下低着头站着,我祖母伸手就是一巴掌:“挨刀鬼,那是我的南瓜种,你也敢偷吃?老天长眼,派蛇神来警告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收拾东西回你家去,再在我眼前晃荡,我见一次打一次。”
小姨没有反驳,像哑巴似的站在那里,双手绞着衣襟。她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临走那几天,母亲给她做了一件红格子的衣服,又把她送过温河。
四
我喜欢的衣服终于穿在妹妹身上时,她也五岁了。
每年春节,我的母亲都会替她拉拽四肢和脖颈,据说这样,她就可以长得跟我一样高了。这种异常滑稽的画面延续了好几年,每次,我都会躲开,或者嗤笑。虽然她的个子并没有长高,但她也当了姐姐。而我,成了双倍的姐姐。我还会成为三倍四倍的姐姐,当我背着流着涎水的小妹妹走在街巷里时,这样想。我渴望上天给我重生的机会,那样,我要改换身份,成为妹妹。乃至每当生日来临,渐渐长大的她开始不停地纠结明明比我早生一天,为什么还得叫我姐姐的困惑时,我也陷入同样的困惑。
她极其喜欢那件我穿了好几年的衣服,忍不住频繁照镜子,镜子里,其实只能看到领子,但她依旧喜滋滋的。那是件鹅黄色的平绒外套,因为不耐脏,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母亲才让我穿两天,但我极其不争气,每次总是不小心蹭了饭渍,惹得母亲不高兴。据说平绒不好打理,我又长得飞快,那件衣服虽然穿了三年,也不过三次,所以没下过水,崭新崭新的。为了让妹妹穿这件衣服,母亲托人捎到城里染成枣红色,绒毛让那件衣服呈现出奇怪的颜色,用手捋一下,它就是泛着陈旧的浅驼色,再捋回去,又变成了暗淡的枣红色。我看着妹妹穿着它,就像看着我自己,那么陌生,那么丑陋。
春天,柳树刚刚发出嫩芽,村里响起了柳笛粗细不同的声音。她用手扯扯我的袖子:“姐姐,给我做个柳笛好不好?”我笨拙地爬到树上,用力折下一支树条,回到院子里,慢慢地转动柔嫩的树皮,然后用剪子剪成长短不一的小节,把树枝从树皮中抽离,放到水里浸泡一会儿。于是,她兴高采烈地吹着柳笛出门了。后来她哭着回来,说有人把她的柳笛弄坏了,姐姐,你一定要给我报仇。我答应了。
不同于我那个呆板且脏兮兮的布娃娃,她的布娃娃有一双随时睁开或闭合的眼睛,还有一条粉花的裙子。她在当了姐姐后,也被遣送到祖母的炕上,睡在我和祖母中间,抱着她的布娃娃。早上,母亲喊我们起床,边喊我的名字,边去亲她的脸,每天她都在暖痒痒中醒来,嘎嘎地笑着。那时我会给她穿衣服,叠起被子,下炕替她梳头发。有次她不满意我给她梳的辫子,嘴里骂我,我一生气,就将她怀里的娃娃摔到地上了。她的布娃娃,从此不会闭眼睛了。
小姨又来长住,是脸上起了藓,让我母亲替她找医生看病。我祖母撇撇嘴:“你住在城沿上的人,生了病不找好先生,来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能找到先生?”我小姨犟嘴道:“我找我姐姐,累着你什么事了。”“你是找你姐姐要钱来了吧?”我小姨到底是长大了,笑了笑就钻回屋。
我母亲开始紧锣密鼓地问询哪里有好医生的时候,我家来了另一位稀客,我祖母的弟妹,也就是我老舅舅的老伴,我的老妗子。花甲之年的老妗子圆盘大脸颇为富态,她一进门就拉住祖母的手,两行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挤出来:“老姐姐给我做主啊!”
祖母拉着老妗子上了炕,给她倒茶,然后才问缘由。原来是老妗子跟大媳妇吵架,媳妇娘家人竟然来帮腔,要赶老舅舅老妗子出门。我祖母一听:“这还了得,他们这是欺人太甚了,不急,你喝点水歇歇,我跟你回去跟他们理论去。”这事后来怎么解决的,我给忘了,唯一记得的是,我小姨住到了老妗子家去针灸去了。
在我弄坏妹妹的洋娃娃后,每次给她梳头,她总有些畏缩。不久,我妈拿剪刀将我们的头发全剪成齐耳短发。不知是为炫耀自己的手艺,还是碰巧照相师来村里,我跟妹妹平生第一次合影,黑白照片中,我们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表情,甚至一样的衣服样式。母亲从城里买回一本水彩条,毛笔头浸湿,在彩条上沾几下,给照片上色。母亲手生,不好把握,我的右脸是一团深红,左脸稍微淡一些,但比起妹妹脸上匀称的粉色,还是难看许多。母亲用手绢在我脸上沾了几下,效果并不理想,无力回天。我跟妹妹上了彩的照片,被放进了照相框里。我从不抬头去看,而妹妹喜欢趴在相框下面,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照片,有一天她竟跟母亲说:“妈妈,你为啥不把我也染得跟姐姐一样好看。”
小姨脸上的藓斑神奇治愈后,母亲在供销社买了饼干和红糖,送小姨过河回家,我蹲在河边等着,看着她们一前一后的身影,摇摇晃晃过了河,没入对岸的小道,上了坡。用了很长时间,母亲才又回到村口。夕阳涂抹着面前的山峰、河流和村庄,深红,艳橘,浅粉,蓝紫,深褐……诡异极了。我眼里的母亲,也在夕光中不停变换。我突然惊恐地发现,这世上,并非只有我被标注成姐姐身份,我的祖母和母亲,早已提前拥有这个身份,比母亲、妻子、婆婆和媳妇这些身份都要早,都要长久。
姐姐,仿佛一枚徽记,烙印在骨头上,被其后不断添加的身份徽记遮盖,复叠,渐渐暗淡,却永无消失的可能。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