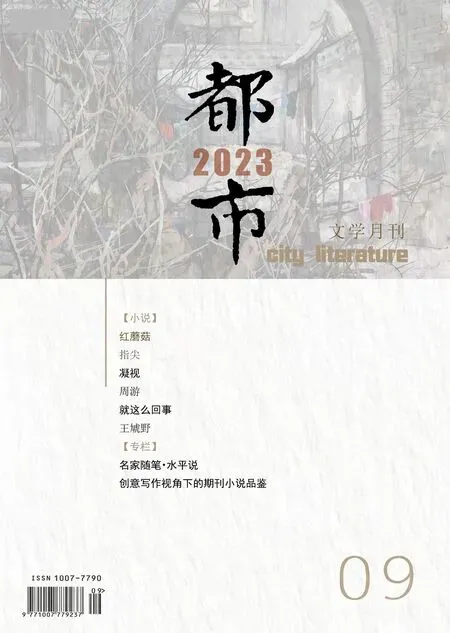红蘑菇
文 指尖
他习惯性地朝衣柜那边瞄了一眼,恍惚觉得有什么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直到洗完脸,湿淋淋的目光停在洗手台上,一支被捏扁的润肤膏像个伤痕累累的士兵横躺在那里,之前包围在它身边的她的面部维护队成员全然不见,他才忍不住开始喊她的名字,从卫生间喊到小卧室,又从小卧室喊到厨房。书房架上稀稀拉拉几本东倒西歪的书,像一块层层叠叠的页岩化石,一下子向他倾压而来。虽不至于猛然倒下,但他听见自己的身体仿佛漏气的气球,正发出持久的呲呲声。果不其然,在茶几上发现了她留下的字条。她倒向右边的长条字体,并没有因为放大而突兀,依旧如她一样恍惚、随意、若有若无。奇怪的是,他从“走了”这两个字里,竟感受到一种陌生、锐利、不可侵犯的冷峻。
傍晚的光线让屋子里起了一层薄雾,湿润、空寂而清净,仿佛她的遽然离场,仅仅是为了让他的空间变得舒缓而开阔,他安静地站在那里,接纳了她的馈赠,并感受着轻松和紧张的轮流敲击,一下又一下,凌乱而持久。
夜里,那个快要彻底抽离的梦境,因失去了她的守候,肆意地通过迟钝的神经末端,最终在视觉皮层和额叶区域壮大成形。他轻易就回到了十一岁时的深山,提着篮子去采蘑菇。穿过低矮的草丛,踩倒脚下几朵野花,弯身捉了一只蚂蚱捏着,蜿蜒的小路上,一只蜥蜴提早察觉他的到来,很快伪装成一条砂石,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他停在山下的小溪边,灰色的小鱼们组成一块浅灰色的薄海绵,在水底粘在一起,又摊成一片,一条小鱼快速而有力地挣脱越来越松软、越来越薄的海绵领地,迅速从石缝里钻出去,他便一路蹦蹦跳跳随着它,不知是他惊扰了小鱼,还是小鱼抵达了专属藏匿地,总之他跟丢了,他捡起一根树枝,试图捅破流水,小鱼早已无影无踪。他不得不踏着嶙峋的石头,朝山上爬。稠密的松枝们交错编成一个大锅盖罩在头顶,很快他就汗流浃背了,心里却十分焦急,视线里,并没有一只蘑菇等着他,用手臂抹去眼窝里的汗水时,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斑驳的光线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先是视线越来越低,后来脚和手变得跟草叶一般大小,而眼前的青草迅速变得跟树木一样粗大。在青草与庞大的树干之间,缀满密密麻麻的黑暗洞穴,散发着潮湿的热气,似乎他要找的蘑菇们就在那里。他怀着紧张而害怕的心情,一步步挪向那些黑暗洞穴。
梦境是一个奇怪的场域,许多时候,做梦者的思维能够在现实跟梦境之中自如穿梭,并决定着自我深入和抽离的秩序。他很确定,自己已成功穿越时间用二十多个年轮叠加的屏障,重新走回熟悉的松林中,去寻找那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蘑菇,那些白色的或深棕色的,带着饱满水汽和柔软触感的蘑菇,那些散发着莫名气味,轻易唤醒味蕾和嗅觉,远近不一、虚实相交的蘑菇,甚至他还对这个梦境的终极走向以及结束部分一清二楚。但即便如此,在低矮潮湿昏暗闷热的松林空间,变小的他依旧被什么东西钳制着、推攘着,不得不重新经历一遍抵达预料结局的过程。他提前在心里撒开恐惧之网,将她的名字像哨子般预备在唇边。只要走七步或者十步,在密集的蘑菇群出现之前,一只鲜红的、硕大的蘑菇就会提前出现,他来不及惊讶,便得迎以虚弱和慌张、害怕和挣扎来与之相对,因为在那只红蘑菇层层叠叠的皱褶之间,早已形成一张巨形大口。即便他停止行动,即便他已经变小,那蘑菇还是要清晰而笃定地向他移来,沿着一条虚拟的直线。他浑身颤抖,牙齿和嘴唇不停地哆嗦,身体却无法动弹,更别说快速躲到旁边树干后面,汗水从额头流下来,经过眼窝时将眼泪一并喊了出来,他很快尝到了又咸又涩的味道。来自深处的低吼传入耳郭,张开的大嘴里,一条深红而然柔软的喉管,正在变粗变大,自己就要顺着那喉管滑进它深渊般的躯体之中,他甚至感觉到它看不见的牙齿,坚硬的,布满纵纹、泛着恶臭的牙齿即将穿透自己的骨头。
时间的秒针终于停在了梦境截止时刻,他用尽浑身力气,在清醒与迷糊中艰难挣扎,一次、两次、无数次,强迫自己的声线通过狭仄的嗓子眼迸发出来,成为液体或石头,从无声无息,到细若游丝,到大声疾呼,血盆大口在闭合的同时将他一口喷出。他习惯地去喊她,那只熟悉的右手并没有如常抚上他的左脸,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坐起来,想起她已经走了。路灯灯光打在窗户上,照得屋子里亮堂堂的,她的枕头也被带走了,之前竟没察觉。她怎么不带走半边床、半边沙发、半把椅子、半台冰箱、半个扫地机?他打开衣柜,三五件衣服黑黢黢地挂在那里,纸片般一动不动。
他和她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都是过了三十岁的年龄,都是中等个子,都戴着近视镜,不好看,也不是很难看,大同小异的履历,彼此来自农村的身份,让他们很快就有了颇为共性的话题。第三次约会,两个人坐在快餐店的塑料桌子两边,突然同时说了一句,我们搬一起住吧。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原本就是奔着结婚去的,这样约来约去,不过多花时间、多花金钱罢了。她本是跟人合租,行李收拾好,便搬了过来。他的出租屋面积也不大,但两室一厅,足够两个人过日子了,虽然距她上班的地方远了些,但便利的城市交通已将所有的空间填满,距离感缩短。通勤时间长点,在她也不是问题。男人的屋子相对简陋,除去房东的基础配置,属于他的也只有床上用品了。他们在网上购置了洗衣机、冰箱、扫地机,换了沙发,一个租来的小家很快就被打理得五脏俱全了。
跟她在一起之后,他差不多半年都没有梦到找蘑菇,更没有红蘑菇的影子,倒是梦到过其他,比如,在漫长的坡道上气喘吁吁,莫名其妙就挂在石墙上上不去下不来,或者不停地拐弯向前之类的,但奇怪,也没有梦见过她。
晚上下班,两个人一起在厨房里做饭,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聊天,畅想未来,结婚时,家里要添置一些什么,这里放一个工作台,那里放一个音箱,墙上要挂个电视机,星期天要一起打游戏、听音乐、追剧。后来,他跟她讲深山里的小村子,天很早就黑了,狼群和豹子以及獾和野猪常常像走亲戚一样来村里,每次都会顺走一些战利品,有一年竟然来了一头熊,全村人吓坏了,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待在屋子里不敢出来。有一个胆大的人,觉得村里人真是没用,便拿一把镰刀去赶熊走,远远看见半间屋一样大的熊,即便它的眼睛里满是不屑,也让他胆战心惊,关键是熊也并没有放过他,仿佛一直在等待他似的,悠悠然向他而来,他赶快趴在地上装死,熊把他浑身上下闻嗅了一遍,这才离开。她也提起自己小时候生活在临河的村庄,星星倒映在河水里,亮晶晶的,让人生出伸手就能抓到一大把的幻觉。雨季,河水猛涨,差不多每两年都会席卷村子一次,那时,她跟父母和妹妹就会抱着家里值钱的东西,站在高地,眼睁睁看着自家房子被源源不断的流水侵占,最终,只剩下一个陌生而虚假的屋顶。
他们对彼此的出生地都有很大的兴趣,以至各自在心里盘算,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对方的出生地亲历一番。两个都是寡淡安静的人,做的总比想的慢半拍,时间一长,这想法越来越淡,淡到好像两个人原本就是孙猴子,连哪里出生都忘得一干二净。
难得一次心血来潮,坐高铁去三清山游玩,在海拔1300 多米的地方,他们遇见了画眉,他对着它们啾啾,它们便也啾啾回应,她很少这么松弛,笑得前仰后合,嘴里突然就发出喵喵声,仿佛那才是属于她的语系,画眉们冷了一瞬,随即便此起彼伏地喵喵起来。看着一群画眉发出猫群的叫声,是件诡异的事。下到海拔500 米的栈道两边,到处都是椭圆或长椭圆形叶片的不甚高大的树,导游说,这是青冈树。她便对着叶片和树干仔细查看半天,回头跟他说自己正在读的一本小说里,到处都是一种叫南水青冈树的影子,虽然它们是不同的两种植物,但它们有相同的学名,大约是一样的植物吧。他也探头过去。“书里的水青冈高大,笔直,其实就是山毛榉。”导游接上她的话头说,“这里的青冈树就是橡树,诗人喜欢把它们写进诗里的。”原来如此,两人相视一笑。一路下山,两个人早已双腿发颤,但因为这场对话,身心变得无比轻松起来。
晚上住在山里,安静得能听到夜鸟扇动翅膀的声音,听到透山水从岩石中渗出跌落下来的声音,当然,他们也听到了彼此的心跳声。面前这座山有1800 多米的海拔,据说每一海拔高度分布的动植物都有不同,比如海拔500 米到1200 米之间的杜鹃花跟海拔500 米以下的映山红是有区别的,而海拔1200 米以上,杜鹃花这种植物将成为草甸,没有任何开放甚至独自生长的可能。就像科学和艺术的终极与宗教重合一样,生命最终也将趋向荒芜,即便有爱、有陪伴、有感动和求生欲念,也再难开出美丽的繁花。一种似曾相识、万古沉浮般的孤独袭来,夜晚变得浓稠阴郁,一面永远也无法冲破的墙横亘在眼前,他突然焦躁起来。
那夜,他又去寻蘑菇。篮子是他梦里必备的器物,既可以替他撑开密密麻麻的树枝,还可以在遇到危险之时让他紧紧攥住,而寻蘑菇,是进入梦境的成因,只有这两样东西同时存在,那只鲜红的、像血一样的大蘑菇,才能冲破他的防线,进入梦乡。是她轻柔地喊着他的名字,冰凉的右手抚在他的左脸,才让他从红蘑菇的口中逃出来的。他忍不住抓住她的手,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从三清山回来,两个人的关系似乎更近了,即便上班间隙,都忍不住要通过手机跟对方多说几句话,好像长在彼此心里的草,随时都得看见对方在风里招摇的样子。奇怪的是,关于结婚以及婚后生活的话题,竟戛然而止,仿佛他们在某个神秘之所,有过一次共结连理的誓言,再不必通过一个仪式来维系彼此的终生,也不必拥有一整套象征性的礼服装饰生命的瞬间,更不必留存一个新生命来作为婚姻的证据。
没有了结婚这个话题,晚上的时间便空出很多。好在小书架上的书,正越来越多,有时是他的,有时是她的。他喜欢历史和佛书,她喜欢文学和艺术。他们就坐在沙发上看书,起先会靠着彼此,特别是她,遇到书里情节紧张时,还会更紧地靠靠他。也不知什么时候,沙发的两头成为他们彼此的据点,甚至根本不会坐错,好像有人用无痕笔画了一个圈,他们照着那样的圈子坐进去才稳妥。有天他回来得早,突发奇想,坐到她的位置上,沙发下氤氲着的一股陌生气息让他感觉不适,即便他们已经在一起五年了,即便他们习惯像影子一样追逐着对方,那一刻,他突然觉得他们终究是彼此的陌生人。
当然,每次蘑菇群尾随那只硕大的鲜红的蘑菇而来,都是那只冰凉的右手来拯救他,有天醒来他抱着这根救命稻草忍不住呜咽起来。如果没有要吃掉他的那只红蘑菇,他的梦里应该是老家的深山,乳白的、潮湿的、花朵般盛开的小蘑菇,父母虚幻的脸,他们还那么年轻,带着日光般的笑意。两人刚同居的那段时间,他特别渴望她能在他噩梦醒来的夜晚,问起他的父母,或者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蘑菇,那时,他或许会将压在自己心底的秘密全部倾吐,说父母在他眼里最后的样貌,像两只干透了的蘑菇重新泡进水里,鼓胀得泛着暧昧的深紫色光泽;说姑丈锥子似的目光,一下一下戳着他少年的自尊;说拙劣肥大的旧衣服,说补满补丁的短裤子,说大脚趾永远露在外面的尴尬;说自己长达七年的村庄嘲弄缓刑期;说自己终于走出深山时的心碎和轻松。可是,没有,她只是静静地,通过双手的意念,来达到安慰和给予的目的。有次她无意提起自己的父母,说留在父母身边的妹妹,也因此她就有了不回去的理由。他想,自己对她的失望大约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萌芽的,一种将自己裹紧并拒绝任何进入的姿态。仿佛迅速传染开来的黏合剂,他渐渐也被她复制粘贴成同样的姿势。她愈发安静,他也不得不愈发安静,他们活成了屋子里的任何一件家具和电器,活成了沙发的左边和右边。
防盗门上的浮尘像睫毛上的霜,只有开关的时候才会让人心里有细微的不适,离开它,进入或转身,其他烦冗杂事纷至沓来,它便会回归于一扇门的功用,封闭的,冷漠的,拒绝的,保持着相对的安全感,以及不可侵犯的边界感。据说事物因其太过熟悉而失去神秘性,变得平淡,会被人渐渐遗忘,最终丢弃。他幻想只要打开防盗门,就能看到她在夕阳中的影子,但屋子里照旧空荡荡的,他像极被丢弃的某个物件。他将钥匙扔进柜上的小篓子里,小篓子略比他的拳头大些,来自许多年前。时间在每一根藤条上都留下深深的痕迹,那是他们在一起时的尘土和湿气,风和光,笑与叹息,乃至愤怒和泪水的组合物。他记得有两次她说过要换掉它的话题,甚至某次夜市摊上,她还相中过一个类似的瓷品,但为什么最终并没有被替换,他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她的出走在他看来也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起码这个头是他起的。那是他们从三清山回来一周后,他跟公司申请了年假,背了一些简单的日用品,住进去了郊外的万松寺。之前他没有跟她打招呼,甚至临走时还故意将手机落在了家里,就是她放纸条的地方。这点上,他承认自己的怯懦,起码她敢说“走了”,即便透着虚弱的气息,那也是超越他的一种勇敢表现。而他只能静悄悄消失。万松寺很小,只有大师傅和小师傅两个出家人在此修行,香客也少,他跟在小师傅身后,做早课、晚课,去山后的菜地浇水、摘菜、帮厨,晨钟暮鼓,一天下来,浑身疲惫,心却又静又满,像一缸幽幽的水。是离开她的缘故吗,还是离开世俗的缘故?他想了好几天,也没想明白。他回来那天晚上,比下班时间稍晚了一会,她正在沙发上看书,朝他淡淡一笑,仿佛他消失的这几天,时间并不存在,他们依旧接续着时间的起承转合,亦步亦趋,步步不少。倒是国庆假期前,她跟他说想回家看看父母,他也跟她一样,朝她微微一笑。他没有从她的目光或行动中看出别的意思,比如,她是想让他陪她回去。两个人在一起,似乎坦诚到不必客套,又似乎各自锁紧房门,抵触着彼此的叩击和进入。
她走了的第四天,下班后他专门买了松菇,这是他后来再也不敢触碰的一种食物。松菇有松树、青草和露水的气味,也有属于真菌菇的浓郁腥味。蘑菇的力量强大到要把人拉进茂密的松林深处,他看着它们很快将清水染成深色,恍惚身在梦中,似曾相识。在极乐世界,年轻的父母也或许还是喜欢吃蘑菇的也不一定。取菜刀时,他发觉厨具竟然一样不少,她全部留给了他,包括她最喜欢的那只炖锅。是来不及带走吗?又或者她早有了离开的准备,提前整理好书籍和衣服?那得多长时间啊,一天,三天,还是更长时间?他记得她也炖过蘑菇,跟鸡块一起,一屋子熟悉的味道让刚进门的他忍不住干呕起来。她满是疑惑地看着在卫生间和客厅之间往返的他,“我闻不得蘑菇的味道”,他捂住鼻子闭着眼,靠在沙发上。她将一锅菜倒进垃圾袋,推门跑到楼下倒掉,回来手里多了一只凤梨。晚上那只凤梨剥了带刺的外皮,切在盘子里,被牙签戳着,舒缓物最终也成了尸体。她只是再不买蘑菇,却也没问他为什么。但有次回家,他还是从她的头发、衣服以及说话的口气中嗅到了蘑菇的味道,心想原来她是喜欢吃蘑菇的。后来她会隔段时间带一只凤梨回家,他知道那是她用来驱散蘑菇残留在她身体以及肠胃里的味道的,想到她偷偷摸摸去吃各种蘑菇,炸蘑菇、炒蘑菇、炖蘑菇、涮蘑菇……他在厌弃她的同时心里竟涌出热辣辣的感动。
他今年已经35 岁了,再活三年,就活到父亲的年龄了,如果在山里,他也会成为父亲那样的好猎手吗?也会遍识山上的草药和菌类吗?可是即便如此,又能怎样?父亲对山上的植物、昆虫宛如对自己的手纹般熟悉,还不是要被最好看的那只红蘑菇毒死?炖锅里蘑菇夹杂着鸡肉的味道很快弥漫开来,胃里涌起熟悉的痉挛,他压住左手的合谷穴,缓解着自己的神经。他必须忘掉蘑菇的味道,就像他永远记得它们的颜色、形状,甚至生长地一样,喜不喜欢、合不合口是无所谓的事,关键它们不过是肠胃的填充物而已。
他用七天时间来等待她,比他消失的时间多出一天。第八天,他开始在生活网找房子,房子住太久,或许她对此生出厌烦之心也不一定。过去和未来之间,有时不过一条线的分割区,此或者彼,前或者后,他是想把拥有过她的过去带到未来吗,还是以此来彻底将她丢弃在过去?
他们的旧小区紧靠一个大公园,在公园跟小区之间,有一道宽阔而茂密的绿化带,像一条二级公路,一直向前绵延5000米左右,有次他们沿着绿化带往前走,竟然走到了一条河边,手机地图显示,这条河是这个城市早年的护城河,也就是说,他们住的地方,很可能是城墙的位置。回来的时候,路变得又长又曲折,石子硌着鞋底,每一步都很艰难。他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歪倒在地上,好半天才站起来。以后每次站在窗前,她总会问他,能不能看见2500 年前的风景啊。他会笑,但也不会觉得她天真幼稚,乃至有次他用一整夜的时间站在窗前,早上起来跟她说,自己真的看到了2500 年前的风景,那是群雄崛起、战争频仍的冷兵器时代,刀光剑影,战马嘶鸣,血流成河,他目睹了一场战争的全过程,城池沦陷,火光冲天,君王自刎,王妃投河,跟随她的宫娥也义无反顾飘然而去,她们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飞蛾,整条河都变成了红色,不知是被夕阳染红,还是被鲜血染红。她突然问,你会不会也能看见自己的前世?他顺着她的话头,说看见了,他从宫墙的某个豁口逃出去了,沿着红色的河流一直往下走,一路风餐露宿,成功躲开野兽和强盗,战争和杀戮,最终抵达一望无垠的海滩,等待海上点点帆影的救赎。突然看见不远处一个女子的尸体,浑身赤裸,像一只饱满的蘑菇。她突然就捂住了他的嘴,一股浓郁的碘酒味传进他的鼻孔,他看见她手上的绷带,试图拉开她的手,她却摇摇头,目光里浮起一层泪意。现在想想,她是怕他只是替她遮体的人,而非那个最终埋葬她的人吗,还是那时就想好要离开?
新租的房子一室一厅,地处市中心,房价却出奇的低,房东催他尽快看房。是一个好看的女子,年纪要比他轻,一根栗色长发突兀地蜷曲在她雪白衣裙的肩头,随着她的走动和说话频次飘来荡去,有几次他试图伸手拿下来,但想到初次相识,如此举动怕是不妥,终是忍住了。房东说最近要结婚,搬新房子里去,所以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她笑的时候,那根头发似乎受到了感应,也笑了几下。她说希望能租给一对情侣或者单身男子,他的目光从肩头抽出来,疑惑地盯住她。她说这是一间幸运屋,住在这里的人会获得幸福的。这个答案出乎他的意料,幸福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影无形,无边无际。倘若她听到这句话会作何反应,淡淡地一笑,还是跟他默契而饱含深意地对视一眼?
他简单收拾了行李,第二天入住新居。70 寸的彩电放大了客厅的空间,显得整个房子富丽堂皇。电话响起时,他在电视机下面的柜子里找到了遥控器。是旧房东的电话,问那些冰箱、洗衣机、沙发们他要不要带走。他跟他说,都不要了,随便你处理吧。他习惯性地再次拨通她的号码,前两次,她都关机,这一次,却传来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他打开微信,想留一句言,你还好吗?或者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最终还是全删了。按下遥控器的开关,镜头正对着一片繁茂的绿化带,他一下子就认出是旧房子跟公园之间的那条绿化带,现场主持人正在播报热点新闻:位于城东某小区与和辉公园之间的绿化带,面积广阔,植被茂盛,一女子不小心在此迷路,三天以来,她靠吃野花喝露水维持体力,据说她本来是在这条绿化带里采蘑菇的……